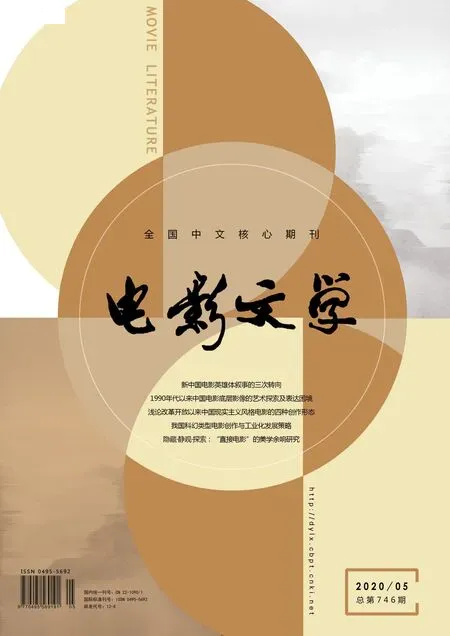德勒兹哲学之精神分裂与电影艺术
2020-11-14康有金何欣格
康有金 何欣格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电影产业从出现、发展、改进、完善到普及,现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艺术产业。它不仅具有审美和娱乐消遣功能,还具有教育功能。电影艺术是精神分裂的产物,没有精神分裂就没有电影艺术。德勒兹哲学中的精神分裂者是潜在的革命力量。革命者具有精神分裂型人格,而革命也是一个精神分裂过程。本文以《我不是潘金莲》和《血战钢锯岭》这两部电影为例,探寻德勒兹哲学思想中的精神分裂人格品质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精神分裂人格品质
“精神分裂”是德勒兹和加塔里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隐喻概念,指的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背景下少数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特征。这类人被称为“精神分裂者”,他们拒绝现成规制,藐视权威。“精神分裂”是游牧民的人格品质。游牧民不会被资本逻辑所捕获,会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分裂不是病,社会使之然也。如果致使患此顽疾的社会环境消失,精神分裂者将会自然康复。
精神分裂式的人格品质也是后现代主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异质性,开始拒绝被社会或他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德勒兹哲学体系中,“精神分裂”与“偏执狂”密不可分。这两种欲望在“无器官的身体”上“注册”。精神分裂者有三种典型症状——解离症、自闭症和时空破碎症,它们共同构成了德勒兹和加塔里关于精神分裂理论的三叉图,这三种症状分别对应德勒兹哲学的其他概念,即块茎、无器官身体与生成。
解离症。精神分裂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设定自己的记录编码程序。因此,外界无法与其匹配编码,更不能为其解码。他们无视规制,不守成规,特立独行。精神分裂者的解离症不是他们自身的病症,是社会顽症在他们身上的集中体现。
自闭症。精神分裂者的物质与精神逃逸线路都已经被堵死,每次试图逃离都只能是越陷越深,越是挣脱,枷锁越紧。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以问题的形式而存在,精神分裂者只能退遁为无器官身体。
时空破碎症。“时”指的是纵向关系。精神分裂者打碎了时间上的阻碍,拒绝承认因时间差别而产生的差异。“空”指的是横向关系。精神分裂者拒绝承认因空间排列顺序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他们拒绝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认为天地间万物皆平等,拒绝金钱诱惑,要去除“脸面性”,拒绝固定生活和工作场所,也拒绝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断地解辖域化。
二、精神分裂人格品质与电影艺术
电影最大的艺术感染力就是能够使观众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而跌宕起伏,使他们不经意间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从而产生共鸣和反响。而且观众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感受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与力量。如今电影作为一种影响颇为深远的大众传媒,既宣扬和继承民族传统,也号召建立良好的为人民所信服并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从而构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和谐社会。
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电影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精神品格都属于精神分裂型的。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性是未来的曙光和人类社会的希望。
首先看《我不是潘金莲》,李雪莲无疑是一名“少数派”。当初驳回离婚判决的法官已经阐释清楚为什么不存在假结婚的理由,各级政府官员也都曾苦口婆心地劝她,但是她拒绝接受别人为她准备好的理由。她一根筋,认死理,非告不可,在她身上体现出的是少数派的特质。她觉得她心中的公平正义就是绝对的公平正义,劝她的政府官员都是贪官污吏,推诿扯皮。所以从起初她只想告前夫秦玉河一个人到最后告各级官员,越告越多。在蔡市长一层层传下来变了味的指示下,李雪莲在派出所被关了几天,导致她对告状死了心。可以看出在“多数人”主导的社会中,他们是不会让“少数派”生存下来的。当李雪莲希望秦玉河说句真话后她就偃旗息鼓时,秦玉河却说她是潘金莲,这再一次使李雪莲陷入了“冤屈”,她患上了“自闭症”并进一步形成了恶化的无器官身体。此时的她不与世界交流,唯一交流的手段就是以暴力形式将异己力量铲除。所以她先后找到自己的表弟和杀猪的老胡,让他们帮忙杀死秦玉河和各级官员。因为她觉得只要铲除他们,自己就得以沉冤昭雪。在遭到拒绝后她决定去北京告状。这时恰逢人代会期间,她告状成功,与李雪莲事件相关的所有官员受到严肃处理。但她却认为这件事还没有完,因为秦玉河还逍遥法外,她不是潘金莲这件事也还没有说清楚。钻牛角尖的李雪莲将精神分裂品质展示得淋漓尽致。后续新上任的官员们,由于害怕重蹈前任们覆辙,就严防死守,阻止李雪莲上访。虽然换了一批官员,但大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只要既定的规制还在,精神分裂者李雪莲的“枷锁”就在,精神分裂产生的环境就在,所以她挣脱枷锁的行动——告状总在进行之中。10年过去了,李雪莲每次都在人代会召开时去北京告状,让各级官员头痛不已,所以,他们都来找这位农村妇女谈话,甚至送礼。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现象,在“多数派”主导的社会下,一般都是百姓找官员们溜须拍马,何曾有过官员给百姓说好话这种事。电影的最后,李雪莲告状这场闹剧以秦玉河意外事故死亡而告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雪莲失去了告状的动力,她认为自己的事情永远也说不清了。但体制的问题并没有改观,今后还会出现其他的李雪莲。这样的时空破碎难免让人怀疑这场意外事故是巧合还是蓄意,但电影并未明说,耐人寻味。同时,电影中对各级官员处理此事的过程没有大肆渲染,时空压缩导致李雪莲本身镜头变多,时空延长,许多的故事情节都是从李雪莲本身的动态及心理反映出来的。
通过《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我们可以从李雪莲告状告了十几年这件事上看到整个体制里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过下属的问题。官员们在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实质。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对上级小心翼翼,对下级颐指气使。正是这样才使本来并不占理的李雪莲“拿捏”住了他们。同时,李雪莲作为整部电影中几乎唯一的女性角色,成为雄性动物环伺并围猎的对象,她是外来者、少数派,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但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弱者”变得咄咄逼人,“强者”变得百口莫辩。在阻止李雪莲上访的过程中,他们派人看守她,当她逃跑后又利用很多资源来找她。有这么大的精力花费社会资源来阻止百姓上访,为何不在最初就好好解决问题?精神分裂者在大众看来是神经病,但在德勒兹的眼中却是革命者,在精神分裂者面前,时空之墙轰然倒塌。时空破碎症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果我国一些封建思想浓厚的领导干部不把自己看成是封建主,我们就不会有那么艰巨的“打虎”“拍蝇”“猎狐”任务。这部电影中的李雪莲就像是“拜伦式英雄”一样,一个人战斗,她是黑暗中的明灯,只身一人与各类贪官斗争。她是个典型的精神分裂者。
再看《血战钢锯岭》。它采用的是倒叙手法。电影一开头即展现了尸横遍野、人间地狱的残酷战争场面,戴斯蒙德·道斯已然受伤躺在担架上,战友们呼喊着让他撑住并发誓会带他离开战场,接下来镜头转向16年前的主人公。电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压缩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短时间内展示了长时间的内容,把时间和空间上无数个节点联系在一起,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通过一系列画面和音乐的变化,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时间上的贯通和换位。道斯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具有精神分裂人格品质的“少数派”。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信仰基督。父亲曾参加过“一战”并见证了战友们的牺牲,受过很大创伤,因此整日酗酒并对母亲施暴,这导致小时候的道斯受父亲的影响也有暴力倾向。有一次和哥哥嬉闹差点失手导致哥哥丧命,他深深自责并看到了教义说杀生是最大的罪恶,这使他的信仰开始内化。还有一次当他听到父亲又在殴打母亲时,他忍无可忍冲进房间拿起枪对准了父亲,虽然最后并未真正杀死父亲,他却觉得在心里已经杀死了他。他开始变得恐慌,害怕,并意识到相信教义还远远不够,在冲动时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犯戒,所以励志无论如何不用枪杀生。在偶然的一次用皮带救人并得到了医生的夸赞时,他进一步对生命感到了敬畏。后来与白衣天使多萝西·舒特一见钟情以及在医院门口看到了被烧伤脸的士兵,这一切都激发了他认为自己需要去战场服役的想法。
道斯体格瘦弱,又坚决拒绝在战场上拿起武器,于是受到了同期服役士兵们的排挤和欺凌。尽管战友、长官、牧师以及女友都劝他装装样子,但他依然恪守信仰。他认为任何对他人信仰的干预都是错误的,他决不会因长官的命令或规章制度动摇自己的信念,也始终认为没有信仰就无法生存。由于道斯是基督徒,他提出了周六是他的安息日,不工作。这是精神分裂的现象,上战场不带武器,作战还要选日子,这在“多数派”主导的社会下是荒谬可笑的,故而长官们希望判断他的精神方面是否适合服役。但他坚持不退役并且最终获准作为一名军医不带武器上战场。
道斯冒着枪林弹雨,当大部队撤退时依然在战场上救助战友,甚至包括幸存的敌人。当他误入日军的地道时碰到了一位受伤的日本士兵,他第一反应是拿出纱布为其止血,并注射吗啡以减轻他的痛苦。此时的道斯进化为丰满的无器官身体,他不认为眼前的是敌人,而是觉得他作为一名医生应该救助病人。因为《圣经》告诉他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有活下来的权利。这虽令人匪夷所思,却不是他一时冲动的恻隐之心或是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是他人性中的一部分。他是地道的“少数派”,体现了精神分裂人格品质。道斯在钢锯岭独自救回了75条人命,他的勇敢、执着和英雄壮举得到了战友的肯定和尊重,并最终获得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战争电影的本质不是宣扬战争,而是借助再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彰显人性的光辉,引导人们崇尚和平,远离战争。
电影艺术中的“少数派”以其精神分裂式人格品质震撼着每位观众的心灵,通过“视觉暂留”在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这些“少数派”所传达的正能量。电影艺术通过这些少数派的精神分裂人格品质影响着观众,构建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