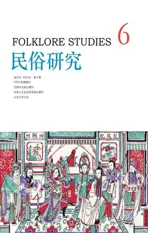山神信仰:韩国佛教寺院中的异域空间
2020-11-12李海涛
李海涛
从文化上看,东亚社会可以归为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等。在东亚文化圈中,中国作为哲学、宗教与思想文化之源头,对韩国、日本、越南都产生了诸多影响。然因时空上、固有传统及思维上的差异,韩国、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化之受容,并不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适时地做出了诸多改变,带有一定的国别化、本土化的特性,同时这也展现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中产生的多种可能性。

一、佛教寺院中的山神信仰
从地形上看,朝鲜半岛多山,山地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70%左右。为此,韩国的山川崇拜和山神信仰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影响深远。《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神话中表现出的山川崇拜和山神信仰最具原始性和代表性。
雄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唐高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庚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4)[韩]崔南善编:《(增补)三国遗事》(异纪卷第一·古朝鲜),民众书馆,1971年,第33-34页。






为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传统佛教寺院中带有巫俗性的山神信仰和韩国佛教信仰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突出表现为奉安山神的殿阁的位置和规模。从位置上看,奉安山神或三圣的殿阁一般都不是在寺院中的某个角落,而多数情况都是在寺院主殿大雄殿或极乐殿的旁边,是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并以左上方位居多。同时,山神阁或三圣阁的地基一般也会高于大雄殿或极乐殿主殿。这充分表明了山神信仰在佛教寺院中的重要性。但若从规模上看,奉安山神或三圣的殿阁一般又都比较小,甚至于有的阁都无法容下一个人直立进去,只能采取跪拜的方式进入。另外,这些建筑基本上都称之为“阁”,而非“殿”(也有例外,如首尔奉恩寺奉安三圣的地方称为“北极宝殿”)。这又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佛教寺院对山神信仰的某种限制。在韩国传统佛教寺院中,山神信仰一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并受欢迎,另一方面又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两者之间的紧张感和张力或许更多应源于韩国佛教传统及僧众与巫俗传统及民众之间的不同追求。
二、韩国佛教寺院中山神信仰出现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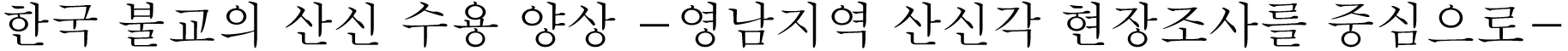
图1 山神阁(山灵阁、三圣阁)建立时间(20)金宪真的统计来自104个调查对象(》,第12-13頁);全道雄的统计来自京畿道山神台建立时间的调查(《》,《人文社會論叢》第12辑,2005年,第84頁);尹秀烈的统计来自对100个山神帧画出现的年代统计(《朝鮮後期山神幀畵硏究》,東國大學校大學院碩士學位論文,1998年,第48-52頁)。

众所周知,随着古代中国文化的不断传入,佛教和儒教文化先后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乃至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统一新罗时期和高丽时期,国家和民众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引领者是佛教,而到了朝鲜朝则变成了朱子学。但无论哪个时期,朝鲜半岛上固有的、由来已久的山川崇拜和山神信仰在国家层面和民众日常生活中一直承担着传统习俗的角色和功能。在高丽朝、朝鲜朝时期的官方正史和文人诗集中常常提到“山神”“山神祭”“山神斋”,如《高丽史节要》中的“锦城山神”(22)《高麗史節要》卷一九,忠烈王一,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山神祭”(23)《朝鮮王朝實錄》,太祖七年,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山神斋”(24)《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十年,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伽耶山神”(25)《朝鮮王朝實錄》,太宗十六年,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而《韩国文集丛刊》中提到“山神”则有292次之多。(26)通过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中检索“山神”而得出。如果具体看这些有关“山神”的记录则会发现这里的“山神”通常是作为独立信仰而存在的,所以供奉这些山神的地方也往往被称为“山神祠”“山神堂”,这与后来融入到佛教信仰中的“山神阁”有所不同。那么,山神信仰是在什么背景下融入到佛教信仰当中而失去原有的独立地位并成为韩国传统佛教寺院中“山神阁”“山灵阁”“三圣阁”的呢?
首先,从历史演变上看,韩国的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不仅仅是朝代的更迭,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即从高丽社会崇尚佛教转变为朝鲜朝崇尚儒教朱子学。朝鲜朝在建立伊始,佛教的发展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既有来自理论上朱子学的批驳,又有来自国家政策上的排佛措施。在理论上,先有韩国儒学家郑道传竖起了排佛的大旗,从外在形式和理论上全面地批判佛教、排斥佛教,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的传播、发展乃至成为官学扫清障碍,后有韩国大儒李退溪确立朱子学在朝鲜朝的独尊地位,斥释氏所言为“灭伦绝物”之教,明令禁止与排斥。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排佛,也许并不能导致朝鲜朝佛教的急剧衰落,因为它的效力相对有限。实际上,真正给朝鲜朝佛教发展带来强大阻力和打击的是政策上的一系列排佛措施。合并佛教宗派、没收寺产、禁止良民出家、禁止度僧、禁止僧尼出入都城等一系列排佛政策的实施,使得僧侣不得不远离都市,退居到山林之中开辟道场,勉强维持其法脉。(27)参见李海涛:《论朝鲜朝山僧禅及其儒佛会通观》,《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2016年,第130-131页。可以说,在整个朝鲜朝五百年的历史中,排佛是主旋律,虽然在太祖、世祖、仁粹大妃、文定大妃和宣祖等个别国王或大妃的支持下佛教偶有短暂复兴,但这并未能扭转佛教发展的颓势。面对如此状况,韩国佛教在理论上、信仰形态上及生存方式上发生了诸多改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山林化”。事实上,山林化本身就是印度佛教在东亚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变化之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渐趋远离政治中心和都市生活,而走进山林之中,强调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修行,从而带有印度佛教寺院阿兰若寺的特性,尤其是禅宗可谓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代表,“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佛教的山林化。但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佛教的山林化一方面体现的是出世情怀,远离都市红尘,与白云为伴,以清风为友,在大自然中学经问道;另一方面体现的是僧尼的自我追求,是一种主动式的山林化。而与此相比,朝鲜朝佛教的“山林化”则是一种被动式的山林化。(28)参见李海涛:《论朝鲜朝山僧禅及其儒佛会通观》,《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2016年,第131页。它是在国家长期排佛政策的打压下,不得不退居或只能到山林之中生存维持法脉。韩国佛教正是在这种被动式的山林化过程中,开始要面对存在于山林之中韩国传统的并具有相当影响的巫俗性山神信仰,从而出现了佛教受容山神信仰的可能性。
其次,从生存基础上看,佛教传入韩国伊始,就开始与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佛教信仰群体多是贵族,而流传方式也多是自上而下地推行,这种状况使得原本僧侣的托钵乞食方式在韩国变为王室和贵族的供养制。这一方面导致韩国佛教与政权的关系紧密,从而发展成为国教,但另一方面也导致韩国佛教渐渐仪式化、世俗化,失去了佛教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在进入朝鲜朝后,佛教不仅失去了国家和贵族的支持,同时又要面对一系列的排佛政策,所以其在生存上面临了巨大的危机。首先是生存空间、信仰群体的缩小和社会地位的降低。朝鲜太宗王时期,开始不断合并佛教宗派,从十二个宗派(29)曹溪宗、摠持宗、天台宗、天台疏字宗、法事宗、华严宗、道门宗、慈恩宗、中道宗、神印宗、南山宗和始兴宗。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六年,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合并为七个宗派(30)曹溪宗、天台宗、华严宗、慈恩宗、中神宗、摠南宗和始兴宗。参见《朝鲜王朝实录》太宗七年,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到世宗王时期则只剩下曹溪宗和天台宗两个宗派,最终在中宗时期因僧科考试制度的废止而使得宗团的存在没有了必要,从而形成了没有宗派特色的通佛教。由于朝鲜朝对承认的宗派及其寺院在数量、田产土地和奴役上都实行一定的限额,因此合并宗派所带来的是寺院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田产土地和奴役被强行剥夺,超额的僧人被迫还俗,僧人地位也一落千丈。其次是佛教在朝鲜朝被迫走向山林化,开启了山僧时代。当寺院及僧尼被限制在一定数量后,又开始禁止民众成为僧尼。从禁止少年出家、禁止良人百姓出家、禁止两班妇女出家到禁止度僧,乃至强令僧侣还俗,严禁供佛等措施,致使佛教几乎完全失去了存活的空间。(31)参见李海涛:《论朝鲜朝山僧禅及其儒佛会通观》,《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七辑,2016年,第132页。最后由于文宗王时期实施“僧禁”,即禁止僧尼出入都城,则彻底把佛教逼到了山林之中。诚如上文所言,虽然佛教寺院,特别是禅宗寺院及僧团很多都选在名山大川之间,在一定意义上也属于山林佛教,但它只是地理上远离都城,强调纯朴的清修生活,却允许与都城发生关联。然僧禁的实施却完全割裂了几乎所有寺院与都城之间的关系,使得寺院及僧众只能偏安于山林之中。而在韩国固有的传统中,山林中的山神信仰由来已久,并在民间盛行,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因此,一方面,进入山林的佛教必然要面对山神信仰及民众的信仰追求;另一方面,进入山林的佛教失去了原来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民间信众来维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但是从功能上看,佛菩萨信仰与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不完全吻合。对于民众来说,主管财富、子孙、疾病及生命的山神信仰更为密切和重要。所以,为了得到民众的供养,满足民众的信仰诉求,韩国佛教开始受容山神信仰,通过建立山神阁、山灵阁或三圣阁等形式把山神信仰纳入到佛教寺院的信仰体系之中。
如应云空如僧(32)应云空如,朝鲜朝时期的僧人,主要生活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所撰“山神阁劝善文”载:
山神菩萨以大权,助化佛事,为物兴悲而迹居神位。故众生求福则与之,求财则与之,求子则与之,度贫则以富度之。况建阁奉安,不亦善乎。以山神阁新建次,普告檀门,同结善缘。万千祝手,仍兹奉祝。四门允穆,百揆时序,上降休宝,下叶祯祥。(33)应云空如:《应云空如大师遗忘录》,《韩国佛教全书》第十册,东国大学出版部,1995年,第743页。
又如金允植所著《云养集》“山神阁记”(34)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1835年生,1922年卒,朝鲜朝末期的学者,著有《云养集》。载:
(灵塔)旧有画帧一幅,寓挂佛桌之西,非所以专敬也。寺僧正基常以为忧,一日梦有一老人坐莲峰下石上,以杖指之曰:“此可以安吾身,汝其识之!”正基觉而异之。戊子春,郡守宋侯在华捐缗钱付正基,俾营一屋以妥之,邑中士民亦乐为之助,遂构数椽精舍于香阁之右,即老人所坐处也。是年五月日,移奉画帧于新阁,以时致敬。是邱也擅一山之胜,负翠壁、临丹壑,苍松荫其上,清泉绕其下,潇洒清幽,俯仰有致。见者皆欢喜,得未曾有,相谓曰:“名区、灵境,只在咫尺而人不知之,必待神喻而得之,山之灵不亦昭昭乎?宜吾沔邑之人长受其福庇也。”阁成正基请志其事。(35)《云养集》卷十《山神阁记》,韩国古典综合DB数据库。
两则材料说明了山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而佛教则主动地接受山神信仰进入到寺院之中,并通过向社会募集资金建立“山神阁”。其中,山神信仰原有的构成要素和社会功能并未得到破坏,而是作为佛菩萨的本地垂迹融入到佛教寺院当中。正如韩国学者金星顺所言,山神阁、山灵阁及三圣阁的出现主要是佛教寺院为获得持续资助而主动与民间信徒结合的僧俗联合,是为了民间信众的现世性发愿而形成的仪礼空间。(36)参见金星顺:《韩国念佛结社中修行方法的变容》,李海涛译,《宗教研究》2016年春季号。因此,对于佛教寺院来讲,受容山神信仰是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所导致的,虽然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却是主动而为的。所以,在建筑规模上和名称上受容主体佛教对山神信仰做出了种种的限制,在等级上将奉安山神的地方称为“阁”,而非“殿”,建筑空间也十分狭小,呈现出佛教寺院中山神信仰与佛菩萨信仰之间的张力。
最后,关于佛教寺院受容山神信仰为什么普遍出现在19-20世纪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虽然朝鲜朝从一开始,就不断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抑佛政策,但在太祖、文宗、世祖、仁粹大妃、文定大妃及宣祖时期都有抑佛政策的缓和与佛教的短暂复兴。特别是在壬辰战争时期(1592-1598),僧人西山休静号召僧团抵抗倭寇,建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朝鲜朝一代高僧和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在17世纪前,朝鲜朝佛教并未完全山林化,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生存空间,可以借助高丽时期遗留下来的佛教传统和基础,以及短暂的排佛政策的缓和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但到了17世纪以后,佛教在朝鲜朝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只能完全退居到山林之中来维持命脉。也正是在完全山林化的过程中,朝鲜朝佛教不得不主动地受容韩国山林之中固有的山神信仰,从而发展到19-20世纪开始普遍性地建立山神阁、山灵阁及三圣阁等,使山神信仰成为韩国佛教寺院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20世纪,朝鲜半岛面临内忧外患,传统宗教势微,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固有的山神等巫俗信仰受到欢迎,并开始盛行。所以,在当时不仅佛教在主动受容山神信仰,韩国很多新兴的宗教团体都在试图从巫俗信仰中汲取营养和传统。
三、结 语
如前所述,在传统寺院中奉安山神信仰是韩国佛教的主要特征,然而它的出现虽是韩国佛教主动为之,但却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所以,韩国佛教寺院中奉安山神的地方在等级上称为低于“殿”的“阁”,建筑空间也要比大雄宝殿小上很多。但其所处的位置却十分显眼,靠近韩国佛教寺院的主殿——大雄宝殿,而且往往其基石也高于大雄宝殿。在功能角色上,山神信仰相比于佛菩萨信仰与民众的生活更为密切。从中可以看出,山神信仰在韩国佛教传统寺院中呈现出强烈的紧张感。以至于近代以来,针对佛教寺院中的山神信仰,韩国佛教的代表者韩龙云、青潭法师等都曾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当性。但这并未改变韩国传统寺院中山神信仰的普遍存在。也就是说,通过山神阁及山神信仰体现出来的佛教僧众与民间信众之间的张力一直存续着,这形成了韩国佛教寺院信仰形态上的一种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