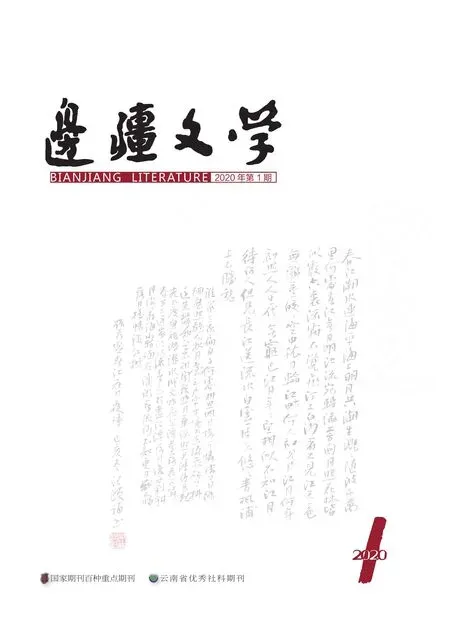德拉姆玛璜
2020-11-12
“如果是你一个人,在藏北无人区,大白天你都会感到恐惧,没有人烟,太辽阔和安静,除了零下十几度的寒冷,除了风在啸,敢接近你的动物就是狼。”
——德拉姆玛璜
1
随着高原最后一抹阳光的隐去,天边的乌云千万头野牦牛一样压下来,直压到德拉姆玛璜的眼皮上。在阿里无人区行驶了一天,第一顶白帐篷出现了,是的,唯一的一顶白帐篷在乌云与金色荒原的挤压下,揉扁成一条线在呼啸的雪风中抖动。这种色彩对比让玛璜有些压抑,但他明白不能再走了,黄昏里, 前方有知也未知。打开炉头煮了一锅云南的酸菜汤,啃完一个青稞饼,天就完全黑了。再默默抽完两支烟,泡一壶热茶,他躺到了后面的床上。一辆新买的依维柯,床是后改装的,像一个流浪中舒适的家。
约后半夜,他被窗外“咵咵”的刮擦声惊醒了,“是狼!”他一秒钟立起身,不敢开灯,黑暗中侧耳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低沉幽咽的嚎叫在寂静的旷野分外尖厉。车身够高,窗外绿光在闪烁,不确定有几条,但不管有几条,他告诫自己不能有任何动静。因为前不久,两个年轻力壮的内地小伙子才在阿里革吉到改则的荒野里被十几条狼嚼得只剩几根骨头。
就这样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到天亮,狼离开了。说不紧张是假的,但也没有多恐惧,后来玛璜给我讲故事时这样说。这样的遇见,玛璜重复了二十年。
这就是德拉姆玛璜的生活,他存在于我们正常的生活维度之外。
一如一匹高原中孤独奔袭的狼,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四千米以上的雪线穿行的。他的时空与视觉,似乎让我们遥不可及,有时候给他打个电话,声音里都裹挟着凛冽的雪风,那穿过几千米海拔的声音,遥远而隐秘,完全藏匿在呜咽的山风和猎猎抖动的经幡声中。
德拉姆玛璜的职业,是西藏深度探险游的领队兼司机。除了一拨又一拨向往西藏的驴友,陪伴他最多的大概就是藏北高原的藏羚羊、藏野驴,众多的神山圣湖,分不清天地万物的暴风雪,数不尽的冰川庙宇,以及返程路上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快意……以致于在路上,他写下了很多流淌在心底的诗歌:多少傍晚/在远方/风吹拂着,远逝的夕阳/途中游子,已不知/归途在何方。
德拉姆玛璜,首先得说说为什么叫德拉姆。德拉姆在藏语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活佛给他起这个名字表达的意思是仙境里走出来的人。我认识玛璜之前,不知道世间还有人可以这样天马行空的活着,人与人在自然界的存在方式,竟然可以这样不同。当我们正常地上班下班吃饭逛街的时候,他或许在五千米的冰雪路段,捆着防滑链、听着《扎西卓娅》翻越阿里的冰山;或许在昆仑山的五道梁,披着零下20度的严寒,在一个小饭馆里一边泡脚,一边饮一口烧酒,用小刀剔着一个羊头,末了跳进车里,钻进藏毯,听着窗外可以扯断夜幕的风声入眠;或许在冈底斯山脚下,听着远处寺庙的梵音,叼着烟斗,写着《玛滂雍措神示》:他们沿着祖先的足迹/从山的那一边走来 /匍匐在这神山的脚下 /风从冈底斯山谷间吹来过/冈仁波齐,众神在俯视着苍生 /蓝色的玛滂雍措,粼粼波光 /如同闪现着神的启示 /生死皆是注定的轮回 /冥冥苍生恍若隔世
就这样一个人,德拉姆玛璜为我展现了完全陌生的人生境遇。他在滇藏线“流浪”二十年,在怒江大峡谷的丙中洛落脚也已二十年。他大女儿从读书到教书一直都在藏北阿里, 他与藏区的渊源这样深,深到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只好说,这一切都是神赐予的。西藏有他二十年的心灵挣扎,到现在,他的灵魂和信仰,都盛开在拉萨的天空下。
玛璜是我行走路上遇到的一位个性奇特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西藏是一种病。当你踏上了,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病下去,不知疲倦地走向那片高原。
凡是上过玛璜车的客人,都说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至今坚持用繁体字。他研究西方文学,喜欢俄罗斯电影和音乐,深刻理解藏地文化,普希金、 泰戈尔、仓央嘉措,不同土壤的诗人,在他骨骼里开出奇异的花。如果这些是能够在与他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的话,他人性的丰富和多面,内心的坚韧和善意,就需要从他二十年的进藏经历一点一点去抽丝剥茧。
我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能够坚持跑西藏。按每年最低进藏六、七趟来算,二十年他已进藏一百二十多趟。我们每个人都把进一次西藏当作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事,跟玛璜比起来,这一次只能算是人生中的点缀。对我们来说,一次点缀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生动不少,那么再多几次呢?
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新藏线,二十年的孤独奔徙,二十年的人性纠葛,使玛璜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常常陷入思考中 。在这条线上跑的人不少,但很少有人能坚持这么久。因为极少有人能像玛璜一样,把西藏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2
玛璜的经历很特殊,甚至有些另类。他进藏之前有十年,也就是他二十来岁最年轻的时候,是在缅甸丛林度过的,丛林里的生死过往,让他常常感到自己是在人与野兽之间游走,两者之间其实就是一张纸的距离。但他童年及少年时期父亲教给他的东西,比如血性,比如坚韧,比如对文学的偏执,又悄悄潜藏在他骨子里,让他始终不低下自己的头颅。他的父亲首先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先后就读燕京大学、广东黄蒲机械学院, 1942—1944年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滇缅公路当运输连长两年多,父亲的理想信仰、家国情怀对玛璜后来的内心蜕变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父亲留下的上万册中外名著、诸子百家,玛璜读了几十年,以致于有驴友发帖子这样评价玛璜:“像一匹雪域的狼,凶狠,但忠诚;冷酷,但优雅;匪气,但绅士。究竟哪一面是他,不知道。”
玛璜第一次进藏是大女儿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因为玛璜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家里生活陷入困境,大女儿5岁时从昆明被送到了阿里,与朋友扎西的女儿一起上学,一起放牧。5年后,玛璜去阿里看女儿,先赶到扎西家,见门上挂着长满铁锈的锁,再赶到牧场,见到了扎西一家。见女儿心切,玛璜与扎西夫妇俩骑马赶到了学校。扎西进去跟老师请假后,两个穿藏袍的小女孩飞快跑出来,扑到扎西夫妻身上阿爸阿妈地叫,玛璜心里就像掉了几个梅子一样酸。扎西把女儿牵到玛璜面前说:“这才是你的阿爸”,女儿看看他没说话。只见她的鞋子破了个洞,里面一双红色的袜子露了出来;玛璜伸手摸摸她的袍子,里面是羔皮的,挺暖和。两个女孩年龄悬殊不大,相反,扎西女儿的衣服却没玛璜女儿好。
在即将回扎西家的时候,玛璜看到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场景,十岁的女儿,抓住马鬃和鞍子,啪的翻身跳上马去,还在马上抖了抖,坐正了身子,因马镫长,孩子脚短,还将马镫挽了挽,坐正了以后,伸手将扎西的女儿拽着拉上了马,一拍马屁股,两个女孩一溜烟就跑远了。这一连串动一瞬间一气呵成,他想,这是我的女儿吗?汉话一句不会说,马倒骑得飞。
到了帐篷,扎西家的亲戚朋友早就杀了牦牛,忙着弄吃的喝的,玛璜想看看女儿,就四处去找,在一个帐篷里,看见两个女孩子从腰里拔出一把刀,生的新鲜牛肉唰唰唰飞快地被剔下来喂进嘴。这一刻,玛璜心里很是复杂,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远离父母的时候,在陌生的环境,就这样把自己磨炼得与当地孩子无任何区别,这都是生存的需要。玛璜女儿的藏族名字是活佛起的,叫乌金帕雅,乌金是莲花生的意思,帕雅在藏语里是纪念父亲。曾经,他们都以为玛璜已不在人世。
从女儿身上,玛璜第一次体会到,在藏北,在这个区域,要想活下去,想活的好一点,那就要完全适应这里的一切生存法则。
因为女儿不会说汉语,升初中考试在即,朋友扎西不愿意玛璜带走女儿,玛璜只有万般不舍地离开了阿里,但他的心却被女儿抽走了一半,阿里也成了他最牵挂的地方。
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玛璜在成都遇到几个外国人,请玛璜送他们去川西。一个星期后,玛璜收到1000多美元的报酬。他很惊讶,原来钱还可以这样赚。他开始留意这方面的机会,又跑了几趟西藏,广阔的雪域高原,为他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视野。
玛璜曾对我说,“我没有理由不热爱,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我就在这样在路上跑,我找到了生存的途径,一句话,我能赚钱。而且是自由地在赚钱。我没有依附任何人,就靠自己。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就这样,也没人教我,也没人告诉我该怎样做,我就被感染了。”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刚好到狮泉河边,天上出着太阳,玻璃却被豌豆大的冰雹砸得啪啪直响。
跑了几年以后,玛璜的区域不断在扩大,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新疆,敦煌,三江源,可可西里无人区,任何一个地方,都让他的灵魂在震撼。
2001年。已两个月没一趟行程,没赚进一分钱,要养两台车,孩子要上学,加上生活费各种,玛璜内心处于很焦虑的状态。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拨北京的客人预约两天后跑西藏。这时已是晚上11点,玛璜与玛璜嫂一人一台吉普车,在黑夜中驶出了昆明。那时成昆线还没有高速,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到达攀枝花。找个路边店吃点东西,洗漱一下找到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停车睡到中午。黄昏时,到达西昌。沿途路很难走,米易、德昌那段正修路,尘土飞扬,时堵时疏。再到第二天,玛璜如约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接了北京八个客人到了成都,住进青旅,第三天以后的行程就是都江堰、汶川、若尔盖、甘南、拉卜楞寺、兰州、西宁、格尔木、纳赤台、昆仑山口、西大滩、不冻泉、风火山口、五道梁、沱沱河源大桥、雁石坪、唐古拉山口、安多、那曲、当雄、拉萨。拉萨修整两三天,羊卓雍措、亚东、珠峰,再返回拉萨飞走。
这个行程结束后,两台吉普车如果空车返云南,成本很高,只能在拉萨等客人。一天,两天,三天,正烦躁的时候,酒吧电话来了,“这里有一趟珠峰六天你跑不跑?一台车”。“跑啊,怎么不跑。”三个人去珠峰,玛璜带上就出发了。羊卓雍措、江孜、定日、珠峰,六天的行程就要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客人从不信任到信任,还没到达拉萨,三个人又跟玛璜商量从青藏线回去。又走了约一星期,到了敦煌,客人留下玛璜的电话愉快地飞走。
送走客人,玛璜就翻当金山、大柴旦几十公里的山坡,到达格尔木。格尔木是一个工业城市,维护汽车的技术很好,玛璜需要把车开进修理厂做彻底的维护。头天下午把车开进去,第二天中午把车接出来,然后去吃东西。进了一家新疆人的店,烤羊脸16块钱一个,玛璜刷刷刷剔下肉,洒上辣椒、花椒、孜然,劲道得不得了,比羊肉还抢手。再买两个饼子,灌满烧酒,吃得饱饱的,一点多离开格尔木。
一路翻过戈壁滩、纳赤台、昆仑山口、不冻泉。过昆仑山口的时候飞着雪花,到不冻泉时变成冰雹,再到可可西里时狂风大作,晚上九点过十点的时候,就接近沱沱河源大桥。那个地方吃别的是不用想了,找一家甘肃拌面,跟老板要个盆子,首先把水壶灌满,再在盆子里放热水,边吃面边泡脚。泡完继续赶路,从沱沱河源大桥出来接近雁石坪、翻唐古拉山已经接近夜里一点多钟了。到山口已经很困,那里有个平台,玛璜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下,拿出指南针,把车头对准东南方向,这样第二天太阳出来容易启动,不会把水箱冻坏。当把车门打开的时候,寒风在呼啸,雪柯子打在脸上又硬又疼。跳上车留一点车窗,保证空气流动,钻进睡袋,只留着眼睛鼻子。半夜三更听着外面几台车在启动,天稍亮还是担心水箱被冻住了,睡不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发动车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终于打着了,这时他觉得这声音动听的不得了。
玻璃雨刮器都冻住了,不能刮,玛璜到窗外含一口酒喷在玻璃上,慢慢让冰融化。捡一块冰渣含化把口漱了,挖一杯雪把脸洗了,手粘糊糊的很难受,抓点洗衣粉在手上搓,再抓几把雪在手上搓,把手搓干净了。车发动了,听着刀郎的音乐,挑一坨羊脸肉,冻得硬邦邦的,摇摇水瓶子,也冻起了,洗脸帕硬得像个扇子。拿出工兵锹敲轮子上的冰,每个轮子上都能敲下来砖头大的三四块。等玻璃终于没雪了,慢慢用雨刮器刮一刮,慢慢地接近了安多,接近了羌塘,接近了那曲,傍晚时分已接近拉萨了。一个行程就结束了。然后又在拉萨等着,不知道下一个行程是哪里,藏北吗?珠峰吗?317吗?还是再走青藏线?他不知道。但他喜欢这种生活,既能挣钱养家糊口,也能结交很多朋友,还能满足自己漂泊的野心。原来觉得很遥远的地方,很多雪山,很多圣湖,知道的不知道的,不经意的就去了,不经意之间就看到了,不经意之间就有所发现了,一杯清茶,一小束野花,一块饼子,都是途中的快乐。
就这样,玛璜每一次绝望的时候都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每做一趟,就对活下去充满了希望;每做一趟,就坚定了干这一行的信心。
就这样,他一步步走了出来。
途中寂寞时他在本子里这样给自己留言:我深深的热爱着这片净土,它远离尘世间那种世俗的尔虞我诈,拒绝弱者,对勇于涉足这片高原的人,它用纯净,震憾,安祥的自然景致给予了最好的回报,风雪,高寒,广袤无际,独特的文化,信仰,音乐,地貌环境深深使我依恋,让我着迷,让我无法不去热爱这片高原。
2004年,已在滇藏线跑了7年的玛璜定居丙中洛。他认为这里就是他理想中的香巴拉。他觉得丙中洛善待了他。他开了丙中洛第一个酒吧,在院子里停了四、五辆车,以丙中洛为起点跑丙察察,开始很浮躁,慢慢发生变化,心境平和下来,有了第一个朋友,第二个朋友,然后不断增多,那些十年前的很恶心的状态慢慢消失了,只觉得不撒谎的状态太美妙了,每天只一个面孔出现,可以每天说真话。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另一种状态又来了,很微妙的一种东西:他爱上了他的工作,爱上了路上碰到的一山一水,而并不只是把在路上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随着这种平和的状态、这种认知越来越明显,他心中又出现了一种状态,即一种感恩、一种冥冥之中对上苍的感激之情,再后来就摆脱了过去的阴影。缅甸的一切似乎有点遥远了。
丙中洛是玛璜的第一家酒吧、第一个客栈、第一个车队诞生的地方,玛璜喜欢它,喜欢到梦里梦外都是他离不开的家。尽管他的出生地与丙中洛毫无关系。
那时,丙中洛到察瓦龙的路还正在修,他就租马匹送客人去那些村子转,在他眼里,丙中洛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美,贫穷,落后,原始,淳朴,素面朝天,让人一眼千年,烙在心底挥之不去。德拉姆客栈几乎成了标志性的驴友聚集地,天南地北的客人,你传我,我传你,来到丙中洛,必找德拉姆。
而德拉姆,长年累月带客人穿梭在滇藏线、川藏线,如一匹不知疲倦的狼。丙察察,也就从这个时候成为最惊艳的一条进藏之路。丙中洛现在的名气,很大程度离不开德拉姆玛璜的传播。德拉姆玛璜这个名字,也已成为丙察察的一个传奇。丙中洛,也就成为玛璜不知疲倦地跑西藏的大后方。
在丙中洛,小芳的故事流传了很久,对小芳最后的归宿,也让玛璜很是欣慰,至少,他觉得,他的善意对一个女孩子的命运产生了影响。
2006年7月,丙中洛来了一个叫小芳的上海姑娘。当天晚上要包车到察瓦龙。那时西藏察隅县察瓦龙的路还没通,沿途是险峻狭窄的路面,当地藏民形容老虎过路都不敢打盹。玛璜带着小芳往察瓦龙里面的左布、密空走了一圈,再也没路往西藏方向走了,当晚就返回了察瓦龙。第二天打算往丙中洛返时,察瓦龙小学的校长白马出现了,问清楚玛璜要回丙中洛,就请求捎他及叔叔去贡山看病。
到了一个叫曲珠的地方,下面有一个温泉,玛璜建议小芳下去看看,她兴致很高,带了个相机就下去了。二十分钟后,她上来了,上车后刚刚起步要走,小芳突然说:“哎呀,玛哥,我的镜头盖你见到了吗?”在车里没找到,玛璜说是不是忘记在温泉那里了。她说真没注意。那怎么办呢?这时白马老师说他下去看看。十多分钟后上来了,说,“是这个吗?”小芳一看,正是她的镜头盖。
这是小芳与白马的第一次认识。
二十天以后,玛璜又接到小芳的电话,问察瓦龙的路通不通,她还想来看看。玛璜以为她上次来了后还有什么东西没拍到,就到丽江机场把她接到了察瓦龙。她说她只在附近转转,然后问了学校位置,让玛璜等她就行。第二天等了一天。第三天回丙中洛,小芳坐班车走了。又过了一个月,小芳又来电话了,要去察瓦龙。玛璜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一桩美事吗?小芳到玛璜德拉姆客栈后,神采奕奕,状态非常好。就这样,小芳连续来了五、六次。
后来有一次,玛璜把她从察瓦龙接出来以后,她情绪很不好,哭兮兮的。玛璜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白马告诉我,他还有个女朋友,是个藏族。”玛璜说,“那他要跟你挑明掉嘛,既然他跟你谈,就要跟那个女孩了断;如果要选那个女孩,就不要跟你纠缠了。”小芳沮丧地说,事情没那么简单的。小芳在上海是白领,父母很疼爱她。她告诉玛璜,她还跟父亲说,如果跟白马能谈得成,她打算辞去上海的工作来察瓦龙当老师。玛璜劝她慎重考虑,别做傻事。小芳说她现在很矛盾,白马并没有表态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玛璜跟她说,谈恋爱这个事,你情我愿的,白马喜欢谁,都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小芳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丙中洛。
过了两三个月,小芳又打电话来,她那里有几个小姐妹,在她的倡议下捐了两万块钱的书,想送到察瓦龙小学。同时要进藏玩一趟。当时丙察察还没通,碧罗雪山的路也没有,玛璜把那些小姐妹从318国道送进藏,她们从拉萨飞走后 ,小芳又跟玛璜到了丙中洛。途中小芳一直跟白马在商谈送书的事。但那几天察瓦龙一直在下雨,喇嘛庙那里的桥被洪水冲断了,谁都过不去。小芳就跟白马商量,让他从乡政府联系个车出来,把书拉过去,他们俩在桥那里见个面。左联系,右联系,这边玛璜已把书装上车,随时可以出发,但两三天过去了,白马始终没有搞定到底来不来。从不喝酒的小芳,喝了酒在玛璜家客栈嚎啕大哭,玛璜去看她,她一直说“他不应该这样对我,我没做错什么。”玛璜劝解她说,“小芳,你不属于这里的,他也不属于上海,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不要伤了自己。因为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差异,对婚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藏区,男人有几个老婆很正常,几姐妹嫁一个丈夫也很正常,你是上海人,你不属于这里,还是回上海去吧。”
小芳慢慢停止了哭泣,问那些书怎么办呢?当时已晚上十点多,玛璜给丙中洛的乡长打了个电话,那边马上回答希望能把这些书捐给秋那桶小学。第二天就在秋那桶搞了隆重的捐书仪式。
从此,小芳离开了丙中洛,再没来过。
3
我和朋友们随玛璜的车在路上的时候,无论是国道317上丁青巴青沿线匍匐在地前往拉萨朝圣的藏民,还是冈仁波齐脚下手摇转经筒转山求来世的人,都满脸虔诚,一脸陶醉。从阿里到拉萨,千千万万匍匐在地磕长头的藏民,他们带上所有养牦牛的收入和酥油,三年时间风餐露宿,蓬头垢面来到拉萨,来到大昭寺,只为听见经殿香雾活佛诵经的真言。大昭寺前的僧侣、漂亮姑娘、老年妇女,康巴汉子、乞讨者、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各种各样的人,戴着皮手套,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移至胸前,再过膝,哗哧一下,下跪,起身,下跪,起身,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有的人,身体还来不及到达大召寺,就在路上疲劳死去,但他的脚趾,会被同伴带到大昭寺,镶进墙缝里,让灵魂代替肉身聆听佛经,沐浴香雾。还有的妇女,身体里孕育着生命走在朝圣路上,到达拉萨的时候,孩子已经三岁。
在藏区跑了二十年,玛璜觉得,藏族磕长头、朝圣,他们匍匐下去的时候,内心世界体现的是对生的敬畏,对死亡的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万物的敬畏,这种宗教的力量,让他内心震撼不已。
“我希望一直都在路上,而且是在西藏这片高原上,只要有尊严,有信仰,我就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感到卑微,我想我会与这片高原融为一体,想到这,心中已没有什么能使我感到畏惧和可怕的了。”
有了这种认识,玛璜对这片土地充满了依恋,同时怀有深深的感恩之心, 他感恩客人让他学会了礼仪,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摄影,学会了敬畏,学会了尊重自然、尊重别人,一个游荡在社会边缘的行尸走肉的人知道了旅行是什么,知道了有尊严的生活。
他的许多感悟,让我常常陷入感动中,也陷入对西藏的无限向往中。在藏北,很多的事,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它却真实而顽强地存在着。
一天黄昏,玛璜与两名客人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走进荒野里一户唯一的藏民家中,一顶白帐篷、一顶黑帐篷在风中摇摆。白帐篷住人,黑帐篷放日用物品。方圆上百公里没有人烟,玛璜进去,这户人家有三个人,一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丈夫出门已两年了。
妇女也许很久没有见到人,几分钟后,换了一套崭新的盛装出来,走到玛璜的面前,拉过玛璜的手,用指尖在玛璜掌心摩挲几下,向玛璜传递着一个信息。她的脸,微黑中带着高原红,她的眼睛,羞涩中盛满了野性和渴望。玛璜明白了她的意思,摆摆手,假装肺部不适咳嗽了几声,说:“我身体不好”,随即出了帐篷,离开很远,还见妇女的袍子在风中凌乱。
我问玛璜,你们进去了三个人,她为什么偏偏找你呢?玛璜说,也许是我穿着藏袍觉得亲切吧。西藏,那个区域,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四、五千米的高度,在极度寒冷,极度荒凉的环境下,藏族特有的习俗,一种生存方式,就出现了。“在那种高度,你没有信仰,也许是支撑不下去的;在那种高度,你没有特殊的生存技能,也是生存不下去的。”很多人没法理解,在藏北为什么会有风干肉,风干肉是生的,怎么可以把新鲜肉一块块吃下去?怎么可以长年累月的没有蔬菜水果?怎么可以不像内地人一样一天冲个澡?不是他不想洗,而是在那种环境下冲澡面临很大的风险。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太过于神秘,太过于严酷,太过于孤独,它的宗教,它的信仰,已经保留了上千年。外来的物种,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宗教甚至都无法留下。
我在阿里的时候,尽管来之前做好了心里准备,但面对那无尽的荒原,内心还是旷凉无比。河谷里看到一帐篷,一个叫卓玛的年轻妇女,在凛冽的寒风中,在帐篷里给四个女孩子煮酥油茶,七八岁大的女孩们,辫子有些凌乱,低下头喝一口茶,咬一口手里的油炸饼子,高原红的脸上挂着酥油茶的热气,见我进来都露出羞涩的笑容。我问女孩们的名字,因孩子们都叫她阿妈,我以为都是她的孩子,她却告诉我有两个女孩是她妹妹的,因为妹妹生病去世了,妹夫离家出走了。两个孩子也就成了她的女儿。
见我惊讶,玛璜解释说,藏区里这样的情况很平常,兄弟姐妹之间,谁出了问题,他们的孩子都是共同的,没有亲疏之分。
在藏北,既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那为了生存,很多的事可以突破正常的理解范围。因为极度的荒凉,有时几个月见不到一个人,如果见到了,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惊喜,惊喜到可以杀一头牦牛。在阿里无人区,如果一个妇女在家带孩子,管牧场,两三年后丈夫回来,家里添了个孩子,一样可以管他叫爸,他一点不觉得生分。如果孩子的亲生父亲还继续留在家里,仍然可以作为家庭成员,两人可以成为兄弟,共同管理牧场,抚养孩子。
受玛璜的影响,我们跟着玛璜在西藏晃悠的时候,有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前方是什么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也不知道,但我们心里没一丝恐惧。也许走了一下午,雪山没有昨天漂亮,河谷没有丰美水草,甚至只是荒野戈壁,我们也很快乐,高原的每一个景致,都是摄人心魄的壮美。
每一拨上玛璜车的客人,都会在雪风强劲的垭口,接受到玛璜赠送的经幡,玛璜会把十几米长的经幡与客人一起挂在雪风凛冽的高原,伴随着他吟诵的绿度母心咒“嗡达咧,度达咧,度咧梭哈……”客人所有的祈愿都会在舞动的经幡中飘向佛居住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