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节选)
2020-11-06儒勒·凡尔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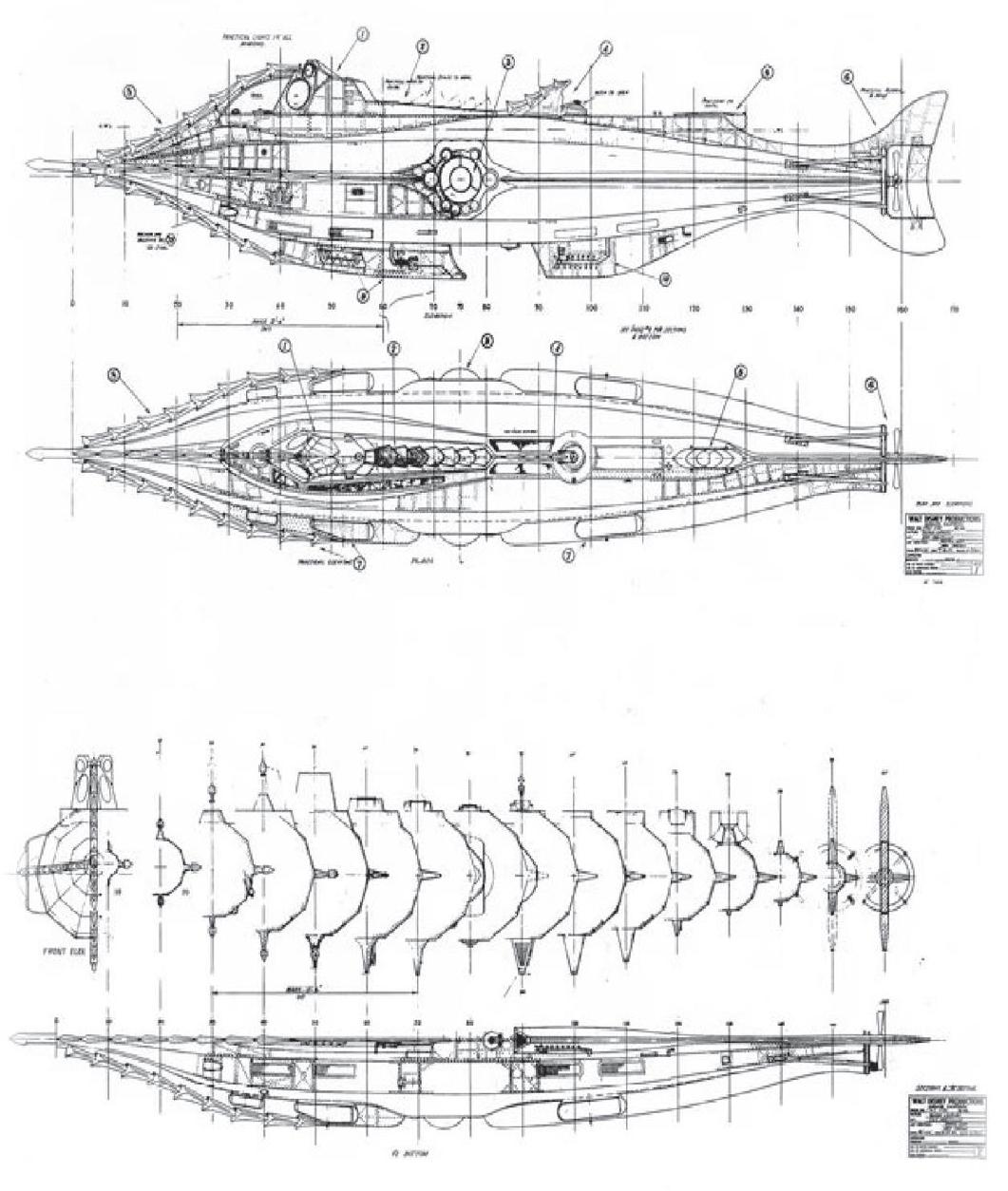
儒勒·凡尔纳(1828-1905),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凡尔纳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
起初,尼摩船长只是吃,不说一句话,后来才对我说:“阿龙纳斯先生,我邀请您到我的克利斯波岛的森林中打猎的时候,您以为我是自相矛盾。当我告诉您这是海底森林的时候,您以为我是发疯。教授,您不能这样轻易判断。”
“不过,船长,请您相信……”
“请您耐心听下去,然后再看看您是不是应当责备我发疯和自相矛盾了。”
“我听您说,船长。”
“教授,您和我都知道,人只要带了充分的可呼吸的空气,他就可以生活在水底下。工人在水底下工作时,穿上一件不透水的衣服,头上套一个金属的盒子,再利用打气机和节流器,就可以从水上面获得空气。”
“那是一套潜水设备。”我说。
“对,可是,带了这套设备,人是不自由的,那条输送空气的胶皮管子把他和打气机连接起来,简直就是一条把他拴在陆地上的锁链,如果我们是这样拴连着鹦鹉螺号,那我们就不能往远处走了。”
“那么,可以自由行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问。
“那就是使用您的两个法国同乡—卢格罗尔和德纳露兹创造的器械。为了符合我的要求,我改善了这种器械,靠这种器械,人可以在新的生理条件下在海水中生活,您的器官一點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它有一个厚钢板制的密封瓶,瓶中满贮五十大气压力压缩的空气。它像士兵的背囊一样,用一条腰带捆在人的背后,瓶的上部像个钢盒,盒中的空气由吹风机操纵,只在一定的压力下才能流出来。现在通用的卢格罗尔器械,都有两条胶皮管子从钢盒通出来,套在口鼻上罩着的喇叭形东西;其中一条是吸气用的,另一条是呼气用的,人的舌头按照呼吸的需要,控制这两条胶皮管的开关。但是,在海底下受到的压力很大,所以我要像潜水员一样,把我的脑袋装在铜制的圆球中,那两条胶皮管—吸气管和呼气管就连结在这个圆球上。”
“好极了,尼摩船长。不过您所携带的空气很快就会用完的,空气中只含有百分之十五的氧气时,就不宜再呼吸了。”
“可不是,但我跟您说过,阿龙纳斯先生,鹦鹉螺号的打气机使我可以把高压压缩的空气装进去,在这种条件下,这套器械的密封瓶能供应的空气足够我呼吸九到十小时。”
“我再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了,”我回答,“但我要问,您在海底下行动是靠什么来照明呢?”
“我用的是兰可夫灯,阿龙纳斯先生。呼吸器放在我背上,探照灯带在我腰间。探照灯装有一组本生电池,但我不用氯化钾,而用海中含量很多的氯化钠来发电。用一个感应线圈把发生的电收集起来,送到特制的灯泡。灯泡中有一根弯曲的玻璃管,管中只有少量的二氧化碳。使用探照灯的时候,二氧化碳发出一种连续不断的白光,提供照明。有了这些设备,我就可以呼吸,可以看见。”
“尼摩船长,您对我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作了十分有力的答复,现在我再也不能怀疑了。不过,我虽然不得不承认卢格罗尔呼吸器和兰可夫探照灯,但我对那支猎枪,就是您要我携带的这件武器,还不得不保留我的意见。”
“这不是什么火药枪。”船长回答。
“那么,是气枪吗?”
“可不是。船上没有硝石,没有硫磺,没有木炭,您要我怎么制造火药呢?”
“还有,”我说,“海水比空气重八百五十五倍,在这种环境中开枪要有实效,首先就要克服这种巨大的压力。”
“这不能算作一个理由。现在有一种枪,是按照富尔顿的设计,由英国人菲力哥尔和布列、法国人傅尔西、意大利人兰帝加以改进的,它装有特殊的开关,可以在海水中射击。但是我要再一次告诉您,我没有火药,只能用压缩空气代替,这种空气是鹦鹉螺号的打气机可以大量供应的。”
“可是这空气很快就会用完的。”
“不错,但我带有卢格罗尔瓶,不是能按需要随时供应空气吗?只要按需要装上一个开关龙头就够了,此外,阿龙纳斯先生,您自己就将亲眼看到,水底打猎并不费大量的空气和很多的子弹。”
“但是,在这种看不太清楚的地方,在这个比空气重得多的海水中间,我觉得发出的枪弹不能打得很远,并且也很难命中吧?”
“先生,用这种枪,每一发都是可以致命的,并且,动物一被打中,不管伤得怎样轻微,它必然像被雷击一般,立即倒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枪发出的子弹并不是普通的子弹,这是奥地利化学家列妮布洛克发明的一种小玻璃球,我船上储备了许多,这种小玻璃球装有钢的套子,下面又加了铅底,像真正的来顿瓶一样,里面具有很高的电压。就是最轻微的冲击,也要炸开,被打中的动物,不管怎样强大有力,也得倒下来死去。我要告诉您,它不比四号子弹大,普通猎枪的弹盒可以装上十个。”
“我再不争论了,”我从桌旁站起来说,“我只有拿起我的枪来就是了。您去哪里,我就跟您去哪里。”
船长领我到鹦鹉螺号的后部,走过尼德·兰和康塞尔的舱房门前,我叫了我的两个同伴,他们立即跟着我们出来。
一会儿,我们到了前面,靠近机器房的一个小房子里,我们要在这个小房子中穿起我们的海底打猎衣服来。
这个小房子,说得准确些,就是鹦鹉螺号的军火库和储藏衣服的地方。墙上挂着十二套潜水衣,等待海底散步者穿戴。
尼德·兰看到这些潜水衣,觉得十分讨厌,不愿意穿。
“您可知道,老实的尼德·兰,”我对他说,“那克利斯波岛的森林是海底下的森林呢!”
“好嘛!”鱼叉手失望地说,因为他吃鲜肉的梦想幻灭了。“阿龙纳斯先生,您自己也要套进这种衣服里面去吗?”
“当然,尼德·兰师傅。”
“先生,您高兴穿您就穿吧!”鱼叉手耸一耸两肩说。
两个船员遵照船长的嘱咐,走上来帮助我们穿这些不透水的、沉甸甸的衣服;衣服是用橡胶制成的,没有缝,可以承担强大的压力,不受损伤。应当说这是一套又柔软又坚固的甲胄。上衣和裤子是连在一起的,裤脚下是很厚的鞋,鞋底装有很重的铅铁板。上衣全部由铜片编叠起来,像铁甲一般保护着胸部,可以抵抗水的冲压,让肺部自由呼吸;衣袖跟手套连在一起,很柔软,丝毫不妨碍两手的运动。
那些不完备的、有缺点的潜水衣,例如十八世纪发明的被人称赞的树皮胸甲、无袖外罩、人海衣、藏身箱等等,跟我们眼前这套完美的潜水衣比较,实在是太相形见绌了。
尼摩船长、他的一个同伴(一个体力过人,像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大力士)、康塞尔和我,一共四个人,全都穿好了潜水衣。现在只要把我们的脑袋钻进金属圆球中,我们就算装备完了。但在戴上金属圆球之前,我要求尼摩船长给我看一看我们要带的猎枪。
鹦鹉螺号船上的一个船员拿一支很简单的枪给我看。枪托是钢片制的,中空,体积相当大,是储藏压缩空气的容器,上面有活塞,转动机件,便可以使空气流入枪筒。枪托里面装了一盒子弹,盒中有二十粒电气弹,利用弹簧子弹可以自动跳入枪膛中。一粒子弹发出之后,另一粒立即填补,可以连续发射。
“尼摩船长,”我说,“这支枪十分好,并且便于使用。我现在真想试试它。不过我们怎样到海底下去呢?”
“教授,此刻鹦鹉螺号搁浅在海底下十米深处,我们只待动身出发了。”
“我们怎样出去呢?”
“您不久就知道。”
尼摩船长把自己的脑袋钻进圆球帽子里面去。康塞尔和我照着他的动作,各自戴上圆球帽。我们又听到加拿大人讽刺地对我们说了一声“好好地打猎去吧”。我们潜水衣的上部是一个有螺丝钉的铜领子,铜帽就钉在领子上。圆球上有三个孔,用很厚的玻璃防护,只要人头在圆球内部转动,就可以看见四面八方的东西。当脑袋钻进圆球中的时候,放在我们背上的卢格罗尔呼吸器,立即起了作用。就我个人来说,我呼吸很顺利,没有困难。
我腰间挂着兰可夫探照灯,手里拿着猎枪,准备出发。但是,说实在的,穿上这身沉甸甸的衣服,被铅做的鞋底钉在甲板上,要迈动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但这种情形是预先料到的,我觉得有人把我推进跟藏衣室相连的一个小房子中。我的同伴,同我一样被推着,跟着我过来。我听到装有阻塞机的门在我们出来后就关上,我们的周围立刻是一片漆黑。
过了几分钟,一声尖锐的呼啸传进我的耳朵。我感到好像有一股冷气,從脚底涌到胸部。显然是有人打开了船内的水门,让外面的海水向我们冲来,不久,这所小房子便充满了水。在鹦鹉螺号船侧的另一扇门,这时候打开来了。一道半明半暗的光线照射我们。一会儿,我们的两脚便踏在海底地上。
现在,我怎样才能将当时在海底下散步的印象写出来呢?像这类神奇的事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就是画笔也不能将海水中的特殊景象描绘出来,语言文字就更不可能了。
尼摩船长走在前面,他的同伴在后面距离好几步跟随着我们。康塞尔和我,彼此紧挨着,好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金属外壳交谈似的。我不再感到我的衣服、我的鞋底、我的空气箱的沉重了,也不觉得这厚厚的圆球的分量,我的脑袋在圆球中间摇来晃去,像杏仁在它的核中滚动一般。所有这些物体,在水中失去了一部分重量,即它们排去的水的重量,因此我进一步了解了阿基米德发现的这条物理学原理。我不再是一块呆立不动的物体,差不多可以说能够运动自如了。
阳光可以照到洋面下三十英尺的地方,这股力量真使我惊奇。太阳光强有力地穿过水层,把水中的颜色驱散,我可以清楚地分辨一百米以内的物体。百米之外,水底现出天蓝一般的渐次晕淡的不同色度,在远处变成浅蓝,没入模糊的黑暗中。真的,在我周围的这水实在不过是一种空气,虽然密度较地上的空气大,但透明的情形是跟地上空气相仿。在我头上,我又看见那平静无波的海面。
我们在很细,很平,没有皱纹,像海滩上只留有潮水痕迹的沙上行走。这种眩人眼目的地毯,像真正的反射镜,把太阳光强烈地反射出去。由此而生出那种强大的光线辐射,透入所有的水层中。如果我肯定地说,在水中深三十英尺的地方,我可以像在阳光下一样看得清楚,那人们能相信我吗?
我们踩着明亮的沙层走动,足足有一刻钟,它是贝壳变成的粉末构成的。像长长的暗礁一样出现的鹦鹉螺号船身,已经渐渐隐没不见了;但它的探照灯,射出十分清楚的亮光,在水中黑暗的地方,可以指示我们回到船上去。人们只在陆地上看见过这种一道道的十分辉煌的白光,对于电光在海底下的作用,实在不容易了解。在陆地上,空气中充满尘土,使一道道光线像明亮的云雾一样;但在海上,跟在海底下一样,电光是十分透亮的,一点也不模糊。
我们不停地走动,广阔的细沙平原好像是漫无边际。我用手拨开水帘,走过后它又自动合上,我的足迹在水的压力下也立即就消失了。
走了一会儿,看见前面有些东西,虽然形象仅仅在远方微微露出,但轮廓已清楚地在我眼前浮现。我看出这是海底岩石前沿好看的一列,石上满铺着最美丽的形形色色的植虫动物;我首先就被这种特有的景色震住。
这时是早晨十点。太阳光在相当倾斜的角度下,投射在水波面上,光线由于曲折作用,像通过三棱镜一样被分解,海底的花、石、植物、贝壳、珊瑚类动物,一接触被分解的光线,在边缘上显现出太阳分光的七种不同颜色。这种所有浓淡颜色的错综交结,真正是一架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色缤纷的万花筒。总之,它就是十分讲究的水彩画家的一整套颜色!看来实在是神奇,实在是眼福!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所有的新奇感觉告诉康塞尔呢?怎样才能跟他一齐发出赞叹呢?我怎样才能跟尼摩船长和他的同伴一样,利用一种约定的记号来传达我的思想呢?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只好自己对自己说话,在套着自己脑袋的铜盒子里面大声叫喊;虽然我知道,说这些空话消耗的空气恐怕比预定的要多些。
对着这灿烂的美景,康塞尔跟我一样惊奇地欣赏。显然,这个守本分的人,要把眼前这些形形色色的植虫动物和软体动物分类,不停地分类。满地都是腔肠动物和棘皮动物。变化不一的叉形虫,孤独生活的角形虫,纯洁的眼球虫,被人叫作雪白珊瑚的耸起作蘑菇形的菌生虫,肌肉盘贴在地上的白头翁……布置成一片花地;再镶上结了天蓝丝绦领子的红花石疣,散在沙间像星宿一般的海星,满是小虫的伪海盘车,这一切真像水中仙女手绣的精美花边。朵朵的花彩因我们走路时所引起的最轻微的波動而摆动起来。把成千成万散布在地上的软体动物的美丽品种,环纹海扇,海糙鱼,当那贝—真正会跳跃的贝,洼形贝,朱红胄,像天使翅膀一般的袖形贝,叶纹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无穷无尽的海洋生物,践踏在我的脚底下,我心中实在难受,实在愧惜。但是我们不得不走,我们继续前进,在我们头上是成群结队的管状水母,它们伸出它们的天蓝色触须,一连串地飘在水中。还有月形水母,它那带乳白色或淡玫瑰红的伞,套了天蓝色框子,给我们遮住了阳光。在黑暗中,更有发亮的半球形水母,为我们发出磷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约在四分之一海里的空间内,我没有停步,几乎不断地看到这些珍品。尼摩船长向我招手,我跟着他走。不久,脚下的土壤变了性质,代替细沙平原的是一片胶粘的泥地,单独由硅土或石灰贝壳构成,美国人管它叫“乌兹”。接着我们跑过一段海藻地,它们是未经海水冲走的海产植物,繁殖力很强。这种纤维紧密的草坪,踩在脚下软绵绵的,足以和人工织出的最柔软的地毯媲美。但是,不只我们脚下是绿草如茵,连我们头上也是一片翠绿。水面上轻飘飘地浮着一层海产植物,全部是取之不尽的海藻类,这类植物,我们已经知道的,至少有二千多种。我看见水中浮着很长的海带(有些作球形,有些作管状),红花藻,叶子很纤细的薛苔,很像仙人掌的蔷薇藻。我注意到较近海面的一层是青绿色的海草,在更深一些的地方是红色的海草,黑色或赭色的水草就在最深处,形成海底花园和草地。
这些海藻类实在是造化的奇迹,宇宙植物界的一个奇迹。地球上最小和最大的植物都产生在海藻类中。因为五平方毫米的地方,可以有四万条这类肉眼不可见的微生植物,同时人们又采到过长度超过五百米的海带。
我们离开鹦鹉螺号有一小时半左右了。正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见太阳光垂直地照下来,再没有曲折作用了。颜色变幻的花样渐渐没有了,翠玉和青玉的各种色度也从我们的头顶上消失了。我们步伐很规律地走着,踩在地上发出异常响亮的声音。很轻微的声响也很快地传出去。这是在陆地上时的耳朵所不熟悉的。本来,对于声音,水比空气是更好的传音体,它传播声音比空气快四倍。
这时候,海底地面由于有明显的斜坡,渐渐低下去。光线的色泽是一致的。我们到了百米的深度,受到十个大气压的压力。但我的潜水衣是为适应这些情况制成的,所以我没有感到这种压力的难受。我仅仅觉得手指不能灵活使用,但这种困难情况不久也就消失。我穿上自己不习惯的潜水衣,漫游了两小时,本来应该疲倦,可是现在丝毫不感到什么。我由于水力的帮助,行动异常灵便。
到了三百英尺的深度,我还能看见太阳光,不过很微弱。尾接着阳光的强烈光辉,是红色的曙光,白日与黑夜之间的阴暗光线。但我们还看得清楚,可以引路,还不需要使用兰可夫灯。
这时候,尼摩船长停下来。他等着,要我到他面前去,他指点我看那在阴影中不远的地方,渐渐露出来的一堆堆模糊不清的形体。
我想,那就是克利斯波森林了。果然,我并没有弄错。我们到底走到森林的边缘了,这可能是尼摩船长的广大领土中最美好的一处。
他把森林看作是他的,他把森林的所有权归他自己,像世界开辟的时候,最初出现的一批人霸占所有权一样。其实,又有谁能够跟他争这海底财产的所有权呢?哪有比他更大胆的开荒者,手拿着斧子,敢来这里砍伐荆棘,开垦田地呢?
这森林中生长的都是高大的木本植物,当我们走到树林中间阔大的拱形枝干之下,我的眼光首先就被林中树枝排列的奇特形状所吸引,感到奇怪的是这种形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林中地上并没有生长什么草,小树上丛生的枝杈没有一根向外蔓延,也不弯曲垂下,也不向横的方面伸展。所有草木都笔直伸向洋面。没有枝条,没有叶带,不管怎么细小,都是笔直的,像铁杆一般。海带和水藻,受到海水强大密度的影响,坚定不移地沿着垂直线生长。而且这些水草是静止不动的,当我用手分开它们的时候,一放手,它们立即回复原来的笔直状态。这林子简直就是垂直线的世界。
不久我便看惯了这种古怪的形状,同时也习惯了我们四周的相对的黑暗环境。林中地上随处有尖利的石块,很不容易躲开。海底植物,据我看,在这里是应有尽有了,比产量较少的南北两极地带或热带区域,可能更为丰富。不过,在几分钟内,我不知不觉地把动植物两类混淆起来,把植虫动物当做水产植物,把动物当做植物。本来,谁能不弄错呢?在海底下,动物界和植物界是十分接近的。
我观察到,所有这里的植物界产品,跟土壤只是表面上连接起来。它们没有根,支持它们的不管是固体、沙、贝、甲壳或石子,都没有什么影响,它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支点,而不是借以生长的力量。这些植物只是自己发展起来,它们生存的唯一资源就是那维持它们和滋养它们的海水。它们大部分不长叶子,只长出奇形怪状的小片,表面的色彩很有限,只有玫瑰红、洋红、青绿、青黄、灰褐、古铜等颜色。我在这里又看到的,不是像在鹦鹉螺号船上风干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似乎迎风招展地作扇子般展开的孔雀彩贝,大红的陶瓷贝,伸长像可食的嫩笋一样的片形贝,细长柔软,一直长到十五米高的古铜藻,茎在顶上长大的一束一束瓶形水草,以及其他许多的海产植物,通通没有花。一位很风趣的生物学家曾说过:“动物类开花,植物类不开花,大海真是奇异例外的环境,古怪新奇的自然!”
在这些像温带树木一般高大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中间,在它们湿润的阴影下面,遍生着带有生动花朵的真正丛林,植虫动物的篱笆行列,上面像花一般开放出弯曲条纹的脑纹状珊瑚,触须透明的黑黄石竹珊瑚,草地上一堆一堆的石花珊瑚—为了使这个幻觉完整无缺,又有蝇鱼,它们像成群的蜂雀,从这枝飞到那枝,至于两腮耸起、鳞甲尖利的麦虫鱼、飞鱼、单鳍鱼,那简直就像一群鹌鹑,在我们脚下跳来跳去。
到一点钟左右,尼摩船长发出暂时休息的信号。在我来说,我很高兴能休息一下,于是我们在一个海草华盖下面躺下来,这海草的细长枝条像箭一般直插着。
这一刻的休息我觉得很舒服,美中不足的是我们不能彼此交谈。没有法子说话,当然也没有法子回答。我仅仅把我粗大的铜头挨近康塞尔的铜头。我看见了这老实人的眼睛闪出兴奋的亮光,又为表示满意起见,他在铜壳子里面乱摇乱摆,作最滑稽可笑的怪样子。
虽然走了四小时的路,我并不感到有吃东西的需要,心里很为惊异。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出来。但另一方面,像所有潜水人一样,我感到很想睡觉,没有法子克制。所以我的眼睛也就在很厚的玻璃后面闭起来,我立即掉到无法克制的昏睡中,这昏睡,刚才也只是靠向前的走动才暂时制止了它。尼摩船长和他的健壮同伴,早就躺在清澈的水晶体中,先给我们作出睡眠的榜样了。
我沉迷在这种昏睡中有多少时候,那我不能估计;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看太阳已经向西边低下去了。尼摩船长已经站起来,我也开始伸展我的四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意外的东西,我立即站起双脚。
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只高一米的梅蜘蛛,斜着眼注视我,就要向我身上扑来。虽然我的潜水衣相当厚重,可以保护我不会被它咬伤,但我也不能不害怕,不能不颤抖。康塞尔和鹦鹉螺号的水手就在这个时候醒来。尼摩船长把这个怕人的甲壳类动物指给他的同伴看,他的同伴一枪托打死了它,我看见这个怪物的丑陋脚爪作骇人的抽搐,拼命挣扎。
这次碰见这个怪物就使我想到一定还有其他更可怕的动物时常到这黑沉沉的海底下来,我的潜水衣可能无力保护我,无法抵抗它们的袭击。我起先没有想到这事,现在我决心要时刻警惕。此外,我又以为这次休息是我们这次旅行的结束,但我错了,尼摩船长并不让我们回到船上去,仍然继续他的大胆的旅行。
地面总是往下陷,斜度更是明显,把我们拉到最深的海底。这时候,想是快要到三点了,我们到了一座狭小的山谷中,这山谷在峭壁间,在一百五十米深的海底下。由于我们使用的器械极完善,我们可以超越好像大自然拿来限制人的在海底旅行不得超过九十米的深度。
我说我们是在一百五十米的深度;虽然没有什么器械可以让我测量,但我知道,即使最清澈的海水,阳光也不能再往下照了。正是在这时候,周围变得漆黑。在十步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只能摸索着走,这时我看见一道相当明亮的白光忽然闪出来。原来是尼摩船长使用了他的电光机器。他的同伴照他那样做。康塞尔和我也学着他们的榜样。我转动螺丝钉,使电磁铁跟曲玻璃管接通,灯亮了,海中有我们四盏探照灯的照射,周围二十五米内都明亮起来。
尼摩船长继续走入森林中最幽深的地方,沿途树木渐渐稀少。我注意到,在海底,植物界要比动物界消失得早些。海产植物虽然已经放弃了这些变为贫瘠的土地,但数量很多的动物、植虫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和鱼类仍然到处皆是。
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们带的兰可夫灯的灯光必然要引起那些沉黑的海底下居民的注意,齐集前来。可是,它们虽然前来,但总是留在猎人力量不可及,距离相当远的地方。好几次,我看见尼摩船长停步,瞄准他的枪,但经过一些时候的观察后,他又把枪放下,再向前行。
后来,大约四点钟左右的时候,新奇惊人的旅行结束了。一道高大的岩石墙和一大堆怪石群矗立在我们面前,那是巨人般的岩石层,花岗石的悬崖,沉黑的岩洞,可是看不见有可以攀爬上去的路径。
这是克利斯波岛的尽头,是陆地了。
尼摩船长突然停住脚步。他向我们打手势,要我们停下来,我虽然很想穿过这道墙,但我不能不止步,这里是尼摩船长的领地的最后界限。他不愿意走过这界限。过这界限便是他的脚步不愿踩踏的地球的陆地部分了。
我们于是开始往回走。尼摩船长又在前面带领他的小小队伍,他总是毫不迟疑地向前走。我觉得,我们转回鹦鹉螺号船上去,好像不是走原来的路。这条新路很陡,因此很难走,显然它是比较接近海面。不过,回到海水上层的行动不能十分突然,防止压力的减小过急,因为压力减小过急,可能在我们肌体中引起严重的疾病,发生使潜水人有性命危险的身体内伤。所以我们是慢慢地上来。很快光线又出现了,又扩大了,太阳已经在天际的低处,曲折作用重新又把七色的光圈套在各种不同的物体上了。
在十米深的地方,我们就走在一大群各种各类的小鱼中间,比空中飞鸟的数量还多,也更敏捷,但还没有值得我们枪击的水产猎物在我们眼前出现。
这时候,我看见船长的枪急急顶在肩上,对着丛林间一个正在走动的东西瞄准。枪响了,我听到轻微的啸声,那个动物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被击中倒下来了。
倒下来的是一只很好看的水獭,一只水兽,它可能是唯一的住在海中的四足兽了。这水獭有一米半长,价值一定非常大。它的皮,表面是栗褐色,底面是银白色,可以制成十分好看的皮筒,在俄国和中国的市场上,是十分罕见的皮料。皮毛的柔软精细和它的光滑色泽决定它的价格至少也是二千法郎。我很赞美这新奇的哺乳类动物,圆突的头,上面有短短的耳朵,圆圆的眼睛,像猫须一般的白色瓮须,掌形带甲的脚,团簇的尾巴。这种珍贵的肉食动物,因为渔人的追赶和捕获,现在已经十分稀罕,它们主要是躲藏在太平洋的北极圈里,就是在北极圈里,它们这一族也快要灭绝了。
尼摩船长的同伴跑上前去把水獭捡起来,放在肩头上,我们又向前走。
在一小時内,一片细沙的平原在我们脚下摆开。平原时常升至距海面不及两米的深度。我当时看见我们的影子反映在水中,清楚地现出来,方向正相反:在我们上面,现出同样的一群人,表演我们的动作和姿势,一切都相同,就是脑袋垂在下面,两脚倒悬在空中。
值得记下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一阵阵的浓云飞掠过去,这些云很快地形成,也很快地消失;但仔细一想,我明白了,这些所谓云只不过是海底厚薄不一的波浪所反映出来的。
我又看到浪头向下折落时变成无数泡沫飞溅的滚滚白涛,像羊群一样。我也见过那些在我们头上的巨大鸟类的阴影,它们从海面疾飞掠过。
这个时候,我亲眼看到一次射击,也许从来没有一个猎人曾经发射过这样准确、漂亮的枪。一只大鸟,可以看得很清楚,两翼张得很大地飞翔而来。尼摩船长的同伴看见大鸟在离水波仅仅几米的上面,尼摩船长就瞄准、射击。大鸟被击落下来,一直掉到这位敏捷的猎人的近旁,他立即把鸟捉住。这是最美丽的一种海鹅,海鸟中最使人赞美的一个鸟类品种。
我们走路并没有因打海鹅这件事中断。在两小时内,我们有时沿着细沙平原走,有时沿着藓苔草地走,相当难走。老实说,我实在不能再走了,这个时候,我看见半里远的地方,有一道模糊光线冲破了海水的沉黑。那是鹦鹉螺号的探照灯。要不了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上船了,一到船上,我便可以自由呼吸,因为我觉得我的空气储藏器好像只能供应我一些含氧很少的空气了。不过我这样打算,并没有估计到下面的意外遭遇,使我们耽搁了一些时间才到达船上。
我走在尼摩船长后面约二十步左右,看见尼摩船长突然向我面前转回来。他用他有力的手,把我按倒在地下,他的同伴对康塞尔也这样做。初时我对于这次突然的攻击,作种种的猜想,但我看见船长也躺在我近边,不敢动,心中就安然了。
于是我躺在地上,正好躲在藓苔丛林的后面,当我抬起头来,我看见有巨大无比的躯体发出磷光,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我血管中的血都凝结了!我看见逼近我们的是十分厉害的鲛鱼,一对火鲛,最可怕的鯊鱼类,尾巴巨大,眼光呆板阴沉,嘴的周围有很多孔,孔中喷出磷质,闪闪发光。真是大得怕人的火鲛,它们的铁牙床,可以把整个人咬成肉酱!我不知道康塞尔是不是正在留心把它们分类,在我说来,我与其说是拿生物学者的身份,不如说是拿将被吞食的人的身份,以很不科学的观点来观察它们的银白的肚腹,满是利牙的大嘴。
十分幸运,这对贪食的动物视力很差,看不太清楚。它们并没有看见我们就走过去了,只是它们的黄黑的尾巴略略触到我们,我们能躲过这次危险真像是个奇迹,毫无疑问,这次危险比在森林中碰见猛虎还要大得多。
半小时后,有电光引路,我们到达了鹦鹉螺号。外部的门仍然开着,尼摩船长一见我们都已经走进了第一个小房中后,就把门关起来。然后他手按一个圆钮;我听到船内部的抽水机活动起来,我觉得我周围的水渐渐低下去,过了一会儿,小房中的水便完全排出去了。内部的门打开来,我们走进了储衣室。
在储衣室,我们把潜水衣脱下来,脱时当然要费些功夫。我非常疲乏,走回自己房中,一方面对于这次海底的惊人旅行,眉飞色舞,赞叹不已,另一方面,简直累得不能动,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摘自译林出版社《海底两万里》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