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只是一种职业,关键就是这几招
2020-10-26呼延苏
文|呼延苏
编辑是做文化的匠人,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不是具备某种特定的学科知识,也不是知识量的多少,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专业能力。

传记片《天才捕手》描写了美国天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与天才作家托马斯·沃尔夫之间的友谊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议将编辑出版学上升为一级学科。提案结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出版界和有关高校的这种努力由来已久。早在1984 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就建立了编辑学本科专业。2009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就我国是否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组织专家论证,结果是一致同意。于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0 年批准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近30 所高校相继获出版硕士授予权。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共有55 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19所高校开设数字出版本科专业,28 所高校开设了出版硕士专业,10 所高校开设了出版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这个专业的学术成就似乎也硕果累累,几十年来,已出版的科研论著(含教材)达千余部,论文在万篇以上。
但是,看上去比较热闹的编辑出版学一直未被列为一级学科,不是挂在新闻传播系(院),就是图书情报系,或者信息管理系。专业的名称也很不一致,“出版学”“出版发行学”“编辑出版学”,甚至“农业文献编辑与数字出版”“出版文化与新媒体实务”等等,五花八门。从而导致该专业在社会上的认同度一直不高,教师缺乏主体地位,毕业生就业也无所适从。而且,还有更令人尴尬的情况:今年7 月初高考刚结束,出版界某公号推文介绍大学院系出版专业,北大和人大赫然名列前茅,但很快被告知,这两所名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已经停止了本科招生。
我想说的是,编辑出版专业列为或不列为一级学科,都不会改变如下事实:这个专业教育目标是为图书出版培养后备编辑人才。从这个角度说,该学科的设立是以职业作为分科标准,而通常的学科设立是以知识体系为分科标准。因此,编辑出版学欲成为一级学科,首先就得把自己弄成一个够大的知识体系。由此便引出一个问题:编辑是项社会分工,编辑出版学却成了个知识体系,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说得刻薄一点,能不能当个好编辑跟学不学编辑出版课程,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在目前的社会分工中,有些职业与学科的关系比较固定,譬如医生、会计;有些职业却跟学科没什么紧密联系,譬如公务员、编辑。就编辑而言,学科知识只构成他的能力基础,而且,不同专业出版社对编辑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要求,如社科类出版社编辑的知识基础应该是文史哲,古籍类出版社是中文或历史,译文类出版社是外语或文学,文学类出版社是汉语言文学或外国文学,艺术类出版社是音乐、美术,科技类出版社是理工。出版社专业分工程度越高,对学科专业的要求也越高,但恰恰很少有出版社会要求编辑的学科背景是编辑出版学。编辑出版课程学得多学得深的人,可能成为这个知识领域的研究者,在出版社却不太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敲黑板:因为,编辑是一种职业,从事该职业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学科知识,但必须具备相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编辑的专业能力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判断能力
有两个向度,第一是文化价值判断。文化价值是一本图书的终极意义,如果说作者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编辑就是文化价值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一本书的出版对于编辑而言,是一个文化价值发现或再发现的过程。钟叔河先生上世纪80 年代初建议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内容是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笔记。当时没几个人看好他这个点子,觉得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笔记没有什么价值,大规模作为丛书出版更没有必要。而钟先生的独特见解恰在此处,他认为这些书拆开来看,有些并不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的出国笔记尽可能收罗到丛书中,就会有其独特价值。几年后,10 册800 多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成为40 年来最有影响的湘版图书之一,被称为“出版业的巨大业绩”。

第二是市场表现判断,即预估一本书的销售情况。未出版的好书稿如石中之玉,编辑就像赌玉人,赌得准不准,最考验眼力。编辑选书稿,看走眼的时候很多。《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出版之前曾辗转过12 家出版社,一致不被编辑们看好。无奈之下的杰克·罗琳在《作家和艺术家年鉴》发现克里斯托弗·李特,请他代理自己的作品。最后,勉强由伦敦布鲁姆斯伯利出版社出版,首印只有区区500 册。《十钟山房印举》是清人陈介祺辑古玺印谱,卷帙浩繁。王启亮先生重新包装成一套定价2980 元的大书后,几乎没有出版社敢接这活儿,包括一些美术专业出版社。这么冷僻的领域,这么高的定价,能卖出去吗?最后虽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却采取了最保守的方式,自家不参与发行。但该书首印1500套,只靠一个微店页面展示,15 天预售卖空,不到3 个月所有库存全部消化,447 万码洋几乎是不打折销售。王先生之所以敢出这部大多人看了很冷僻的古印谱,是基于对金石篆刻爱好者这个特定群体需求的了解。
凡有大成就的编辑,首先就得具备良好的判断能力。而判断能力的形成,靠的是专业知识、个人经验和悟性。
策划能力
这种能力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无中生有的策划。十几年前,魏东先生入行出版业时,深感优秀的丛书既是出版社的门面,也是编辑个人事业成就的标准,便起意搭建一套名为“文学纪念碑”的丛书。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合适的书跟合适的译者,这两项工作都需要编辑有专业而独到的眼光。最初的成果是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然后是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到目前为止,这套以经典作家传记为主要特色的丛书已推出30余种,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之一,在人文阅读领域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俄苏文学界有良好口碑。这套丛书的起点只是编辑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因此,无中生有的策划最能表现编辑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在这个过程中,编辑始终是产业链的整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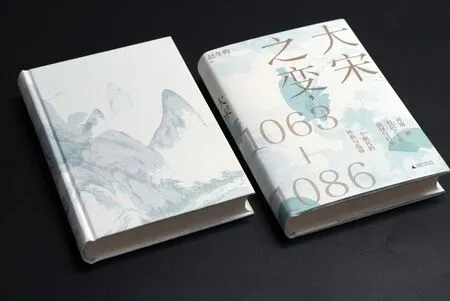
其次你还要会由小变大的策划,即由一篇文章甚至一条信息引出的策划。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大约是2003 年左右,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几个诗人以及文学人物患肺结核的事,于是与作者取得联系,约他从这个话题出发写一部书稿。经过反复商讨,定位于表现历史上的天才人物与精神疾病的关系。一年后顺利完稿,书名叫《天才就是疯子》,其独特的文化视角获得了不少读者的关注。
最后是由旧翻新的策划。《浮生六记》是一本著名的文言自传体散文,因为没有版权问题,很多出版社和图书公司都有出版。因此,当果麦文化公司决定再出一本白话版《浮生六记》时,很多人心里是有疑问的。首先就是市面上已经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版本,再添个版本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吗?其次,对文言古籍进行白话文翻译,向来为不少专家学者诟病,经常会弄个费力不讨好。但果麦的编辑请来了80 后实力派作家张家玮担任文本翻译,又在装帧方面精心打磨。个性独特的译文,漂亮的封面,精美的印刷,别具一格的装订方式,使这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洋溢着直达人心的时尚气息。该书甫一面世,就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最后销量竟然超过300 万册,长期位于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而今原创资源稀缺,旧书(特别是公版书)翻新便成为各出版社竞相开展的业务,但翻得不好只是颗手榴弹甚至哑弹,翻得好就是核弹。同样的东西,经过不同人的策划,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谈到策划能力,我们通常会以为就是一个创意,其实创意只是策划的起点,而完美的策划一定包括良好的执行和控制。没有后者,再好的点子也只是空中楼阁。
获取能力
就是获取书稿的能力。对编辑而言,判断与策划是属于战略层面的能力,获取书稿则是战术落实的关键步骤。拿不到书稿,编辑的所有工作都会成为断头路。如果选题出于编辑的策划,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能顺理成章拿到书稿。现在我把获取能力单提出来,就是强调选题非其策划而书稿能被拿到的能力。获取能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这是能准确判断稿件价值并与作者建立共同话题的基础,进而才能讨论书稿内容和读者的情况。
熟悉作者情况,掌握作者动态,保持与作者经常性的联系。用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海的话说:“就是知道谁在写什么,知道最适合的作者正在写最适合的选题,并能找到作者签下这个稿件。”他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单位的王保顶同志就是这样,他每次去北京、广州跑一趟就会带回很多稿件。(摘自《一家出版社走过的弯路和一位老总对此的反思》)”在出版社待过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工作年限相同的编辑,有些人就是能约到稿件,有些人则基本上约不到稿件,这就是获取能力大小的差别。
良好的沟通技巧,包括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青年编辑张洁的一次约稿经历是个很好的范例:她在网上发现一篇对某历史学者的采访,觉得其学术方向切合自己的选题思考,但联系到作者后获知已有两家著名出版社先于自己发出了邀约。但她没有退却,而是知难而进。列举自家公司成功的案例,并做了一个关于这部书稿编辑、营销推广的详细方案,还耐心解释了经济回报的各种问题。编辑在沟通过程表现出的诚意和专业精神打动了作者,最后拿到了《大宋之变,1063-1086》的书稿。我认识一个业余编辑,经常帮出版公司拿书稿,有时还能约到一些名家的稿件,而约稿的方式就是给作者写信。我问她只凭写信何以能约到书稿,她说:“我的信对于作者特别有杀伤力!”可见有效的沟通在约稿时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整理能力
文字整理,这是编辑最重要的基本功。又可以分两个层面,其一是知识层面的整理,其二是修辞、错别字层面的整理。作者的书稿很少有不须修改就能直接拿去出版的,书稿中的知识性错误和文字表述错误会普遍存在,这些“雷”和“坑”,都必须编辑排除、填平。“雷”不排尽,“坑”不填满,轻则是校对错误超标,整本书成为不合格产品;重则越线犯规,触发导向问题,带来更大麻烦。最近这些年,出版机构比较强调策划和营销,对编辑的文字整理能力有所忽视,文字上能够把关的优秀编辑有后继乏人之感,这是整个出版界都应该重视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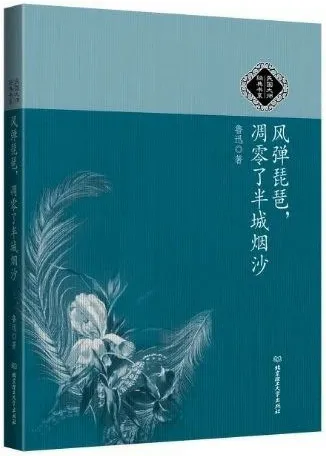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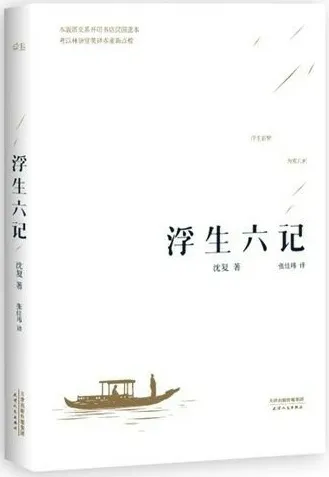
结构整理。关于这点,我直接引用资深编辑淡霞女士的一段话:“存在结构缺陷的书稿或许是作者没来得及整理,只是将所有文章收集在一起就发给编辑;或者是作者自己有大致的想法,但这种构想不太理想或者不符合当下的市场需求;或许是作者已去世,作品庞杂无序,后人没有能力整理。这时就需要(编辑)理出一种思路,用这思路将所有文章按照某种规律组织起来。(摘自《披荆斩棘的编辑:审稿能遇几多坑》)”杂乱的书稿经过编辑的整理成为条理分明的出版物,是编辑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
书名和标题的整理能力。在信息超载时代,吸引人们注意力已形成一种商业价值,而吸引注意力重要一招就是视觉争夺。因此,书名和标题作为导读门窗,对于图书的销售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好的书名应该简洁、生动、准确反映主题,以下是读者认可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追忆似水年华》《追风筝的人》(国外引进版),《藏地密码》《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儿》(国内原创),《浮生六记》《夜航船》《红楼梦》(古籍)等等。平庸无趣的书名固然不好,但过于花哨也是大忌,如苏轼的诗文集起名《用一生把别人的苟且活成潇洒》,鲁迅的散文集则名为《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看上去诗情画意,实则故弄玄虚,不知所云。
营销能力
以前,传统出版社的主要业务分为编辑和发行,两拨儿人泾渭分明,而且总是矛盾重重。现在越来越强调两者的融合,特别提倡编辑参与营销,因此还催生了营销编辑的独立岗位。编辑的营销能力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营销文案的写作。这要求编辑具备良好的写作基本功,对图书内容和目标读者有双向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营销文案,一方面要能准确把握图书要点,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表述,达到唤起读者阅读欲望的目的。
联络、运用媒体,特别是运用新媒体、自媒体扩大影响、促进销售。目前,很多出版机构都有自己的新媒体,一些头部出版社、出版公司的新媒体甚至形成矩阵,拥有上百万千万的粉丝群。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购买潜力,如何将这种潜力变现,就是营销编辑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此外,营销编辑还应尽量多了解、联系社会上的新媒体平台和公号,掌握它们的粉丝特点和带货功能,实施有效的文案、信息投放,进而达成有销售量的合作。今年以来,直播带货成为风靡一时的推销方式,出版业的直播带货也方兴未艾,作者、编辑乃至出版社领导纷纷出镜,一派热闹景象。这种方式对图书促销的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大小出版机构都已无法回避它所掀起的风潮。反应快的公司已将直播带货视为重要营销手段,如民营书商的头部公司之一磨铁就专门成立了新媒体营销部,目前已签约多位主播,每月做一百多场带货直播。
组织落地活动。地面书店在网络销售的进逼下步步后退,已经失去了一般图书销售的半壁江山。为聚攒人气、提升销售,很希望出版社带上作者(特别是有名气的作者)到店里搞活动做签售。一些市场活跃度较高的出版社,此类的活动每年可达一两百场,而图书的责任编辑往往在其中承担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作为组织活动的中枢,编辑要能统筹,擅沟通,设计流程,安排细节,还得有预案以防不测。这种能力的形成,除了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没有什么捷径。
总结一下:任何一个编辑都难以诸能皆备,但只要某项能力突出,在出版社就会有一席之地;兼具两三项能力,就算得上优秀编辑了。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矩近乎知识,巧就是能力。编辑是做文化的匠人,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不是具备某种特定的学科知识,也不是知识量的多少,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专业能力。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手眼高低全凭灵活运用而生成的“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