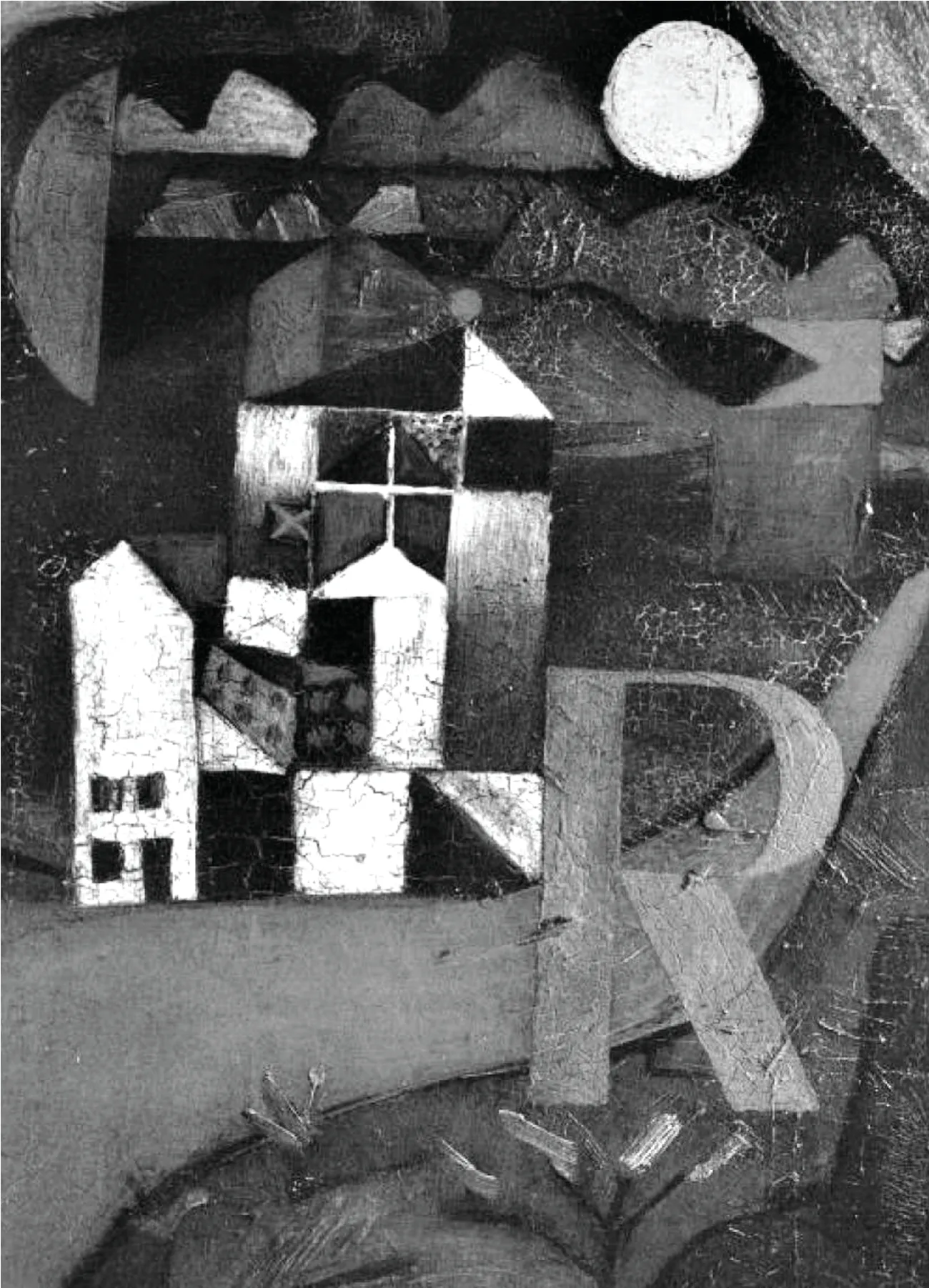落在您脸上的每一滴光尘都是回归
2020-10-21唐朝晖
◎唐朝晖
2000 年前后, 我经常走在长沙的一条路上——东风路。 右转进湖南省博物馆, 左侧一条缓慢的坡被水泥加宽, 以前是条破损的柏油路, 时时冒出一些大小不一的坑。 坡右边的大石头庄重而高大, 像波德莱尔应合的圣殿, 但这里没人知道有个 “巴黎佬”住在这里。 路左转, 有九级台阶, 正前方一楼是彭燕郊先生的家。花草的迎接总是那样的惬意, 植物自得其乐地生长, 这都是女主人的趣味所在——张兰馨老师, 彭燕郊的夫人。
彭燕郊自觉于精神本质的核心事实: 诗性。 他始终谦和如一学生, 敬畏的灯盏在他的呵护下温暖地亮在时代的每一次呼吸上。住所房屋拥挤, 三四间。 有多少秘密甬道为我的目光所无法通达?有多少良知和苦难淹过他的身体? 他依旧以自然为则, 以天的空茫为题, 不断地在大地上演算着 “我” 与 “世界” 的习题, 接受一切命题——他用心做答。 局限和飞翔的难度制约着他诗性的魂灵, 也成就了他的高度。
我尝试着用诗歌的形式解读、 应和, 并致敬彭燕郊先生的散文诗作品。 本文引号内的文字均摘自他的 《混沌初开》。
“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 界限已被取消, 界限不再存在。”
彭燕郊发现了 “混沌”, 无论是梦里还是幻想中, 昨天很远的叹息和发霉的日子已经过去, 记忆存活在曾经居住过的房舍周围, 树已经砍伐过半, 草终究还是盖过了黄土的色泽。 界限曾如此牢不可破地竖在人与人、 人与事之间, 人自身的界限正把人的每一部分端放在物质的界限里。 经历了万千劫难以后, 公元1986年的某天早晨, 彭燕郊依旧起来很早, 院子比以往更加安静, 临近中午, 他突然发现自己临境于界限消失的空茫之地——混沌之地。
“混沌之色于是五彩斑斓……无色最为耀眼夺目。”
欢乐和美在这里凝结成晶, 滋润着我干涩的眼角, 曾经漫步过的溪流小路, 还有我喊一声鲜花就开得漫山遍野的山岭, 这里都有, 比曾经的更美。 他来到空茫无穷之地, 抛开大小概念, 具象的形体和可言说清楚的学问统统消失在悠长的叹息之前。“无” 是这里唯一可以勉强说出的字, 在话音消失之时, 我握住他的大手。 我明白, 这个 “无” 字也不甚准确。 我用心在空茫中道出了感受: 美。 他大声地笑了, 认同的手在稿纸上一挥——混沌出场。 这是他美的高峰和他的融汇贯通之术, 一场美的盛典。
“这里是漂浮的海、 气体的海…………混沌发光同时吸收光的反射。”
我欢呼着, 从混沌的每一面空茫中站起来, 于混沌中。 我看到了我们站起来的不同的姿势, 都被混沌入怀。
“空旷里没有高山之顶, 要知道高度也是一种局限……有的只是亿万光尘在和你一起浮游。”
每一个字, 谨慎而直接地浮现于大海的天空, 稍不小心, 词语就会破坏这 “零” 的境地。 其实 “零” 也是不存在的, 有的只是亿万光尘。 我对他说, 先生, 我明白的, 我会努力绕开那些词语的密林, 直接道出混沌之地: 无、 零、 有、 前、 后、 正、反———都是没有的!
“人的悠远的憧憬是凌空。”
彭燕郊终于在千万语言中为我找到了一个词语, 词语浮游在混沌里: “凌空” ——美妙的花香清幽起落, 没有负重的思虑和痛苦。 “凌空” 的状态是心灵飞翔的饱满。
“混沌是一片坦途, 没有围墙、 豁口、 关卡、 暗礁。”
从他的履历文字中, 从他侧身的身体里, 我看到这些词语在他物质的身体上烙下一个个印迹。 围墙: 他被困其中。 豁口: 他经过一座山, 又跌落于此。 关卡: 他与家人一次次分离和汇合,他们一起走过检查处的那些暗示。 暗礁: 他被弃的那条船, 沉没在暗礁不远处的海底, 他只身游浮的位置, 是他梦中的梦呓, 他用文字作为自我的通行证, 试图与梦神通融, 失败曾一次次警告过他尝试是有数字限制的! 他在混沌中专致地走到诗歌的空茫高地——凭他的混沌初开!
“你也就敢于相信你也是一股气浪。”
我是否该站在他的后面, 告诉身边的人: 他状态很好, 他已经浮游于我们很远的地方。 通过语言的绳索, 传递到我手中的,也许成了光学原理和环境等问题。 没有恰当的文字来承载他所看见和体悟到的: 意义、 本质和真实的状况, 只留在文字的尾音上。
“落在你脸上的每一滴光尘都是回归。”
毫无疑问, 回归就是我们所到之处的所有处所, 回归的心情没有漂移, 此地与彼地的差别在光线的普照下毫无二致。 他声音质朴地装点着我所到之处的每一空间, 华美的线条, 回旋起伏于所有花草树木丛林, 思念他处的残质都已不存。 出生的故土与熟悉的口音在另一面镜子里成像, 每一个思绪里生发出来的水雾都是家和故乡, 回归的歌谣清闲地唱响每一朵高贵的野花。
“而被某个银河系吞下去, 又不得不把它吐出来的某个巨大的影子。”
黄昏暗下来的街道, 人们待在屋子里, 在某一条转角的街道,一个巨大的影子走过来, 影子覆盖了整座城市, 马尔克斯在他的马孔多城镇里也感知到了这个巨大的影子。 巨影轻轻拨弄着丛林, 像风一样吹过, 只是动作时疾时缓, 没有风那样均匀。 巨影落在我们每个人的黄昏里。 他感觉到的是一个气吞星系的影子,星光源于巨影偶尔的泪珠。 同情的星光在银河系闪烁。
“非我的出现…………有点像从灰烬中复活的火苗。”
两个音符的中间, 歌者的嗓音跨过栅栏下的小溪, 有一低坎,有一小空白段, 两者相对的瞬息之间, 非我漂游其间。 他说, 非我是第二我消失间凸现的一个可以触摸的幻影。 混沌的呈现和进入, 对于我们和他本人都是一次冒险, 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的历程如果出现差错, 交流的一个眼色也是重要的, 符码重新确立,混沌中的重要部位硬突出来。 非我出场, 假如没有火苗在灰烬中的复活, 那么, 风自会来清理这一残局。
“有一朵光紧跟住你。” 终于有了自己的光, 或者说, 感谢他, 让我在混沌中找回了自己的光, 多维立体的金光, 可以任意发射和吸收。 我们 “是一个活泼的存在”。 我把光射向他, 这是他借用地球语言来表达我在此情境里最准确的一个词: 活泼。 我庆幸成为 “金光的混沌”, 或者是 “一个结晶体”。
当我写完上面的文字, 打印出来, 邮寄给居住在湖南省博物馆宿舍的彭燕郊先生之后的第七天, 彭燕郊先生打来电话, 说很喜欢这些文字, 并要我再给他打印几份邮寄过去。 我照做了。
但今天, 当我把这篇一万五千多的文章缩改成两千多字之后,从一万九千两百字的 《混沌初开》 节选出五千多字出来之后, 我却不能再快递出去了, 只能闭上眼睛, 让敬畏和感激轻轻地漂浮在渺渺茫茫的空境里, 抵达 《混沌初开》 的暗涌和宿命。
2020 年9 月, 彭燕郊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为感恩彭燕郊为中国诗歌作出的无私贡献, 尤其是对世界散文诗的整理和挖掘,《散文诗》 杂志特别推出纪念专辑, 缅怀彭燕郊先生,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彭燕郊先生的散文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