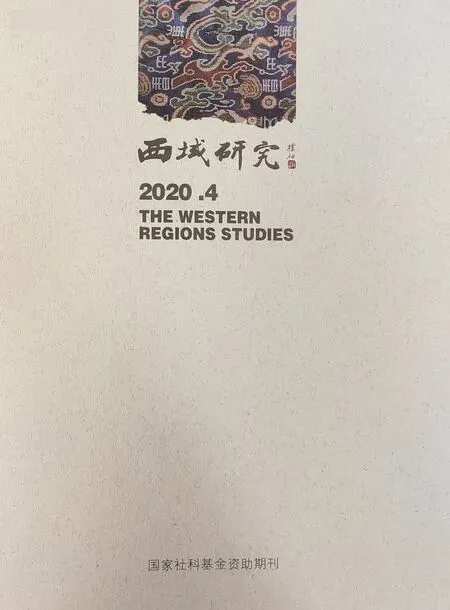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述评①
——以史前生业模式为视角
2020-10-14丛德新贾伟明
丛德新 贾伟明
内容提要: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20世纪后期,以苏联考古学家哈扎诺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在史前游牧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游牧的概念、分类、起源、遗址判断标准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中以哈萨克斯坦的拜尕什遗址、塔什巴遗址、塔尔加尔河流域的游牧考古和巴尔干半岛的动物考古等为例,评述了国外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对国内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评述,集中于新疆东天山地区和阿敦乔鲁遗址以及西藏三个典型地点。利用一切手段积极开展对生业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史前畜牧业的判定多基于考古发现中的家养动物骨骼如牛、羊和马与种植谷物数量的大致比较得出的。与畜牧业的判定不同,以往研究中对于史前游牧生业的认定则经常是一种推测,或是根据史料记载来直接定性,如对斯基泰、匈奴等即如此,因而,对他们的考古遗存也冠以“游牧文化”和“游牧经济”的标签。在畜牧生业广泛分布的欧亚大草原、蒙古高原、中国北方,基于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史前考古学研究相对滞后,造成了学术界对畜牧业、游牧生业的定义并不十分清晰,为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阻碍。(1)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2007年,第425~457页。本文的评述所涉及的史前游牧考古的案例,是那些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以史前游牧经济为主要对象的考古学研究,其中包含三层涵义:首先这个研究是史前时期的,其次是以畜牧业的考古研究为主,再次这个研究是以游牧的畜牧生业为中心的。(2)丛德新,贾伟明:《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故宫博物院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故宫出版社,2018年,第160~172页。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
一 史前游牧考古的发端
以生业形态分析为基础的史前游牧考古是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考古学对史前游牧社会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以宾福德(Lewis Binford)、苏珊·肯特(Susan Kent)为代表的一批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为始点。他们为了解决考古遗存所反映的史前人类行为,对现存美洲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以及非洲、大洋洲和欧亚大陆的一些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察,并以此来阐释一些史前遗迹的形成过程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将采集、狩猎部族的生活方式与史前考古发现的现象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加深对史前特别是对旧石器时代的人们采集、狩猎行为及社会构成的认识。(3)路易斯·宾福德著;曹兵武译:《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1991年,第43~55页。这些现代原住民包括许多现代的游牧部族,尽管对游牧部族研究还不能算作是游牧考古,但是之后在欧亚草原游牧考古中广泛应用的“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接受。这一概念也在张光直先生的倡导下,逐渐在西方考古学中自觉地形成一个新的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上世纪西方考古学基础理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ism)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近些年来尽管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4)Gosselain O.P.,To Hell with Ethno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 Dialogues.2016,23(2),pp.215-228.但经历了“后过程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后,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在不断的辩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摒弃了比较研究中的简单化类比,向深层次的阐释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发展和完善,(5)有关西方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之争可参考:Agorsah E.K.,Thnoarchaeology:the Search for a Self Correc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st Human Behaviou.The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8(1990),pp.189-208.Biagetti S.,& Lugli F.(Eds.),The Intangible Elements of Culture in Ethnoarchaeological Research.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Hamilakis Y.,Decolonial Archaeologies:from Ethnoarchaeology to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y.World Archaeology,2016,48(5),pp.678-682.Hamon C.,Debates in Ethnoarchaeology Today:a new Crisis of Identity or the Expression of a Vibrant Research Strategy? World Archaeology,2016,48(5),pp.700-704.为今天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考古学界对游牧社会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但以游牧生业为中心的考古研究则相对晚近。直到进入21世纪后的多年间,把史前游牧考古作为一个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课题也并不多见。这其中,除了研究区域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田野工作条件艰苦,甚至有些地区经常处在战乱的原因外,史前游牧社会的研究边缘化现状是其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被视为现代考古学探索的三个重大课题,成为占有大量研究资源的热门课题。其中“农业起源”也常常认为是“文明起源”的前提,甚至常常被认为是唯一的前提。这样观点几乎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农业起源”的研究成为地区性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相比较而言,“畜牧业和游牧起源”则没有像“农业起源”的研究那样被列在考古学的重大课题之中,甚至存在被排斥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之外的状况。
此外,在畜牧业起源的研究上,某种程度上国内外学者受到“畜牧业晚于农业”“畜牧业是从农业部落分离出来的”观点的影响。(6)杨阳:《关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的再认识——从考古发现看我国农、牧业起源和发展的多样性》,《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第37~44页。不可否认,这个观点在很多地区的考古研究中是得到证实了的。正像埃兰·克·奥特拉姆(Alan K.Outram)指出的,在世界各地农业起源中心地区,谷物种植农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要早于动物的驯养,即农业早于畜牧业。(7)Outram A.,Pastoralism.In G.Barker & C.Goucher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2015,pp.161-18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doi:10.1017/CBO9780511978807.中国史前家猪畜牧业的出现也是以水稻、粟和黍的人工栽培为主的史前农业为前提而发生的。但是,如果在畜牧业起源的问题上只强调农业起源中心的产生过程,就很容易忽略了独立于农业经济之外的畜牧经济和游牧经济起源的特殊性。(8)邵方:《中国北方游牧起源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44~149页。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尝试以生业模式的视角对国内外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进行回顾和评析,为今后主动地开展史前游牧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提供参考。
二 国外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
西方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涉及到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等内容。有关这些讨论,可以参考郑君雷的《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9)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217~224页。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草原文物》2007年第2期,第72~83页。文中介绍了西方学者对游牧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游牧文化起源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在这类研究中,很多西方研究者在努力寻找“纯粹的游牧人”的社会(pure nomadic pastoralism)。现在看来,这种所谓的“纯粹的游牧人”几乎是不存在的,是缺乏对游牧民族的深入了解而造成的。
回顾20世纪后期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欧亚草原上的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的、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相比较,进而确定这些史前遗存的性质。通过这些比较研究,他们认为这些史前居民主要是以牧业(pastoralism)为主、兼营采集和狩猎。早期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颜那亚(Yamnaya)文化存在传统意义的“游牧经济”(10)传统概念的“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是指非固定远距离的移动放牧,根据现代民族学研究来看,这种“游牧”的现象带有更多的主观臆测的色彩,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nomadic pastoralism),即不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内或固定的地点之间的“移动式放牧”(mobile pastoralism),而是一个非固定的远距离游牧形式。(11)〔苏〕阿纳托利·M.哈扎诺夫著;贾衣肯译;朱新审校:《游牧及牧业的基本形式》,《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1~110页。部分研究者们进而将颜那亚文化归于这种传统意义的“游牧”民族的遗留。
这里,必须要提及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及其著作《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12)Khazanov,A.M.,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Khazanov,A.M.,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Nomadic Commun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s.In W.Weissleder (Ed.),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n-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The Hague:Mouton,1978.pp.119-126.作为长期从事欧亚草原史前田野考古的苏联考古学家,他较早接触和开展了对史前畜牧业、游牧部落遗存的研究,他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前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民族考古学”运用于研究之中。《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是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哈扎诺夫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世界范围现存的传统游牧民族进行比较研究,对游牧经济的具体运作,个体、家族和集体,社会关系,游牧社会的基本构成进行综合考察,还探究了这些游牧社会与当地现代国家管理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第二章讨论“游牧的起源”问题,颇有创新之处。(13)Khazanov A.M.,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85-118.哈扎诺夫把游牧按所谓的从“纯粹的游牧”到“半定居的畜牧”划分成五大类。(14)哈扎诺夫的分类简述如下:第一类是指较大型的人口迁徙,即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认为是没有固定的路线、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传统的游牧”,并认为公元前七、八世纪的斯基泰人,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匈奴人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第二类则是一年四季都在不停的游动,没有固定的冬季中心。列举的现代例子是生活在哈萨克斯坦最干旱、没有雪的地区的,以及包括土库曼斯坦和蒙古的游牧人。第三类是全部人口都使用固定的迁徙路线,在冬季中心过冬,全年以饲养牲畜为基础,农业匮乏。他认为古代斯基泰的萨马尔泰(Sarmats)人、卡尔梅克人,以及一些现代的哈萨克人等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是在春季、夏季和秋季的三个季节里,全体成员都在做平面或垂直高度的迁徙,冬季则在永久的冬季定居点过冬,而农业仅仅是作为一个附属部门。第五类是一部分人口在一年或一年的某个季节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游牧,而其余的人从事定居的农业。Khazanov A.M.,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Nomadic Communities in the Eurasian Steppes.In W.Weissleder (Ed.),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n-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pp.119-126.这是对游牧经济的一种比较全面、细致的概括和总结,尽管存在一些主观的因素,对进一步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现存的欧亚及非洲、美洲的游牧民族的深入观察后我们会发现,游牧活动是相当复杂的,很难将实际的游牧活动与这五大类别一一对应。个体牧民家庭在实际游牧活动时相当灵活,基本的游牧范围大都是固定在几个季节性牧场之间,或在这些季节性牧场中间的数个过渡性牧场之间移动。农业作为附属经济,只要条件允许几乎都存在于各个游牧社会之中,只不过其占有的比例随着各地所能拥有的耕地资源、气候条件多少不同而已。有时一家人会同时经营转场游牧和谷物种植等活动,即春天播种谷物、饲料草,然后妇女儿童留守、照顾谷物,男子则结伴转场去夏季牧场放牧。作为一种单一的经济形式,即所谓的纯粹的游牧经济有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具备像耕地、合适的气候等的农业种植所必要条件地区的人们,游牧兼营采集和狩猎会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15)陈祥军:《阿勒泰的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第6~31页。这些地区的家庭或团体相对于其他具有一定农业种植地区的牧民来说,可称为纯粹的游牧人群。但作为一个多业并存、地域广阔的游牧社会来说,很难认为是个纯粹的游牧经济,或称之为纯粹的游牧社会。也就是说,包括哈扎诺夫在内的很多人类学家所寻找的那种“纯粹的游牧社会”(pure pastoralism society),即不存在农业种植的、完全以畜牧、游牧经济支撑的牧业社会在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关于游牧经济起源的原因,包括中国北方畜牧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很多西方学者将其与公元前2000~前1000年的全球大范围气候的干冷变化相联系,认为正是这样的干冷变化导致了农业经济的锐减和畜牧的发生与发展。这种观点被钟焓所质疑,认为是受到“气候启动论”的影响。(16)钟焓:《重释中亚史——以研究方法的检释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第321页。许多研究者认为环境变化导致了欧亚草原西部颜那亚文化的畜牧、游牧经济的产生,但事实是,同一地区内颜那亚文化也存在不间断的农业种植。(17)Frachetti M.D.,Multiregional Emergence of Mobile Pastoralism and Nonuniform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cross Eurasia.Current Anthropology,2012,53(1),pp.2-38.中国北方公元前2000~前1000年很多地区经历过经济转型,畜牧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农业经济,(18)Zhou X.,Li X.,Dodson J.,& Zhao K.,Rapi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ehistoric Hexi Corridor,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6,426(28),pp.33-41.也显示了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系。可以认为,这种农牧转换离开了气候和环境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对于欧亚草原以及中国北方这样一个广大区域的牧业、游牧的起源以及农牧业的转化,统统以环境变化来解释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了。而且,在大规模接受牧业之前,各地区无论自然环境抑或史前农牧业经济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例如,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 Shelach-Lavi)与吉林大学的同行们一起对辽河上游做了多年考古研究后发现,环境因素的确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非决定的力量。(19)吉迪,张玲,余静:《公元前1000年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牧业生活方式的兴起 ——区域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周邻地区的互动》,《边疆考古研究》2004年,第237~262页。不论环境的作用如何,那些构成牧业特别是游牧业基本因素如羊、牛、马等,这些可以远距离移动的家畜以及当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才是畜牧、游牧起源研究更应该重视的因素。(20)Haruda A.,Regional Pastoral Practice in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Kazakhstan in the Final Bronze Age (1300~900 BC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15(2018),pp.146-156.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游牧经济起源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各个地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和途径。用单一的原因和方式去解释世界各地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背景下游牧经济的起源,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无论是游牧文明起源,还是游牧文化的起源,都必须要从研究游牧经济起源入手,而对游牧经济起源的研究则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核心。所以,哈扎诺夫在《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这本书的第二章“游牧起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欧亚草原的史前考古学。(21)Khazanov A.M.,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p.85-111.他认为畜牧业在欧亚草原出现的年代并不是很晚,特别是欧亚草原的西部。伴随着羊、牛等家养动物的传入,小规模的畜牧业逐渐在公元前四五千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至青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存在游牧经济。他还认为,像斯基泰和匈奴那样的以骑马作为放牧主要工具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书中他多处强调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以区别一般的定居的畜牧业。
哈扎诺夫认为的斯基泰或匈奴那种常年远距离的、非固定地域的、“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是不存在的,很可能是对这些游牧民族的片面理解或误解。很多欧亚草原现代游牧民族的游牧实际上是转场放牧,是在固定的季节性牧场之间或短、或长距离上的移动,或在一个季节性草场内短期地、有计划地移动放牧。所以,目前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季节性游牧”(transhumance)这一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居无定所的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
如何评价西方和俄罗斯学者在欧亚草原的游牧考古实践呢?我们从欧亚草原西部典型考古学文化经济模式的认识历程来评判。
颜那亚—洞室墓文化(Yanamnya-Catacomb)是欧亚草原西部最具代表性的、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颜那亚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在欧亚草原西部,位于乌克兰东部、横跨黑海和里海以及俄罗斯南部和哈萨克斯坦西部,其主要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600年,处于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偏早的阶段。该文化早期居民的经济模式被认为是以牧业为主,同时从事采集和渔猎。而与之同时或略晚些的、分布在欧亚草原东部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的人群,被认为是颜那亚文化向东传播而形成的,其生业形态也被认为是经营畜牧业为主。与哈扎诺夫相似,俄罗斯的学者科亚阔娃(Ludmila Koryakova)也认为颜那亚文化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从事着畜牧经济。(22)Koryakova L.,Epimakhov A.,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45-110.原因之一是这些遗存都有相当数量的饲养动物,如发现的羊、牛和马的骨骼。阿凡纳谢沃文化主要分布包括了现今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区域,近年来在新疆的西部也发现了这一文化的遗存。(23)于建军,何嘉宁:《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7年12月1日第8版。然而,阿凡纳谢沃文化与颜那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饲养动物的构成。颜那亚—洞室墓文化的很多遗存中的动物种类除了牛、马和羊之外,还有家猪,而阿凡纳谢沃的遗存中则不见猪的踪影。这种无猪畜牧的现象,在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的奥库涅沃、安德罗诺沃以及卡拉苏克等文化的考古遗存中是一脉相承的。(24)Koryakova L.,Epimakhov A.,The Urals and Western Siberia in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pp.45-110.
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是否存在谷物种植业呢?多数西方学者都在使用“agropastoralism”这个概念——“从事少量农业的畜牧经济”——来描述这些铜石并用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生业模式。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以下简称安文化)的研究中,库兹米娜(Kuzmina)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安文化的农业经济。她从使用的工具(尤其是青铜镰刀和锄头)分析,认为当时是存在农业种植业的,这个推测在后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安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人工饲养动物骨骼,包括羊、牛、马等。早期的辛塔什塔遗址中还发现了双峰骆驼的骨骼,说明畜牧业也是其主要的经济形态之一。库兹米娜特别指出,安文化分布的地域十分广大,包含了诸如森林地带、草原地带和沙漠绿洲等不同的自然地理形态,不同地区安文化的畜牧和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库兹米娜认为生业形态在同一个考古文化联合体中会根据所在的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个认识在目前的史前游牧考古研究中相当重要。
对于安文化是否出现游牧的问题,库兹米娜也做了深入的分析。在她看来,安文化的畜牧是一种定居的放牧方式,但也认为,由于畜群中马匹的存在,使得畜群(包括羊群)即使在冬季雪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吃到雪下的牧草,因而存在游牧方式是可能的。她推测安文化的最后期已经具备了游牧的一切准备,处在从定居牧业向游牧的转型期。当然,这些推测在当时还没有相应的考古学证据。(25)Kuzmina E.E.,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Boston:Brill.2007.pp.141-161.
事实上,对于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无论是农业种植还是畜牧经济的推测,都缺乏系统的、清晰的考古学论证。所以,像上述的研究中简单地把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形容成一种从事少量农业、固定居住的“牧业社会”,并认为这种“牧业社会”经过千年的发展诞生了后来著名的塞人、匈奴这样的游牧王国,这样的认识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从以往的研究看,早期的欧亚草原考古学研究,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停留在以发现饲养动物骨骼为主要依据,并由此而推定牧业经济存在与否,而没有更多地追寻牧业缘起和游牧起源的原因以及确切的田野考古学证据。
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有所改进,在苏联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西方考古学界开始渐次展开对欧亚草原史前牧业的考古研究。华盛顿大学的弗拉崔悌博士(Michael Frachetti)进入哈萨克斯坦东边的西天山东北部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参考当地牧民的游牧生活方式,结合考古发现的遗存形态,对欧亚草原的史前游牧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之后,他的团队长时间在这一地区从事游牧考古学的研究。另一个进入欧亚草原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是美国斯特布莱尔学院(Sweet Briar College)克劳迪娅·张(Claudia Chang),她早年在希腊南部的一个叫Peloponnese岛上作游牧民族学调查,1981年后也一直从事游牧民族的民族考古学教学和研究。1996~2018年间,她以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考古为研究课题,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哈萨克斯坦南部西天山北坡的塔尔加尔(Talgar)地区。
欧美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影响到了俄罗斯考古学界,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娜塔莉亚·施什丽娜(Natalia Shishlina)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寻找季节性移动游牧在考古的具体证据,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以考古学的证据来具体判定史前季节性游牧的考古学研究范例之一。(26)Shishlina N.I.,The Seasonal Cycle of Grassl and Use in the Caspian Sea Steppe During the Bronze Age:A New Approachtoan Old Problem.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2001,4(3),pp.346-366.在利用民族考古学方法进行史前游牧考古的研究中,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罗杰·克里布(Roger Cribb)博士也是十分杰出的,他于1982年获得英国南开普敦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成果于1991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游牧考古学》。(27)Cribb R.,Nomads in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3-109.尽管他的著作中没有多少涉猎欧亚草原的史前牧业考古,但他以独到的民族考古学的田野视角和方法,对土耳其晚近的游牧部落社会形态的实地考察,进而展开对史前游牧民族的多角度研究,应该是当下史前游牧考古领域的先驱。罗杰·克里布博士于2007年时(年仅59岁)离世,但是他的《游牧考古学》是留给考古学界的珍贵遗产,也是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的必修课。
这里例举几个史前游牧考古研究的实例。
1.拜尕什(Begash)遗址的发现(28)Frachetti M.,Pastoralist Landscap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Bronze Age Eur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p.133-140.Frachetti M.a.B.,Norbert,From Sheep to some (some) Horses:4500 years of Herd Structure Art the Pastoralist Settlement of Begash (South-eastern Kazakhstan).Antiquity,83(2009),pp.1023-1037.Frachetti,M.M.Y.A.,Long-term Occupation and Seasonal Settlement of east Eurasian Pastoralists at Begash,Kazakhstan.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32(2007),pp.221-242.Spengler R.N.,Frachetti,Michael D.,Domani,Paula N.,Late Bronze Age Agriculture at Tasbas in the Dzhungar Mountains of eastern Kazakhstan.Quaternary International,348(2014),pp.147-157.
拜尕什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流域,地处卡拉塔尔河(Karatal) 上游的科克苏(Kuksu)河岸上。遗址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天山山脉阿拉套山北坡,附近是以半干旱的草原植被为主,海拔950米,距离居住址500米的东北部是墓葬区。对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弗拉崔悌自博士学习期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游牧考古项目之一。他和团队对于这一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对周边的多处史前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拜尕什遗址就先后经过了2002、2005、 2006年三个夏天的发掘,重点是一个多层堆积的居住址的发掘清理。遗址年代跨度较大,自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公元17世纪。
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青铜时代的遗存,除了陶器之外,还包括了饲养动物羊、马和牛的骨骼,炭化的小麦和黍、粟的种子等多类遗物。(29)Spengler R.,Frachetti M.,Doumani P.,Rouse L.,Cerasetti B.,Bullion E.,& Mar'yashev A.,Early Agriculture and Crop Transmission among Bronze Age Mobile Pastoralists of Central Eurasia.Proceding of the Royal Society B,281(2014),pp.1-7.Frachetti M.D.,Robert N.Spengler,Gayle J.Fritz,Alexei N.Mar’yashevet,Earliest Direct Evidence for Broomcorn Millet and Wheat in the Central Eurasian Steppe Region.Antiquity 84(2010),pp.993-1010.由于这是一个多层堆积的遗址,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建筑与晚期的遗迹相互叠压,年代跨越了4000多年;发掘者认为,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后的遗迹,可能是塞人或乌孙人的聚落建筑;遗迹被公元17世纪(以后)近代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建筑所叠压,而且聚落建筑形式比较接近。他们分析了遗址内涵,并结合对该地区牧业地貌(pastoral landscape)的判定,最终以游牧遗存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定性。这一结论,在弗拉崔悌团队的一系列植物考古和综合研究文章中多次被强调。特别是经过了他们对当地草场的电脑数据和游牧转场的电脑模拟之后,拜尕什遗址属于游牧遗存的结论被广为扩散,也贴上了游牧经济的显著印记,他们认为,它还是这一地区青铜时代游牧(形态)冬季居址的代表。(30)Frachetti M.D.,Smith C.E.,Traub C.M.,& Williams T.,Nomadic Ecology Shaped the Highland Geography of Asia’s Silk Roads.Nature,543(2017),pp.193-198.
总体而言,弗拉崔悌和同事对拜尕什以及其他几处遗址的研究,为如何开展游牧考古打开了新的综合研究范式。受各种条件和因素的限制,拜尕什遗址中居住址的发掘面积只有155平方米,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制并没有被完整地揭露出来,这就大大限制了对遗址整体性的研究。目前对拜尕什遗址的研究中,并没有见到能够说明是季节性游牧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对遗址的游牧性质的确定多是基于合理的推测。甚至,斯摩丝博士(Tekla M.Schmaus)在后来对该遗址的动物牙齿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季节性使用的迹象,包括后面要提及的塔什巴(Tashba)和吐祖赛(Tuzusai)遗址,她都认为是四季定居的。(31)Schmaus T.M.,Sea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Prehistoric Kazakhstan (Vol.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2015.但弗拉崔悌团队以这样小的发掘面积和有限的发掘资料,能够对遗址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也实属难能可贵。
2.塔什巴遗址
塔什巴遗址在拜尕什以东大约100多公里的位置,遗址仍然属于科克苏河上游,海拔约1500米,比拜尕什的海拔高出600多米。遗址所处草原与拜尕什相似,属于当地牧民的夏牧场。面南背北,北依一座小山丘,南面十余公里外是河谷平原,宽广的河谷对面是高耸入云的天山(阿拉套)山脉。
遗址最初由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考古研究所在2001年进行小型的试掘,(32)Doumani P.N.,Frachetti M.D.,Beardmore R.,Schmaus T.M.,III,R.N.S.,& Mar'yashev A.N.,Burial Ritual,Agriculture,and Craft Production among Bronze Age Pastoralists at Tasbas (Kazakhst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2015(1-2),pp.17-32.2011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多曼妮博士(Paula N.Doumani)进行了新的发掘。尽管发掘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但在一个小型的石棺墓内的填土之中发现了这一地区最早的小麦(cal.2596-2515 BC)和黍、粟遗存。(33)Spengler R.N.,Frachetti,Michael D.,Domani,Paula N.,Late Bronze Age Agriculture at Tasbas in the Dzhungar Mountains of Eastern Kazakhstan.Quaternary International,348(2014),pp.147-157.这个遗址与拜尕什遗址同样被视为青铜时代季节性游牧的临时居址,其理由与认定拜尕什遗址相同,即大量的饲养动物骨骼、海拔较高的草原地貌等。他们认为塔什巴是当时的夏季居址。但在动物牙齿的研究中,却没能给出季节性使用的相关证据。(34)Schmaus T.M.,Sea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Prehistoric Kazakhstan.Indiana University:Unpublished Dissertation.2015.
此外,对土库曼斯坦穆尔哈勃(Murghab)地区奥加克里(Ojakly)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与上述两个遗址非常相似。(35)Rouse L.M.,& Cerasetti B.,Ojakly:A Late Bronze Age Mobile Pastoralist Site in the Murghab Region,Turkmenistan.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2014.39(1),pp.32-50.DOI:10.1179/0093469013Z.00000000073.发掘者在遗址中发现了草拌泥的建筑残片,但除了一个陶窑之外,并没有发现确切的居住址。根据出土的饲养动物骨骼种类、遗址地层堆积较薄等情况,发掘者认为是属于青铜时代游牧的遗存,但并没有发现确切的季节性游牧的更多证据。
3.塔尔加尔(Talgar)河流域的游牧考古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之际,克劳迪娅·张在哈萨克斯坦东南的塔尔加尔河流域进行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历时20多年。虽然关注的重点是公元前1千纪后的遗存,但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早期青铜时代的游牧考古颇有启发。
1992年开始的塔尔加尔项目就是以寻找分布于欧亚草原南部边缘的、形成于公元前一千纪左右的早期骑马民族的游牧社会联盟为目的。塔尔加尔河是伊犁河下游的一条支流,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面的天山北坡,河流自南向北汇入伊犁河。考古研究人员在该地区做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吐祖赛遗址是其中之一。该遗址位于阿拉木图市东面25公里处的塔尔加尔河冲积扇上,遗址的北面是海拔5000米的天山塔尔加尔峰。遗址周边自天山脚下的2000~1700米开始呈现缓慢的斜坡,形成海拔1100米左右的广大冲积扇,在其西北延伸的过程中海拔逐渐降低至650米左右。(36)Chang C.,& Grigoriev F.P.,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1994-1996 Field Seasona at Tuzusai,an Iron Age site (ca.400 B.C.-100 A.D.) in Southeastern Kazakhstan.Eurasia Antiqua,Band 5(1999),pp.391-410.Chang C.,Benecke N.,Grigoriev F.P.,Rosen A.M.,& Tourtellotte P.A.,Iron Age Society and Chronology in South-East Kazakhstan.Antiquity,2003.77(296),pp.298-311.
吐祖赛遗址的面积非常大,地面调查了50,000~120,000平方米。这一地区的野外工作长达20多年,但发掘面积仅有500余平方米。遗址的年代根据测年确定为公元前400~前200年,使用时期200年之久。研究者根据连续的层位和其他一些迹象,认为可能是一处四季连续居住的遗址。
克劳迪娅·张在这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重视多学科的考古人类学研究。为了深入解读这个遗址,克劳迪娅·张充分利用她之前在希腊北部的民族学调查的经验,展开了对塔尔加尔当地哈萨克牧民的民族学调查。通过调查,她不仅发现这里的牧民转场的方式与希腊北部牧民十分相似,而且这一地区有较好的农耕土地和与此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她开始对历史上记载的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塞人、乌孙等所谓的“纯粹”依靠畜牧业的游牧民族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斯摩丝博士(Tekla M.Schmaus)对该遗址出土一百多只羊的牙齿做了分析,认为这是一处四季都使用的遗址。这是为数不多的从驯化羊死亡(屠宰)年龄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以说明遗址使用方式的尝试。(37)Schmaus T.M.,Sea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Prehistoric Kazakhstan.Indiana University:Unpublished dissertation.2015.
克劳迪娅·张和她的团队的考古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思考,即在寻找和认识游牧考古遗存的过程中了解游牧经济的真正含义、客观地复原这些古代游牧社会的结构及其运作过程。(38)Chang C.,Ethnoarchaeology of Pastoral Land Use.In J.Rossignol & L.Wandsnider (Eds.),Space,Time,and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1992,pp.65-89.New York and London:Plenum Press.
4.巴尔干半岛的动物考古
在探索游牧经济起源的道路上,以动物骨骼鉴定为主要方法的传统动物考古学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者们使用最多的证据是遗址中出土的一定数量的饲养动物特别是具有游牧特征的羊、牛、马和骆驼等骨骼。民族考古学为指导的动物考古研究对史前游牧考古的贡献尤为显著。典型的范例是美国格兰德沃蕾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的伊丽莎白·阿诺德博士(Elizabeth R.Arnold)和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哈斯克尔·格林菲尔德博士(Haskel J.Greenfield)的动物考古研究。(39)Arnold E.R.,& Greenfield H.J.,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Vertical Transhumant Pastoralism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Marginal Habitats in Temperate Southeastern Europe.In M.Mondini,S.Muoz,& S.Wickler (Eds.),9th ICAZ Conference:Colonisation,Migration,and Marginal Areas.2002,pp.96-117.Durham.他们的研究地区并不在欧亚草原,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他们的这项研究持续20多年,其数据涵盖了南欧巴尔干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不同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同时,他们也收集了当地现代游牧民族在不同季节宰杀的牲畜骨骼标本。他们发现,分布于这一区域的高地和低地的古代遗址中的动物种类和死亡年龄,自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1900~前1600年)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与当地现代牧民在高地牧场和低地牧场于不同的季节进行转场游牧的数据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而且,这一现象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并在青铜时代晚期特别是早期铁器时代变得越来越明确。这就说明:与现代牧民相似的垂直转场的游牧经济在青铜时代出现,并在早期铁器时代达到成熟。这项研究为寻找游牧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其研究的细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堪称典范。(40)Arnold E.R.,& Greenfield H.J.,The Origins of Transhumant Pastorialism in Temperate South Eastern Europe: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Central Balkans.Oxford:Archaeopress.2006.
5.关于欧亚草原西部颜那亚—洞室墓文化游牧的推测
俄国学者娜塔莉亚·施什丽娜和她的团队在2001年发表了关于里海西北的颜那亚—洞室墓文化存在游牧的最新研究成果。(41)Shishlina N.I.,The Seasonal Cycle of Grassland Use in the Caspian Sea Steppe during the Bronze Age:A new Approach to an old Problem.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2001,4(3),pp.346-366.在这个研究中,他们除了综合民族学、古环境等学科的研究外,主要是通过对墓葬填土中包含的植物种类以及动物骨骼和牙齿的牙骨质进行分析,以此确定墓葬的埋葬季节,从而为转场游牧的假设提供支持。他们基于不同牧场的植物种类受其季节环境变化而不同的理念,比较该地区现代牧民饲养的动物骨骼与考古发现的动物骨骼的同位素食谱的结果来推定当时转场游牧的存在。其中一个具体的成果是,在里海西北的顿河下游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大麦植硅体被推测是由于转场游牧的过程中通过交换获得的。(42)Shishlina N.,Sevastyanovb V.,& Kuznetsova O.,Seasonal Practices of Prehistoric Pastoralists from the South of the Russian Plain Based on the Isotope Data of Modern and Archaeological Animal Bones and Plan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http://dx.doi.org/10.1016/j.jasrep.2017.02.013),online version Shishlina N.I.,Bobrov A.A.,Simakova A.M.,Troshina A.A.,Sevastyanov V.S.,& Plicht J.v.d.(2018).Plant Food Subsistence in the Human Diet of the Bronze Age Caspian and Low Don Steppe Pastoralists:Archaeobotanical,Isotope and 14C Data.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online),https://doi.org/10.1007/s00334-00018-00676-00339.使用现代草场植物种类与考古发现的孢粉、植硅体,以及人和动物同位素食谱所显示出的植物类别进行对比研究,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去搜集大量的现代游牧民族的同类数据作参考,这一过程很难通过几次简单的实验就能解决。
6.蒙古高原的畜牧、游牧业的起源
欧亚草原东部、蒙古高原畜牧与游牧发生的时间及动因也是游牧考古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欧柏林学院人类学与东亚学系的耶和华·莱特(Joshua Saint Clair Wright)博士,在蒙古国北部的额金河流域开展的考古工作与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考察当地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生业形态。他结合人类学田野方法,对当地现代蒙古游牧民族的季节性转场进行跟踪观察。(43)Wright J.S.C.,The Adoption of Pastoralism in Northeast Asia,Monu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giin Gol Valley,Mongolia (Vol.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 USA:Harvard University.2006.据此,他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是游牧经济,其过程是5000年前由欧亚草原西部的“从事少量农业的畜牧经济”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来到蒙古高原的西部,带来了西亚的牛、羊和欧亚草原的马,使得蒙古高原的居民从采集狩(渔)猎转化为移动的放牧者——游牧民族。他的推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研究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宏观人类学、民族学与考古材料的比较研究上,缺乏必要的科技考古的微观证据的支撑。
三 国内史前游牧考古
在中国北方地区考古研究中,以史前畜牧、游牧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并不多见。类似内蒙古朱开沟遗址生业形态的讨论(4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89~290页。以及像冠以“游牧文化”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研究等,都还是对考古遗存的后续分析,并非是在田野工作中明确以畜牧、游牧考古学研究为中心,而且,多数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畜牧“和“游牧”的区别,所使用“游牧经济”概念实际上多是指“畜牧经济”。佟柱臣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便开始涉猎游牧考古的研究,领风气之先,但他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游牧业的概念,目前来看主要是指畜牧业。(45)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的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第188~195页。早期的游牧考古研究甚至把北方的细石器遗存与游牧经济联系在一起。(46)乔晓勤:《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21期,第 21~25页。即便如此,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考古难题,这些早期的、开创性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然值得参考。国内的研究更多是以古代畜牧、游牧社会的考古文化为对象,多集中于公元前一千纪之后,如斯基泰、早期匈奴等介于史前向历史时期过渡的阶段,集中在称为早期铁器时代的、历史记载中比较成熟的游牧社会。这些以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是史前游牧生业考古的重要基础,乌恩先生对斯基泰文化的论述就属这一类。(47)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7~470页。杨建华教授和包曙光博士对俄罗斯图瓦和阿尔泰地区斯基泰的游牧文化的遗存分析,指出这一地区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多是发生在贵族阶层中。(48)杨建华,包曙光:《俄罗斯图瓦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第75~84页。田澍教授与马啸总结了过去游牧考古研究,并注意到了不能简单地把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相比较,认为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新。(49)田澍,马啸:《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评述》,《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第116~124页。最近,邵会秋与吴雅彤撰文对欧亚草原的三个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起源做了详尽的论述,并指出各地早期游牧的起源并不同步,起源方式也不尽相同,提出了游牧起源的“原生地”与“次生地”概念,认为发达的畜牧业和熟练的骑马术等可能是早期游牧得以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50)邵会秋,吴雅彤:《早期游牧文化起源问题探析》,《北方文物》2020年第1期,第28~38页。
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游牧考古的领域逐步兴起,田野调查和发掘的规模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如此,国内学者也在史前游牧考古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林沄先生关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带的论述,对深入认识这一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51)林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1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5~146页。杨建华教授在向国内介绍西方有关欧亚草原史前考古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出了目前国内历史和考古学界亟待解决的缺乏对欧亚草原全面研究的问题。(52)杨建华:《国外关于欧亚草原史前时代晚期的综合研究评介》,《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第355~362页。王立新教授和胡平平博士基于对史前墓葬的经济形态的分析,指出当时赤峰地区可能存在随季节移动的游牧兼渔猎的经济形态,(53)王立新:《关于东胡遗存的考古学新探索》,《草原文物》2012年第2期,第55~60页。首次使用了“牧猎经济”一词来概括这一形态。(54)王立新,胡平平:《内蒙古中南部与东南部地区东周时期含畜牧业成分诸遗存的葬俗比较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2013年,第139~160页。这些都是史前游牧生业考古研究的基础。
郑君雷教授总结了西方学者在游牧文化的起源方面的研究,并根据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实践,对田野考古中如何判定游牧性质的遗存做了深入的讨论。(55)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2007年,第425~457页。他在评述了西方游牧考古之后,总结性地对今后游牧考古研究提出了七个要点,其中的游牧起源“要考虑各种发生途径”“注意游牧起源技术前提的考古分析”“岩画对游牧考古的意义”“加强自然环境的研究”“提倡考古学者参与现代游牧族群的民族学调查”等都是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56)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 217~224页。近些年来在新疆的考古实践也体现了这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王建新教授通过对新疆东天山地区的史前游牧居址的野外工作,简要地概括了游牧性质的遗存所具有的居址、墓葬和岩画的“三位一体”的特征。进而指出了古代游牧民族也建造相对固定的居址,从考古学的角度纠正了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这个误导考古、史学界和公众多年的错误观点。(57)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页。霍巍教授根据西藏史前考古的证据,提出了西藏史前游牧居址的三种类型。(58)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第57~67页。笔者也根据新疆西天山的考古实践提出了新疆西天山地区早期转场游牧出现于当地的青铜时代的观点。(59)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丛德新,贾伟明:《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故宫博物院编:《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第160~172页。
近年来科技考古广泛地应用于游牧考古的遗存分析。吕红亮教授和唐莉博士介绍了国外是如何在考古遗址中发现和分析家畜粪便遗留,(60)唐莉,吕红亮:《动物粪便分析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南方民族考古》15(第2期),2017年,第297~308页。邵孔兰和张健平等对遗址土壤与动物粪便中的植硅体的比较分析等,(61)邵孔兰,张健平,丛德新,贾伟明,崔安宁,吴乃琴,《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第四纪研究》第39卷(第1期),2019年,第37~47页。都为史前游牧考古提供了新方法、新资料和研究的新领域。此外,国内也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史前游牧考古的发展。例如,人类学家王明珂教授对古代游牧民族的研究,他在《游牧者的抉择》(6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3页。和《华夏边缘》(6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的论述中,参考了世界各地的民族学资料,结合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解释形成游牧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深层原因。钟焓教授在《重释内亚史》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游牧民族的起源和游牧文化。(64)钟焓:《重释中亚史——以研究方法的检释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6~321页。民族学家陈祥军博士的《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65)陈祥军:《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他所编著的《杨廷瑞“游牧论”文集》(66)陈祥军:《杨廷瑞“游牧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是近年来国内最新的游牧民族生业形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对史前牧业经济和游牧生业的研究尤为重要。尽管上述研究在方法、对象上都不尽相同,而且有些观点之间相去甚远,但这都是目前国内史前畜牧、游牧考古研究中可喜的现象,而这些成果都是值得研究者去深刻思考的。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包括西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其畜牧和游牧业的起源是与羊、牛、马这些外来的家畜分不开的。在北方地区的农牧交错地带,伴随着不断积累的考古材料及研究的深化,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确实存在我们常说的农牧业的转化过程和亦农亦牧的混合经济形式,这与欧亚草原的牧业产生和游牧业的起源模式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域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近几年来新疆、西藏的史前考古及生业形态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包括新疆哈密地区的东天山史前游牧聚落的研究(67)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页。、西藏地区史前畜牧业和游牧经济的研究(68)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第57~67页。以及新疆博尔塔拉河上游的青铜时代畜牧、游牧经济的研究。(69)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丛德新,贾伟明:《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第160~172页。这些研究大大提升了对包括中国北方地区在内的欧亚草原史前畜牧、游牧业形态的认识,也把欧亚草原的游牧考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新疆东天山的史前游牧考古
在国内首先明确以游牧为主题开展的大型考古研究项目当属新疆哈密东天山研究。(7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哈密地区文物局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的大型考古综合研究项目——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这项研究是以2000年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组织的新疆东天山和甘肃西部的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开始的。(71)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页。他们在天山东部的巴里坤伊吾地区的天山坡地上发现了多处石头垒砌的建筑群、墓葬群和岩画,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前200年,大致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遗址多集中在东天山南北两侧的坡地、沟谷、海拔在1900~2100米的高山草场上。这些遗址中柳树沟遗址(72)王永强,张杰:《新疆哈密市柳树沟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4~126页。(海拔1800米)坐落在天山南坡,岳公台—西黑沟(海拔1900多米)(73)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哈密地区文管会:《新疆巴里坤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调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第3~17页。、东黑沟(石人子沟)(海拔1900多米)(74)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管所:《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第3~12页。、红山口遗址(海拔2000多米)(75)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哈密地区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局:《新疆巴里坤红山口遗址 2008 年调查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第17~30页。分布于天山北坡的巴里坤县。这些遗址包括居址和墓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大都是石构建筑,居址、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人工遗留的遗存以及位于相似的海拔(1800~2200米)的山坡(或沟谷),与草场及河流这些自然景观紧密相连,构成了天山地区典型的古代畜牧业景观地貌。
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发现这些遗址的年代大致是在公元前1500~前500年之间。(76)王永强,张杰:《新疆哈密市柳树沟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掘》,《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4~126页。王远之:《柳树沟遗址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第24~25页。基于这些发现,王建新教授对传统的史籍记述的古代游牧民族的“逐水草,居无定所”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依据大量的考古学材料,提出古代游牧部落的固定的聚落群的存在,并根据古代文献和现代游牧民族学的研究提出了古代游牧民族存在冬、夏固定的季节性营地和居址的推论。(77)王建新:《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哈密东天山古伊州文化研究院编:《东天山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8年,第37~48页。根据大量的调查和资料,他总结出了游牧文化所具备的居址、墓葬和岩画“三位一体”的游牧景观特征。
该项目还做了多项研究和分析。首先是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者指出了游牧社会存在固定的聚落的事实。特别是通过对大型聚落和高台建筑的分析,研究者认为这些聚落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等级构成,具有高等级中心聚落的性质。(78)张凤:《新疆东黑沟遗址石筑高台、居址研究》, 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 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其二,区分出两类不同的遗存,其存在的年代和各自的文化性质都具有明显差别。第一类大致在公元前1300 ~前300年前后,跨越1000年左右;(79)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二类遗存年代跨度较短,大致处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后。结合了当地的地理、地貌和自然环境资源并参考了大量的当地和其他地区游牧经济的民族学资料后,研究者认为第一类是属于定居的农业、畜牧或半农半牧,晚期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化,而第二类的生业形态完全属于游牧。这些分析也得到了植物考古学证据的支持。(80)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从第一类到第二类的过渡体现了定居农业、半农半牧和定居畜牧向游牧的转化。(81)张坤:《东天山地区第二类早期游牧文化墓葬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针对不同的自然环境,马健注意到了东天山山地草原区与哈密绿洲盆地的生业模式的差异,认为农业比重后者大于前者,而且谷物种植的种类也体现了这个环境区别。(82)马健:《东天山早期聚落形态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所有这些研究和认识在新疆地区的史前考古中具一定的代表性。(83)李雪欣:《新疆北部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
该项目还展开了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环境、动植物、金属冶炼等多方面的科技考古实践。如对出土的羊、马、骆驼等家畜的动物考古,(84)尤悦,吕鹏,王建新,马健,任萌:《新疆地区家养绵羊的出现及早期利用》,《考古》2016年第12期,第104~114页。植物、同位素(85)凌雪,陈曦,王建新,陈靓,马健,任萌,习通源:《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2卷第2期,第219~225页。,石器、有机体残留物(86)井明:《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初步科技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陶器产地分析等(87)尤悦,钟华,余翀:《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生业考古的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第116~122页。李悦,尤悦,刘一婷,徐诺,王建新,马健,习通源:《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考古》2016年第1期,第108~120页。尤悦,王建新,赵欣,凌雪,陈相龙,马健,任萌,袁靖:《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双峰驼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34卷第1期,第173~186页。赵欣,尤悦,王建新,马健,任萌,袁靖,杨东亚:《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家马的DNA研究》,《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34卷第1期,第187~195页。申静怡:《东天山地区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址陶器制作工艺和产地的研究》, 西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其中动物、植物考古分析中的家畜种类、年龄鉴别,植物考古中的栽培谷物的分析以及同位素食谱分析都进一步证实了前述的各个研究中对几处主要聚落的农牧兼顾的古代生业形态的基本认定,而且,植物考古学的证据表明这里古代游牧也仍然保留少量的农业经济。(88)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 ——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不惟如此,田多博士的植物考古研究中引入了民族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动物粪便燃料遗留下来的植物遗存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以此深入认识当时的畜牧经济,为今后系统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9)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 西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第180~183页。此外,尤悦博士在动物考古研究中首次应用了民族考古学的方法,(90)尤悦:《新疆东黑沟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博士论文。为全方位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任萌的研究还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对遗存的族属做了详细的考察,认为东天山的游牧遗存与历史记载的匈奴文化有密切联系。(91)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部考古》第五辑,第252~290页。
就目前而言,东天山的史前游牧聚落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对以游牧聚落为中心的田野考古研究开风气之先,为史前畜牧、游牧考古学的发展辟出了新思路,也将中国和欧亚草原的游牧考古学研究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上述研究的一些结论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很多认识需要在更多的田野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例如,如何在田野考古中区分定居牧业和游牧业的居址/聚落群,是否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景观考古,特别是绿洲农牧业和山地草场游牧业典型遗址的景观考古研究,如何利用科技考古对典型遗址的农牧结合的成分做更加细致的研究等等。
2.西藏地区的游牧考古
以牦牛、黄牛和羊组成的现代西藏游牧经济是世界上最具特点的牧业形态之一,适应高海拔、高寒地区,其起源也相当古老,经过世代相传至今。位于青藏高原的西藏自治区不仅海拔高,各地自然环境差别也大。藏北高原是主要的牧业区,而藏南谷地,海拔平均在3500米左右,地形平坦,土质肥沃,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和半农半牧的地区。西藏的史前考古或多或少都与畜牧、游牧发生一定的联系。(92)霍巍:《西藏史前考古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第5~12页。吕洪亮:《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第1~34页。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霍巍教授曾几次论及西藏的史前游牧经济,(93)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西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8~136页。根据不同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景观,提出了西藏存在早期游牧遗址,北部和西部的“羌塘高原”应是古代居民从事游牧的主要地区。藏南河谷和藏东山脉地带,则应是半农半牧的古代经济分布区。(94)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第57~67页。这些古代游牧居民并不是“居无定所”,而是有固定的石头垒砌的季节性居址。根据西藏地区早期聚落的考古发现和分布,他将这些聚落分为三类:季节性半定居式聚落(丁东遗址),临时性营地遗址(加日塘遗址)(95)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 科学出版社,2005年。和大型城寨聚落(“穹窿银城”遗址)。
丁东遗址是藏北地区典型的史前居址之一,遗址中发现几个石头垒砌的房址都是不规则形状,内有隔间,与新疆东天山发现的居址很相似。丁东遗址的房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房址依坡地而建,建筑多东西宽、南北窄。从建筑本身的遗迹很难确定房址的门道和朝向,这可能也是游牧居址的一个特点。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新疆天山夏季牧场上,牧民的夏窝子并不一定要坐北朝南,可以朝东或朝西,甚至会朝北。而丁东遗址的F1很可能是朝西的。
房址F1的年代在公元前208BCE~66CE(92.7%),是一处2000多年前的居址。与遗址相邻的东嘎墓葬区应属于同一时期,都处在海拔4100米的坡地上。(9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第14~31页。遗址中除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外,还在房址(F4)的地面和立石周围发现了近百粒碳化青稞。说明这里的古代居民与今天类似,除了在高山草场放牧外,也在河谷低地从事一定的青稞种植。(97)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藏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第36~46页。
目前,西藏的游牧考古研究还在不断深入,也存在一些疑问。如西藏的史前游牧经济是否存在与邻近地区的联系,是否也存在像新疆东天山地区定居畜牧向游牧的转化过程,除牦牛之外,绵羊、山羊如果也是来源于西亚、中亚的同一物种,那么这些家畜是什么时候、经过什么路线、又是如何传入这一地区的,牦牛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驯化的,那些方形和圆形的石围居址,是否是转场游牧时使用过的帐篷式的临时居址的遗迹,早期游牧的具体形态和游牧转场的方式是否和现代居民相似?这些疑问都需要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中去寻找答案。
3.新疆西天山阿敦乔鲁遗址的研究
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位于新疆西天山博尔塔拉河流域,是继西北大学东天山游牧考古项目之后,又一个以畜牧、游牧生业为中心的考古项目。遗址的年代属于青铜时代中、晚期的遗存。(9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馆,温泉县文物局:《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4~30页;Jia,P.Betts,A.,Cong,D.X.,& Doumani,P.D.,Adunqiaolu:new Evidence for the Andronovo in Xinjiang,China.Antiquity,2017,91(357),pp.621-639;丛德新等:《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 2017年第4期,第 15~27页。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地处博尔塔拉河谷,阿拉套山的南坡山前地带,海拔1800~2100米,碳十四数据显示其开始使用的年代为公元前19世纪。与之相似的遗址和墓葬在博尔塔拉河流域中上游多有发现,说明当时这里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古代文化分布区。(99)尼·葛丽:《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早期青铜时代军事遗存》,《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14日第2版;贾笑冰,葛丽:《新疆温泉发现一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2日第8版。Jia,P.,Betts,A.,Domani,P.N.,Cong,D.X.,Bronze Age Hill Forts:New Evidence for Defensive Sites in the Western Tian Shan,China.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15(2018),pp.2352-2267.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的发现与研究,是最近一个时期新疆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重要的研究课题。
阿敦乔鲁遗址中,房址F1的规模和复杂结构都十分值得注意。与西藏的丁东的房址及东天山发现房址的朝向不同,阿敦乔鲁F1是坐北朝南,房址(院落)外部规模为22米×18米,双石墙以内区域为18米×14.6米。石墙所用的石头都很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约为3米×1.5米;房址内分区呈对称布局,其间发现一些灰坑,可能用作窖藏。墙体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内各有一个四分之一圆形的双石圈遗迹。此外,内部还可辨认出多个小区域,其界限往往是石墙分隔。而F2、F3作为F1的延伸,位于F1北侧。这组建筑形式与丁东和东天山的十分相似,说明这些畜牧生业的居住址结构和分布具有独自的特点,形式相通。例如,这些居址都存在很大的、多个隔间和扩间,除了少数主体建筑比较规整外,包括扩间在内的其他建筑经常是沿地势建造,不甚规整。这种结构、分区和选址等与本地的现代牧民的房屋的平面布局非常相似,即房址与牲畜圈结合紧密,甚至牲畜圈也出现建有带屋顶的房子。通过民族考古学的调查与分析,(100)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丛德新,贾伟明:《转场游牧的起源: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民族考古学的尝试》,第160~172页。并结合现代地理环境与古环境及古植物学等的研究结果,(101)Casparia G.,Betts A.,& Jia P.,The Bronze Age in the Western Tianshan,China:A new Model for Determining Seasonal Use of Site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14(2017),pp.12-20.丛德新,贾伟明:《史前生业模式的环境考古学观察——以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为例》,《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39卷第1期,第218~226页。邵孔兰,张健平,丛德新,贾伟明,崔安宁,吴乃琴:《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39卷第1期,第37~47页。可以初步推定在公元前17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博尔塔拉河中上游已经出现了季节性的转场游牧。
四 研究趋势和展望
史前社会生业模式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之一,直接涉及到对史前社会经济能力以及以此来支撑的社会组织、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在开展对考古遗址的年代、文化内涵、属性及与周邻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研究的同时,利用一切手段积极开展对生业模式的研究和探索,是目前欧亚草原史前游牧考古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1.史前生业模式的属性
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单一的生业模式几乎不见,多种生业模式并存的样态成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常态。如何准确地判定多种经营社会中的主要生业模式,即确定遗址的生业模式的属性是考古学研究的具体任务之一。在研究中我们常常用到如采集、狩(渔)猎、农业种植业和畜牧业等的相关概念,但是严格意义上讲,确定史前社会的生业模式的属性,需要用到许多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技术才能实现。简要的说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动物遗存(包括微生物)、植物遗存和除此之外的其他考古遗存的科技考古分析。采集和狩猎生业模式的考古遗存的判定看似直观,但要真正做到用证据来判定某个遗址是史前采集狩猎居民的遗留就不那么容易了。合理的判定要从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同位素食谱鉴定、工具分类、地层堆积、聚落形态、景观地貌等等的诸多不同的方面去寻找证据。(102)李永强:《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现状与思考》,《南方文物》 2018年第2期,第41~51页。徐紫瑾,陈胜前:《上山文化居址流动性分析:早期农业形态研究》,《南方文物》2019年第4期,第165~173页。
对欧亚草原现代从事传统经济活动的人们观察得知,一个家庭常常会既放牧也种植谷物,同时还兼具采集和狩(渔)猎活动。即使是在工业化之后的乡村中,那些我们认为专事农耕的农民,他们在传统经济活动中也在扮演多种角色,除了种庄稼之外也会饲养鸡、鸭、鹅、猪,甚至饲养羊、牛、马等家畜。类似的情况很可能在史前社会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准确地在考古实践中分析和认知这种多种经营的、但主导的生业属性仍然是畜牧、游牧的家庭和社会,从而对史前畜牧、游牧考古遗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今后史前游牧考古的重要课题。
2.开展考古学的游牧民族学调查
史前游牧考古学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对现存的游牧民族的考古民族学调查,以民族学的资料来帮助我们认知和阐释考古遗存。(103)郑君雷:《关于游牧性质遗存的判定标准及其相关问题——以夏至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为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2007年,第425~457页。如若我们自己对游牧本身的经济运作和游牧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居住形式等知之不多,就很难在支离破碎的考古遗存中发现游牧经济的证据,也很难对游牧遗存的作用、意义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史前游牧考古离不开对游牧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许多西方人类学家对包括中亚、西亚、非洲和美洲的现存游牧民族做过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研究资料,是史前游牧考古的重要参考。(104)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 217~224页。但是对于国内的史前游牧考古来说,更重要的是来自国内的民族学研究的参考。例如,对于新疆的史前游牧考古研究来说,陈祥军的《杨廷瑞“游牧论”文集》和《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民族学参考资料。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无论是国外的和国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大多是由人类学和民族学家完成的,而考古人类学家参与的、如澳大利亚的罗杰·克里布(105)Cribb R.,Nomads in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3-109.和美国的克劳迪娅·张(106)Chang C.,Pastoral Transhumance in the South Balkan as a Social Ideology:Ethno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ern Gree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3,(95),pp.687-703.Chang C.,Rethinking Prehistoric Central Asia Shepherds,Farmers,and Nomads.New York:Routledge.2018.的民族学研究并不多见。这些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往往缺失了考古学研究所必需的内容,像游牧居址(包括牲畜圈)的具体规划、建造及其使用过程,牧民是如何宰杀动物,如何烹饪,如何祭祀,游牧路线的具体确定,临时居址留下遗迹等等。
对于史前游牧考古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资料莫过于掌握其研究区域内的传统游牧经济的民族学调查成果,即以考古学研究为目的,并通过调查详细了解当地的传统游牧经济,和与这个传统游牧经济相关、相适应的自然资源状况,传统生产、生活甚至宗教祭祀、社会分工等方面的内容。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这种调查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史前游牧考古的另一个趋势。
3.史前游牧考古的全面、系统性研究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和技术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史前考古发现的局限在于发现的残缺不全和支离破碎。我们很少能以一个单独的方法和手段来明确回答考古学研究中的复杂问题。研判古代遗存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的属性等更要客观、全面。如同位素食谱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和牲畜的食物来源种类,但却不能直接判定当时人们的经济类型或生业模式。也就是说吃的是什么不等于种植什么或养殖什么,食物完全可以依靠交换获得。包括植物考古学的大植物种子的研究,如果不参考任何其他的考古学证据,仅仅根据浮选发现的种植谷物的种子,还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时存在谷物种植。也就是说,动物、植物考古学的单一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当时人们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和一些商品交换的种类,但并不能给出简单的、直接的生业模式的结论。要想确定这个遗址的生业模式,一定要参考其他一些发现,如农田、草场、牲畜圈等证据,并利用一些新的科技考古的手段,如土壤微量元素分析等来确定这些土壤是否曾用来种植谷物或放羊牲畜等等。未来,除了上述确定生业模式的研究之外,对整体游牧经济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是游牧考古的重要任务之一。例如,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除了肉食之外,奶制品在其食物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包括对奶酒、酥油、奶酪(107)Yang Y.,Shevchenko A.,Knaust A.,Abuduresule,I.,Li,W.,Hu,X.,...Shevchenko,A.,Proteomics Evidence for Kefir Dairy in Early Bronze Age Chin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45(2014),pp.178-186.等奶制品的起源(108)Hong C.,Jiang H.,Lu E.,Wu Y.,Guo L.,Xie Y.,...Yang Y.,Identification of Milk Component in Ancient Food Residue by Proteomics.PLoS One,2012,7(5),pp.1-7.洪川,蒋洪恩,杨益民,吕恩国,王昌燧:《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在古代牛奶残留物检测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1年第1期,第25~28页。以及作为牧业经济附属产品的毛纺织业、皮革业起源的研究也将是未来史前游牧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史前游牧文明的研究
综观史前游牧考古研究,确定生业模式仅是研究的第一步。而对于一个特定区域的、长期的史前生业模式的发展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革和游牧文明的研究,则是畜牧、游牧考古研究的纵深区域。对于一个特定地区的史前生业模式的发展与变化的认识,会帮助我们进一步对当时与生业模式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进程有更深刻的了解。通过对生业模式的考察,进一步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些可以引起生业模式变化的自然环境资源、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宗教或其他的原因,包括探求社会组织进化过程、游牧国家的建立等,从而为分析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的趋势和动因提供参考。
以往史前社会进化过程的理论源自对采集、狩(渔)猎经济向农业社会转变的研究,聚落考古的理论主要基于农业社会聚落形态的研究得出的,这些研究方法和理论,在牧业社会研究中的运用,需要在游牧考古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将应用于定居的、集中的、边界清晰的一户一居的农业村落的聚落考古理论应用于游动的、分散的、边界模糊的、一户多处居址的游牧聚落的研究,其本身就极具挑战性。(109)王建新:《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哈密东天山古伊州文化研究院编:《东天山文化研究》,第37~48页。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年第1期,第28~37页。霍巍:《西藏早期游牧文化聚落的考古学探索》,《考古》2013年第4期,第57~67页。以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对传统游牧聚落的分布形式进行考察,并与这些聚落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考察作比较,以此作为游牧社会聚落考古的参考,或许是将来游牧聚落考古的主要研究方法。

文中涉及欧亚主要遗址位置示意图(制图: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