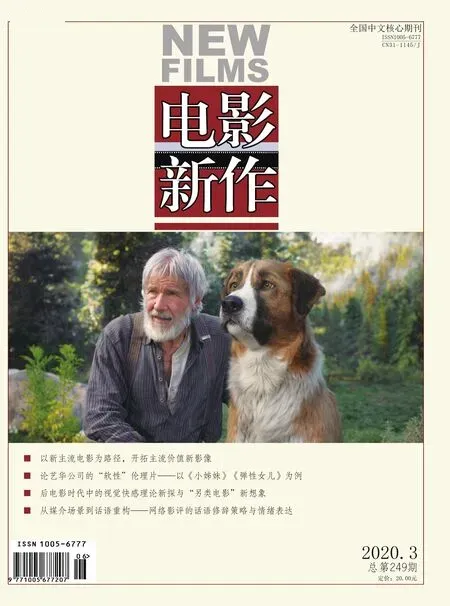异化生活、镜像式对话与心灵信码重构:《乔乔的异想世界》中的战争寓言与人性童话
2020-10-09李墨
李 墨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叙事为表达主体的作品序列,构成了当代欧美战争电影样态的重要谱系,譬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兵临城下》《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等巨制,都以成人个体的视点镜头去复现酷烈的战争记忆,集中呈现携带创伤美学表征的成长经验,从而生成以反思、避免战争为旨归的言说范式。而与上述的文本相比,2019年10月于美国本土上映的好莱坞战争片《乔乔的异想世界》,则是以孩童的视角复现了二战末期纳粹法西斯极权统治覆灭前夕的异化生活状态,通过聚焦男主人公,十岁的德国男孩乔乔·贝茨勒,从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预备团员到解救被戕害的犹太女孩艾尔莎的“觉醒者”的转变,展现出其在认知取向、情感投向、人生导向等维度上的成长经验获取过程,由此书写了携带精神创伤疗愈色彩、种族和解意味,以及本真心灵复归的战争寓言与人性童话。
一、异化生活:战争阴影下的非常态社会图景
在当代欧美战争电影的美学样态与主流叙事之中,二战背景之下的欧洲社会生活,更多地被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化的视觉情境:即狂热、畸形甚或失控的“全民战时”状态,取代了原有的部分相对平和的生活内容,使作为个体存在的民众,在镜头中被迫卷入战争泥淖,使既有的生活受制于威权、极权的掌控,显现出压抑、吊诡、荒谬的异化表征。影片《乔乔的异想世界》对二战末期德国纳粹统治覆灭前夕的战时非常态社会生活的描述,并未集中呈现战争场景的酷烈、惨痛,而是通过设置以乔乔为代表的部分德国儿童被裹挟入希特勒青年团这一“战时军事集训基地”、接受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教育、面临被驯化为狂热的战争机器的危机等具有背景指涉性的情节,同时借助呈现具有视觉标识性、隐喻指向的符号和场景来完成表达。
在影片的前半段叙事中,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训练活动、接受纳粹主义的灌输,成了乔乔这十岁儿童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在乔乔尚未进入希特勒青年团集训基地之前,影片用大量的以纳粹时期战时民众为呈现主体的黑白纪录片影像,进行了视觉渲染,营造了一种异于正常的社会生活经验的癫狂、怪诞乃至可怖的叙事情境,显现出了阴沉、诡异的战争阴影底色。

图1.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随着乔乔从家中奔跑而出、进入街道,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军事集训基地等更为开阔的社会空间之中,影片又设置了多种与纳粹法西斯建立直接联系的听觉、视觉意象和隐喻情节,进一步呈现战争情境下的非常态生活场景。
在影片对于乔乔穿过街道,来到集训基地途中的呈现上,镜头多次捕捉到室内外墙壁上的希特勒的画像、纳粹征兵海报等元素。这些指涉极权主义、纳粹主义的战争符号,同样强行介入民众的生活空间之中,在隐性层面上彰显着窥视、监控、规训等的权力意志,成为与舒缓、温和的常态生活相互区隔的畸形景观。
在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军事集训的过程之中,影片又设置了纳粹女军官怂恿乔乔等儿童“烧毁书本”这一颇具荒诞性的情节。在结束了对犹太人种族历史进行污名化的知识讲授之后,女教官拉姆告诉讲台下的希特勒青年团预备团员:“现在把东西都收拾好,孩子们,该去烧点书了”,孩童们即刻呈现出欢呼雀跃的兴奋状态。接着,影片以密集的慢镜头去展现包括乔乔在内的希特勒青年团预备团员们将书本抛掷入火中的场景:火光映照下的孩童们,纵情沉醉于焚烧书本的恣肆之中,似乎烧毁书本成为一种集体狂欢式的情绪宣泄与“被解放”的情感表达。而在这种颇具戏谑感、反叛性、颠覆性的美学表征之下,“烧毁书本”又在深层喻示着纳粹主义企图扭曲人格、践踏知识、毁灭文明的极端诉求。原本应当爱惜书本、渴求知识的儿童,却被有意引导塑造为背离正常学习生活的反智主义盲从者。
绞刑架这一在前现代欧洲长期存在的代表王权、国家暴力的惩罚机器,也在影片中成了德国纳粹政权屠戮反法西斯人士、维护其残暴统治的工具与权力符号。矗立于城市广场中的绞刑架,令在战争阴影笼罩之下的日常生活更添僵硬、冰冷、阴森之感。而乔乔的母亲罗茜最终也因为参与反纳粹活动而被处于绞刑,致使其原本残缺的家庭结构、长期渴求的完满的亲情生活归于彻底的破碎与幻灭。
影片正是通过呈现各类具备辨识度、隐性指涉性的感官符号,构筑起战争幽灵时刻在场的畸形景观,影片得以复现了纳粹极权统治之下的异化的生活样态,营造出了融合热烈、亢奋、沉闷、诡异等异质性图式的美学形态与叙事语境。也是在这种非常态的生活情境之下,乔乔在其善良、纯粹的孩童天性的驱动之下,跨越了纳粹设置的企图异化、奴化民众人格的精神藩篱,渐次完成了自我无蔽心灵的指认、本真人性价值的释放。
二、镜像式对话:“两个自我”的“真伪”博弈
镜像美学和自我想象源自那喀索斯临水自照这一古希腊神话原型,其后经由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演绎,逐步被赋予了主体位置和社会意义。在当代欧美战争电影的人物形塑、关系设置和情节推进等结构之中,镜像美学的表达策略,多采用以自我之外的他者去驱动目标对象的主体意识建构、成长经验的获取、社会身份指认等表现形式来完成。影片《乔乔的异想世界》对于镜像美学的表达,则基于童真的自我想象,设置了“两个自我”的人格意象,彼此对照,相互映衬,使乔乔与作为其“自我镜像”存在的“阿道夫”,构筑了携带超现实色彩的平行对话的美学场域,以及本真、澄明与异质杂陈并置的孩童的内心世界,由此呈现出“柔弱”与“狂热”、“善良”与“暴戾”、“纯真”与“癫狂”等自我精神场域之中的纷繁的人性光谱,从而显影“本真自我”与“虚幻自我”既相互区隔又反复交叠的深层博弈。
在影片中,作为乔乔的“另一个自我”的镜像而存在的“阿道夫”,除了在具象化的人格意义上指称着“阿道夫·希特勒”之外,更多负载着影响乔乔建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精神导引功能。譬如在乔乔与“阿道夫”的首次对话的情节之中,当面对镜中的自己自诉“青年团的周末训练会非常艰苦。乔乔最终还是说出:“阿道夫,我觉得我不行”。此时,早在一旁来回走动的“阿道夫”则立即回应:“你当然可以”,并继续对其进行鼓励:“你都十岁了,连鞋带都不会系。但你还是我认识的最棒的、最忠心的小纳粹。更别提你看起来有多帅气,所以,你要大胆走出去”。在这一情节设置之中,“阿道夫”这一自我镜像既标志着纳粹主义话语意志的在场,又扮演着促使乔乔建立生活自信的“鼓励者”与“引导者”的重要角色。
影片这一表达,投射出了乔乔柔弱而纯粹的性格特质,以及其作为孩童特有的渴求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又容易缺乏自信、需要得到他人理解与认同的微妙与复杂的群体心理,为其后乔乔从纳粹主义信仰者到“犹太女孩的拯救者”这一认知与身份的逐步转变,提供了逻辑转化的合理性支撑。其后,在因不忍杀死一只幼兔、而被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军事集训的其他人员嘲讽为“胆小的乔乔兔”之后,“阿道夫”也再次出现,并鼓励乔乔:“你就做一只兔子。小小的兔子可以战胜它所有的敌人。它勇敢、狡猾又坚强”,以鼓励其重新振作。所以,在前两次对话之中,“阿道夫”作为“激励者”与“引导者”的形象而存在,成为乔乔坚定人生信仰、守望社会理想、指认生存价值的“本真自我”的镜像。
影片关于镜像对话叙事的情节突转,发生在第三次对话。当乔乔无意中发现被其母收留的、藏匿在暗室里的犹太女孩艾尔莎,被其夺走佩刀、且遭到驱赶之后,“阿道夫”既向乔乔提出了诸如“谈判”“反向心理控制”等解决方案,并提醒乔乔“记住,一个犹太人住在你家墙里”。其后,随着与艾尔莎由剑拔弩张到趋于正常、平和的交流,“阿道夫”又告诫乔乔:“别让她禁锢你的想法。那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发生在一个德国人身上”,尽管对此进行了口头上的认同式的回应,实际上之后乔乔所展现出的认知、行为,却逐渐将艾尔莎指认为了“我的朋友”。而在明确告知艾尔莎“我们是朋友”之后,气急败坏的“阿道夫”则再次告诫乔乔:“不要像一颗可悲的沙子掉进了毫无价值的沙漠,要将轻重缓急拎拎清楚”,接着朝向洗手池啐口水、踢开默不作声的乔乔的身旁的椅子,然后忿忿而去。这一具备冲突张力的对话情节呈现,也喻示着“两个自我”开始在关于“雅利安人”与“犹太人”的“种族优劣与相处”等问题上产生了分裂,“真与伪”的冲突和对抗由此展开。
在最后一次对话的情节设置中,面对要“尽自己所能”去解救艾尔莎的乔乔,作困兽之斗、狼狈不堪的“阿道夫”试图让其重新佩戴纳粹袖章,并咬牙切齿地训诫他:“忘记那个恶心的犹太佬。回到我身边,这是你的归属”。乔乔在接过“阿道夫”抛过来的纳粹袖章之后却将之摔掷在地上,并说出:“滚出去,希特勒”,随后又将“阿道夫”踢出窗户。于是,在将作为“伪的自我”的镜像而存在的“阿道夫”从室内这一物质空间踢逐之后,乔乔也同时将“阿道夫·希特勒”所象征的纳粹主义观念驱逐出自己的精神场域,由此完成了自我主体意识与社会身份的清晰指认:一个柔弱却不怯懦、单纯却不盲从、拒绝做战争机器与纳粹覆亡陪葬品的“善良的十岁的德国男孩”。

图2.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剧照
三、心灵信码重构:情感创伤疗愈与种族裂隙缝合
从文学意蕴呈现、社会意义显现的维度看,一些兼具艺术特质与商业成功的当代欧美战争电影作品,普遍都具备侧重纪实美学呈现、强调主体意识询唤,以及思辨历史记忆等的人文母题与叙述样式,力图标志其高扬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价值言说,由此也在心灵维度上建构起了彰显现实超越性、理想投射性,以及召唤无蔽、本真人性复归的精神场域。影片《乔乔的异想世界》虽然具有较为轻快、舒缓、缺少密集冲突性的叙事基调与情节设置,并以相对完满的结局作为收尾。然而在这些显性的美学表征之下,实则负载着巨大的现实痛感与崇高美感的悲剧内核,无论是通过深刻思辨与痛切体悟渐次完成蜕变与成长的乔乔,抑或是被迫终日藏匿于无光暗室内、却始终坚守生存希望、捍卫民族尊严的犹太女孩艾尔莎,以及“热爱祖国、痛恨战争”的乔乔的母亲罗茜,还有厌倦了无义战争、挽救乔乔免遭盟军士兵枪杀的K上尉,都经历了情感碎裂抑或是生命陨灭的洗礼与荡涤,然后才生成了本真、无蔽的心灵信码,释放出能够疗愈情感创伤、弥合种族裂隙的精神驱动力,令他们涌动不止的生命经验完成汇合、交融,从而共同构成了战争暗影笼罩下的不灭、熠然的人性图谱。
与同类型的前文本相比,影片基于童真视阈去呈现人物完成情感创伤疗愈的过程,进而将心灵能指的维度延展至种族裂隙缝合的社会建构指向上。其中,对于乔乔与犹太女孩艾尔莎从相互对抗到渐次契合、最终建立动人友谊的展现,成了影片聚焦个体心灵蜕变这一成长叙事、弥合情感创伤疮痕以及消解种族主义话语的核心情节。从影片的叙述可知,由于被希特勒青年团内的其他人员嘲弄为“胆小的乔乔兔”,且其父亲也被污蔑为“胆小的逃兵”,乔乔因此被贴上了“胆怯”“懦弱”“逃兵的儿子”等歧视性标签,陷入了羞愤、懊恼、挫败等负面情绪的泥淖之中,因此也遭遇了由孩童向成人这一社会身份转化过程中,暂时未被他人接纳与认可的情感创伤。
对于乔乔而言,尽管作为“另一个自我”的镜像而存在的“阿道夫”,也会适时出现去鼓励、引导自己重建自信,然而其同时又总是试图以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去阻碍自己了解关于犹太种族的真实历史,扭曲与控制自己的情感取向,导致其依旧难以通过建立正常认知、辨识真实与虚伪、指认主体身份,去疗愈自身的情感创伤。而孩童无邪、纯粹的心性,则驱动乔乔通过不断加深与犹太女孩艾尔莎的接触、共处,以及独立思索,来分辨出原来“犹太人并不丑陋,也不是长着犄角、像蝙蝠一样的恶魔”,而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类”。于是,乔乔的社会认知经验与情感逻辑也渐次复归正常。同时,在一种朦胧的男女情爱的驱动之下,也激发了乔乔“作为男人”的责任担当意识与区分善恶、真伪的理性认知,促使其去保护、拯救随时可能被盖世太保戕害的犹太女孩艾尔莎。而在获得了艾尔莎的感谢、接纳之后,乔乔也不再是“胆小的乔乔兔”,而成了一个“男人”,他祛除了之前因被他人嘲笑、歧视、侮辱而产生的情感创伤经验,经由艾尔莎的认同再次指认了自我主体身份。
由于纳粹的屠戮与戕害,艾尔莎接连失去了父母、未婚夫和自由。在被乔乔的母亲罗茜收留之后,只能终日藏匿在其家中阁楼的暗室内,长期被恐惧、悲恸、忿恨、无助甚至绝望等情感创伤所困囿。随着乔乔无意闯入其所在的阁楼暗室这一封闭空间,以及与乔乔从相互敌视、对抗到彼此契合、最终成为朋友的情感经历,艾尔莎逐渐被乔乔善良、真挚、纯粹的本性所触动与感染,她不再称呼乔乔为“小纳粹”,而是将之视作“对自己真的很好的弟弟”。在乔乔的引导之下,艾尔莎走出了阁楼暗室,来到室外的街道上,重获自由的她开始舞动身体,积郁内心的情感创伤瘢痕也开始随之抖落。
在影片结尾,以双人中景对切镜头所呈现的乔乔与艾尔莎在晴明日光下的街道上相对起舞这一场景,通过“身体舒展”与“精神脱缚”这一双重指涉的修辞表达,喻示着从个体情感创伤疗愈到种族裂隙缝合的寄寓指涉。对于艾尔莎而言,纳粹暴政覆灭,生活恢复正常,种族迫害解除,她重新获取了个体自由,自身所具有的犹太人的种族身份也不再被污名化。而乔乔也同样获取了“自由”,他的情感、思想、行为均不再受制于纳粹主义的钳制,由“希特勒青年团预备成员”到“觉醒者”“犹太女孩拯救者”的蜕变,使其与艾尔莎成为情感同构、心灵互哺的生命共同体。于是,由纳粹所蓄意设置的所谓“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种族裂隙,也被舒缓曼妙,又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身体舞蹈与丰富的情感所填补,显现出本真自我回归、无蔽人性涌动的诗化心灵图景。
【注释】
①[中]路春艳,兰朵.不知所终的战争,不拘一格的讲述——后“9·11”时代美国战争电影类型的承继与新变[J].当代电影,2015,(8):146-150.
②[中]吴克燕.从《光明与阴霾——德日二战反思录》看多重对比视角下的二战反思[J].当代电视,2016,(3):65-68.
③[中]蒋宇辉.失真模拟与终极杀戮——晚近好莱坞战争电影中的后人类幽灵[J].电影艺术,2018,(1):61-67.
④[中]冯果,孟畅.电影创作的战争场面气氛营造:以《敦刻尔克》为例[J].电影新作,2019,(1):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