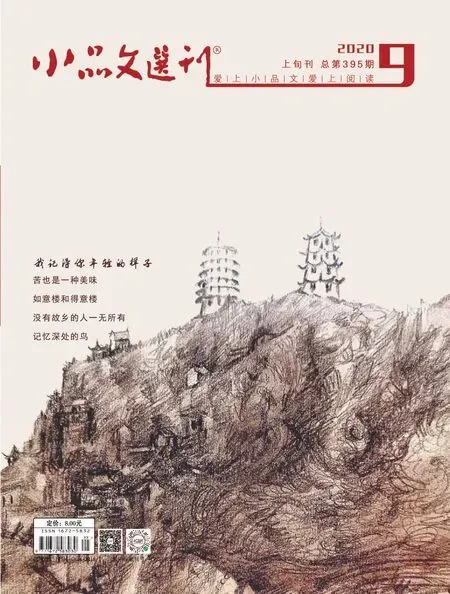时间与生命
2020-09-28阎连科
阎连科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
当然,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
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和枯干。
甚至以为让我写点有关作家和死亡、和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和写作的敬重。
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讯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讯息是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
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大概是最为醒目的链环。
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很有道理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
由此我就想到,对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
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
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
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和生命。
作品无法逃离时间而存在。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开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
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
二十世纪后,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具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如同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
似乎时间的存在,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从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它是单线还是多线,是曲线还是直线,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
总之,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与故事、人物、事件和细节剥离开来,独立地摆放或挂展。时间欲要清晰却变得更加模糊,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
而我愿意努力的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原。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有血有肉,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
在理顺之后,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
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能够呼吸的,富于生命的,能够感受而无法简单地抽出来评说晾晒的。我把时间看作小说的结构。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形式千变万化,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而结构丰富和奠定了故事,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样。
人的命运,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我们不能忽视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时间的意义。
时间在根本上左右着小说,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才会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其实就是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
有了头绪,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没有头绪,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
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才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
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被条理,可谓结构的开端。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
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
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
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喃喃自语道:“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