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仍然自愿走向反智
2020-09-22欧吉丧
欧吉丧

塔拉,成长于新旧世纪之交的美国爱达荷州,她生活在一个颇为奇怪的摩门教家庭中。
在这个家里,父母的七个子女都没有医疗记录。他们都由助产士接生,在家里出生。孩子们都没有上过学,因为父亲反对联邦政府的统治,决不会让公立学校给孩子们“洗脑”。塔拉从未看过电视、听过收音机,在7岁之前她甚至没有用过电话。
父亲不让孩子们上学,却带他们去主日学校,给他们读《圣经》并从中搜寻“启示”。无时无刻,父亲教育孩子以一种“末日降临”的紧张感准备生活。
这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的亲身成长经历。
我们似乎很难想象,现代的美国社会,仍然有人自觉自愿地过着一种异类的生活—不仅对现代科技文明表现出拒绝的姿态,还用几乎站不住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教育自己的后代。
可别把与世隔绝的宗教信徒的生活想象成世外桃源,韦斯特弗家族并非“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就是说,父亲是出于对政府的反抗,而选择过一种反对现代科技文明的生活,一旦选择了与主流相反的立场,连带的文明成果似乎注定了一并遭到反对的命运。
但這只是反智的一种形态而已。
互联网时代的反智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表达了对现代美国人思想状况的担忧。作者托马斯·尼尔科斯写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专家敬若神明,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们渐渐失去了原则,失去了有见识的争辩。
一种要命的错误观点在泛民主社会里蔓延开来: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这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法。现如今,任何一个人的笔记本电脑里的信息存储量,远比一座图书馆里的资料总量来得多。互联网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便利性,我们可以把繁复冗杂的海量信息发布上网,成为信息和资料的提供者;我们也可以机会均等地获取信息,只需点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成百万上千万的页面就链接到一张A4纸大小的窗口里。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根据作者塔拉·韦斯特弗的亲身成长经历而写
一种要命的错误观点在泛民主社会里蔓延开来: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因此,每个现代人都生出一种错觉:无限的知识就在这块电子屏里等着我,剩下的就是说服自己点击网页、移动鼠标,万事万物尽在掌握。
事实并非如此,机会均等的前提并不一定导向结果的均等。根据史特金定律“大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作品,质量都低……任何事物,90%都是垃圾”,网上的信息质量的总体水平堪忧。而能否筛选有效信息,使其内化为知识,就成了网上冲浪的关键。而筛选能力却是对逻辑思维能力、判断力及价值观的一次考验。
同样根据史特金定律,90%的网民都无法在“信息筛选”的考试中取得合格的成绩。这直接导致信息获取的结果与初衷呈相反态势,机会均等的前提导向结果的两极分化。
互联网的便利性让接受过系统训练、明白自己在找什么的人获取了更多知识,因为他们能判断信息的可信度,从而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但是这种便利性却让爱看热闹、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人吸收了更多激进、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并且,在吸收了不良信息之后,他们对自我的满意度不减反增,因为“我好像变得更有知识了”。
泛民主社会的反智
知识和信息相互混淆,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必然偏差。对专家的不信任背后,是对所有权威的蔑视,人们倾向于接受一劳永逸的方法和一锤定音的判断,但是科学研究永远是个过程而非结果。当专家的说法与人们的预期不相符时,甚至当专家无法对所有问题给出解答时,通过互联网的“放大”作用,民众对科学研究本身的信任度就断崖式下跌。
6月,美国传染病研究专家福奇对美国民众抗击新冠病毒的前景感到担忧,就算2020年年底新冠疫苗得以问世,美国仍然面临着无法控制疫情的窘境。这是因为在美国,很多持有反科学观点的人拒绝接种疫苗。
并非在这次疫情中美国人才表现出对科学的不信任,对科学的不信任是美国的民间传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成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当低。2013年,美国政府颁布《Healthy People 2020》文件,设定了肺炎球菌病、带状疱疹和乙肝三种疾病疫苗的注射目标,希望到2020年,年龄在65岁以上的群体要实现90%的注射率。但在当时,该群体中只有60%的人接种了肺炎球菌病疫苗,仅有25%的人接种了乙肝疫苗。
反智主义作为阻碍科学发展的力量的存在,是政治理念向科学领域不断渗透的恶果。如今的美国民众,很多人不理解民主其实是一种“政治平等”,即人人享有投票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愿意相信民主其实是“实际上的平等”,关于世间万物的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好的。
但是尖端的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是由一小撮的精英实现的。如果民众不承认每个人的天资、潜力、意志和机遇是不同的,那他们就会对极小部分人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持反对态度。
“不知者无畏”发展到反精英的泛民主社会中,就变成了“不知即真理”:无知的人和在某一领域“全知”的人,他们的社会价值是均等的,没有高低之分。
科技进步与反智兴起的相关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科技本身的反思中,来看一看反智主义的兴起是否有其事实依据。
在印刷时代到来时,人类的认知观第一次发生了剧变:不再需要把每一个世间现象、每一个事物细部具象化地记在脑子里。
在印刷时代,比起积累的知识,蒙田认为拥有一个健全的头脑更加重要,掌握图书在图书馆里摆放的位置、掌握进行思辨活动的逻辑方法,成了人们获取知识的直接途径。我们的知识因而从零散逐步变为一个整体,从松散的各个部分走向变为一个由逻辑和分类编织而成的紧密的综合之网。
当来到Z时代,有知识的人为我们所整理的东西,全都变成信息发布上网。《拇指一代》的作者米歇尔·塞尔,将Z时代人的认知模式等同于“被砍脑袋的人”。“既然知识已经放在那里,在眼前,客观的,搜集起来的,集体的,在线的,可任意获取的,被多次查看和检查过了的,拇指女孩也就没有必要再为涉猎知识而苦苦学习了。”
当我们把印刷时代辛苦建立起来的人的“认知力”赋予电脑主机和显示屏时,知识时代就走向了终结:记忆力因为信息变得唾手可得而不再是人生存的关键,人的理性能力再强,似乎也不可能强过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软件。电脑被看作是人脑的外接处理器,确认我们独特主体性的认知能力,如今化作了电脑—一个客体化的认知盒。
当脑袋不再属于人类自己,那我们还剩下什么?一条富有本能和直觉的脊柱神经,易怒、应激、简单的条件反射,和同类反复的不断增殖。当知识与获取之间的鸿沟可以被搜索弥合,我们就放弃了深度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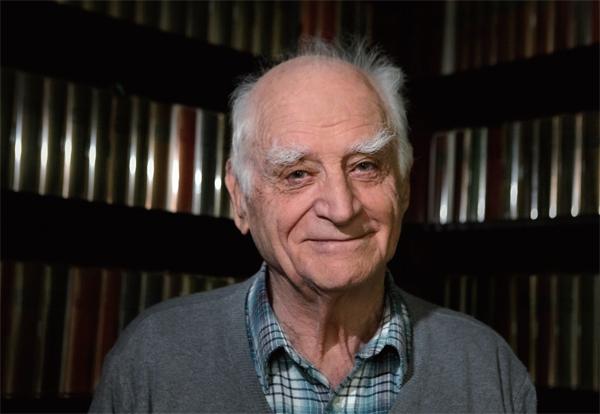
《拇指一代》的作者米歇尔·塞尔,将Z时代人的认知模式等同于“被砍脑袋的人”

對科学的不信任是美国的民间传统。
用搜索、浏览、复制和粘贴、抄袭拼凑起来的信息影印本,构筑了现代人全新的“知识观”,与扁平的景观社会具有同构性。这也就必然意味着知识权威的消失和反智观点的兴起。
在反智的一端是对观点均等的迷信,而在反智的另一端则是对生活压力常态化的反抗。科学技术的进步,总体上看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它就不必然让我们过得更自在了。
在早期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娱乐、工作和休息的时间被严格划分。19世纪,劳工运动兴起,罗伯特·欧文提出10小时工作制,几年后变成8小时工作制;劳工运动的口号是:8小时劳动,8小时休息,8小时睡眠。缩短工时的愿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依然被社会主流认可。
1972年,英国出版了一本科幻读物《2010:未来生活》,书中对人们未来的生活状态有着乐观的预期:到2010年,人们每周只用工作三天,玩四天。但是到了2011年,作者霍伊尔却对世界现状灰心了:“人类将会非常辛苦地工作。真是背道而驰,人们将一周工作七天。我现在非常悲观。”
科技的发展推动着生活不断走向便利,但享受便利就意味着要付出前所未料的代价。首先是生存压力的问题,更多的技术,更多的服务,更多的人口,更多张吃饭的嘴,意味着更多的工种和更多需要操心的事务。对于绝大多数工薪人士而言,业余时间变成了一个奢侈的词。
其次,本来社会进步应该带来更大的公平,但现实却是科技恰恰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不可逆转的自动化潮流,让劳动力变得更容易被取代,而互联网又创造了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利益最大化,科技的不透明性进而又导致了权力和知识的集中化,在不用担心吃不饱的现代社会,社会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
反智主义生发的土壤,是泛民主观点从政治向普罗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惰性,人们完全听不进不一致的声音,选择性地目盲耳聋。
反智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应激反应,在科技进步、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每个个体所能认知与掌握的知识,在互联网数据库的大背景下变得更有限、更狭窄,从而引发了对自我独特性的怀疑,和被科技取代的焦虑。
责任编辑何子维 hzw@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