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版本述略
2020-09-10陆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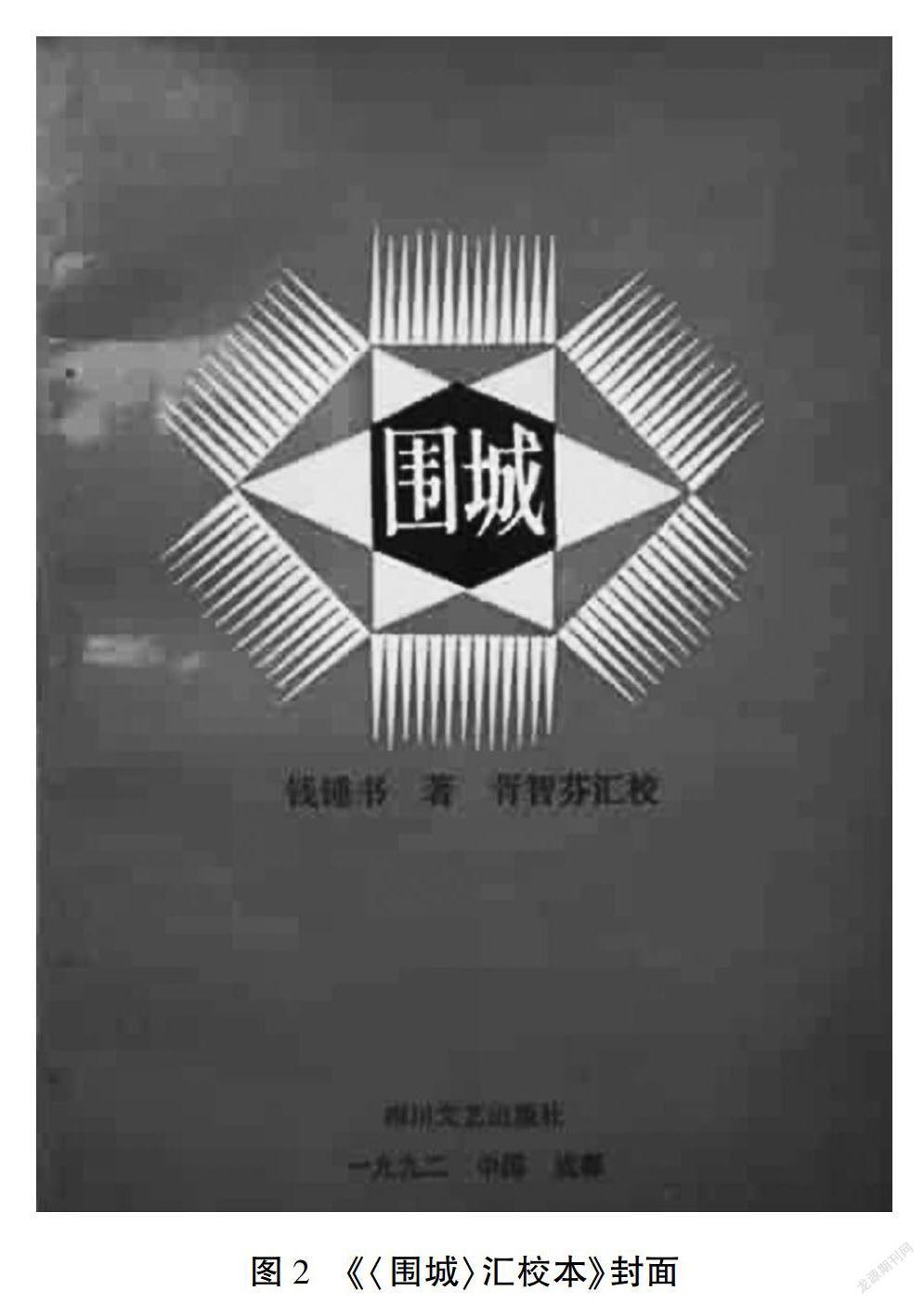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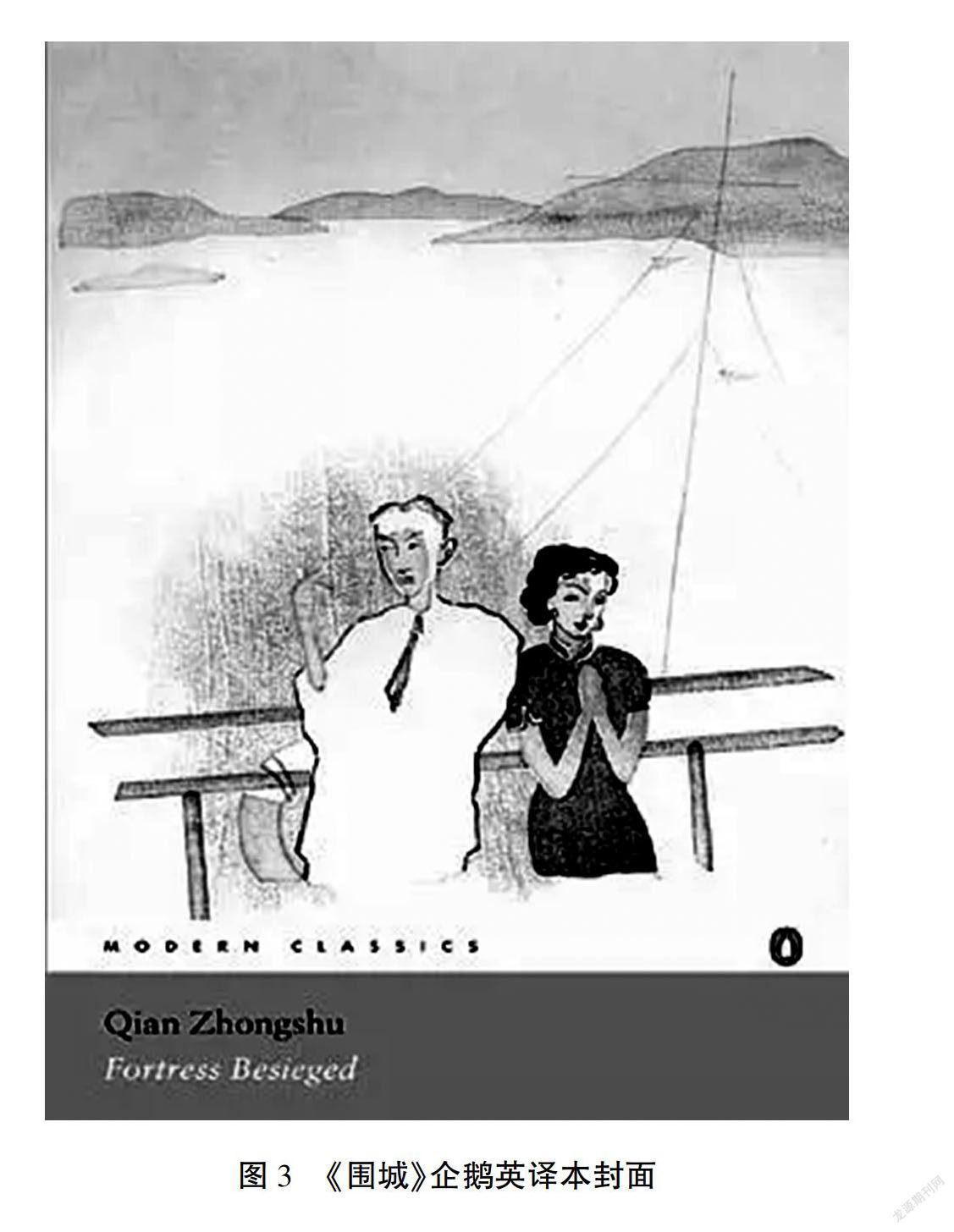
【摘要】《围城》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先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自1946年问世以来,曾先后以不同的版本与语种面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本文对《围城》在国内出版以及外文译本的版本情况加以梳理,以便读者了解其间的变迁情况。
【关键词】钱锺书 围城 版本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1944年初,蛰居上海的他开始动笔写作《围城》。据杨绛回忆,钱锺书创作《围城》很是认真严谨,“锱铢积累”般整整写了两年,至1946年初才完成。钱锺书曾指出,“围城”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一、初刊本和初版本
《围城》成书后,在文艺刊物《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文艺复兴》杂志是抗战胜利后由郑振铎与李健吾两位先生主编的一本大型文艺月刊,于1946年1月在上海创刊出版。《围城》先刊载于1946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后在第1卷第3至第6期、第2卷第1—2期和第4—6期上连载,分10期刊出,至1947年1月止。第2卷第3期断登一期,主要是悼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和钱锺书生病的缘故。这是《围城》首次与读者见面,学界一般将此称为初刊本。
《围城》面世后,当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和欢迎。1947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围城》,为赵家璧主编《晨光文学丛书》之第八种。这是《围城》最早的单行本,即小说的初版本。赵家璧的女儿曾回忆:“父亲看好它,决定把它编入新出版的《晨光文学丛书》中。书稿是由陈西禾帮助邀约成功,并交给父亲的。父亲与钱锺书先生好像没有经历一般图书出版前的协商谈判、签订出版合同等过程,也没有互相谋面。”赵修慧:《谁是〈围城〉首版的出版者》,《上海采风》2016年第2期。
《围城》初版本共有9章。卷首有作者《序》云:“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好朋友像柯灵、唐弢、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勖,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为惨酷的对照。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明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围城》初版本是32开本,479页,封面上有“晨光文学丛书”的字样。按照“晨光文学丛书”的惯例,书籍的第四页应是版权页,上面印有版次、印数、公司地址等信息。可能是为了节约开支,《围城》初版本却缺少了这一页。
“晨光文学丛书”封面设计沿用基本统一的格调,装帧形式趋向于色彩浓艳。每种只更换书名、颜色及右下方的一幅图片。比如丛书中徐志摩的《志摩日记》和老舍的《老牛破车》,右下方都用了作者的肖像画,巴金的《雾》则使用了一幅木刻。《围城》封面由丁聪设计作画。丁聪在有限的框架内,用十分简练和流利的线条,描画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半身肖像:男主角手拿烟斗,着春秋装束,闭目沉思,满面愁容;女主角头披长发,身着露肩旗袍,手护臂膀,似有怒状。方寸之间,男女主角背靠背,相互依撑,却又穿着季节各异的服饰,貌合神离,在婚姻的“围城”里苦苦挣扎。这是丁聪对《围城》另一形式的诠释。
据了解,丁聪在新中国成立后还为杨绛的著作设计过封面。三联书店出版的《干校六记》(1981年初版),其封面设计就出自丁聪手笔。封面背景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和深蓝的夜空,右侧是冬夜里树木枝杈萧疏的暗影,左下角远远地有几排从窗户漏出灯光的干校宿舍。杨绛所记的干校是在河南息縣,而封面给人的感觉却仿佛置身于东北的林海。《读书》1991年第3期(总第144期)发表了赵一凡《〈围城〉的讽喻与掌故》一文,文前有钱锺书头部漫画像,也是丁聪所作。画像笔调简洁明了,将钱锺书的聪明睿智、幽默风趣勾勒了出来,已成为钱锺书不多的经典画像之一。
1948年9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再版了《围城》,到1949年3月又出第三版。再版本对封面进行了修改。画面上是一男士坐在桌旁吸雪茄,一女士背对男士伏在柜前面壁沉思,仿佛也暗示着男女之间存在的矛盾和烦恼,与丁聪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据当今学者考证,此为英国印象派画家华尔德·理查·锡克特的油画作品《烦恼》。在第三版的扉页上,还有署名DG创作的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一身着博士装的男士、一裸女、一艘远洋客轮,博士帽、文凭、论文、洋装书和笔在周遭漫天乱飞。画面直白,但很容易让人想到《围城》中“克莱登大学”“赤裸裸的真理”等噱头。
新中国成立后,《围城》等文艺书籍逐渐远离大众阅读的视野。直至30余年后的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新版《围城》,13万册迅即售罄,后又多次印刷。不过,这一版的封面剔除了所有装饰,非常庄严古板地在灰绿色的纯色背景上题着“围城”二字,别无他物。
钱锺书写了《重印前记》,对这本书的重新排印感到意外和欣幸。钱锺书坦言:“《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添进去的。”他还说,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对照初版本,这一版所删去的文字是:“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至于删去的原因,钱锺书并未明言。或许当时除了郑西谛(振铎)已盖棺定论外,另外一些序言中提及的人物,其政治定论如何,他此时可能还不完全知悉。这当然只是猜测,其间的“隐情”还必须留待“钱学”专家去索隐。
二、国内的其他版本
1980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新版《围城》。以后的1981年9月、1983年8月、1985年8月连印三次。
钱锺书虽不悔少作,但对其中不太中意的地方在重版之时仍做些了修订。“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一些字句。”《围城》问世以来,经历过两次全面、系统的修改:从《文艺复兴》初刊本到晨光初版本是一次,主要是对内容多所痛删;从初版本到新一版又是一次,全然是精磨细琢,涉及典故、比喻、结构中的枝节、太露的描写、外语原文及音译等。学者金宏宇在他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一书中,对这次修改加以分析:“大致说来,初刊本多少带点‘肉书’的痕迹,初版本则减少了这些印象,定本差不多是‘洁本’了;初刊本、初版本用典和引外语过多不免有点像掉书袋,定本则通过删改、注释而成为便于阅读的普及本,初刊本、初版本保留着当时的国语特点,定本则体现了七十、八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初刊本误植太多,初版本校勘稍好,而定本则是精校本了。”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据研究者统计:“修改总计三千余处,涉及内容变动的一千余处。”
除了这两次修改,钱锺书此后还进行了三次小改。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8月第4次印刷的版本,成为《围城》的定本,后来1992年2月的第二版没有再改动。
新版《围城》发行后,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书。据统计,自1980年至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印刷和发行《围城》共计25印次,计134万余册。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亦十分轰动。
1991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胥智芬校注的《〈围城〉汇校本》。《汇校本》以初刊本为底本,将初版本、定本的修改之处汇集校勘,用页末加注释的形式予以说明。不过,钱锺书对此并不认可,称这是“一种变了花样的盗版”。享有《围城》专有出版权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围城〉汇校本》侵犯了本社和钱锺书的合法权益,与四川文艺出版社多次协商不成后对簿公堂。1993年6月2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场著作权纠纷案。一审判决四川文艺出版社败诉,被告不服上诉。1996年12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决。从《〈围城〉汇校本》出版算起,一场官司迁延了五年半之久。《〈围城〉汇校本》累计印行超过10万册,官司败诉后被禁绝。
2001年1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钱锺书集》,这是当时收集最为齐全的钱锺书创作与著述的汇编。对于出版文集,钱锺书起初并不持赞同态度。“他不愿意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杨绛语)《钱锺书集》初版于2001年,2007年9月再版。第二版《钱锺书集》从初版的10种13册改为10种10册,且都收了《围城》,第一版为简体字版,第二版改成繁体横排。
除此以外,国内的一些其他出版社也都出版过《围城》单行本,如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北方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等。漓江出版社还出版过伪托钱锺书之名的《围城之后》。
为了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了中英对照版,增加杨绛撰写的中文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英译本,收录杨绛作、凌原译的《记钱锺书与〈围城〉》汉英对照文。201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出版《围城》汉德双语版。华语教学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简写注音版的《围城》。新疆人民出版社在1991年10月出版了维吾尔文译本,译者为司马义力。
新版《围城》面世以后,迅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旋风,并影响到港台地区。早在1969年7月,香港基本书局就印行了《围城》,1978年再版。不过,这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盗印本”。此后,香港文教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分别于1981年和1996年出版《围城》。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推出的那一版是真正得到钱锺书授权的。因为在书中有对蒋介石讽刺之文字,所以《围城》在台湾地区一度被列为禁书。香港文教出版社在1981出版了台湾版《围城》,此后台湾地区出版热度不减,有金安出版社1982年版、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谷风出版社1987年版、辅新书局1987年版、全兴出版社1988年版、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大地出版社2007年版等诸多版本面世。台湾于1995年还发行有声图书。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卷首有钱锺书的授权书手迹,第二年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又出版了台北英文本。
三、外译本
《围城》问世之初即受到广泛关注,法国来华传教士秉善仁等人在《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中肯定钱锺书创作中的幽默艺术,但站在宗教立场上又否定小说的价值。1961年,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序幕,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参见余承法:《〈围城〉海外旅行70年》,《外语学刊》2018年第1期。。
英译本。珍妮·凯利1974年在香港《译丛》杂志上发表《围城》第一章的英译文。197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译本,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本为底本,由凯利、茅国权翻译。《译者序》指出:虽然钱锺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锺书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这部英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杰出学术著作”。198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英译本。2004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推出新的英译本,收入“新方向经典系列”。史景迁在《前言》中指出,《围城》“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作,即便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一部立于不败的作品”。在英国,企鹅出版社2004年出版英译本,收入“企鹅现代经典”,旗下的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年再版,企鹅出版社2006年再次印刷。
日译本。日本汉学家荒井健1956年开始接触《围城》,多次尝试翻译未果。1975年前后,他翻译《围城》前四章,连载于《飙风》杂志(1977—1981)。后来,他与学生中岛长文、中岛碧夫妇合译全本,由岩波书店1988年出版,列入专收外国文学名著的“岩波文库赤系列”,2002年再版。钱锺书应邀为日译本作序,相信原著“会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荒井健在“跋”中写道:该小说在日本最初以“被包围的城堡”为题名出现,日语中找不到“围城”的准确译法,只好选取作品的一个主题——“结婚”,因此将书名改译为“结婚狂诗曲”,并将直译的“围城”附在其后。荒井健还指出,《围城》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好作品”,像钱锺书“这样的雄才,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
俄译本。原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符·索罗金的《围城》俄译本,收入“中国文学文库”。俄译本首印5万册很快售罄,1989年再版时印刷10万册。《围城》俄译本对向苏俄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組织力量发行新版《围城》。
法译本。巴黎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1987年出版西尔维·塞尔望—许来伯和华人记者王鲁合译的《围城》法译本,收入“东亚丛书系列”,1997年再版。法国汉学家毕仰高在序中评价钱锺书是“中国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
德译本。1978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钱锺书流利的英语演讲为德国汉学家莫宜佳打开通向中国文化的大门,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她决心跟德籍华裔学者史仁仲合译《围城》,并跟钱锺书保持书信往来,到北京向他求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为底本,1988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2008年由慕尼黑施尔默—格拉夫出版社再版。《围城》德译本迅速跻身于畅销书之列,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最佳翻译奖。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高度评价道:“就其独一无二的构思和深度而言,《围城》堪称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最为讲究的、在此意义上也是无可逾越的标志。”
西译本。1992年,巴塞罗那阿纳格拉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围城》西班牙语译本,于1996年、2009年和2011年多次印刷。
韩译本。1993年,韩国的李惠兰将《围城》从英译本转译成韩语,书名为《黄河的晚霞》,由韩国皇帝出版社出版。1994年,吴允淑将《围城》直接从中文译成韩文《被包围的城》,由韩国实录出版社出版。
其他外文译本。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黎金坦的《围城》越南语译本,河内作家协会出版社2004年出版智闲王、山黎合译的另一译本。阿姆斯特丹雅典娜—波拉克和范根纳普出版社2013年出版荷兰汉学家林恪的译本。钱锺书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过《围城》的捷克语译本和波兰语译本,目前尚未搜集到具体信息。
四、《围城》版本演变之文化意义
《围城》的版本演变和文字修改,可谓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经典成长和打磨的典型个案。这部作品随着被文学史家叙述并广为人知,已经逐步成为一门显学。经过前面的梳理,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民国时期文学批评与作品修改之互动
钱锺书在《围城》晨光初版本的序言中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刻画中国知识分子众生相,考察复杂的人性,显然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重要意图。然而,《围城》与当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相比,“像”很多东西,又全然“不是”:既非纯粹京派或海派小说,也非源于延安经验的“革命文艺”;走了一条类似鲁迅批判国民性的路子,但曲折精彩的故事情节、类型化的知识分子题材,特别是令人发噱的笑料,似乎与批判之旨又有所偏离。
《围城》诞生之初的境况比较尴尬,正如美国学者胡志德所指出的那样:“钱的小说吸引了评论界的瞩目,也吸引了读者……但大部分评论多少带点敌意,表示出失望的看法:如此显著的才华,竟然倾注于这样琐屑平常的题材。”胡志德:《钱锺书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一些左翼的作家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方典(王元化)“从《文艺复兴》上读到”《围城》后,认为“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方典:《论香粉铺之类》,《横眉小辑》1948年第1期。。王元化另以“张羽”为笔名发表《从〈围城〉看钱锺书》,直言《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张羽:《从〈围城〉看钱锺书》,《同代人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无咎(巴人)则否定了小说立意,“他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段阶级斗争意义”无咎:《读〈围城〉》,《小说》1948年第1期。。忽视意识形态、关注婚恋问题、怜悯知识者的命运,也是批评者攻击《围城》的重要原因。熊昕(陈炜谟)断言:“如果以全体而论,这书依旧是失败的……《围城》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几乎嗅不到一丝丝火药气。作者甚至描写战争,也是带欣赏态度,仿佛完全置身事外。”熊昕:《我看〈围城〉》,《民讯》1949年第4期。署名林海的作者在《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1948年11月27日出版)上发文说:“它(《围城》)在过去一年里面所受的‘谴责’和‘赞美’,如果全体搜罗起来,大约总可编成一巨册的。”
由于《围城》从发表到初版的时间间隔很短,许多文章的批评对象无法断定是初刊本还是初版本。钱锺书显然注意到了这些批评,虽然并不认可,但在初版本中对原先连载的初刊本进行了一次完整的修订,主要对内容多所痛删。据统计,此次修改有770多处。在民国时期,文学批评虽在起步阶段,但对文学创作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围城》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过,文学批评在后来日益显现政治意识的特征。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该文是一次革命文艺对非革命文艺的“划线”。按照郭沫若的理解,非革命文艺包含两类:“黄色文艺”和“白色文艺”。“黄色文艺”指色情、武侠、侦探等类型文学,“白色文艺”指“表面无色、实际上杂色”的写作。按照这一批判标准,《围城》的“黄色文艺”和“白色文艺”嫌疑不可避免。新中国成立初,在全新的“当代文学”语境之下,《围城》更是成为反面教材受到一定的批评。钱锺书也很快结束小说创作,专心于学术。
(二)从《〈围城〉汇校本》侵权案看钱锺书对修改和校勘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的《〈围城〉汇校本》(以下简称《汇校本》)侵权案,是《围城》版本演变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汇校本》侵权案,如果撇开法律问题,则反映出当时文学界和出版界对于文本修改和版本校勘认知的不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汇校”通常是用于古籍整理的一项专门性工作。古代作品的流传本已进入公有领域,人们可以自由使用,而当代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却受法律保护。《汇校本》没有任何创作因素,只是变相使用了原作,理应承担侵权责任。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理由则是:新文学作品因为传播方式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语言规范和文学规范的改变以及作者在艺术完善方面的要求等诸多原因,版本的密度很大,版本的变异同样值得研究。《汇校本》逐字、逐句、逐标点符号地对各种不同异文一一比较,写出详细的注释文字,已经属于学术性质的史料成果。
钱锺书又持什么样的观点呢?据报道,钱锺书说:“什么汇校本呵,这是变相的盗版嘛。要使用我的作品,也不预先征求我的意见。再说,个别排校错误,或者疏漏之处,我在再版时已经改了过来,作者有对他自己作品的修改权呀,有什么必要特别将它标明出来呢。”由此可见,钱锺书对《汇校本》的出现极为不满。钱锺书有大量谈论文本修改问题的文字,但多半是从写作角度谈论而较少从校勘学角度去看修改。在《谈艺录·七四》中他对王安石爱改他人之作深加讽刺,说:“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而在《管锥编》中他又对删削他人之作而能“剥肤存液、点铁成金者”加以赞美。在手稿中对院本小说之遭删抹改窜而难见真面目又表示无奈:“使原作显本还真,其志则大,其事则难。犹洗铅华以见素质,而已深入腠理,揭代面以露真相,而已牢粘头目矣。”《钱锺书论学文选》第三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232页。
对修改自己的旧作,钱锺书也表示了一种矛盾的看法。他在《〈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说:“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紧接着说:“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又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掘史料工作表达了这样的心态:“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償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编:《钱钟书 杨绛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8—79页。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钱锺书对文字的修改持谨慎的态度,对研究者加诸自家作品的校勘持反对之观点。
在黄裳《珠还记幸》(修订本)收录的钱锺书所书信函中,他更是直言:“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屣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港商越在化外,非王法所及,只得听之;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惟衔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1982年3月)钱锺书对校勘之事如此深恶痛疾,《汇校本》侵权案的发生也就不能理解了。
(三)必须重视对版本演变的研究
《围城》是近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初刊本、初版本和定本这三个重要的版本。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围城》这三个版本的变化大致是一个从“肉”到“洁”、从丑化到美化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对于这三个版本,金宏宇认为这三个版本有不同的文本“本”性,折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写作风格参见金宏宇:《〈围城〉的修改与版本“本”性》,《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20世纪80年代,在对定本修改之时,钱锺书已经确立起“学者”的地位和身份,在文字、修辞的运用以及价值选择的倾向上更趋成熟,既有学者的眼光、智慧和抽象思考,也兼具小说的趣味性、故事性。但是否可以因此断定文本越改越好呢?并不一定。《围城》在修改过程中也存在“过改”与“错改”的。略举一例,在《围城》的后期修改中,将有些名词如“马将”改为“麻将”、“微生虫”改为“细菌”等,即属于“过改”,改掉了原作的时代气息。其实,《围城》的修改是有得有失的,许多人看重其“得”,往往会不见或少见其“失”。
对于《围城》这样的优秀作品,要研究修改和版本问题,让读者从它的修改史和版本变迁史中了解它的成长史以及接受史,让读者看到文学经典之作自身发展的轨迹和历程。目前有些文学史在讨论作品内容、形式时往往笼统叙述,并无精确的版本所指。其实,如果只提定本而不提初刊本、初版本,只写《围城》的成长而不写《围城》的诞生,那么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不全面的。反之亦然。
〔作者陆阳,文化学者〕
Introduction to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Versions of Fortress Besieged
Lu Yang
Abstract:Fortress Besieged is a Chinese novel written by Mr. Qian Zhongshu, a famous writer and scholar. It is also his sole long novel. The novel was firstly published in 1946, and has since then been publish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and languages, produc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ublishing of Fortress Besieged in China and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 novel so that the readers can have a glimpse of and comment on the changes.
Keywords:Qian Zhongshu, Fortress Besieged, ver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