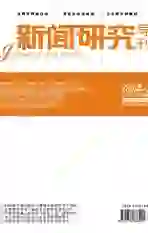纪录片的媒介语言运用
2020-09-10李梓毅
摘 要:焦波导演的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为拍摄点,驻扎当地373天,记录了杓峪村自2012年立春到隔年新春的“鸡毛蒜皮”:修路建广场、民告官、苹果丰收愁销路、婚嫁丧葬……他试图以该村为切入口,真实展现中国农村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本文从符号学、叙事学角度分析并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乡村里的中国》;纪录片;媒介语言;符号学;叙事分析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2-0115-02
《乡村里的中国》的总导演焦波在《我拍<乡村里的中国>》一文中说道:“纪录片的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观察、判断,在每天发生的纷繁的事情中抓取需要的东西。”[1]该片以“文人庄稼汉”杜深忠、操心村官张自恩、单亲大学生杜滨才3户为主要对象,讲述该村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琐碎又现实的故事。尽管是真实记录,但纪录片的内容是主体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它只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带着主题的社会倾向、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等,因此,纪录片既是真实的,也是建构的。[2]通过有选择性的呈现带有象征意义的视听语言、选取特定的叙事方式,《乡村里的中国》在真实的基础上完成了意义的建构。
一、声画共振,完成符号意义生产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会有其自身的传播语言系统,纪录片的传播符号则是画面和声音,因此,纪录片也被称为声画艺术,这其中画面语言是纪录片传播的基础。[2]
《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纪录片,一开场便是冰雪消融的立春,土墙上用红漆刷下的大字“春”、热闹非凡的“咬春”仪式无不给人浓厚的乡村气息。按索绪尔符号学理论来看,迎春的喜悦是“春”字等符号的能指,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则是其所指。在杓峪村,苹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年好不好过全看苹果收成如何。从家家户户话不离果、寒露收成时吃住都在果园可知苹果对村民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苹果就是未来的粮食。可见,在农村,靠天地吃饭依旧是不变的规则。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是生活的依靠,村里唯一一个看《新闻联播》的“文人庄稼汉”杜深忠却说,“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一语中的,土地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的羁绊。
片中,丰富的听觉语言加深了对乡村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刻画。“咬春”时的铜锣声、播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用来通知育龄妇女体检的广播声、沂蒙山小调以及前来凭吊外出打工摔死的张自军的吊丧声……无不在告诉受众,这是中国沂蒙山脚下保留诸多传统、较为落后的村庄。
片中还运用到文字码加注主要人物个人介绍以及二十四节气时间。文字的编码是信息最直接的传递手段,为受众理清片中人物关系和时间背景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视听语言相结合,达到声画共振以完成符号意义的生产,使得纪录片从感官到意识给人传输一副生动且深刻的乡村画卷。
二、交叉叙事,讲述乡村小人物的故事
纪录片不像电影,没有精心设计的铺垫,没有刻意安排的冲突,而是更加贴近事实的记录。《乡村里的中国》采用“真实电影”的语言风格,这一风格以现场原始音响作为主要表意元素,用直接展现不受干预的事实来增强真实的效果。[3]
全片无一句解说词,秉持原生态的形式风格,全靠人物对话和互动、场景和时间的切换来推进故事。[4]与此同时,该片采用交叉叙事手法,变换着讲述3户主要对象这一年的经历,仅仅3户却拉扯出一整个村庄。巧的是,到了片尾也是年初,3家人的故事也各告一段落:杜深忠嫁女,临行前给15岁便出来打工的女儿塞了两捆现金;单亲大学生杜滨才终于肯见因父亲患精神病而改嫁的母亲,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在母亲怀里痛哭,联欢会上献唱《父亲》给爸爸;被查账的基层干部张自恩,年初还是挨家挨户慰问,年薪一千九的他赚了一肚子酒和一把辛酸泪。这些在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中交错出现,无须一句旁白加注,老百姓自己用最接地气的话一一道来。
为了防止从头到尾未经设计的对白给受众带来观看疲劳和枯燥感,《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作为隔断。这一结构方式也使片子在没有解说词的情况下能保持流畅,而乡村地区的春种秋收本就根据节气行事,因此这一叙事安排再合适不过。
这种内涵故事型叙事,讲述着生活本身没有很强事件性和情节性的故事,但为了表达某种主题内涵的需要,它将这些本来零碎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乡村都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
三、纪实呈现,乡村里的中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2018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为40.42%。[5]《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故事,讲述的却是中国5亿农民的生活。总导演焦波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当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诚意去记录他的时候,就会有特别意外的收获。”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意识形态是个人和他们真实生存情况的想象关系的再现。[6]而《乡村里的中国》所要传达的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力,有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城市急剧发展,“市民”越来越多,占据的注意力也多,而“村民”却常被隐匿,《乡村里的中国》呼吁人们关注乡村发展,关注个体发展,因此它把中国的乡村搬上了荧幕。
村民张自军外出打工摔死,下葬时,儿子在边上问:这是爸爸的家吗?门怎么那么小?与此同时,家里却为了抚恤金争吵着。杜深忠一语中的,“拿人肉换猪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没有人不想过上好日子,可好日子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村里老树被刨,载去城里搞绿化,杜深忠说这是“剜大腿的肉贴脸上”。孩子们的乐趣不是手机游戏和游乐场,而是抓蟋蟀、找蝎子,冬天里有人拉拽着跑就是滑冰,很简单,却也悬殊。村里修广场“杀”了张家门口的树,他马上要村支书给树磕头,双方相互嚷嚷恶语相对,甚至闹出棍棒打人和药死树苗的事。在农村,如此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依旧普遍,少有人能遇事平和协商。种种矛盾下展现的是最为真实的乡村,也是真实的中国。而最为矛盾的莫过于杜深忠这样的存在,他打破了人们对农民的刻板印象,拉二胡弹琵琶、写毛笔字出口成章,这个村里唯一一个看《新闻联播》的人和他一身泥土、黑褶子的搭配尽显违和感。在他看来,“人得吃饭得活着,精神也得吃饭也得活着”。他老婆却说:“人没钱,你再好也白搭。现在只要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胚。”这再现实不过,也是悲凉不已。可见,农民有迫切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渴望精神文化需求能得到保障,而这一点目前还是欠缺的。
以人为本的口号从不缺宣传,但实实在在落到每个个体身上,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纪录片不像电影、电视剧有诸多设计,它是靠导演、摄像师敏锐的观察捕捉细节来进行最贴近真实的呈现。《乡村里的中国》反映的是一个靠山而居的村落,是一群淳朴真实的农民,他们是中国乡村的缩影,也是中国农民的写实。该片一直用中景和特写表现,到最后巧用俯瞰全景的画面作结,意在表明,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版图上渺小的一点,但是它又代表着千千万万个村落,代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个杓峪村便足以成为当时农村生活的标本。而要了解真实全面的农村,就要切切实实到黄土地上走一遭,要了解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那就到农村去吧。
参考文献:
[1] 焦波.我拍《乡村里的中国》[J].党建,2016(03):57-58.
[2] 范文德.真实与建构——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170.
[3] 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3.
[4] 郭巍.浅议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从《乡村里的中国》到《小岗纪事》[J].科技传播,2019,11(18):150-151.
[5] 董峻,杨静. 70年,中国农民占比少了五成[N].新华每日电讯,2019-09-04.
[6] 李彬,王君超.媒介二十五讲[M].北京:清華大学出版社,2004:68.
作者简介:李梓毅(1998—),女,广东汕头人,本科,研究方向: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