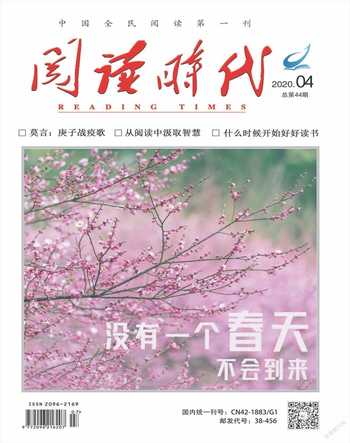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2020-09-10陈平原
陈平原
01
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得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
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
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02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夏曾佑说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经典。
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03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
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
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
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饶宗颐先生曾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
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
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響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04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来,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传统。
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05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
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结语。
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
合起来,就这样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责编:胡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