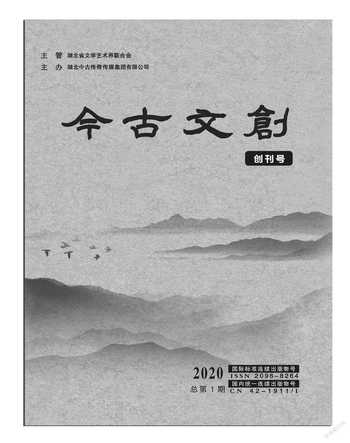从“好手琴者”看《燕丹子》的语言艺术
2020-09-10张冲
张冲
摘 要: 《燕丹子》成功塑造了荆轲这一经典艺术形象,而个性化语言的表现是荆轲形象塑造得以成功的关键。荆轲个性化语言中,以“好手琴者”一语最为关键,因为它埋下了三条隐线:一是荆轲“不解音”而被秦王“乞听琴声而死”所骗、致使刺秦失败;二是此语出现的场景乃太子丹为樊於期所设的酒会上,荆轲与会,故樊於期是文中第一次出现在荆轲的视线之内,“好手”或为荆轲赞樊於期之首;三是从太子丹对“好手琴者”的第一反应,可见出君臣之间并不默契。这三条隐线均与刺秦相关,从而不难窥知“好手琴者”一语的惊心动魄之功。
关键词: 《燕丹子》;荆轲;琴声;美人手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1-0059-05
《燕丹子》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篇,以其高妙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燕太子丹为报仇派荆轲刺秦的始末,其中荆轲的形象塑造,最为经典。
而通过个性化语言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是该文尤可称道者。荆轲诸多言语中,以“好手琴者”一语,最具惊心动魄之功,它把荆轲的性格、情性和命运等全部点带出来,真可谓字字千钧。
此语所隐含的信息是极其丰富微妙的,最主要的信息包含以下三个方面:荆轲被太子丹误读为好色者,点出二人并无默契之感,为太子丹催促荆轲以秦舞阳作为副手赴秦之必然;“美人能琴”荆轲“但爱其手”,点出荆轲非知音者。此细节埋下刺秦失败伏笔;“断美人手”出现的场景乃太子丹为樊於期而设的酒会,为荆轲劝说樊於期献出首级埋下伏笔。
这三个方面涉及到与刺秦相关的三个主要人物:太子丹、荆轲与樊於期,从中不难窥知“好手琴者”一语在文中“四两拨千斤”的妙用,亦可借此一语领略《燕丹子》卓越的语言艺术。
一、荆轲被太子丹误读
“好手琴者”一语,出现的具体语境为:秦国樊於期将军得罪于秦,逃到燕国投奔太子丹。太子丹为其置酒华阳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当荆轲夸赞“能琴”“美人好手”时,太子误以为荆轲是喜“美人”之色,故“即进之。”
太子之所以如此理解,显然他把荆轲一般化,甚至于庸众化了,因为女子之“手”,自“執子之手,与子偕老” 以来,就蕴含了男女情爱在里面。
男子往往借赞美女子之手曲传欲“携手”之情;再者,“手”可弄妆、可弄小弦、可采荇菜卷耳、可拈花、可添香、可弄团扇、可绣鸳鸯等,故使得女子之“手”,成了善在男子“痒处挠”之“撩拨”情思之物。
故在男子眼里心中笔下风情万种,是情色之思的代言物。明乎此,就会明白何以太子丹闻荆轲赞美“琴者”乃“好手”时,不假思索就以“美人”奉赠之举。
荆轲之言意在“手”,太子之解则在“色”,君臣之间相违如此,自然谈不上“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为何时赴秦且选谁作荆轲副手的关键问题上,二人产生龃龉埋下伏笔。
除了太子丹把荆轲庸众化即太子以天下一般男子好色之行来看待、对待荆轲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太子丹并没有真正了解他将委以重任的荆轲,这显示出二人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膜。
把荆轲一般化、庸众化,便暗示着实际上太子丹并没有真正尊重荆轲自己的意志;没有把荆轲作为一个独特的神勇者来对待。只是在声色口腹等物质享受和感官满足上努力去营造自己重士、善待士的“士”形象而已。
他只是在以最简单的方式演绎着“与荆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的礼贤下士的太子形象:看似惟荆轲之意是从,实际上都是重的形式。
太子丹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鞠武劝他联合别国抗秦时,他“睡卧不听”;田光分析他门下客“无所用者”之言,他也完全当成耳旁风;荆轲欲得“督亢地图”“樊於期首”的话也以“不忍”予以拒绝。
另外,太子丹性格中的多疑,亦是致命的弱点:他因怕田光泄刺秦之谋而“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此语害得田光羞愤自尽;荆轲待刺秦同行者未动身,太子丹竟“恐轲悔”,仍是用人而疑最典型的表现。
正是基于太子丹多疑且自以为是的性格和待人处世特点,所以他根本不会去细致地了解荆轲。他太习惯于把人简单化了,以为“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和断“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就足够“信于知己”了。
而荆轲的志向,则是“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显而易见荆轲刺秦绝非仅为太子丹报仇而已,故他必欲得一堪用之人作为副手才会动身。
荆轲欲赴秦庭刺杀秦王,是怀着功成、身返之志的,这自然需得堪用者为副庶几可望成功。荆轲当一如田光,已然深知秦舞阳等的不堪为用,故当太子丹“欲先遣武阳”时,荆轲发怒,谓:“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显然,荆轲不欲与“竖子”武阳同行,深知如此则“往而不返”。
荆轲对太子丹言之回应,点出荆轲亦具知人之明。正是因为深具知人之明,故其深知太子丹之为人;深知太子丹之为人,故知太子丹已无耐心让他等到得力助手。
太子丹在一语害死田光之后,当明了如田光、荆轲之士,是“耻以丈夫而不见信”的。前事之鉴不远,又因“恐轲悔”拿舞阳进行激将:“居五月,太子恐轲悔,见轲曰:‘今秦已破赵国,兵临燕,事已迫急……今欲先遣武阳,何如?’”
毫无疑问,荆轲会为了维护自己“士”的尊严,明知不可而为之——别无选择地只能以舞阳作为副手“不择日而发”。而到秦庭后舞阳的表现,则毫无疑问地预示了刺秦的必败:
“西入秦,至咸阳……轲奉於期首,武阳奉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轲顾武阳前,谢曰:‘北藩蕃蛮夷之鄙人,未见天子,愿陛下少假借之,使得毕事于前。’秦王曰:‘轲起,督亢图进之。’”
秦舞阳果如田光所言,仅仅是“骨勇之人,怒而面白”“无可用”。关键时刻,“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而让秦王生疑、不得随荆轲至殿。荆轲缺失了唯一的助手致使“奇功不成”,而这一切都是在条件不成熟时、太子丹催促荆轲行动的必然结果。
“好手琴者”被太子丹误读,不仅仅是点出太子丹对荆轲的不了解,更暗示着君臣之间全无默契,这才是刺秦失败的必然因素所在。
二、 断美人手与断樊於期首
太子丹断美人手,盛以玉槃奉荆轲,荆轲了无替美人痛惜之颜色言语,仅仅把这看成是太子丹的“厚遇”,这正是田光评价他的“不拘小节,欲立大功”之语。
显然美人断手之痛,属于“小节”类,是荆轲向来不在意的细节。这一点和杀千里马而食其肝是一脉相承的,在荆轲眼里,“千里马”和“美人”丝毫没有生命的存在意义,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是“好手”尚可爱、“肝美”尚可食。
而这些骇人听闻之举,正是荆轲所追求的“超世之行”。“千里马”和“美人”,绝非易得且可爱者。而荆轲于此二者,毫无怜爱痛惜之情,则其心如铁石自可知。
惟其如此,方能做到忘情即“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他对一切物、人的生命均漠然视之,对他自己的生命亦复如是。
他曾对田光言:“有鄙志;尝谓心向意等投身不顾;情有乖异,一毛不拔”,他考验太子丹是否与自己属于“心向意投”者的手法,是“黄金投龜,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太子丹对“金”“千里马”和“美人”并无一丝一毫的悭吝,被荆轲误读为“知己”者。
其实太子丹需要的是能帮他复仇的勇士,只要可以刺秦,太子丹绝对都会如此“厚遇”。所以荆轲之于太子丹,完全不是荆轲自以为的那样。太子丹需要刺秦报仇灭耻,根本不会在意行刺者是否可以生还;这正如荆轲为了试探太子丹,而根本不会考虑千里马和姬人生命一样。太子丹以荆轲为复仇之利器,而荆轲拿太子丹为“心向意投”者。
故太子丹会完全不考虑荆轲的安危催促他赶快行动,而荆轲则为报答太子丹的“厚遇”之恩,定以不辱使命为志。为此,他需要为避秦祸至燕的樊於期之“首”:
“于是轲潜见樊於期,曰:‘闻将军得罪于秦,父母妻子皆见焚烧,求将军邑万户、金千斤。轲为将军痛之。今有一言,除将军之辱,解燕国之耻,将军岂有意乎?’ 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饮泪,不知所出。荆君幸教,愿闻命矣!’ 轲曰:‘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讐,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 於期起,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刭,头坠背后,两目不瞑。”
荆轲与樊於期的这次会面,是在华阳台酒会断美人手之后。在酒会的“后日”,荆轲就向太子丹表达了“得樊於期首”以近秦王的想法。可见,华阳酒会是荆轲在以“美人手”试探太子丹能否舍得“樊於期首”,是在投石问路。而太子丹能做到“即断美人手”,却不能做到“即断於期首”:“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
这与太子丹平生最在意所“遇”之厚薄有着内在联系:秦王“遇”丹无礼,使得太子丹切齿于秦,不惜一切代价而必欲报之。若“卖”樊於期,显而易见自己比秦王“遇”己“无礼”尤甚。他“厚遇”的荆轲,竟然提出要他另一个“厚遇”者——樊於期的人头,而这个人还是和他一样切齿于秦王的同仇敌忾者,太子丹除了“不忍”,另有怕“必令诸侯指以为笑”的隐衷。
而荆轲是一个欲立大功不拘小节者,故他可以置太子丹之感受于不顾、更可以置樊於期生命于不顾这些“小节”,“默然不应”太子丹的细节描写表现出荆轲必欲得樊於期首之意已决,其斩截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他司空见惯了鲜活的生命在他眼前戛然而止:“(田光)向轲吞舌而死”、千里马被杀取肝、弹琴美人断手等惨烈的场景一再在小说中出现,正是凸显荆轲的“勇士”“英雄”和“烈士”的心如铁石。无所留恋无所爱,方可决绝了断非常之事。
如果说,田光等生命消逝在他眼前而他只是一个冷眼旁观者的话,樊於期自断其首则是荆轲直接促成的,其场景之悲壮惨烈让人发指。“潜见樊於期”的一番说辞,字字诚恳,句句切心。樊於期是第一个听到荆轲刺秦全盘计划者,而他的人头是这个计划能否得到执行的关键物件。荆轲把“国事”全盘泄露给一个逃亡到燕国的秦国罪犯,比太子丹泄露“国事”于田光更具潜在的危险性。
为了报答太子丹的收留且“厚遇”之恩,田光就应该是樊於期必须效法的榜样,更何况荆轲此举也能为自己报仇雪恨。樊於期慨然自刭,“头垂背后,两目不瞑”的细节,不仅点出樊於期的报仇心切、视死如归的勇烈;而且点出樊於期深明荆轲此行是抱了必得其首之志的:要么自我了断,要么荆轲“替”他了断。某种程度上讲,华阳酒会上的“即断美人手”,实际是此刻“即断樊於期首”的预演。
华阳台酒会,本是太子丹为樊於期而设,樊於期当是酒会的主角,但整个酒会的场景中,他并无只字片言。话语的被取消,意味着主体性的被取消。没有了主体性的樊於期,只能如“能琴”之“美人”一样,成为被主宰、被支配者。“美人”能被“即断手”,则樊於期亦能被“即断首”。
名义上为主角的樊於期在此酒会场景中唯一也是关键的功用,“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使得荆轲有赞美人“好手琴者”之语。此语暗示了荆轲一见於期而得计谋的茅塞顿开之感:投奔太子丹三年,尚苦于无计可近身秦王;秦王此时正重赏购求於期之首:“求将军,邑万户,金千斤”,樊於期首如此贵重,自然是可以用作近身秦王的最好诱饵,故荆轲一见樊於期则如醍醐灌顶般心机开窍,竟不由自主失声喊出 “好首,期者!”樊於期的出现,他看到了刺秦的希望:秦王欲得樊於期首,故荆轲欲得樊於期首。
他本为赞樊於期首的语言“好手,期者”,或因听琴的场合而被太子丹误听误解为“好首,琴者”。因为这两句四字的声母完全相同,明乎此,才会明白何以此酒会后的“后曰”荆轲即向太子丹讲出欲得樊於期首以近秦王之谋。
三、秦王为荆轲误读
欣赏琴,荆轲不赞琴声却赞美弹琴人之“手”,这一语点出荆轲乃“不解音”者,“听琴”而不解琴,这个场景点出荆轲在没有做到“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就贸然前往秦国采取行动:他的行刺对象即《燕丹子》中的秦王,是一个“解音者”;更是一个不讲信义者。从荆轲对樊於期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荆轲多么天真幼稚,他把秦王看成了如他和田光一类的“士”,这一点荆轲和太子丹一样,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把高深的人肤浅化了、把特殊的人寻常化了。他们要对付的是欲扫清六合、吞并天下的秦王,而竟欲侥幸成功且事前没有系统周密的方案,当然备用方案更是谈不上。小说一开始就围绕着秦王“无礼”于太子丹一事,交代出秦王乃一毫无信义可言之人: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
对待毫无信义可言的秦王,荆轲则从来是以自己信士的习惯性思维去思考如何刺秦这件事的,即仍站在自己“士”的道德高度、从道德制高点上来谴责秦王“负燕之罪”“责以(樊)将军之仇”。他没有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而是扮演了一个道德裁判者的角色。道德要求诚实守信、仁爱守礼,是宜彰显而不必隐秘的;而政治斗争则是波谲云诡、讲究机谋的,是宜隐秘而绝不可彰显的。
用显性的道德标准去要求隐性的政治行为,显然这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他以道德的标准谴责秦王,亦如是在对牛弹琴一般。他在秦庭上确实做到了他答应樊於期的话,而这也正是他的政治幼稚之處。他以为秦王肯定会悔过、会觉得自己死是罪有应得且会乖乖等死以谢罪,所以当秦王“乞听琴声而死”时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这个细节点出荆轲是多么不了解他的对手,所以竟然丝毫没有察觉这只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对刺秦这件事的定位是不准确的,所以根本也不会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这一突发状况该如何应对,因为秦王这个要求本来就没有在他的行动预计之内。事发仓促却不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且对秦王之语丝毫没有产生警觉,显而易见不是秦王的对手:秦王见秦舞阳色变而“怪”,在荆轲曲为回护后仍然高度警觉、即刻终止了秦舞阳的脚步。这显示出秦王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与老辣,也点出秦王对秦舞阳少年杀人一事信息的掌控,这才是知己知彼。
秦王与荆轲面对面且受制于荆轲,竟然从容要求“听琴声而死”,异于常人的沉着表现竟然引不起荆轲对对手诡诈的丝毫防范意识与戒备心理,再次凸显荆轲刺秦根本没有做到周密详备、甚至连最基本的对秦王的了解都没有做到,一味地高自期许。既不知己,焉能知人?这正与华阳台“听琴”一节遥相呼应。“不解音”的荆轲,答应了“解音”的秦王“听琴声而死”的要求: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
秦王的机变与荆轲的教条形成鲜明的对照:赴秦之前对樊於期描述的“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的场景完全没有因为秦舞阳突发的状况而进行丝毫的调整。在事前不清楚秦王衣着质地情况下所拟的“左手把其袖”的“规定动作”在已清楚秦王所着乃“罗縠单衣”时毫不改变;明知自己“不解音”竟答应“解音”之秦王听“琴声而死”的要求,并且丝毫不提防姬人之“琴声”。这从“好手琴者”的赞叹已经表明荆轲向来对“琴声”是听而不闻的。
更可怕的是出于习惯,他或许同样会对秦王鼓琴姬人之“手”产生了兴趣而被转移了注意力,甚至进而联想起了被燕太子丹所断的弹琴美人之“好手”,否则绝对不可能会察觉不到秦王“奋袖”和“拔剑”的声响举动。
无论如何,小说中的“琴声”对荆轲是致命的,秦王在“琴声”导引下成功大反转:“(秦王)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刃入铜柱,火出然。秦王还断轲两手。”“匕首”为短兵器,攻击时宜近不宜远。
而秦王“奋袖超屏风而走”,就迫使荆轲只能“拔匕首擿之”,“匕首”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弃“匕首”之长用“匕首”所短之态势,正如荆轲答应秦王“听琴声而死”的要求一样,是倒持太阿、扬人所长而不避己所短所致。最终荆轲省悟到这一点:“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轻易”的根源,是他的超高自信:
“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
此番话可以看成是荆轲的内心独白,他不屑于做琐屑的实际工作,只是幻想着突然一天时机到来会证明自己是“超世”之“士”。在初心与志向之间,缺乏必要的行动,故对刺秦的复杂性与可能存在的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知与充分的考量,尤其是没有围绕行刺对象秦王做一番事无巨细的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后制定出相应的细密行动方案,故仓促间答应其“听琴而死”。
“好手琴者”的率尔,显示出本应是“听琴”的高品位的音乐欣赏活动,在荆轲那里成了“观琴者”的诉诸视觉一般的、简单的观赏性宴乐。化高品位的“听”为低俗的“观”,就可以看出荆轲惯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性格与行事风格,这才是“好手琴者”一语在小说中隐含的句意之关键。
清代学者孙星衍在《燕丹子·叙》中谓:“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此论对《燕丹子》高超的语言艺术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在诸多“辞令”中,“好手琴者”以四两拨千斤之功,把荆轲与太子丹二人的真实关系、把荆轲的性格等点逗出来;勾连起“断美人手”与“断於期首”两个重要场景;埋下荆轲“不解音”而致刺秦失败的伏线等。《燕丹子》近三千字的篇幅,以“好手琴者”四字,就能够架构起文中三个主要人物——太子丹、荆轲与樊於期的复杂微妙关系、勾连起一系列的典型场景、揭示出主要人物深层的性格命运等,窥一斑而见全豹,由此可见《燕丹子》语言艺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参考文献:
[1]佚名撰,孙星衍校.燕丹子卷下[A].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41.
[2]《击鼓》[A]梁锡锋注说.诗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93.
[3]张文成.游仙窟[A].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