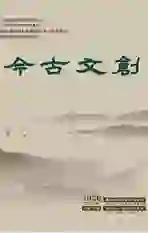论苏童《妻妾成群》的悲剧意识
2020-09-10刘珂彤
刘珂彤
【摘要】 苏童,当代作家。本文从爱情的悲剧矛盾、人性的悲剧色彩、意象的悲剧意蕴三个标题来探究苏童《妻妾成群》的悲剧意识。通过对苏童《妻妾成群》悲剧意识的分析,蕴含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人性泯灭的哀叹。
【关键词】 苏童;《妻妾成群》;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25-02
苏童,原名童忠贵,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代表作家之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驻会专业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红粉》《妻妾成群》和《碧奴》等。苏童发表了《1934年的逃亡》而一举成名,同洪峰、格非等一起成为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之一。小说《妻妾成群》讲述了陈家大院里的四房姨太太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互相残杀,身心俱伤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一、爱情的悲剧矛盾
爱情是文人墨客书写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妻妾成群》通过对大院里不同角色的爱情故事的讲述,展现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不同的人生所经历的不同的爱情悲剧,而这些爱情也引导了他们的命运。
三太太梅珊是一个洒脱到有些离经叛道的女人。但是梅珊的儿子飞澜并没有在个性上遗传梅珊太多,飞澜身上现出更多的是和哥哥飞浦一样的懦弱和冷漠。当父亲迎娶了新妻子时,飞澜是缄默的;当母亲因为偷情被抓去死人井时,飞澜是冷漠的。一个童真的形象被赋予了冷漠的性格,这与人们思维定式中的孩子形象是相悖的,这种扭曲体现了大院冷漠的氛围,衬托了单纯的颂莲在大院中举步维艰的境地。“苏童在剥离人性的同时,生命在非理性的人性阴暗面中凸显了个体价值的狂欢,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飞澜是受过初级西方新式教育的孩子,他与颂莲的不同就是他还没有被封建礼教的腐朽思想所荼毒。飞澜代表着一股崭新的西方意识正在成长,而这股力量在与封建礼教思想对抗的同时,在原生家庭的无爱环境下,滋生出了一种冷暴力,而他沉默的反抗最终也只能变成为封建礼教发展推波助澜的毒手。
颂莲的长箫是影响她情感变化的重要意象,箫的存在与否也是颂莲是否真正融入大院的标志。当箫在颂莲身边时,她对飞浦产生了感情。通过赏菊,颂莲与飞浦之间建立了一种无言的默契;箫的消失,是陈佐迁在陈府中权力的体现。颂莲与飞浦的感情纠葛表现了女性在封建思想和本性欲望之间的拉扯,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成年男女的本性欲望在野蛮生长,生成一种近乎疯狂的力量,但就是这样疯狂的力量,却依旧被残漏的封建礼教所压制。
陈佐迁看似只是一个配角,但实际上他掌握着真正的生杀大权。在陈佐迁的眼中女人都只是廉价的生育机器,他迁经常会提到大院里的一切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这样的规矩逼着大院的女人们互相厮杀,逼着她们争宠,逼着她们臣服在绝对权力之下。可悲的是,没有人有异议,所有人都漠然地生活着。这种规则中的爱情不止束缚着大院里的女人们,也反噬了享受这种规则带来的权利的陈佐迁。陈佐迁在掌握着院女人命运的同时,也为女人们的钩心斗角感到头疼不已,他意图通过身体上的放纵回避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就是身体上的放纵,带来了更深层的精神上的折磨,这种轮回式的宿命悲剧正是缠绕着陈家的最沉重的枷锁。
二、人性的悲剧色彩
作者塑造了封建牢笼里四个性格截然不同、命运却极为相似的女人,她们正是社会上不同的女性的缩影。姨太太们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悲剧正是封建制度的压迫下人性被迫扭曲的悲剧现实。
毓如作为原配太太,终日被养在院子里,失去了姿色,失去了丈夫的宠爱,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从踏入陈家大院开始,颂莲的命运就已经开始改写为悲剧。“这种家庭意外变故的‘偶然性’打开了颂莲悲剧的大门,而其自身内在的传统本能,使得其成为彻底的‘必然性’悲剧。”对于拥有新思想的颂莲来说,她是主动踏入旧社会的牢笼中的,虽然这种主动是迫于现实,但这种自我毁灭令已经深受封建礼教残害的毓如扼腕叹息。毓如在陈家的地位十分尴尬,陈佐迁厌弃她,儿子也认为她是一个固执呆板的女人,她是一个被封建礼教侵蚀迫害至遍体鳞伤的封建女性,她信奉着封建礼教规定的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她人性的悲剧体现在一种墨守成规的依附性,她的人生都是依附于陈佐迁而展开的。毓如人性中的悲哀是一种无欲无求带来的虚无感和面对颂莲产生的怒其不争的无力感,而她的存在感就在这种矛盾中被抹杀了。
卓云和梅珊、頌莲的命运都被陈佐迁的一喜一怒牵动着,在男权的压制下,她们只能将不满和郁闷发泄在彼此身上。“痛苦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颗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这种争宠意识并不只体现在陈家的女人身上,这是整个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共识,正是这种共识性,增添了太太们作为被封建制度压迫的女性典型的悲剧性。从颂莲被迫加入女人们的战争开始,女学生颂莲就死了,封建礼教把一个单纯的女学生变成了满腹心计的怨妇,悲哀的是,工于心计竟成了颂莲能在大院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生存在阴郁、窒息的环境中为了自我生命的自由, 他们进行了无数次逃亡与找寻的尝试。”梅珊不能保证牢牢拴住陈佐迁的心,所以她勾搭了医生,尝试通过与医生偷情逃离封建礼教的约束。无论是作为传统封建牢笼的陈家,还是伪善恶毒的卓云都容不下梅珊放荡自由的灵魂,所以梅珊的死既是偶然被卓云捉奸所致,也是自由灵魂无法逃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必然结局。“‘新女性’颂莲在觉察到丫鬟雁儿给自己造成潜在威胁时,根本丝毫没有运用其本该有的新气息来哀怜女人终究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颂莲在惩罚雁儿吃下草纸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以陈家四太太的身份在惩罚自己的丫鬟了。颂莲已经被封建礼教改造成了一个以“夫权”为中心生活的封建女性。包括颂莲在内的所有太太们,都已经被封建礼教摧残得无法对女性同类的悲惨遭遇产生共情了。如果说颂莲是逼死雁儿的元凶,那么其他太太们的默认就是无形之中推动了雁儿的死亡。在男权的压制下,女性们互相争斗,最后三太太死,四太太疯,大太太和二太太又迎来了年轻貌美的五太太,没有人是赢家。
三、意象的悲剧意蕴
意象在小说中有渲染气氛,表达人物性格,喻示剧情走向的作用。出现的意象都体现了死亡意识与悲剧性,它们对于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变化起到了导向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小说中的菊花意象主要出现在颂莲与飞浦的交往中。因为菊花代表的是颂莲对爱情的向往,人性中的纯洁。当颂莲遇见飞浦的时候,她对爱情的向往是强烈的,她沉溺于自己营造的一种暧昧的假象;当颂莲安心地做陈佐迁的太太时,她为陈佐迁顾忌其他太太是否吃醋而生气,“颂莲的内心是矛盾的,一面想要追求人格的独立,在陈佐千面前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格,却又发现陈佐千是这大院里唯一能做主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一个受到新思想教育的女学生彻底沦为封建礼教的祭品,颂莲人性中那些被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领导的奴性被激发,她不再为争宠而努力,她变成了像所有被封建礼教改造过的女性一样的沉默和顺从。菊花象征着封建社会女性群体的反抗意识,在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女性为了人性解放,人权独立进行了无数次的尝试。但每一次从怒放到凋零的过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象征着女性最终只能被封建势力吞噬的悲惨命运。美好事物终将毁灭的悲戚,推动着颂莲最终走向疯癫的深渊。
紫藤花这一意象其实代表的是颂莲的潜意识。如果说颂莲就是一朵紫藤花的话,那么嫁人之前,父亲就是粗壮的藤架,藤架倒后,花就飘零着,直到有一口深井在接应她。紫藤以为找到了可靠的归宿,但其实深井才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地方。颂莲绝不是被迫出嫁,她甚至主动要求找个好人家,说明她虽受新思想的教育,但骨子里还是传统保守的,所以她注定要堕落。颂莲嫁入陈家不仅是一种自甘堕落,另一方面这代表着西方意识向封建思想妥协。面对身世飘零的颂莲,没有人表现出对弱者患难的共情,这种对于死亡、毁灭等现实的漠然体现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人性的摧残。梅珊和颂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梅珊毫不掩饰自己的叛逆,不受宠就找别的主去依靠。颂莲没有别的主可以依靠,她只身来到陈家,像漂泊的紫藤,遇见了枯槁的井也觉得温暖。梅珊与颂莲的不同在于,梅珊具有坚定的自我意识,她不拘泥于顺从的生活;但颂莲表面上是具有清高品格的“菊”,实际上她是随风飘零的“紫藤”,在陈家的斗争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矜贵的性格。
井是死亡的象征,是整个陈氏家族中的女人命运轮回的象征。文本中描述的死亡的宿命感来源于井。井的存在说明,历代陈氏家族中出现过像梅珊一样,将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敢于反抗男权至上的女性。井不仅是封建礼教对敢于反抗的女性的强硬束缚,井的存在更是一种对美的扼杀。小说中鲜活的、积极的元素都毁灭于井,反倒是阴狠的卓云和冷漠的毓如作壁上观,逃避了被井毁灭的命运。井是整部小说中最阴暗,最压抑的元素,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女性们的恐惧。作者在小说中对传统死亡意识颠覆的同时,赋予死亡以新的内涵,即殉葬。梅珊的死和颂莲的疯,是女性在新思想与旧文化的斗争中做出的有意义的牺牲。
四、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从陈家大院四房太太的爱情婚姻经历出发,分析了爱情矛盾、人性的悲剧及悲剧的意义和价值,挖掘了女人的互相残杀,制度的摧残及死亡的解脱,让悲剧有了深度。结合先锋小说中的死亡意识,苏童创作中的悲剧叙述等概念挖掘了小说《妻妾成群》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苏童通过讲述人物的悲剧,讲述男性和女性的人格扭曲、道德沦丧,他们只能通过互相残杀、互相迫害的方式寻求灵魂解脱,用血与泪凝聚成了一曲悲歌。
参考文献:
[1]周夕楸.论苏童小说中的创伤书写[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3.
[2]刘虎.浅析苏童《妻妾成群》中的“人性(女性+男性)”悲剧[J].名作欣赏,2018,(32):109.
[3]龙梦.浊世里的菊——浅谈苏童《妻妾成群》里的颂莲悲剧[J].艺术科技,2017,30(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