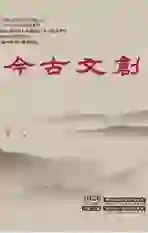“坎”和“陷”再考察及其关系补说
2020-09-10宋涛
【摘要】 本文对“坎”和“陷”的形体部件和意义进行了讨论,认为“坎”和“陷”字形构成相似,均为“凵”加“动物”,两者意义接近。其次讨论两者的关系,在两者共同遵循“凵+动物”的意义模式上,通过对所从动物之形以及后带宾语的区分,得出:“坎”似乎多用于祭祀之事,指埋牲于坎以陷鬼神,“陷”多用于田猎之事,指掘坑坎陷牲以猎。
【关键词】 坎;陷;意义考察;意义模式;关系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3-0050-03
一、坎系文字考察
《新编甲骨文》坎字目录下有 (H14610)、 (H1
9800)、 (H21257)、 (H14313)等字形。罗振玉、孙海波、屈万里等将其释为“薶(埋)”,《甲骨文编》吸收了他们的意见。裘锡圭认为“释此字为埋,从卜辞文义看是合理的,但是在文字学上缺乏根据。”
查看该字的字形,应为上下结构,上部从“人”“牛”
“豕”“犬”,其意义已经比较明晰。下部从“凵”,历来说法较多。《说文·凵部》:“凵,张口也,象形。”似乎不确。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一说坎也,堑也,象地穿。凶字从此。”杨树达认为“凵”为坎之初文,裘锡圭认为杨说较《说文》更加合理。艾阴范(1994)认为“凵”为远古房坑之纵剖面形。这几种说法虽然对下部所从“凵”的认识有所差别,但是都包含了“凵”是所掘“坑坎”的意思,本文采取这种意义。总的来看,“坎”应该是一个象形兼会意字,上部为家畜或人,下部是所掘坑坎,象掘地为坎以陷动物或人。《左传·昭公·昭公六年》:“柳闻之,乃坎、用牲、埋书,而告公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晏子春秋》:“为坛三仞,坎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是其动词用法。古代汉语名动相因,因而坎的名词义应该为“坎牲之处”,即“坑坎”。《周易·序卦传》:“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仪礼·士丧礼》:“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甲骨卜辞中“坎”多不带宾语,有时也带宾语。
裘锡圭(1980)认为上述字形为“坎血”“坎其牲”的专字,最初 可能表示“坎牛”两个词, 表示 “坎犬”两个词。裘说从卜辞的文义来看似乎是合理的,如图1上部:“卜:今日坎。”这一片甲骨虽有残缺,但是此句可以算得上完整,且“坎”字上下均有空出,但却没有记录宾语,因而“坎”作“坎犬”解释从文义上来看是似乎是合理的。但是由于能搜集到的卜辞完整且“坎”后未带宾语的甲骨资料极少,因此也无法断言这种说法就是准确的,还需要之后更多的考古发掘的新资料来加以佐证。
能搜集到的甲骨卜辞中“坎”后带宾语的占多数,并且所带宾语与“凵”中所从动物之间联系紧密。现在对合集中带宾语的情况做简单统计,本文共收集可以辨认的“坎”后带宾语的卜辞17例。
由统计可以发现,凵中所从动物与后接的宾语基本上是一致的, 似乎是凵豕的专用字, 是凵犬的专用字,
是凵牛的专用字。 后所接宾语有牢和 ,张秉权、姚孝遂认为:“牢”为圈养而用于祭祀的牛,“ ”为圈养而用于祭祀的羊。古代祭祀有太牢少牢之分,太牢规格比少牢要高,用到太牢的次数也就比少牢要少,因此 后接宾语多为“ ”也就说得过去了。
那为什么坎后既有带宾语的情况也有不带宾语的情况呢?朱生玉(2019)认为:“凵+动物”为早期融合型的词化模式,后来宾语逐渐地分离而发生了词汇合并,使用频率较高的“ ”字被保留下来记录该词”。由此认为朱说是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卜辞记载的多是王室贵族的祭祀,而天子祭祀又用太牢,太牢中“牛、羊、豕”齐备,其中又以“牛”最能代表祭祀祭品,因而从“牛”来记录这个詞也就是合适的。正因为此, 之外的其他字形在使用的过程中慢慢并入 中,成为其异体字。
二、陷系文字考察
《新编甲骨文》目录下“陷”有 (H10951)、 (H7 363.正)、 (H10659)、 (H3373) 、 (屯2589)等字形。罗振玉将其解释为“阱”,《甲骨文编》把 、 、
都当作是“薶”的异体。从字形上来看分为上下两部分,其构成似乎和表示“陷人”的“臽”相同。胡厚宣认为此字“象挖地为坑坎,以陷麋鹿之状,当为臽之古文”,进而将其改释为“陷”,本文从之。以上所选的字形中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凵/井”上的动物不同,二是下部有从“凵”的,也有从“井”的。
前者将在后文讨论,先来讨论从“凵”和从“井”的问题。《说文井部》:“井,八家一井,象構韩形。瓮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许说令人费解。郑慧生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井”不用作水井义,而是和“凵”一样用作坎陷义。即“凵”为阱之初文,在作陷阱义时,又是“井”的后起加形区别字。上文提到杨树达认为“凵”为坎之初文。古文字中类似的事物用同样的符号来表示也是常见的事情,无论是坑坎还是陷阱都是在地上所掘的小坑,因此采取郑慧生的说法,即 下所从“井”应是“陷阱”之“阱”。孙雍长(2007)从甲骨文字形入手归纳出的殷周时代的八种捕猎方式,即:徒手捕捉、棍棒搏击、弓矢射取、布置网罟、安置陷阱、投放诱饵、烈火焚攻、猎犬相助。八种方法各有侧重,结合实际推断,先民在对付大型的动物时候应会采取安装陷阱和投放诱饵结合的捕猎方法,即在地上挖掘坑坎,加以伪装,在其中放入诱饵,引诱猎物进入“凵”或阱内,将其猎杀,这种方法即是“陷”字形所描述的狩猎情形。《说文·井部》:“阱,陷也”。段注:穿地陷兽。因而陷字下部从“井”是合理的。陷字下部所从“凵”和“井”意义相同,之所以出现两从的情况,可能是观察角度不同所造成的,“凵”象坑坎的侧面造型,而“井”则象从上俯视所见坑坎之形,正因为观察角度的不同,所以先民也就采取了两种形式来记录所“陷”坑坎之形。
再来讨论所从动物之形不同的问题,陷在甲骨卜辞中多不带宾语,但也有带动物为宾语的情况。
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征,即“陷”字所从动物之形与其后所带宾语基本是一致的,这说明在殷商时候,先民对陷捕的不同动物区分很细致,并且“专字专用”,用来记录和表达。
此外,甲骨卜辞中“陷”后面不带宾语的情况中,上部所从动物之形以“麋”为最多,“鹿”“兕”次之,还有从“犬”的情况。不带宾语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甲骨残缺,看不到下部的卜辞;二是不带宾语不妨碍理解。第一种情况受制于材料,不做讨论,现简要讨第二种情况。
如图2卜辞:“鼎(貞):我其陷, 。 五。 二告。”该卜辞内容完整,且甲骨上下均有空位,却仍未刻出“陷”后的宾语,大概是记录者认为不刻出宾语,意义也可以自足。若想了解所“陷”为何种动物,就需要观察“陷”字上部的动物形状,才能获取准确足够的信息。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合文现象,但是卜辞中又存在后接宾语的情况,因而合文说是不合理的。这里的构成“陷”的意义的模式,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坎”的“凵+动物”模式。
三、坎和陷的关系
上文讨论了“坎”和“陷”的意义及其意义构成模式,“坎”和“陷”在意义上都有“以坑坎陷动物”之义,两者在意义的构成也都遵循“凵+动物”的模式,其不同之处在于所从动物之形。从上文列举的字形来看,“坎”多从“牛”“羊”“豕”,“陷”多从“鹿”“麋”,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从思维上来说,这种区别符合原始思维形象性和具体性的特点,正如列维·布留尔所说:原始语言“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而且“永远是精确地按照事物和行动呈现在眼睛里和耳朵里的那种形式来表现关于它们的观念”,先民在选择文字符号记录“坎动物”和“陷动物”时就是将所能看到的最直观的、形象的现象加以简化描述,又受具体性思维的影响,对所用不同动物做了细致的区分,从而出现了不同的记录符号。按此来说,“坎”多从“牛”“羊”“豕”自是因为“坎”所用的动物多为牛、羊、豕,而“陷”則多与“麋”和“鹿”相关。另外,就文字的产生来说,“人们最先需要为它们配备正式文字的词,其意义大概都是难用于一般的象形方法表示的,如数词、虚词、表示事物属性的词,以及其他一些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此外有些具体事物也很难用简单的图画表示出来,例如各种外形相近的鸟、兽、鱼、虫、草木等。”“坎”和 “陷”所记录的祭祀和狩猎在先民的生产活动中出现频繁且地位极其重要重要,因而对其进行记录的需求也就十分强烈,“坎”和“陷”便是应这种需求所造的正式的文字。
“坎”和“陷”意义相近,都有“掘坑坎以陷动物之义”,但是二者到底还是有区别的。“坎”多用于祭祀之事,指埋牲于坎以祭鬼神,“陷”多用于田猎之事,指掘坑坎陷牲以猎。二者的区别可以从字形和文献及考古发现来看。
首先从字形来看,“坎”所从动物之形为“牛”“豕”,古代祭祀有太牢和少牢之分,其所用牲畜不出牛羊豕三种,另外,“坎”字还有从“犬”的字形,据考证,犬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自然不用掘陷阱来捕犬。“坎”所从几种动物皆是先民驯化饲养的动物,用他们来进行祭祀之事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再与“牧”字进行类比,牧字主要有
(H36969) (H20017) (H3208) (H28351),象以手持杖,驱赶牛羊。《说文解字》:“牧,养牛人也。”“牧”字形多从牛羊,因为牛羊是人类驯化并且已经家养的动物。“坎”“牧”二字所从动物之形多为已经驯养的家畜“牛”,在意义上也应该有共通之处,即表示“对已驯养家畜进行处置”,所以“坎”表示意义就应该是和已被人类驯化圈养的牲畜有关,祭祀之事用牲显然包括在其中。
“陷”字所从动物之形多为“麋”“鹿”。麋和鹿是先民们所着衣物皮毛的来源,且麋和鹿行动敏捷,采用寻常的徒手捕捉和棍棒搏击的方法自然是不行,捕捉麋鹿所采取的方法应是安置陷阱。另外,“陷”还有从“兕”的字形,《说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在文献中常和犀并举,如《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 有人认为兕就是雄性的犀牛。《国语·晋语》:“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无论如何,兕应该都是体型巨大的猛兽,而且被作为狩猎的对象,这样的猛兽自然不可能用于祭祀,而应该是“陷捕”的对象,因此“陷”指田猎之事是合乎事实的。
其次从文献来看。H19800:丙申卜王鼎(貞): 勿于门。辛丑用。十二月。《发凡》说:“古有祀门之祭……用女俘也。”既是在“门”处,又是埋“女”,自然不可能是“陷”,而应是“埋人于坎以祭祀”。另外《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根据井中伟的解释,这里的“瘗薶”当于“坎陷之祭”。又《礼记·祭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左传·昭公·昭公十三年》:“观从使子干食,坎,用牲,加书,而速行。”可以看出“坎”是和“坛”相对的一种祭祀方式。H33404:鼎(貞):于戊 , (擒)。“陷”之后有一“擒”字,应该是麋掉入陷阱之后将其抓捕。《礼记·中庸》:“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其中“陷阱”并用,应是“陷”和“阱”两者意义相同,为田猎之陷阱。
再从考古发现上来看:
王克林(1982)提到了两种人祭:一种是房子奠基仪式时的人祭,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邯郸涧沟、汤阴白城和登封告成的遗址均有发现。另一种人祭来源于原始宗教崇拜,和第一种同时发生,在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有两座圆形窖穴内发现屈肢状的人躯。这种人祭遗迹,先后在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发现十余座。同葬的还有猪、狗。这种人祭习俗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发展,在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六座圆形人狗埋葬坑尤为典型。第二种人畜祭祀,至殷商更加发展,在安阳殷墟遗址中祭祀所用人畜之多更是远超前代。
第二种人畜共祭的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坎”字所描述的“掘坑坎以祭”,遗迹中发现的人、狗、猪,与“凵”上所从动物也是吻合的;祭祀所挖掘的圆形灰坑、窖穴及废井,“凵”极有可能描述的就是它们的侧面之形。结合考古发现来看,确实存在一种埋人畜于坑坎的祭祀,“坎”字极大可能是先民对这种祭祀情况的描述。
四、总结
总之,“坎”和“陷”意义相近,都有“以坑坎陷动物”之义,并且两者的意义构成模式都是“凵+动物”,但是两者在意义上仍有区别。本文分别从字形、文献、考古发现三方面对其进行了区分,发现“坎”多用于祭祀之事,指埋牲于坎以祭鬼神,“陷”多用于田猎之事,指掘坑坎陷牲以猎。
参考文献:
[1]裘锡圭.古文字论集·释坎[M].北京:中华书局, 1992:48.
[2]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艾荫范.说凵[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5):99-100+103.
作者简介:
宋涛,男,汉族,陕西咸阳人,本科在读,郑州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