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笙箫
2020-09-10宋欢筠
宋欢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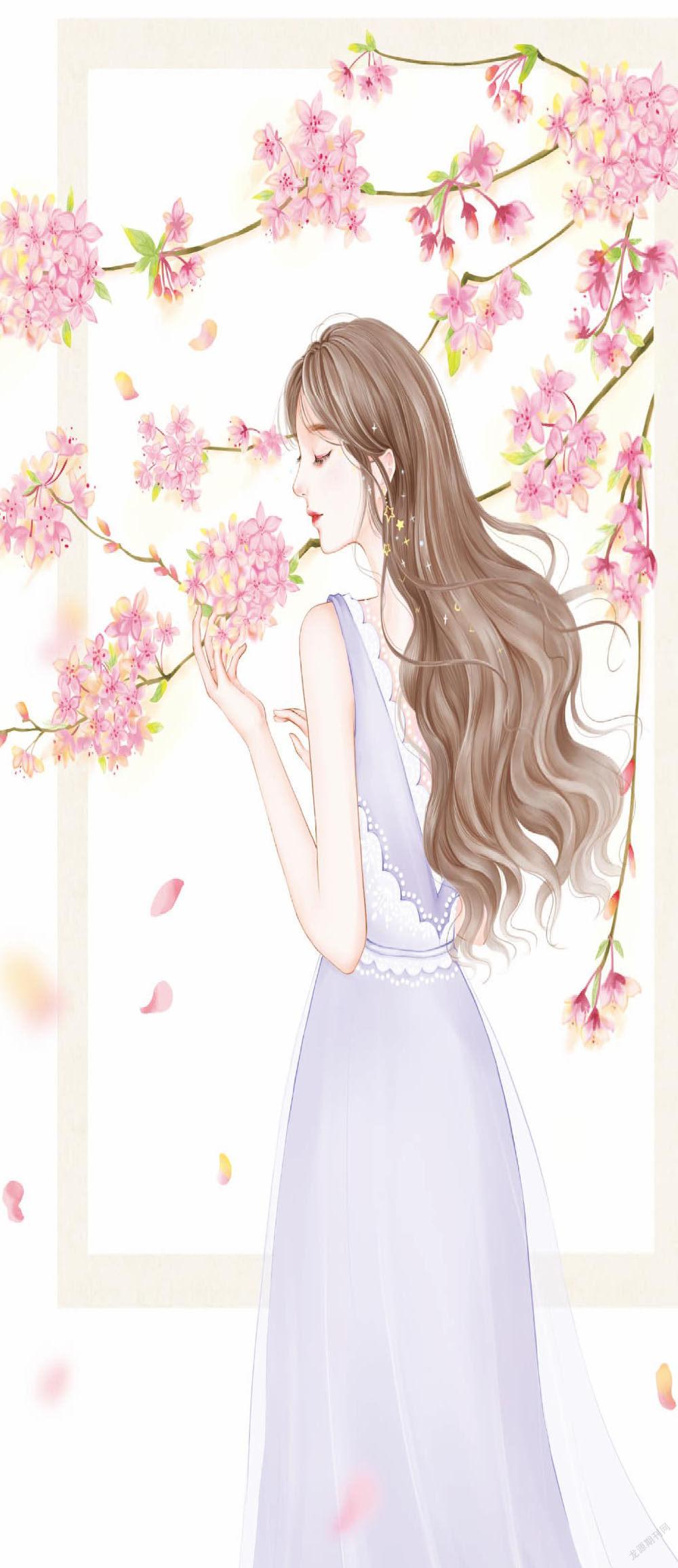
楔子
秣陵城的冬天,很少下雪。
就算是要下,也是纤细瘦弱的雪。薄的一层,莹白的颜色,没什么温度,后劲却是冰凉得麻了手指。
笙清是裹着绛红戏裙跑出去的,她哈着热气,绣着如意的厚底彩鞋被她踩得摇摇晃晃。
她怀里抱着取暖的雕花袖炉,把冻僵的右手从披风下面偷偷伸出来抹眼泪,还没来得及把戏妆卸下,整张脸被她抹得花里胡哨,像白面的鬼。
滑凉的石阶上落了一层薄如蝉翼的雪,笙清脚下一个没踩稳,扑腾着就跌进那个人的怀里。
她冻得通红的耳朵亲昵地蹭着他的军大衣,毛呢材质的大衣蹭得她耳廓微微发痒。
“对……对不起。”笙清揉着眼睛带着哭腔,眼睛还未睁开,只觉得是撞到了人,嘴里含混不清地道歉。
她抹着眼泪,朦朦胧胧瞧见被撞的是个军官,藏青色军装笔挺,腰间还别着一把冰冷的手枪。
笙清瞬间下意识地退了好几步,在心里责怪起自己的毛躁,眼泪却更不争气地连串掉下。
“笙清,最近连年战火,这秣陵城里可不太平。”笙清记得跑出来之前,云仙停滞了理妆的动作,侧过身睨着她低语。
萧平意的右手下意识地把腰间的手枪按住,狐疑地扫了她一眼。
漫天的小雪里,穿着红戏裙的姑娘低着头,应该是刚从戏坊里跑出来,细碎的刘海遮着前额,露出一张冻得惨白的小脸。她眼角的妆晕开,不像唱戏,倒像在扮鬼。
“笙清?”
他犹疑了半晌,轻轻喊出这个名字,如释重负般松开按住枪柄的右手。
笙清抬起头的时候,正望见刚刚那个跟自己撞个满怀的军官,他犹疑地唤自己的名字,语气疑惑又不无惊喜。
他认识自己吗?
笙清抬起头想看个清楚,眼睛却被泪水模糊得看不清眼前,只朦朦胧胧感觉那应该是个长相俊秀的军官。
“你忘了?我是萧平意。”
他语速不疾不徐,眼眸里宛若星火闪烁,唇边是温和的笑意,骨节分明的双手上裹着纯白军用手套,递给她一方素灰格子边手帕。
萧平意?
笙清讶异地抬眸,对于这个名字,她太熟悉也太陌生。
俊秀军官左眼角底下有颗小小的痣,掩在下睫侧反倒显得双眸漾着清辉。
是,他的确是萧平意。
红戏裙的笙清激动地拽着他的军大衣,个子不高的她头顶只到他肩膀,整个人就像窝进他怀里一样。
她鼻尖冻得通红,笑靥如秣陵初春的红梅。
果然是她啊,萧平意淡笑着。
“六年了,本来还以为会记不得你的模样,但是你这哭花的脸可真有辨识度,偌大的秣陵城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你还爱把脸哭花的角儿了。”
萧平意嘴角噙着笑,温柔地俯下身子,他拿着那方素灰的格子边手帕,仔仔细细擦拭着她脸上的残妆。
六年前也是这样,她总是喜欢把脸抹得花里胡哨。
笙清记得那天秣陵城很冷,萧平意温暖的指尖触碰到她冻得煞白的脸颊,就好像在她心里也燃起一束温暖的火光。
一
“笙清,这场戏你就别上了。”
戏坊这样通知她。
笙清揪着衣角,把头低了些,像是在咽什么极为黏腻苦涩的东西,半晌才喃喃道:“好。”
和从前的许许多多次一样。
笙清想起那天萧平意称她是“角儿”,不由得在心里暗自苦笑着。
她哪里是什么角儿,不过是连一次角儿都没机会唱的龙套。
笙清转回头对着黄铜镜,细细理了理绾好的青丝。铜镜里的美人发髻上是花钿垂珠,绞丝银篦,眼波流动如同清溪的涟漪。朱丹唇轻抿,衬得她眉目含情。
只是美人只有皮,没有骨。
苍白的脸色、消瘦的身姿,没多大力气似的,摇摇欲坠。
师父把她捡回来那年,她就一直咳嗽,给她看病的郎中说,她活不过二十岁。
云仙已经戴得了流苏凤冠,披着荷花式的茜色云肩上了台。云仙上完妆,活脱脱是真的李香君。
笙清拾起裙袂,踩着那双她素日最常穿的如意纹彩鞋,不动声色地躲在大厅圆柱后面。
今日人少,她看一看也好。
等到她终于学会把《桃花扇》倒背如流,却再也没能有过一次上台的机会。
不在台上,看一眼也好。
毕竟她也不知道羸弱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
胭脂色的纱幔遮住绛红的戏裙,笙清躲在石柱后,没望见云仙,却被打杂伙计一声谄媚的高喝打断思绪。
“副团长,您怎么来了。”
萧平意的身姿忽然流星般映入她眼帘。他正掀帘走入,还未坐定,双眸浸着高山远雪般的寒芒。藏青色军装上落着浅淡的雪渍,一双军靴带着穿堂而过的疾风,飒飒作响。
他没对伙计答话,只微微点头,找个僻静的桌,取下头上的藏青色军帽,弹了弹上面的薄雪。
笙清想起那天他笑着称她“角儿”,忽地就涨红了脸。六年前她刚背会台词就曾对他夸下过海口,说假以时日,她一定能成喜来戏坊的角儿。
然而自从师父离世,她再没登过台一次,如今只能丢脸地躲在台柱后。
不过,他居然真的来了。
六年前他答应得清脆,她还记得彼时少年笑着,身姿若芝兰玉树,他说:“好,到那时我一定去给你捧场。”
笙清终于还是忍不住偷偷地从台柱后望他。
印象中還是小时候鼓着腮帮的白绸衫男孩,转眼就一身戎装,眸光沉稳凌厉似宝剑出鞘时四射的寒星。
她扒在台柱上入迷地端详着他,竟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里的团扇,“咚”的一声,那扇子突然就掉在地上。
萧平意掀起茶盅的细瓷盖,耳畔传来清脆的“咚”声。
声音不大,但他是从军之人,对声音时刻都很敏感。
他回过头,只来得及看见石柱后匆匆逃离的那抹绛红的影子以及被丢在地面的白缎面团扇。
锣鼓震出喧天的响声,小三弦泠泠奏唱,演出开始了。
云仙轻移莲步,行至台中,开口是咿咿呀呀的水磨腔。
不过看不看这场戏,对萧平意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想要见的人,不在台上。
萧平意走近那根台柱,弯腰捡起地面的团扇,那是一把白缎面的锦绣团扇,萧平意认得,是她最喜欢的那把。
二
笙清打算从后门偷溜出去的时候,被萧平意拽着衣裳后领,如同拎小鸡崽一般把她整个拎了起来。
“清瘦了。”萧平意歪着头说。
“那我也可比六年前重多了。”笙清小声辩驳道。
“为什么躲我?”萧平意没有看她,只是望着戏坊雕花的漆木门,木门右侧挂着一盏绘花的红纸灯笼,北风呜咽时,在夜色里微微摇曳着,像是把这浓烈的黑生生烫出一个洞。
笙清低头抿着朱唇,半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害怕在你面前丢脸。
这句话,含在嗓子眼像是炙热的火炭,呛得她鼻腔一酸。
笙清感觉有什么温暖的东西落在她肩膀上。萧平意脱下毛呢军大衣,轻轻盖在她肩头:“冷吗?我带你去吃馄饨吧,就去你从前最喜欢的那家。”
笙清裹在温暖的军大衣下面,她冻僵的手指触碰到那件大衣,衣服上还残留着他的体温,是丝丝缕缕的暖意。
心间涌起的一阵酸涩模糊了笙清的眼睛。
上一次有人对她这样好,是多久以前了?
萧平意,我不过是个戏子,不值当的。
她抬起头望着他瘦削的下颌,终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笙清吸溜着鼻子,和萧平意坐在街口的一家馄饨摊上。在锅里翻腾着的小馄饨,香气袭人。
笙清下意识紧了紧衣服的领子,等第一碗馄饨上来时,把白瓷的碗推到他面前。
她的眼睛在夜里亮晶晶的,像小鹿:“你吃。”
萧平意甚是好笑地望着她,从筷筒里拿出一双木筷,摆在碗上:“什么时候和我要这样客气,还在生我不告而别的气?”
然后他习惯了一样拿起桌上的醋,沿着碗边倒入少许,再推给她,毫不客气地说:“快吃掉。”
笙清愣住一秒,他怎么还会记得自己喜欢沿着碗边往馄饨里放醋。
离他们上次见面,明明已经过去六年了。
“你怎么还会记得我喜欢这样放醋的?”笙清小口吞咽着诱人的馄饨,不抬头地随口问道。
萧平意含着笑,看笙清小口吃着馄饨,只觉得食欲也好了许多。
“一直都记得啊。”
你的每一个习惯,我都从来没有忘记的。
笙清差点呛得喘不过气,她很努力地咽下馄饨。萧平意并不像是和她开玩笑,他很认真地望着她,眼睛里深情得像是一池春水。
“下雪了。”萧平意没动碗里的馄饨,只是出神地望着夜色。
笙清抬起头,秣陵城下了漫天的雪。耳畔雪花簌簌,她只觉得是恍惚回到了第一次遇见他那天。
三
六年前他们遇见时,秣陵城也是雪花簌簌的冬天。
秣陵城里长者寿宴,红白喜事,请得起戏班唱戏的人家不多,萧家就是其中之一。
萧家做丝绸生意,连带着茶叶、米庄等好几种產业,在当地算是出手阔绰的主儿。萧家老太太七十大寿,就请了喜来戏坊在门口搭戏台,唱几出有意思的戏。
城里请得起戏班子的人家本不多,萧家这次又颇为大方,就在门前,城里人都图个热闹,戏台子前面被围得水泄不通。
笙清就挤在人群后面,她那时候年纪小、个子矮,蹦着跳着,踮起脚来看师父在台上唱戏。
她心里急得火烧火燎,戏台就要搭好了,师父今天唱最拿手的《桃花扇》。但是前面人太多,任她怎么踮脚都看不着。
笙清就是在这个时候,猛地起身蹦跶却不小心撞翻了一个人的布包袱。
她就是这个时候,遇见了那个让她铭记一生的人。如果岁月不那么恰好,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叹息流泪。这个问题,仿佛是没有答案一样。
包袱里书卷、毛笔散落一地,有的书卷还被推推搡搡的人踩上好几个灰脚印。
白色绸衫的少年一声不吭地蹲下来在地上捡书卷,他拾起被踩得脏兮兮的书,拍拍上面的尘土,又一股脑收进包袱里。
但是仍然有书卷被踩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地散落在大街上。
笙清晓得是自己撞翻了别人的包袱,就冲过去捡那些书,还冲着那些踩到书页的人大声喊道:“别踩啦,别踩啦!”再将手里的书卷码好,小心翼翼地递给白绸衫的少年。
她是低着头递过去的,脸庞藏在刘海儿下面。
少年不仅没有生气,还朝着她明媚一笑,很是书生气地对她说:“谢谢。”
“你是看不到前面的戏台吗?”他拎着包袱,向着台上正唱一折戏,水袖起落的伶人努努嘴。
笙清点点头。
“我带你去。”少年笑着,夕阳余晖把他的脸庞染上一层蜜橙色,他拉住笙清的衣袂往里跑,竟然也没个人拦他。
后来笙清才知道,她撞到的人,是萧家上私塾学国学的小少爷。那里的人哪个敢拦请戏班的东道主。笙清跟着他跑,头花被推来搡去的人群挤得颤巍巍掉落。她最终兴奋地站到了离戏台最近的地方。
她转过头去看他,他眼睛是笑着的月牙。
“一箫一剑平生意,我叫萧平意,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笙清。”笙清抬头望着他,笑得像秣陵初春的梅花半绽。
“你还记得那幕戏结束后你请我吃了一次小馄饨吗?”萧平意在笙清面前挥挥手,把她迷离的思绪拉了回来。
“记得,说好我请,却还是你付的钱。”
笙清低着头讪讪地笑,萧平意望着她面前空了的碗,轻声说:“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那你这次不会不告而别了吧?”笙清走在路上,脚步轻盈像翩飞的蝴蝶。
“不会,我还有很多很多地方要带你去呢。”萧平意含笑望着她轻快的步伐,想伸手揉她的头发。
却在伸手触及的那一刻,他愣在原地。
她发间戴着的,是六年前自己送给她的绒花发夹。
发夹上的绒花,颜色褪得半旧,就好像是被岁月一点点磨去了原本的生机。
四
六年前绒花颜色还是艳丽的红,花蕊缀着琉璃珠子,在那时候是个新奇玩意儿。
萧平意放学在售货的摊子上一眼就相中了,他知道笙清的旧绒花看戏时被挤掉了,这个她一定喜欢。
等到他兴冲冲地跑去给笙清展示漂亮绒花的时候,却发现笙清在被罚跪。
笙清小时候总爱偷偷戳一戳师父梳妆台的胭脂,学其他伶人的样子上妆,把自己的脸抹得花里胡哨。但师父格外宠爱她,总是不忍心说她。
只是在戏上对她的要求格外严格。
“阿清,人这一生,要得有本事,靠自己安身立命。”
但戏班里的生活总是枯燥的,年幼的笙清总是爱偷懒,每次看到巷口小朋友嬉戏打闹,都要投去渴望的目光。每一天她从睁眼开始就得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摇头晃脑地背那些拗口的唱词。
有一次,她再也耐不住寂寞,偷偷溜出门,却在一家馄饨摊前面停住,眼巴巴地看着,流着哈喇子。
等偷吃完回来,师父冷着脸站在门口,她吓得大气不敢出。早上背的词本来就记不清,哆哆嗦嗦没背出几句,就没了下文。
“去后门罚跪半个时辰。”师父扔下这句话,看也没看她一眼。
笙清耷拉着脑袋,老老实实跑去后门跪着。
萧平意就是在这个时候,天降神兵一般出现了。戏班颓圮的篱笆墙上,突然偷偷探出一个小脑袋,吓得笙清差点没叫出来。
少年白色绸衫在篱笆墙上蹭得脏兮兮的,但他好看的眉眼在清冷月光下仍是令人心动。
“吃小馄饨也不知道叫我。”萧平意语气不满,从上面丢下一个垫子,垫子里面裹着一个木匣。
“试试这个,每次我背不出书罚跪,都偷偷在膝盖底下放这个,就不疼了。”
笙清忙不迭地接过垫子,咧开嘴嘿嘿一笑:“你那时候不是还没下学呢嘛。”
笙清打开雕花的檀香木匣,里面安静地躺着一朵大红绒花,花蕊处缀着几颗润泽的琉璃珠子,她见了喜欢得不得了。
她把绒花戴在发间,傻笑着望向他。
萧平意每天上私塾,都要经过戏班的门口。只要一朝里面张望,准能看见哭得抽抽搭搭,脸也抹得跟小花猫一样的笙清。她记性是真的差,戏本里的唱词念好多好多遍,也记不得。
残阳欲尽的时候,萧平意下了学,就慌里慌张地赶去给那个傻姑娘念戏本。
她跟着他一句一句念,挠着头皮,努力地记着词,日子竟过得这样快。
萧平意不喜欢私塾里别的小伙伴,他们总要嘲笑他眼角的那颗痣是“美人痣”。笙清就会大大咧咧地赶过来,义正词严地对萧平意说:“他们是嫉妒你好看。”
这个看起来还小他一两岁的傻姑娘,却总能把他的生活变得格外明媚。
她总因为吊不好嗓子被罚,萧平意每次见她,她都哽咽着背:“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鹦鹉洲阔,黄鹤楼高,鸡犬寂寥,人烟惨淡,市井萧条。都只把豺狼喂飽,好江城画破图抛。满耳呼号,鼙鼓声雄,铁马嘶骄。”
的确拗口了些,萧平意对着手里的戏本子,望着坐在门槛上努力背词的笙清。
不知道若有一天他走了,她该怎么背这些唱词。萧平意想着想着,就用手里的戏本子轻轻敲了一下傻丫头的脑瓜。
“鼙鼓,pí ,第二声。念错了,重来。”
笙清满脸怨气地瞥了他一眼,又不敢光明正大地瞪他,要是萧平意撂挑子不干,她背不下来就遭殃了。
但萧平意突然就不告而别了。
笙清记得那天她倚着门,一直等到天色暗透。她抱着戏本,突然抽抽搭搭地吸起鼻子来。
等萧平意明天来,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顿,她最后望着夜空中闪烁的几点残星,心里愤愤不平地想。
但是后来,笙清再也没见过给她念戏本唱词的萧平意。再后来,她才知道萧家为着生意搬去了上海,他再也没回来过。笙清去过他念国学的私塾,私塾先生说,他不会回来了。哪怕是笙清日日黄昏坐在门槛上等他,都没等来一句道别的话。
五
喜来戏坊给笙清排的戏总只有几句唱词的角儿,笙清唱完就赶着去卸了妆,笑眯眯地坐在戏坊廊檐下等着萧平意。
萧平意每次巡防结束,都要带她去逛秣陵城最有趣的地方。
笙清咬着红彤彤的糖葫芦,糖渣粘在嘴角,嘴里还含糊不清地问着:“你后来去哪了?”
萧平意逆光站在廊檐下,藏青色军帽下的清秀脸庞被日色晕染得英气而温暖:“上海,读了两年书,就跟着叔父参军了。”
萧家早就败落了。
进口的洋布、洋缎样式新、价钱也较为便宜,战乱年代丝绸生意不好做。
萧平意在上海念大学,还没读两年,学校里抗议游行之风盛行,后来他跟着叔父参了军。
“战火迟早会烧到这里的吧。”笙清低头不安地绞着衣裳边。
梨园里几株早梅开得娇艳,萧平意伸手折下一枝,那花开得正像她发间那褪色的大红绒花。
“绒花别戴了,旧了。”萧平意把红梅递给她。
“这是你送我的。”笙清低着头斜倚在朱漆廊柱上。
她感觉萧平意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开始靠近她,气氛突然就变得暧昧起来。
他一眨不眨地望着她的脸庞。笙清下意识地就躲开他的目光:“看什么,我脸上没画儿的。”
“阿清,你知道的,我喜欢你。”
他最后低着头说出这句话,一贯是征战沙场的男儿,此刻却罕见地红透了耳根。
笙清低头不语,眼眶里泛着泪花,耳边是簌簌的秣陵雪。
六
边疆战事四起,萧平意终于还是去了边关。
她那天发烧,烧得厉害,咳了一夜,把帕子咳得满是血,睡醒时队伍已经开拔了。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一个月以来,她每日如此,白日都是强打着精神跟在他身后,看他笑着把糖人递给自己。
只是那夜她梦见了师父,她梦见六年前师父带着咳得厉害的她进了医馆,求了好几个郎中,却都摇着头叹她是娘胎里带着的病,可能是活不到二十岁。
笙清那时候还不太懂生死,只懵懵懂懂地抬起头,问师父:“真的吗?”师父回头望着那落满雪的医馆,然后蹲下来把她身上的斗篷紧了紧。
梦里师父说:“阿清不会的,阿清一定会好好活在这世上的。”
睡醒后她揉了揉湿润的眼睛,怅然望着窗外的雪。
可是师父,阿清真的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阿清没有答应喜欢的那个人啊。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拖累他。
萧平意在部队开拔那天没等到他心上的女孩,最后回望秣陵城的方向,天边是小雪簌簌。
笙清的头疼咳嗽近日发作得厉害,来看的大夫都连连摇头。
她本来命就不长,笙清惨淡地笑着,面容像覆了江南的霜,有些苍白。
这天她咳嗽得尤其狠,像是要把心肺都咳出来。她的屋子里烧了驱寒的火炉,那炉火摇曳着微弱的光,照得她身影格外单薄。
她知道,这次她是真的到头了。
喜来戏坊里唱李香君的角儿云仙被军团长丢弃在秣陵城,那团长就是想娶一房姨太,没怎么想真心待她。
“笙清,我原来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虽然你未登过台,可你最适合扮演李香君这个角色。”
云仙眉眼疲惫,看见笙清走进,只是起身为她了一杯茶。
“唱什么白云不羡仙乡,人不能成仙,人这一生,终究是免不了入俗。”云仙笑得一脸惨淡,她太过消瘦,那香君的云肩,竟也穿不上了。
“今日还有一折戏,你想唱吗。”云仙知道的,她这个同门小师妹,小时最得师父宠爱,自小身子骨弱,一生只想登台唱曲。
也是自己当初年纪轻,怕她成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没给过她一次机会。
也不是没嫉妒过师父的偏宠,毕竟在那凛冬里,师父只为她披过斗篷。
笙清剧烈地咳嗽着,血咳在素白手帕上,像染上点点瘦梅。
“要唱的,说不定便是最后一次唱戏了。”
笙清身子单薄,摇摇欲坠,眸子却似刀戟寒光凛冽。云仙轻轻叹,终究是没有拦她。
笙清戴了发冠,搽香粉,绘朱唇。她戴上珠翠花钿,步摇金钗,披上云肩。
“你看城枕着江水滔滔,鹦鹉洲阔,黄鹤楼高……都只把豺狼喂饱,好江城画破图抛。满耳呼号,鼙鼓声雄,铁马嘶骄。”
这是他曾经带着她念的那段,一字一句。好像她现在一回首,还能望见那个少年,就坐在门槛上。
笙清轻抖袖口,珠圆玉润的水磨腔,一升一降,都恰到好处。引得许多人围观,惊动前台看客。
七
江南烟雪刚朦胧,塞北隆冬已至。摇摇欲坠的城墙布满污浊的血腥,死尸近乎要堆成新的堡垒。
萧平意的队伍弹尽粮绝被围困三天,再等不到援兵,只有以身殉国。
萧平意弓着身子,钢笔在发黄的纸上洇出墨滴。漫天飞雪裹挟着沙砾,呼出的热气被凛冽的寒风掳走,刮得他脸颊由白转紫。
他思忖良久,只写下“绝命书”三字。
他想起口袋里放着那支前几天在市集巡逻时看见的簪子,镂刻着红梅花和流云纹,她戴上一定好看。
但他不一定回得去了。
他还不知道笙清的病情早已经加重了,就算他现在风雨兼程赶回去也见不到最后一面,她日日咳血,怕是挨不过二十的大限。
他抬笔,落下“阿清”二字。
想写些什么,却迟迟没有落笔。
那封信终究是没能写完,炮弹把阵地炸开的时候,信纸在惨烈的火光里化成千万个碎片。
炮弹呛人的白烟和浓重的火药味在落雪的阵地里弥漫着,洁白的雪上铺着厚重的鲜血。
君可知,金戈铁马若不入梦,是灵魂飘荡在他乡,是等待故人来立新冢。
北方那一战何其惨烈,萧平意的队伍并没等到援军。
萧平意闭上眼睛之前,雪好像还在下着,眼前一片白茫茫。
阿清,我再也等不到看你唱《桃花扇》了。
若以后能得入你夢,就为你绾一次发髻吧。
还没为你绾过一次呢。
你穿戏装、绾发髻在台上唱《桃花扇》的样子,我看不到了。
但一定是很好看的吧。
萧平意的胸口,开出一朵血花。合眸之时,雪还在下,他恍惚间就回想起那日他说喜欢她时,她垂下眸子,眼里含泪,脸颊却是绯红的。
有雪花落在耳边,真冷。
萧平意合眼的时候仍在想,等他头七的时候,有谁能替他掬来一捧江南雪就好了。
他想江南了。
血污把镶嵌着军徽的军帽,染成棕红色。
骸骨都胡乱地埋葬在冰冷的战壕里。这些南方军人最后都化作北方战场上的亡魂,他们没有一个能等来江南的雪,他们这一生,都再也回不去了。
笙清唱这折戏时,喜来戏坊里萧平意最爱坐的位子空着。
她似乎还能望见茶盏上缕缕白烟仍绸带般舒展,但听戏的人不在这里。
他终究是错过了这折戏啊,笙清咿咿呀呀地唱着,圆润的水磨腔婉转如莺啼。
笙清摸着那扇面上冰凉的白色缎子,她突然就剧烈咳嗽起来。她咳出的血,星星点点溅落在缎面扇子上,开成一朵朵瘦弱的红梅。
我是千里故人,烽火里幸得惊窥你容颜,此生亦足矣。
一折《桃花扇》唱罢,笙清以袖掩口。潮水般的掌声里,她只低头笑叹道:
“怕是大梦碎了,成一场空。”
她恍惚间好像看见萧平意常坐的角落里,那个人仿佛是刚刚风雪兼程地赶来,他一身军装,镶嵌着军徽的帽檐上方落着星星雪渍。
茶盏上白烟舒展如绸带一般,他对着她笑,双唇一张一合,好像在说:“阿清,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