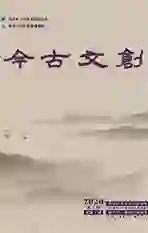走不出的黑森林
2020-08-25孙雪
孙雪
摘 要: 鲍特金认为悲剧这一文学形式具有相对应的原型模式,而这种原型模式是自我保护和屈服这两个倾向的某种组合,即本文称为“自我屈服”的心理原型,它是个体自我与群体角色之间冲突的外化表现,具体的表现为“自我”在“超我”面前的屈服与妥协,它不仅限于主人公,也与读者心理体验中同样的情感模式相对应,映射着人类心理中的某种需求感,本文将从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出发,结合悲剧作品所具有的原型模式,对仇虎复仇前后的心理进行分析,发掘《原野》中“自我屈服”的心理原型。
关键词: 自我屈服;悲剧;心理原型;赎罪;净化
中图分类号: J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4-0031-04
《原野》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悲剧故事,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仇虎的复仇看作农民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典型,并以此激发人类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痛感,但是它的艺术魅力并不仅限于此,《原野》的成功有着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那就是在这个悲剧故事中隐秘着的人类共通的心理原型。
仇虎在复仇过程中,表现出的心灵冲突,既和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关,也与他的自我相关,更与人类的心理和人类的命运相关,自我在与群体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自我只能作出无奈的屈服和妥协,这是人生无法摆脱的命运枷锁,《原野》以仇虎的自我屈服表现出了人类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迷失自己所造成的悲剧。
一、“自我屈服”的心理原型
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它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凡是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影,因而它们基本上是一种神话的形象。更为深入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些原始意象给我们的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赋予形式。可以说,它们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它们呈现出一幅分化为各种神话世界中的形象的普遍心灵生活的图画。”①也就是说原型与人类童年期的某些认知有关,是一种原始的文化模型(比如祭祀、仪式等),它随着历史过程一代代流传下来,并演变出许多类似的模式,这种模式积淀在人类的文化中,从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经验和文化共性,激发着人类关于本源的探索和流变,而文学作品中再现的意象,都有原型所表现的共同意义,“每一个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②作家将这些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努力挖掘出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声音,并汇聚成全人类内心的力量。
曹禺的戏剧《原野》在表现农民仇虎复仇的悲剧故事时,同样隐含着深刻的原型心理。莫德·鲍德金曾在《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中认为,与悲剧这一文学形式相对应的具有原型意义的人类情感模式,是由对立性质的两种感情倾向所组成,这两种倾向易于为同一物体,同一情景所激发,他认为这种性质可以通过对自我持一种矛盾态度的概念来说明。③
《原野》中,仇虎复仇前后所表现出的人格的分裂与毁灭,不仅仅是复仇带给他的内心的折磨,更多的是他陷入相对立的两种情感倾向中所造成的悲剧,这两种情感倾向呈现为自我的保护与屈服两种矛盾的存在,即“自我屈服”的心理,而这个模式同样不是单一地体现在仇虎身上,它与无数被《原野》所感动的人的心灵中的那些感情倾向的某种模式是相对应的,它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结构,也就是“自我屈服”的心理原型。
“自我屈服”具体体现为“自我”在“超我”面前的屈服,“自我”和“超我”常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在矛盾发展到无法平衡的状态时,时常发生分裂与冲突,从而表明悲剧的态度,仇虎的悲剧正在于他的“超我”的力量完全抹杀了“自我”的存在,从而导致“自我”的分裂与冲突,陷入痛苦无法自拔。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这两种人格结构,“自我”代表的是人欲,是人类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本能,遵循自由和纯真的原则。
“超我”则代表的是群体对个体的塑形与规整,也就是社会道德准则对人的要求与期望。主人公“仇虎”复仇前后的“自我屈服”离不开封建社会强加在其身上的传统观念,作为儿子,他不得不完成“父仇子报”的基本道德使命,作为兄长他必然要承担起身上的责任,作为男子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是他无法逃避的道路,心中的仇恨使得他必然放弃“爱情”与“友情”,在家族利益面前牺牲掉天然的情欲与自由。
他的“自我”完全被囚禁与吞噬,因此这一悲剧是个体的情欲表达与群体对个体的塑形与规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仇虎的“自我”在“超我”面前不断退让的消极后果,仇虎野性的“自我”在社会中总是被压抑与掩盖,最终被“超我”的巨大声浪所吞噬,他一边呼唤纯粹野性的心灵,一边又摆脱不了社会活动强加在他身上的责任与使命,道德与限制,这些心理体验既是决定悲劇的感情模式,也是现实中每一个个体生命所走不出的困境,而这种心理体验也恰好决定着《原野》的悲剧态度与走向,这正是《原野》作为曹禺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中外文学名著中,也存在很多以“自我屈服”为原型的悲剧作品,比如:《哈姆雷特》《长恨歌》《红楼梦》《西游记》等,它们以独特的魅力在不同的时代映射着个体的自我表达与群体对个体的塑形与限制之间的矛盾,表现着个体在集体的洪流中苦苦挣扎无路可走的悲剧命运,这似乎是人类生存中永远都逃不掉的困境,也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宿命,曹禺在《原野》中也基于这一人类共同的心理经验,表达着人类无法言说的哀痛与诉求。
二、“自我屈服”的形成与转化
《原野》的“自我屈服”原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作品中的,而是隐藏在仇虎复仇主题背后,这种“自我屈服”在相互对照的过程中造成文本持续的紧张,并决定着文本的结局。表面上看《原野》的悲剧是仇虎的人性的毁灭,但从更深处挖掘,导致“仇虎”走向毁灭的恰好是他的“超我”杀死了“自我”,也就是说这两个“自我”的矛盾同时存在于文本之中,构成文本矛盾冲突的源头。
主人公仇虎一出场便背负着一身的仇恨,当地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仇家的土地,并将他的妹妹送进妓院而导致惨死,他的未婚妻也成了焦家的儿媳。为防止仇虎报复,将他也送进了监狱。八年的牢狱之灾,仇虎早已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样子,在他身上留下的只有复仇,也因此注定了仇虎无法挽回的悲剧命运。
传统文化语境中“父仇子报”的旧观念已深入人心,儒家“父之仇不共戴天”的道德准则更是成为社会的共识,在这些“不复仇,非子也”的封建思想的压迫下,仇虎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被铐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他在社会所强加的“超我”面前屈服,在知道焦阎王的死讯后,依然没有停止复仇的脚步,而是将屠刀挥向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焦家母子身上,显然被仇恨所塞满的仇虎已经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从受害者到加害者这一角色的转变,是“超我”的胜利,也是“自我”的妥协。
他被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到焦家人面前,没有回头的余地,在这场复仇中他巧妙地将爱情和友情作为复仇的工具,他用自己和金子的感情激怒焦大星,刺激焦大星先动手,他精心设计着一场复仇计划。
对焦大星性格的设定,也加深了对仇虎的谴责。焦大星是一个好人,他完全抛开两家的仇恨,视仇虎为好朋友,甚至在仇虎入狱时也为他东奔西走。而焦大星对金子的爱也是毋庸置疑的,面对妻子和朋友的背叛,他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性格的软弱,最终死在仇虎的屠刀下。
仇虎也利用金子的感情,将金子拉进了复仇的圈套。他明知道焦母会来报复自己,便让金子将黑子放在了自己所睡的位置,又利用焦母的眼瞎间接杀死了尚在襁褓中的黑子。焦家的人都死了,唯独留下焦母苟延残喘,仇虎用无辜人的死去报复恶毒的人,当双手沾满洗不掉的鲜血,他作为一个复仇的胜利者出逃了。
吉尔伯特·墨雷把“悲剧的观念”看成是“高潮后有衰歇或骄傲后受制裁”的观念,因此《原野》的结局也适应了这一模式,罪恶终将得到审判,复仇胜利的喜悦将得到某种力量的制裁,而这个制裁者则是原本处于沉默地位,不起作用的“自我”,这是悲剧特有的模式,也是《原野》的深刻之处,没有人能够带着罪恶安然地离开,他必将走向毁灭。
仇虎逃向黑森林后,并没有获得复仇之后的成就感与满足感,而是陷入了深深的不安与谴责之中,他对自己良知的谴责,不只是他杀死了那些无辜的人,更多的是仇恨带给他的苦难,他身上肩负的复仇重担彻底压垮了他,使得他找不到他的“自我”,一个善良的灵魂,一个追求爱情友情的灵魂,当他的“自我”向“超我”做出屈服开始,爱情、友情等一切感性的东西都可以为他理性的复仇计划做出牺牲与让步,他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疯狂寻仇的人,他杀死了仇人,却杀不掉自己内心的仇人.
“自我”與“超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仇虎的分裂,在这种“自我”屈服中遭受着酷刑与煎熬,这是他必将在无尽的原野中承受的苦难,这是“自我”没有得到保护的苦,是“自我”对外在力量的“屈服”之苦,是“自我”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挣扎之苦。读者在走不出的原野中感受着自己生命中无法摆脱的困境与失落,在仇虎的无助中寻找着自己内心的自由与热情,每个个体的现实体验与故事的悲剧形成同构,唤醒灵魂最深沉的自由与渴望。
三、“自我屈服”的救赎与净化
仇虎复仇成功所带来的生命的毁灭感,并不是作者想要传达的理念,当我们还沉迷于血腥的残忍、悲痛于无辜生命的死亡,曹禺又将这所有的情感试图消解在茫茫的原野中,第三幕中仇虎和金子一同逃奔黑森林,那里“盘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森林中到处充满着恐惧,“无数的矮而胖的灌树,似乎在草丛里伺藏着,像多少无头的战鬼”,黑森林作为《原野》叙事的中心场所,从始至终都在建构着一个完整的隐喻世界,是仇虎和金子走不出的心灵困境,正如“那禁锢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永远摆脱不掉命运的泥淖。
中西方文化中,“树”都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圣经》中“树”象征着智慧,从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开始,人类便走上了罪恶的流浪旅程,而在《佛经》中,“树”象征着醒悟、觉悟,代表着赎罪等,是一种启发性的意象,因此黑森林的两面性便象征着仇虎和金子心灵的两面性。
仇虎第一次从黑森林出来是为了复仇,是原罪的开始,再一次逃入黑森林则是良心的谴责与不安,由此而带来的拷问和救赎,从“原罪——赎罪”的过程也代表着从“超我——自我”的转变,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式结构。
吉尔伯特·墨雷认为“悲剧冲突的真正特点”是“一种神秘的成分,其最后根源出自古代宗教的净化和赎罪的观念”,即“悲剧主人公的死亡或没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净化或赎罪的牺牲的性质”。④仇虎的死亡正是这一悲剧的原型模式的再现和发挥,因此自杀的结局对仇虎来说正是他走向新生的开始,也是他摆脱命运的枷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渴望,而这种呼声与困境在“今天的经验中也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存在着”,唤醒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体验与感受。
仇虎在逃亡的过程中,“惊惧,悔恨与恐怖交替袭击着他的心,在这一刹那几乎使他整个变了性格,幻觉更敏锐起来”,被他所残害的焦大星、瞎子、小黑子都开始在他的眼前出现,而他的妹妹、父亲的悲惨遭遇也频频浮现,“幻象”的出现也并非只是仇虎内心的不安,作者试图利用“幻象”去找回仇虎的“自我”人格,荣格曾在《无意识心理学》中考察将死的主人公在个人幻想中呈现出来时候的象征,他认为:“这象征近于一个趾高气扬的幼婴人格——这是一个孩子的自我,如果情欲进一步积极活动起来,这个孩子的自我必须牺牲掉。”⑤
仇虎在仇恨中杀掉了“自我”,他的人生一开始就不由自己做主,正如他所说:“我们是一对可怜虫,谁也不能做自己的主,走这条路都是被人逼的。”从焦阎王弄得仇虎家破人亡开始,仇虎就再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与期盼,再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幻象”中,作者为仇虎描画了一个自我的“补偿类型”,补偿他敢于抗争命运的不公,补偿他对焦大星、黑子、焦母的愧疚与悔恨,补偿他在社会的压迫面前牺牲掉的“自我”,补偿他不向社会活动强加的“超我”而屈服的原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