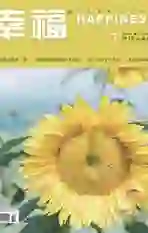又见炊烟升起来
2020-08-20李燕
李燕
父亲平时住在老家,春节这段时间,我们留父亲多住些日子,他开始不愿意,说是年龄大了,和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怕打扰我们。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好说歹说,父亲总算同意了。
过了一些天,父亲开始心心念念,不是担心寄养在邻居家的狗被饿着,担心鱼池里的小鱼小虾被人偷走,就是担心地窖里面存放的甘蔗都烂掉了……
我能理解,即便在儿女家的老人生活得再好再开心,也终究抵不过自己的家,老人已经在自己家里待习惯了。
俗话说,老小老小,老了就像个小孩子。开心时,他会笑,笑得直流口水;委屈时,他会哭,哭时掩袖抽泣。每每不小心弄掉了米饭,他会用只剩半截的大拇指配合食指,将掉到衣服上的饭粒拈起来再递进嘴里;每晚睡觉的时候,只有电视会陪伴着他,对他不离不弃;每晚起来上厕所,在隔壁闹出的动静总会很大,一高一低的脚步声足以在夜深人静时震耳欲聋,将我的心揪得老紧。
父亲前些年因意外伤害导致左脑受伤,右腿不受控制,还因右脚后来又受过一次伤,我担心他身体失衡会磕碰到哪里,甚至担心他会不会从三楼楼道摔倒滚到一楼去……直到他从厕所出来,“咚咚咚”的声音响起来再消失我才又安心睡去,一晚几次,如此反复。
有时我也会很纠结。先生和孩子们不让父亲多动,跟他端茶放洗脚水,开饭前把饭和筷子送到他手上。而我担心的则是他缺乏锻炼,回家之后会不会不适应,是不是对身体反而不好?每每此时,先生一句“我们就该好好待他”以此打消我的疑虑。
实在拗不过父亲要回家的念头,我们决定送父亲回去。
一路通畅。路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车,车子载着一路春风,也载着父亲久违的期盼回到了家。
天公很配合我们,太阳出奇的灿烂,将久久的阴郁一股脑儿收了起来。
下车,开门开窗,一股股霉味狠狠袭来。一看,原来是偏屋里的几桶柚子、几个肥胖的冬瓜和南瓜都霉得黯然失色,像一个个久病的人伤了肝烂了肺。简单地清理之后,我们又抱出衣服和被子,铁架、铁栅栏一会儿就被铺得满满的。
洗衣机也沉寂了许久,正好让它也好好运动一番。
再放眼一望大院子里的那块菜园子,还真是“满园春色”:
燕麦已大半人深,将腰勾背驼的大蒜薹遮得严严实实的;茼蒿頭顶土黄色圆盘似的花瓣,探出瘦长瘦长的身子;红菜薹、白菜薹、菠菜挥舞着手臂,像在问候主人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这段时间,它们没有主人的关怀与问候,寂寞地生长。
忙了一阵子,该是做午饭的时间了。
我们做完厨房卫生,拜托电饭煲蒸上饭。拎着菜篮子,去几步开外的园子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点现成的菜回来。
豌豆藤开出紫色或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稀稀落落的,藤蔓爬满了周围的院墙,可是豆荚却是相当的少。转了一大圈,里里外外老老少少加起来估计没两盘子。
蒜薹就更难抽了。暗藏在远远高于它们的燕麦之下,被鸠占鹊巢。见我无从下手,面露难色,父亲拿着镰刀,踉踉跄跄地走来,弓着腰割掉了那些燕麦,让一根根蒜薹暴露在阳光里,算是帮它们出了口闷气。
家里有煤气灶,但我决定用土灶炒菜。
很久没有闻到柴火的香味,没有看见袅袅炊烟。如今,父亲的烟囱外炊烟再起,真好!
炒菜时,隐约听到摩托车的响声。后来我问父亲,他说是村长看到父亲回来,过来问候了几句。
三个人的中餐很简单:五花肉炒蒜薹、清炒豌豆荚、红烧豆腐。没做汤,但也吃得有滋有味。
吃完饭,与父亲坐在客厅里聊了很久,尽管在这之前也聊过。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这些天的计划。我说,就请人付点工钱,让他帮你割掉这些杂草吧。他说,不用。好久不干活做起来是没有以前轻松,但我每天早上只割一块地,就用几天来对付吧。等把草都除完了,再翻好土,栽上四季豆、辣椒、丝瓜等秧子,用不了多久,又有吃不完的菜。我嘱咐他要知道休息,累了就歇歇。
说起来,我和先生真是惭愧,看着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也许,我们都在为帮不上忙找借口,能做的就是帮他买些好用的农具,再偷偷地放点钱塞在枕头下面。
残疾的父亲,他决定要留守在这里,面对地里的农活。这么多农活,怎么做得完。
父亲安慰我们说,不怕,我慢慢做,没问题。
可他的腿……让人悬着的一颗心如何能放得下呢?
临走前,父亲不忘让先生把甘蔗窖打开看看。只见先生趴在地上,用双手刨开铺在上面的厚厚一层土,然后往外拎,一根两根……臭味扑鼻,我赶忙捂紧了鼻子。看到此景,父亲满脸的无奈,我们也唏嘘不已。
幸亏父亲开朗,难过一会儿之后已收拾好心情。他说,今年再种!
父亲在我们车后愈来愈远,瘦小的身影刹那间便消失在反光镜中。
所幸,他屋顶的炊烟又会按时升起。
静静的夕阳快要落幕,大地饱满又辽阔。我不禁望向窗外这片绿茵茵的田野,深深祈祷:愿父亲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