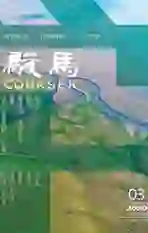疯婆子
2020-08-18于芳潇
于芳潇
“我想杀人!杀了那个疯婆子!”
雷小佳把车钥匙重重地砸在我桌上,“嘭”的一声,惊得正在低头看手机的我,头发竖了起来。
我很生气。再怎么着,我是他的顶头上司,平时对我很尊重,现在却在我面前奓翅,摔碟子摔碗,大脸拉耷着比驴脸长,反了他了。
“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讲!杀人?给你把刀都扛不住,给你把枪不会搂火!”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拍了拍他微微颤抖的肩膀。
雷小佳脸色铁青,嘴里好像嚼着一只小老鼠,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腮上的肌肉横成一棱棱的形状,突突跳动着。眼睛里好像爬着一条黑色的蜈蚣,随时会冲出来咬人的样子。
他说的疯婆子是刘阿婆。我很惊奇,刘阿婆有那么大本事,能把性格温和的雷小佳气得如此狼狈不堪?杀人嘛,不至于,怎么说他也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我和他都在一个街道办事处负责拆迁工作,怎么可能去做违法犯罪的事。
“我现在被挤巴得不成人样了,你用大铁锤呼呼往头上砸,砸得我血糊满面。那个疯婆子用千斤顶往上扛,顶得我的骨头喀嚓喀嚓响。我这身子骨成木头片了,风一吹就倒。这日子还有法过吗?夜夜失眠呀!”雷小佳胸脯剧烈起伏着,像涨潮时的大海,有风,更有浪,呼啦啦澎湃着。
我知道雷小佳说的是马二巷拆迁。昨天,我去过那里。不知存在多少年的民房大部分已经被推倒。水泥块、红砖块、破布、旧沙发、破柜子……一片狼藉,好像发生过地震一般。
在一片废墟中,有一栋孤零零的房子站立着,好像是用纸片折叠而成,很瘦。风一吹,就会飘散了一般。房前有兩小溜花地,栽了一棵葡萄,还有三四株开得正艳的月季。葡萄顺着院墙,枝枝蔓蔓地爬进了院子里。月季花坠着暗红色的大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摆。在一片陈旧的气息中,隐隐约约浮着一股清香。竟然还有几只蜜蜂隐在花瓣中。暗红色的木头门,斑驳着。看来刘阿婆是一个老住户了。
马二巷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片区,又破又旧,像一块折了无数次的黑布,随意地丢弃在城中央。不知什么年代建造的黑瓦石墙的老房子,紧鼻夹眼,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一般,夹在高楼大厦之间。小巷又深又长,坑坑洼洼的地砖和破损的墙壁上,长满了深绿的苔藓。两个人对面走,碰了面,需侧身而过。这里的居民盼了多年的拆迁改造,终于在今年年初开始启动。
雷小佳曾经喜气洋洋地告诉我:“搞了这么多年拆迁,马二巷工作开展得最顺利,居民敲锣打鼓欢迎我们。进展迅速,像喝面条一般,呼呼隆隆进了肚子,痛快!”
这才多长时间,雷小佳却碰了个头破血流。我知道他的工作水平,在以往的拆迁工作中,不管有多难缠的硬骨头,他都会侧敲旁击做通住户的工作。这个刘阿婆难道是钢做的?碰得雷小佳这个工作能手找不着北?
“看来需要你领导亲自出马了。我是草鸡了,肚子里的二两油都涮光了,再涮下去,肠子就破了。如果再攻不下这个山头,会影响整体工作进展。”雷小佳抚了抚乱糟糟的头发,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决定去见见这个刘阿婆,摸摸她不肯搬迁的原因。这个纽扣即便是铁做的,也要用温和的手段解开。让每名群众满意,是我们工作的职责。
刘阿婆家的情况我知晓一些。五十多岁,老伴十年前已经去世,孤身一人生活,和邻居交往不多。邻居说,她老伴在世时,多是他对外处理事情,很少看到刘阿婆的身影。老伴去世后,刘阿婆深居简出,很少与邻居打交道,能和她搭上腔的没几个人。
我和雷小佳去超市买了点水果和营养品,来到刘阿婆家。我敲了很长时间的门,却没有人应答。院子里传出了很嚣张的狗叫声,在空旷的废墟上,越发听着凶猛。
“她肯定在家里,故意不给开门的。”雷小佳站在葡萄树下,随手摘下一颗半青半紫的葡萄丢进了嘴里。“挺甜,看样子是喂豆粕了。”
我顺着门缝往院子里看,一只黑色的小泰迪,上蹿下跳,龇牙咧嘴叫唤着。院子收拾得特别干净,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阳光如一层薄纱,轻轻笼在灰白的地面上。
我继续敲着门。也许她年岁大,耳背。我不相信她故意不开门。敲了一会儿,终于传出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走路声。她呵斥了狂叫的小狗一声,小狗绕在她身边,哼哼唧唧撒着欢。
门开了一半,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的刘阿婆盯着我。她的皱纹又多又深,纵横交错。我想起了大山里雨水冲刷后的沟沟壑壑。她的眼睛像兔子眼,红通通,布满了血丝,一层泪水随时要滚出眼眶的样子。
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不言不语。小狗跑到我脚下,探出鲜红的小鼻子,嗅来嗅去。
“我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今天专程来看看您……”我晃了晃手里的水果和营养品。
刘阿婆目光转到了雷小佳身上,很熟悉的样子。看样子,俩人打交道不止一次两次了。雷小佳半蹲着身子,脸靠在月季花上,贪婪地闻着浓浓的花香。他伸手想要掐一朵花。
“别动,掐我的花砍你的手!”声音有些凶,目光凌厉。刘阿婆的声音吓得雷小佳缩回了手。他的脸瞬间像喝醉了酒,潮红一片。
刘阿婆开了门,枯瘦的身体像一根腐朽的木头,大幅度左右晃动着,迈着蹒跚的脚步,往屋里走去。阳光被她的身影切割开来,一块一块像补丁缝在地面上。
屋里很清洁。地面没有铺瓷砖,而是很少见的水泥地面,还有水迹,看样子刚刚拖过。灶台擦得锃亮,锅盖反着亮晶晶的光。一张暗紫色的八仙桌,年月肯定很久了,结结实实地摆在屋子中央。桌子上摆了一个瘦腰胖肚的瓷花瓶,插了一枝带着两片绿叶的月季花。娇艳的暗红色花瓣上凝着几个圆圆的水珠,越发娇艳。一台浅红色的电话机,与花瓶并排摆放着。一根电话线,穿过客厅,在地上大摇大摆伸着腰身,爬上桌子,连着话机。
我很奇怪,刘阿婆为何要把话机摆放在这里。蜿蜒的电话线,不影响她活动吗?
刘阿婆扯过两个凳子,示意我和雷小佳坐下。她抱着小狗,爱怜地抚着它的头。小狗伸出浅红色的小舌头,舔着鼻子,伸了个懒腰,很享受的样子。
“我今天来看看您,是想征求您对我们拆迁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我们工作有漏洞,您尽管提,我们改正。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大家有个更好的居住环境……”我清了清嗓子,开始做起了她的思想工作。
雷小佳沉默不语,脸上有着深深的无奈,像一个长满了绿色浮萍的池塘,看不到粼粼波光。他扯起电话线,缠在手指上,在手里把玩着。
“别动!弄断了怎么办?”刘阿婆好像对雷小佳有意见一般,说话一点不客气。雷小佳尴尬地扔掉电话线,缩回了手。
我吧吧讲了半天,嗓子里好像放了一块红炭,又干又涩。刘阿婆脸上波澜不惊,一副置之度外的样子。她盯着桌子上的月季花,眼睛很长时间竟然不眨一下,然后流出了几滴清泪。她不去擦,任由眼泪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摇摇欲坠,却没有掉落。眼睛更红了,像电压不足时,灯泡暗红的钨丝。
我看到她流出的清泪,特别别扭,很想提醒她擦一下。犹豫了很长时间,我也没开得了口。我想起了故乡大山里的一汪泉水,无论干旱,还是暴雨,水位不升不降,宠辱不惊的样子。这汪清泉,是山里野兔、刺猬、蛇等各种小动物的生命之源。
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联想,眼泪怎么能与泉水划等号呢?八杆子打不着哩!但是细一琢磨,又有某种说不清楚的相似之处。
“您对补偿标准不满意吗?这么长时间,没有一家住户提出异议!”我小心地问道,看着她的脸色,生怕哪句话不合适,刺激到她。窗外的阳光越发浓烈,像一杯浓茶,肆意泼撒在水泥地面上。
刘阿婆闭上眼睛,轻轻摇了摇头,又有几滴清泪滚了出来。她怀里的小狗迷瞪着眼,似睡非睡的样子。
“你是不舍得离开这里?我知道一些老人不愿意离开老房子。但是政府都替你们考虑到了,楼房盖好后,可以马上回迁。这期间,过渡住房都安排好了……”我吞了几口唾沫,其实没有唾沫,只有干涩的空气,刺得嗓子又涩又痛。
刘阿婆睁开眼睛,又摇了摇头。她目光散淡,很累的样子,就像撒在蛋糕上的黑芝麻,星星点点,却拢不起力量。
“你们走吧!我不会搬的,除非我死了!”没想到,刘阿婆这时说出的话咬钢嚼铁,很有力量,不容人有丝毫的反抗。
我半天没吭声,肚子里生气,却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瞅着那条幸福的小狗。它的黑毛瞬间变成了一块无边无际的黑布,蒙在我的头上。
我和雷小佳灰头土脸,灰溜溜地出了刘阿婆的家门。来了一趟,连刘阿婆不肯搬迁的理由都没搞清楚。这工作开展的,憋气!
“就是一个铜扁豆,咬不动,嚼不烂!谁能撬开她的嘴?我前几次来,好话说尽,只差下跪了,鸟毛都没捞到。”雷小佳撿起一块石子,斜着身子扔了出去,身子又像弹簧般缩了回来。石子像一只扑棱着翅膀的小鸟,冲进了远处的废墟里,激起了一团灰白色的烟雾。
“找她的亲戚,好朋友,帮忙做工作。”我也头疼,感觉刘阿婆像个烫手山芋,又像一块掉进草灰里的热豆腐,吹不得打不得。
“拉倒吧!她这里有一两个亲戚,多年不走动了,根本靠不上边。也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平时独来独往。”雷小佳脸上挂着不耐烦的神情。看来,刘阿婆已经消磨了他的干劲。
能有什么办法?强拆?是万万不行的!与政府的政策相违背。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多来几趟,用温情感化她。
第二天上午,我第二次来到了刘阿婆家。雷小佳找了个理由请假了。我心里清楚,他是在躲避刘阿婆,把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扔给了我。我心里也没了底,不知道牙口能否啃得动。
我敲了很长时间的门,一点反应没有。那条小狗的叫声没有响起,院子里静悄悄。我判断刘阿婆出门买菜了。葡萄和月季花被浇过,叶子绿油油,花瓣红得深沉,萄萄像透明的水滴,香甜诱人。
果然,不到十分钟,我看到刘阿婆提着玉米皮编织的手提篮,低着头,急匆匆地赶了回来。小狗在她脚下绕来绕去,不时打个响鼻。
刘阿婆见了我,头不抬,眼不睁,一声不吭地进了家。我羞咧咧地跟在她身后:“阿婆,去买菜了?”
她晃了晃手里翠绿色的芹菜,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她放下菜,一阵风一般刮到了电话机旁,探着身子看了半天来电显示屏幕。然后身子慢慢缩了回来,脸上蒙了一层深深的失望。
“阿婆,今天又来打扰您……”我的话还没说完,刘阿婆坚定地举起了手,截断了我的话题。
她闭着眼睛,脸憋得红通通,喘着粗气,说:“还是那句话,我不死,不搬家!你走吧!”
“为什么呀!总得给我个理由呀!”我有些生气,这个古怪的阿婆好像迷雾,让人看不清,摸不透。一股痒痒挠挠的恨意从我心底升了起来。如果她是一个年轻人,我会伸胳膊露腿地和她好好切磋探讨一下。但是她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虎咬天,无处下口,有劲无处使。必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那条小狗,仿佛会察言观色,围着我的腿,呲着雪白的小尖牙,呜呜叫着,随时下口的样子。看来,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不告诉我你不搬迁的理由,工程开工后,只能断水断电,会影响你的生活……”我边后退边说,小狗汪汪呜呜地叫着。
刘阿婆拿起八仙桌上的水杯,倾倒在我脚下,水珠溅湿了我的裤角。
我落荒而逃,狠狈不堪。
我打电话把雷小佳找来,不能让他躲在门后看热闹。他必须和我一起冲锋陷阵,攻克刘阿婆这个山头。
雷小佳脸丧丧着,如丧考妣,嘴里咝咝啦啦抽着冷气,抽得我浑身发冷。
我俩分析了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相对无言,坐着抽闷烟。
“只有一条路可通……”雷小佳重重拧灭烟头,话却犹犹豫豫。
我瞪着他,等他继续说下去。
“断水断电,把她逼走……”雷小佳手插进头发里,仰头瞪着屋顶,半天才说出这句话,好像卡在喉咙里的一个枣核,终于被挤了出来。
“嘁,你以为我没想过?一个违背政策,咱们不是黑社会,要把好事办好。二个那么大岁数的老人,不能惹她生气,万一气出好歹来,怎么交待?”我心里清楚办事的底线,不能乱来。
“实在不行,可以先把她家的电话掐断。这样不影响她的生活,至多电话不通。投石问路,探出她不肯搬迁的原因。”雷小佳又点了一支烟。袅袅白烟,在头发里盘来旋去,好像一个生着红炭的铁盆。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烟雾幻化成一条狗、一只猫,然后飘散得无影无踪。我仿佛看到了孤零零的刘阿婆站在家门口,手遮在眼眶上,眨着红眼,流着清泪,望向远方。含有土腥味的微风轻轻吹过,她的花白头发飘散开来,像一个大大的,蓬松的棉花糖在招摇着。她在看什么?盼着什么?我不知道。
雷小佳的提议,在目前的困境中,算是一个上策。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行,就这么办!”我下定了决心。
停刘阿婆家电话的事办得并不顺当。电信公司说,用户每个月准时来交话费,从来没欠过一分钱。又没提出停机或搬迁电话的请求,怎么可以随便给停机呢?用户来要说法怎么办?
我理解电信公司的难处。但这事不能停,头拱地,也要想办法办成。
我的高中同学大成在电信公司干副总,找他应该没有问题。大成在电话里哀声叹气,难处摆了一大堆。我火冒三丈,眼见我在深渊,你不拉一把?算哪门子同学?大成看我火气冲天,答应停机,但是出了任何问题,由我出面解决。我痛快答应,难道一个老太太还能把电信公司的大楼给炸掉?
第二天,我正在会议室开会,接受领导对工程进度迟缓的批判。我蔫头耷脑,败军之将的样子。这时,电话响了。我有不好的预感,一看,是大成来的电话。
“你快来吧,大爷!那个疯婆子疯了,又蹦又跳,骂人的话不重样,就差把楼点着了。”看样子大成真急了眼,都喊我大爷了,声音里的烟气味十分浓。我对大成心生愧疚,无缘无故给他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我真就不信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能怎么着?还真能捅破天?我来到电信公司,傻了眼,这还是刘阿婆吗?只见她花白的头发像炸了庙,天线一般根根竖直。滑稽的是,有一根白色的鸡毛和一根黄色的枯草扎在头发里。她脸色铁青,像深秋被霜打的紫茄子。每一条皱纹,都深深陷进肉里,像一根根导火线。眼睛红得吓人,好像眼眶里生了红炭,烫手。眼泪像开了闸,哗哗往外流。
她的声音异常尖锐,在营业厅里像秋风一般穿来穿去。我仿佛听到玻璃哗哗啦啦的响声,有随时掉落的可能。大厅里的营业员和客户,都抻着脖子看这个异常勇猛的老太太。
大成像个小学生一般,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尴尬的笑容。他脸上的汗水冒了一层又一层,鼻子上还粘了一块白色的餐巾纸,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他一看到我,像一个掉进深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快把她劝走吧!打不得,骂不得!影响了我们公司的业务开展了……”大成的手奓撒着,剧烈抖动着。
“阿婆,去办公室谈好不好?我今天就呆在这儿,您老的事不解决,我不离开!”我过去搀她的胳膊。一股抖动的力量,像电流一般传到我手上。
刘阿婆斜着红眼,不屑一顾,往重里说就是蔑视地盯着我。
“为什么停我的电话?我欠费了吗?”她的语速很快,像机关枪密集的子弹,朝我突突射来。
“我扶你去辦公室休息一下……”我能如何回答她?难道说是我的主意?还是告诉她是雷小佳的招数?
刘阿婆没再犟,随着我往大成办公室走去。我和大成都松了一口气,一人搀扶她一条胳膊。
大成把刘阿婆让到沙发上,倒了一杯茶水放在茶几上。我拿起茶杯,递到她手上。她喝了一口。一瞬间,不大的办公室陷入了深深的寂静中。气氛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清晰地听到挂在墙上石英钟指针走动的声音。咔嗒咔嗒的声音,像一根棍子搅在水里,搅得我心神不宁。办公桌上鱼缸里红黄的小金鱼,吐着白色的泡泡,上下游荡着。
“阿婆,能告诉我,电话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吗?”我的口腔又涩又硬,像硬生生塞进了一块干燥剂。
嘤嘤的哭泣声传来,刘阿婆捂着脸,身子抖动着,头发像片片雪花一般飘浮着。我和大成面面相觑,手足无措。
“我不是钉子户!”刘阿婆忽然抬起头,盯着我。血红的眼睛浮着一层蒙蒙的泪水。我现在很怕看到她的泪眼。我总想起枯井,深不可测,黑咕隆咚。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你是钉子户。我很内疚,工作没做细……”我说的话是真诚的,没有一丝虚假的成分。
“快把我的电话恢复,我求求你们了。我要回家,别来电话我接不到……”说完,她颤颤巍巍起了身,迫不及待往门外走去。
“安排人尽快给老人开通电话吧!”我像被抽去了骨头一般,瘫痪在沙发上。我呼出了一口粗气,感觉疲惫不堪。
“断线是你,接线也是你……”大成一边念叨,一边打电话。
我又来到刘阿婆家。弄不清楚她不肯搬迁的原因,是我工作上的失败。
刘阿婆没关街门,一推门就开了。小狗趴在院子里,无精打采地瞅了我一眼,用前爪抱着头,闭眼睡觉了。
刘阿婆坐在八仙桌前,像一尊石像,更像一段枯木,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电话机。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她收回的目光,转到我身上,声音沙哑,像钉子划过玻璃一般,说:“谢谢你!电话通了……”清泪又滚落了下来。“你坐着,听听我的故事……”
我坐在凳子上,知道刘阿婆要向我讲述她的故事。看着她的满头白发,我好像在翻着一册孤本旧书。
“我的女儿丢了,到今天,十一年零八十八天。女儿丢后一年多,我老伴急火攻心,去世了……”她颤颤地站起来,慢慢挪到一个衣柜旁,缓缓打开柜门,拿出一本相册,放到我面前。
我翻开相册,看到一个笑容如向日葵花般的女孩。她青春靓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独特气质。我想起了门前吹弹可破的葡萄和娇艳欲滴的月季花。
“漂亮吧?这就是我女儿……”说到这儿,刘阿婆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意,皱纹舒缓了很多。
“我和老伴结婚晚,一直不生育。我吃了无数副汤药,拜了所有能拜的神仙,才在三十八岁那年怀了孕。孩子一生下来,把我和老伴乐得,阴天也有太阳……”她沉浸在回忆中,话语暖融融的,完全没有了锋利的尖角。孩子是温暖她的阳光,是调拨心弦的巧手。
“孩子就是我俩的命。她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是,没想到,孩子在十八岁时,因为和她爸爸生气,赌气离家出走,找了许多地方,也没有找到。我老伴内疚得要死要活,很快得病死了。”她又抹起了眼泪。
我坐着,静静听着,不插一言。我知道,现在任何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
“孩子丢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个电话号码。我知道,孩子如果想回家,一定会打这个电话。我怕错过电话,出门从来不超过十分钟。”刘阿婆起身,拿起一块抹布,仔细地擦拭着话机,好像在抚摸一个孩子的脸。
“门口栽的葡萄和月季,是女儿最喜欢的。这么多年,我一直照料得很好。孩子如果回来,有花,有葡萄,该是多美。我不搬迁,是怕女儿找不到回家的路。”她沉重的叹息声,重重地捶在我心上。
“阿婆,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处理好……”我说道。
“叮铃铃……”这时,电话响了。
我和刘阿婆同时伸出了手……
责任编辑乌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