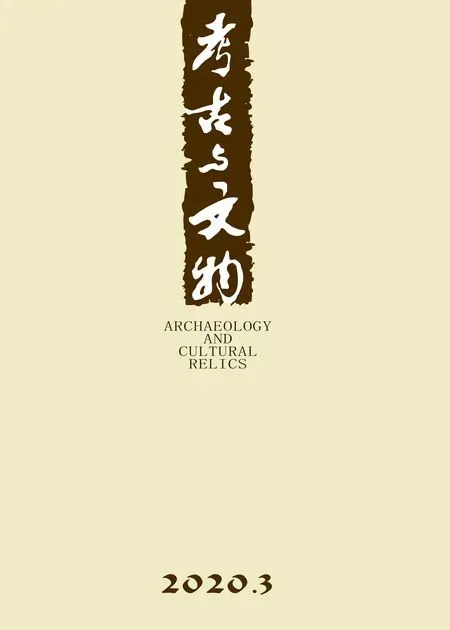妇姒启鼎与商代妇女称姓说*
2020-08-17雒有仓
雒有仓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旅游学院)
妇姒启鼎著录于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编号0046。该器的尺寸大小、重量目前未见公布,器物图像显示为扁足圆鼎,内壁铸有“妇姒启”三字。妇姒启鼎铭文虽然简单,但反映的问题较重要。兹写出我研读的意见,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妇姒启鼎时代
妇姒启鼎(图一)为立耳浅腹扁足式圆鼎,这种鼎形制各异,常见为中小型,口径不超过26厘米,最明显的特征是腹部较浅,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不多见。因此,《铭图续》将其时代定为商代晚期是恰当的。
进一步看,妇姒启鼎为窄沿方唇,双立耳,半球形浅腹,圜底,三条夔形扁足,足尾平直,具有立刀式向卷尾式过渡的特征(图一),俯视耳足位置呈五点配列式。这一特点与河南安阳戚家庄东M269商墓出土的疋未鼎(图二)相同。疋未鼎的时代为殷墟三期,扁足尾部上卷,形制应比妇姒启鼎略晚。从纹饰看,妇姒启鼎口沿下饰一圈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与瑞士玫茵堂收藏的商代晚期舌鼎(图三)相同。
二、妇姒启鼎铭文

图一 妇姒启鼎(铭图续0046)

图二 疋未鼎(铭图00652)

图三 舌鼎(铭图00162)
我们知道,甲骨金文记载的商代妇名,主要有妇某、某妇两类。“妇”作为已婚妇女称谓,多指王妃贵妇,某妇则指某国、某族、某人之妇。对此,学术界认识基本一致。然而,对于“妇某”之某,学界争议较大。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分别有女字说[6]、女姓说[7]、女名说[8]、女氏说[9]、女子私名说[10]等不同见解。目前,学者倾向于否定女姓说,主张“妇某”之某为妇女所属的国族名或父家族氏名[11]。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商代“妇某”之某较为复杂,除国名、氏名外,还有私名和姓。其情形犹如周代女子称姓,但金文女名仍有国名、族氏、行第、尊号以及单称名、字而不称姓等多种形式[12]。因此,面对新出现的“妇姒启”铭文材料,需要我们对商代妇女称姓的问题重新审视。这将有助于深入认识商代姓氏制度与婚姻制度。
三、商代妇女称姓说
商代妇女称姓,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然近代以来,自王国维提出“凡此记录,皆出周世。据殷人文字,则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同。诸侯以下之妣亦然。虽不敢谓殷以前无女姓之制,然女子不以姓称固事实也”[13]。此论一出,商代女子不以姓称之说翕然风行,至今仍被视为定论[14]。然而,新材料的出现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新著录的妇姒启鼎铭文(铭图0046)打破了商代女子不称姓的旧说。重新检视有关材料,我们以为“商代妇女称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否认。
关于商代妇女称姓的见解,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1939年唐兰指出:“妇好者妇子也,好为女姓,即商人子姓之本字,此武丁之妇。同姓不通婚姻,周之制也。”[15]唐氏的这一见解,实际上已否定了其师王国维“殷代女子不以姓称”之说,此为商代妇女称姓说之开端。1944年胡厚宣明确提出“帚妌、帚好之类,皆女子之名,亦即姓也。观武丁之配,有名帚嫀、帚周、帚楚、帚杞、帚、帚、妇庞者,嫀、周、楚、杞、、、庞皆其姓,亦即所自来之国族”[16]。此说虽未区分女姓与国名之别而显得不够精审,但无疑为商代妇女称姓说之滥觞。1948年丁山指出:“商为子姓,子应当从女作好,甲骨文数十百见的妇好夫人,正与武丁同姓,殷商王朝可能是与古代埃及、希腊一样也是实行族内婚制。”[17]此说肯定了内婚制与商代妇女称姓的存在。1983年张政烺率先找出卜辞“妇好”称“妇子”的例证(续存407、合集2833),确认“好”当读为“子”,即为商王同姓的女姓[18],进一步确定了内婚制下的商代妇女称姓。1985年张亚初指出,西周仲卣、仲师父簋铭文中的好姓,也是子姓的女化字,“好字作为好坏之好的出现,是西周中期以后的事情”,所以“殷墟卜辞和铭文中的妇好之好,是女姓,应读为子”,商王族实行父系内婚制,在族内婚制下的“商代妇女是既有称氏的,也有称姓的,称氏称姓二者并存兼有。”[19]同年,饶宗颐也指出:“殷代诸妇名称,多是地名,与诸子名每每相配合,应是邑号及族姓。”[20]1995年他在整理甲骨材料时,认为“帚下一字多同于地名,直可视为氏姓矣”,甲骨文所见古姓有姬、酉、蕲、杞、滕、任、荀、喜、环、衣、壴,“卜辞从女之诸字,皆女子专名,或即其姓”[21]。此论实际上已将商代妇女称姓,从内婚制推延至外婚制。1996年雁侠指出商代姓的使用有“姓+某”、“某+姓”两种形式,“商代晚期女子已开始称姓,只是女子称姓还属于偶然现象,未形成制度”[22]。2002年曹兆兰指出,商代已有妊、姒、姜等姓,分见于石磬、铜器和甲骨,“不过其用例极少”[23]。2005年赵林从古姓形成角度指出,商代女名尚未制度化呈现出“女子系姓”的现象,但“妇”所缀的氏名可以被女化,其中有些被女化的字就是古姓,如好、姜等[24]。2010年宋镇豪指出,甲骨文“妇”前后相缀的女化字,有些是姓,如“妇妊似为妊姓,妇喜似为僖姓,姜妇为姜姓,妇为陶姓”等,但“商代女子称姓的确例毕竟不多……故与妇相缀的字是否是姓,尚应具体厘析”[25]。
与上述见解不同,1934年郭沫若率先提出“妇某”为人名女字说,认为其身份为“殷王之妃嫔”,又说“殷王之妣母以甲乙称,而妃嫔则以姓字著”[26],可知其在主张人名女字说的同时,又认为妇某中有称姓者。1956年陈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妇下一字常常是女旁的,它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女字即女名,一种是女姓”;作为女姓的卜辞例证有妇好、妇、妇妊,见于金文分别有好姓、妊姓、姜姓;但卜辞“妇某”与古姓相合者少,故“妇下一字是名不是姓”[27]。陈氏之说较谨慎,一方面指出了商代妇女称姓的主要例证,另一方面又认为“妇某”之某“是名不是姓”。后来,于省吾直截了当地说:“早期卜辞称妇某者习见,妇下一字都是妇的名或姓。”[28]这个见解不局限于把“妇某”之某看作一种成分,而认为其中包含名、姓二种成分,显然比陈氏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对此,学者们见仁见智。张光直认为“妇下的字到底是族名还是私名,恐怕还是未定的问题”[29],钟柏生表示“在没有找到确定证据之前,不敢肯定妇下一字都是代表姓”[30],沈长云认为“虽不好径作女姓,但至少是与女姓性质相近的氏族名称”[31],李学勤认为是女氏或女名[32],肖楠认为是“国名或族名”[33],赵诚认为是“私名”[34],曹定云认为是“母国的国号或封邑之号”[35],曹兆兰认为“有二种情况:一是‘妇+私名’,一是‘妇+出生国族地名’”[36],齐文心认为“代表该妇原来所属的国族”[37],陈絜认为“是该女子所自出之国名或族氏名号,也就是父家之族名”[38],赵鹏认为是国族名或私名,商代“女子不以姓称”,“从它们在殷墟甲骨文中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其说他们是‘姓’,不如说他们是‘国族’”[39]。
综上可知,商代妇女是否称姓的争议,主要是由于人们对甲骨金文所见“妇某”的认识不同,同时也与反映商代婚姻制度的材料缺乏有关。而妇姒启鼎铭文的发现,可以补充这类材料的不足,有助于揭示商代存在族外婚的事实真相。
事实上,只要我们抛开上述对具体材料理解上的分歧,从婚姻制度的角度来看,史实还是较为清楚的。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结构复杂,婚姻习俗千差万别,任何一个社会的婚姻制度都不可能整齐划一,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婚姻形式。正如周代实行“同姓不婚”但仍有同姓通婚的事例一样,商代在族内婚盛行的同时也有族外通婚存在。外姓女子嫁入本族,人们自然会以名与姓相称作为区别。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妇女称姓的情况。《国语·晋语》载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韦注:“有施,喜姓之国,妹喜其女也。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40]这个记载表明,早在夏商之际,已有妇女称姓的先例,如“妹喜”是“名或字+姓”形式,而商代晚期的妲己,也是己姓之女嫁入子姓商族中的称谓。正是由于她们所嫁分别为姒姓的夏王族、子姓的商王族,为了与其他妇女相区别,当时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用其名与姓相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称名形式在商代金文中也有例证,如商代晚期铜爵铭“遣妊”(8137)。“妊”为姓,“遣”为名或字,说明商代妇女确有以“名或字+姓”的称名形式。在同姓不婚的周代,这种形式的妇名较常见,如西周金文有鹚姬、幾姜、嬴以及嘉姬、姞、姒(4056、684、680、3903、3793、3849)等,说明妇女称姓大多与族外通婚有关。
商代妇女称姓,除内婚制下前人论述较多的个别女子称姓外,族外婚的存在实为妇女称姓的重要前提。因此,只要我们找到商代族外婚的例证,商代妇女称姓的事实就不难明确。《楚辞·天问》载:“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这段文字所述,其实就是针对子姓的商汤与姒姓的夏人后裔有莘氏通婚。《世本·氏姓篇》曰:“莘,姒姓,夏禹之后。”有莘即有侁,《吕氏春秋·本味》载:“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这些记载虽无商汤所娶有莘氏之女的妇名[41],但据此可知商代早期已有子姓王族与姒姓有莘氏通婚的事实。商代晚期,据《诗·大雅·大明》记载,王季之妻“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而有莘氏之女大姒嫁于周文王,“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思齐》云“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可知当时王季所娶挚国任姓之女的妇名为“大任”,周文王所娶有莘氏之女的妇名为“大姒”。“大”即“太”为身份高贵者的尊称,说明当时的妇名有“尊称+姓”形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周文王孙女嫁于妫姓陈胡公称“大姬”,可知与异姓通婚的周人女子也以姓相称。《大雅·思齐》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妇。”所谓“周姜”,《緜》诗称之为“姜女”,所指为姜姓女子嫁于古公亶父为妻者,说明商代晚期有“夫国+姓”的妇名。同类妇名,见于商代金文则有“者姒”(5935、5936),说明商代晚期的妇女还有“夫氏+姓”的称名形式。
众所周知,殷墟甲骨刻辞中有大量贞娩卜辞,贞卜对象多数是“妇某”,少数为“子某”。后者如:⑴庚午卜,宾贞,子目娩,嘉。贞,子目娩,不其嘉。王占曰:惟兹勿嘉。⑵贞,子媚娩,不其嘉。⑶□□卜,贞,子娩,嘉。□□卜,贞,子娩,不其嘉。⑷贞:子娩。(合集14034正、14035正丙、14032、17999)这些卜辞“娩”原篆为,作双手接生之形,是怀孕分娩之义,说明子目、子媚、子、子均为女性确定无疑。殷人子姓,按“女子称姓”惯例,可知这类妇名应为“姓+名或字”的结构形式,即为商代子姓女子称姓之例。同类妇名,见于商代金文还有姒康、姒丩(1906、9098),见于西周金文则有姜萦、姜淠(3772、4436)等,见于文献则有前述古公亶父所娶姜姓女子称“姜女”以及周人始祖后稷之母曰“姜嫄”等。《诗·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经典释文》:“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42]《史记集解》引《韩诗章句》曰:“姜,姓。原,字。”[43]说明“姓+名或字”是商周妇女称名的常见方式。1965年陕西长安县沣西大原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器子黄尊,铭文有“子光赏姒员”云云(6000)。其中“姒员”就是姓下加名或字,也是较典型的例证。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长条形石磬刻辞有“妊冉入石”四字,发掘者认为“妊冉”是族名或人名,“原意大概为妊冉入贡之石”[44]。其实,“冉”原篆作,应释为“竹”,国族名。“妊竹”是妇名,其命名方式应为“姓+国族名”,铭文原意应是“妊竹入贡石磬”之意。前述妇姒启鼎铭文又有“妇姒”之称,表明商代晚期妇女称姓还有“妇+姓”形式。宝鸡戴家湾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铭文“女母作妇己彝”(10562),其中“妇己”向来被视为“妇+日名”形式,从新出的妇姒启鼎铭文看,“己”同妀,应为姓,其称名方式应当是“妇+姓”形式。以上事例证说明,商代妇女称姓应确定无疑。
按照《礼记·丧服小记》记载:“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郑注:“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孔疏:“此云书姓及伯仲是书铭也,姓谓如鲁姬、齐姜也,而伯仲随其次也,此亦殷礼也……殷无世系,六世而昏,故妇人有不知姓者……若妾有不知姓者,常称氏矣。”[45]这是文献关于商代妇女称姓的明确记载。孔氏所谓殷礼“六世而昏”,就是指殷商之族在六代之后,同姓可以通婚。在族内婚制下,对于六代之后嫁给同族男子的女子来说,由于她与丈夫同姓,而且生活在同一族内,自然没有称姓的必要。因为在族内婚的情况下若以姓相称,则同姓已婚妇女就无法区分彼此,所以当时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用氏名或私名来称呼同族内婚妇女,这样就会出现“常称氏”亦“称名”的情况。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甲骨文中为何会有许多妇名与“子某”或“某子”的氏名一致,而“妇某”“某妇”中还有许多与子名不一致的私名。正因为如此,宋镇豪指出:“商代女子出嫁前在母族一般有私名,出嫁后夫方亲称为妇,凡‘妇某’‘某妇’前后所缀除了谥干、身份区别和身份关系指示词之外,也有一些氏名,恐怕是经夫族据妇的出身氏族重新命名,妇在母族受有领地田产者,其名颇有“女子系姓”的意义,用来别其所出族氏。”[46]这是十分有见地的见解。按照这个认识,商代妇名中的氏称,应当具有“分辨出身”的作用,这是一些氏名逐渐转化为姓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商代盛行族内婚,商代妇名多见以氏名、私名或姓加私名为称,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妇名则以姓为称,这是由于当时存在族外婚的缘故。由于商代的族内婚与族外婚同时存在,所以商代妇名分为不称姓和称姓两种情况。从现有甲骨金文材料看,商代妇名不称姓而称氏、称名者居多,称姓者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不称姓不等于无姓,更不能由此推断“殷人似无姓”[47],甲骨金文许多不称姓的妇名其实大多是子姓商族。无论称姓或不称姓,商族子姓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综合文献及甲骨、金文材料来看,商代妇女称姓,至少有如下六种形式:⑴姓+名或字,如子目、子媚、子、子、姒康、姒丩、姒员、姜女、姜嫄。⑵名或字+姓,如妹喜、妲己、遣妊。⑶妇+姓,如妇姒、妇子、妇妊、妇己、妇姜、妇。⑷夫国或夫氏+姓,如周姜、者姒。⑸姓+国族名,如妊竹、妊冉。⑹尊称+姓,如大任、大姒、大姬。深入了解商代妇名称姓的这些不同形式,不仅有助于甲骨金文人名释读,而且对深入认识商代姓氏制度、婚姻形态,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融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a.吴大澂.说文古籀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8:49.b.裘锡圭.说㚸[C]//裘锡圭学术文集(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23-526.
[2]张亚初.对妇好之好与称谓之司的剖析[J].考古,1985(12).
[3]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802-803.
[4]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金文形义通解[M].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2864-2866.
[5]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41-243.
[6]郭沫若.骨臼刻辞之一考察[C]//郭沫若全集(考古1).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422-430.
[7]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C]//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36.
[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492-493.
[9]李学勤.论殷代亲族制度[J].文史哲,1957(11).
[10]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J].考古,1987(3).
[11]a.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7:33-41,114.b.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7-89.
[12]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C]//金文人名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460-465.
[13]王国维.殷周制度论[C]//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473.
[14]同[11]b:100,111.
[15]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M].北京:辅仁大学,1939:61.
[16]同[7].
[17]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8:55-56.
[18]张政烺.帚好略说[J].考古,1983(6).
[19]同[2].
[20]饶宗颐.妇好墓铜器玉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C]//古文字研究(12).北京:中华书局,1985:306.
[21]饶宗颐.论殷代之职官、爵、姓[C]//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34—937.
[22]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109-112,137.
[24]赵林.论商代的母与女[J].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05(10).
[25]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08-409,445.
[26]同[6].
[27]同[8].
[28]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J].历史研究,1959(11).
[29]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C]//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148.
[30]钟柏生.帚妌卜辞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C]//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1),1985.
在天然湿度状态下的土层中开挖沟槽,且地下水位低于槽底时可开直槽,不设支撑,但对槽深有限制要求:砂土和砂砾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0 m;亚砂土和亚黏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25 m;黏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5 m。
[31]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迁[J].历史研究,1997(6).
[32]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J].历史研究,1991(5).
[33]肖楠.再论武乙、文丁卜辞[C]//古文字研究(9).北京:中华书局,1984:163.
[34]赵诚.诸帚探索[C]//古文字研究(12).北京:中华书局,1985:99,104.
[35]曹定云.“妇好”乃“子方”之女[C]//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83.
[36]同[23].
[37]齐文心.妇之本义试探[C]//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54.
[38]同[11]b.
[39]同[11]a.
[40]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250.
[41]丁山认为有莘之妇即甲骨文“妣丙”“高妣丙”。参见丁山.商周史料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8:44.
[42]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46.
[4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一册)[M].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145.
[44]中国社会科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99.
[45]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18.
[46]同[25].
[47]同[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