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无声息的悲伤
2020-08-04王雁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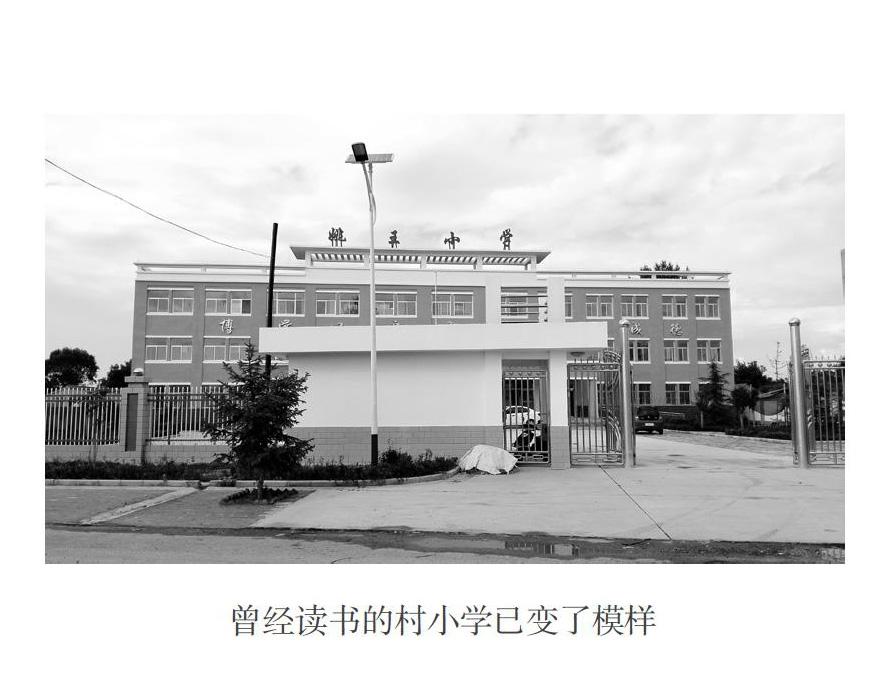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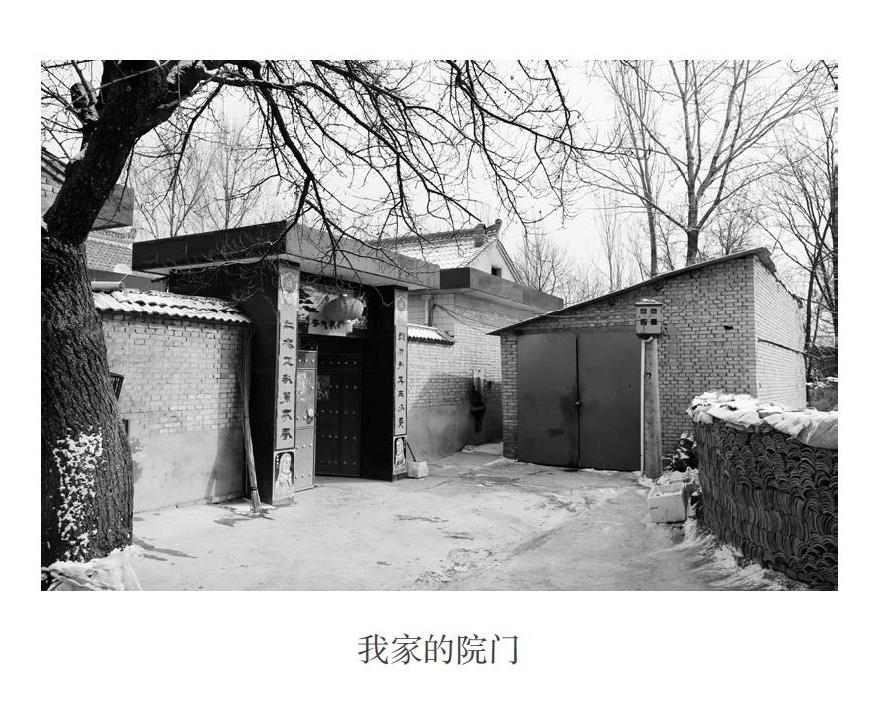
→ 王雁翔 甘肅平凉人,作家、资深记者,现居广州。诗歌、散文作品见诸《解放军文艺》《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天涯》《作品》《滇池》《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作品曾获第十三届、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年度精品奖,长征文艺奖等,出版非虚构作品集《走在高高的山冈上》,散文集《穿越时光的河流》《我的故乡下雪了》等多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
一
我在村子里闲转,几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女人从身边过去,都回头看我。他们或许心里疑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村子里瞎转什么?
我不晓得他们是村里谁家的儿孙、媳妇。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村庄对我是亲切、熟悉的,亦是陌生的。
经过长庆家屋后,几个女人坐在阴凉里埋头做针线活。“这人是谁?”“你们不认识,那是谁谁的三儿……”她们的问答、议论从身后传来。
我忽然记起,那个称呼着我母亲辈分说我的老人,正是长庆的老伴儿。
长庆是四年前过世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生活,她一个人守着一座空荡荡的院落。
我跟她们之间,隔着一段并不算久远的时光。长庆老伴头白得像顶着一层梨花。她是那堆女人里唯一认识我的人。
这个村庄是我人生所有秘密的源头。我离开村子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三十年时光,将我和这个村庄里的人,隔在了时间的两岸、生活的两岸。她和村里那些老人曾经看着我吵闹、奔跑、劳动。现在熟悉我的长辈越来越少,他们像深秋的树叶,被时间的风一片一片吹落,埋进了大地。
我已想不起她的名字,只晓得她是长庆的老伴,就像她知道我的乳名,兄弟里排行老三,在外头工作,其余皆被时间模糊。我的漂泊生活,对这个村庄里的人是遥远的、隐秘的。
繁密的杏花,从房前屋后、村道、崖畔、峁梁、沟涧,向远处川道里铺排、绵延。一树树粉红与洁白,在巨大的寂寥里肆意怒放。麦苗刚返青,还未挺起身子,耀眼的绿里,夹杂着一块块等待春播的空地。
田野里长满干枯蒿草的坟包多得让我恍惚,似乎村庄里的人,都一个一个走进了那些土堆堆。清爽的风徐徐漫过那些引人注目的坟茔,像吹拂一些古老的农具与传说。
二
这是我在外漂泊三十多年第一次清明回乡。
我转到梨花娘小屋前时,正是一天中的正午。梨花娘坐在门口的小凳上,静静注视着眼前干净、空旷的场院,仿佛场院里铺满了丰收的庄稼。门前三棵高大的杏树,花瓣随微风一层层飘落,在树下铺出偌大一片花毯。麻雀忽而飞起、忽而落下,像我儿时伙伴间的游戏。
旁边两座气派的庭院是她两个儿子的家。东边是辽阔的田野。天空瓦蓝,村庄和田野宁静而朴素。
她不声不响地注视着眼前的乡村世界,也注视着岁月留给她的种种伤痛。挥锄劳作,大呼小叫,驴嘶狗吠,那些曾经的日常,在她心里已瘦成黑白颜色的梦,遥远而苍凉。
身后小屋是她的家,低矮、窄小、简陋。她仍保持着年轻时干净爽利的习惯,屋内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杂物。靠窗是断砖垒砌的灶台,案板上两只碗、一双筷子,黄色塑料脸盆里有几颗土豆和一把芹菜,一个小篮子里十几粒鸡蛋。屋角一面大土炕,炕席上一床被子。
“哎哟哟——,你从远路上回来给我老大烧纸,看我老大,乖得有心得很。”说着,她把屁股下的小凳让我,自己转身从窗台上拿过一块砖坐。
我没坐她递过来的小凳,像庄稼人一样蹲在房檐台上。我觉得那凳子是一面墙,会影响我们说话。
她说的“我老大”,是我去世二十多年的父亲。
梨花娘生有三儿三女。四十多年前,她是一个眉清目秀、脚下生风的漂亮女人。性格耿直、爽朗,脑子活泛,人极勤快,持家过日子村里没几个女人能比。
儿孙们都在城里打工、念书,漂亮的四合院门上常年挂着锁。她栖身的小屋显得很不像样子。小屋水泥檩条上是薄铁皮,上边稀稀疏疏一层青瓦,像大户人家门外的杂物苫子,或者看场院的陋屋。铁皮屋顶防雨,却不挡寒热,夏如火炉,冬胜冰窟。
她的丈夫在十年前一个炎夏去世。她在三个儿子家轮换着生活过几年,小心翼翼,洗衣做饭,带孩子,但三个儿媳跟约好了似的,皆给她脸子看,指桑骂槐,摔碟子拌碗。她不想给儿孙们添争吵、烦恼,不声不响离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请人盖了这间小屋,一个人过生活。
她埋怨说,自己都七十九了,阎王爷咋还不来收她。声音沙哑,黯然。
那个闷热夏日,儿女们披麻戴孝,在声嘶力竭的哭声里为丈夫料理后事时,她或许在悲痛和疲倦里眺望、臆想过自己的晚年岁月。她知道老伴死了,剩下的日子就得一个人过。在农村,寂寞和孤独,是守寡老人生命尽头的一杯苦酒。
几年后,她发现自己的幸福在那个夏天,真的被丈夫带走了。生活比先前好了百倍,日子却轰然倒塌,碎成了一地瓦砾。那杯酒比她想象的更苦涩。
小鸟的欢唱,轻盈如花瓣,不时从树枝上飘落。我抬头仰望穹庐,天空澄静,白云如蚕丝。再过一阵,村庄及田野的梨花、苹果花、槐花、油菜花会争相绽放,整个视野将是花的海洋。
“我现在是一个没用的人,就盼着阎王爷早些收我走。”她说。她皱纹里的忧伤与哀愁,让我的思绪飘忽不定。三轮车在乡间柏油大道上突突突,商贩收购各种农产品的吆喝声,像天空的云朵,漫卷、盘旋、奔跑。
杏树下废弃的狗窝棚上,丢着残破的木犁和断头犁铧,露着大豁口的青石碌碡,乱石般在我脑海里击溅起牛马、犁铧的岁月。
这些曾被乡亲们视若宝贝的农具,正在黯淡、消失为乡村简史里细节丰沛的传说。
除了一些老年人的慢性病,她的身体还算硬朗,两餐简单的吃食后,她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眺望田野。有时候,鸟声和狗吠会唤醒她的沉思。丈夫的坟茔就在不远处,她在心里反复与他对话,沉浸在虚泛的往事里打发时间。
我们之間的闲话生疏、隔膜,时断时续。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一点她的情况,怕话头不慎触到她心里某些痛处,闲聊只能往时间的上游回溯。
生产队时代,靠挣工分分口粮。她家只她和丈夫两个劳力,跟我家不差上下,都住在崖畔不知年月的旧窑洞里,破门烂院,吃了上顿没下顿。从牛羊窑圈里往塬畔上挑粪,往大田里拉粪肥、割麦,多跑一趟,多割两犁麦,就能多挣一分工。她背上汗渍一层叠。她要用汗水多换回一点口粮,养活自己的六个儿女。
田间休息,别人坐在阴凉里说笑,她不歇,砍柴割草,地塄上挖出的一把冰草根,她也要拿回家去。割麦、碾场,掰苞谷,割豆子,揽荞麦,收什么她身上藏什么。有时被生产队长骂得涶沫星子乱飞,她从不吱声,像一个哑巴,呵呵地听着。转过身,仍旧不改。
我觉得她爱偷,并非习性,是现实的无奈与催逼。她含着泪的笑里有光,一大堆儿女就是她的希望与幸福。
母亲说,修水库和平田整地,活重,大灶上每人一餐三个玉米面窝窝头,她一餐留两个,自己饿得晕倒在工地上。
我坐在她对面,眺望、回忆她年轻时的故事以及她的儿女们。鸟儿在树上唧唧唧,欢唱与花瓣一起在微风里飞。
去年,她找村干部要低保。村干部说,你儿孙满堂,不符合规定,等过了八十领养老金。
她翕动着嘴唇,一句话没说,转身就默默离开了。
夏天,杏子熟了,一层一层烂在地里,没人拾,她去树下一筐一筐捡拾,没力气背,就分成小份,一趟一趟拿回家,洗净,晒一点杏干和杏核,卖给上门收购的小贩,能换两三千块钱。还有一粒一粒积攒在篮子里的土鸡蛋,就是她看病、生活的开销。
她的一群儿女,我已多年没碰过面。她是我敬重的人,在贫穷与饥饿的揉搓、拍打、碾压中,她和丈夫咬着牙,供孩子都读了书,大儿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毕业生。
村里从早到晚,一片寂静,很少有人串门,她孤零零一个人,万一跌倒在屋里,谁会及时将一双温暖的手伸给她?
三
豌豆娘热头热汗,正在简陋的灶台上艰难地给自己下一碗面。
门口的乡村大道上,不时驶过一些低档轿车,唰一声过去,卷起一股风,将门上的碎花蓝布门帘掀起又落下。我坐在进门靠墙一把咯吱响的旧木椅上,努力回想她曾经的时光。
豌豆娘八十岁高龄,头发花白,面容却光洁,脸和手背上看不到一粒老年斑,衣着朴素,说话不急不缓。她的贤惠与慈祥,让我心生温暖。
她说,你坐凳子上缓着,我把这碗面下出来。
她一手拄着一根粗糙的细木棍,一手扶着炕沿、桌子、墙壁、案板。借助棍子和屋里的固定物体,一点一点挪动身体。
我进门时,电磁炉上小锅里的水已沸,她身子靠着案板,窸窸窣窣打开小纸箱,捏出一小撮挂面丢进锅里,又丢进几根切好的白菜叶子和土豆丝。
面条和菜在锅里沸腾,她一边拿筷子搅动,一边对我说:“唉——,做了一辈子饭,愁得习习的(方言,实在够够的了),连一碗面都不愿下了。”
她把面一点一点盛到碗里,撒上盐和切好的葱末,淋一点香油和醋。一碗开水煮面,前后十来分钟,因为腿痛得挪不动身子,额头上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一个四五岁小女孩掀帘子进来,头发扎成一绺儿细细的小辫子,大眼睛忽闪忽闪,一脸若无其事。
“玲玲,你奶奶下午给你做了啥好吃的?”她笑呵呵问小女孩,眼里满是温情、慈爱和喜乐。小女孩不吱声,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对豌豆娘的问话不感兴趣。她盯着我打量了几秒,一句话没说,又转身掀帘子出去。
她说,刚进来的是豌豆的孙女。
“豌豆的孙女都这么大了?”我有些惊讶,脑子里嗡儿一声,瞬时觉得自己老了。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年轻着,女儿还在上高中。
“这是老二,老大是男孩,八岁,在城里上学。”她说。
她有三儿两女,豌豆是她最小的儿子,在外头当包工头,生有两儿一女,给仨孩子在城里都买了商品房。但我不知道,他已经当了多年爷爷。
她窄小的屋子干净、整洁,屋角塑料框里的粗炭,码得齐整的劈柴,看上去已很久没动过。见我目光落在电磁炉上,她开心地说:“豌豆去年回来,看我做饭生火、烧柴不方便,给我买了这么个电炉子。”
一股浓郁的肉香从门外飘进来。是屋后豌豆媳妇在煮肉吧。我心想。
她的小屋与豌豆家四合院只隔一面砖墙。从这边小屋绕到后边院子,不到十米。这是一个不愁吃穿的年代,儿媳做好饭,顺便给年迈的婆婆端一碗,只是举手之劳。看她忍着疼痛给自己下面条,我心里忽然莫名地难受。
坐在她的小屋,我有些恍惚,像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我知道人生有些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
我回忆起豌豆娘早年的岁月。小学四五年级时,我个子已蹿得很高,下午放学,有时也跟着大人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些农活是分组包干,有的大人不愿要孩子,嫌力气小,不顶事。豌豆娘看我落下,就会叫到她身边。她懂得一个穷困家庭的难处。
她会提醒我干农活要用慢劲,不能拼命把浑身劲往完里使,搬重东西,要试着慢慢往起拾,不敢使猛劲,闪了腰,落下病根,一辈子就干不了重活。
小屋不远处,是她二儿子的院落,也是她曾经的家。生产队解散前,她和丈夫看管队里的菜园和果园,负责机井每天早晚抽水、放水。井旁看园子的两间瓦屋,是她和丈夫临时的家。
园子很大,一半菜园,一半果园。
仲夏,月光如水,我和两个六七岁的同伴,从哗哗响的玉米地潜进园子。虫鸣声使月光下的田野无限寂静。远处她的瓦屋里亮着昏暗的灯光。风里弥漫着撩人的瓜果香气。
没想到她的丈夫一声不响地蹲在果树下等着我们。我们被拎到亮着灯光的屋子,她的丈夫虎着脸,说要把我们交给队里处理。我们浑身被露水打得透湿,吓得抖个不停。她给我们每人一根黄瓜和一个拳头大的小甜瓜。说:“快回家去,别让家里大人担心!”
瓦屋后边,是学校通往村子的公路。有时放学我一个人背书包路过园子,她会叫住我,笑盈盈地往我手里塞一个苹果或桃子。她知道我家没一棵果树。
在我十八岁离开村庄前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宽厚、贤淑、温柔的女人,与丈夫相濡以沫,没见她跟村里任何人红过脸。
生产队解散后,她家连着看园子的两间瓦房,新建了一处新院落。
她的老伴去世已好几年。因为腿痛,她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待在屋里。有时,她会慢慢挪到门口,坐在小凳上,跟碰面的熟人说几句闲话。
她大儿的家离她也不远,去学校、幼儿园、村委会、菜铺子、商店、赶集,去村文化广场跳舞,她的儿孙们每天路过小屋门口,会想到里边这位年迈、迟缓的老人吗?我不得而知。
我不说话,她也沉默不语,似乎失去了表达的欲望,抑或她觉得人生已没什么诉说的必要。她不知道,我的心里一直装着她许多不曾老去的故事,她青春、贤惠、善良的模样。
从豌豆娘小屋出来。东边一排商店、药铺门口,坐着一些老汉,有两堆围在一起下象棋。有几个靠墙蹲着,一动不动,有的半眯着眼睛,有的沉默着抽烟,有的发呆,互不理睬,疏远,一声不响。
只要不刮风下雨,那里每天会汇集一些老人。到了下午,他们起身夹着小凳,缓缓离去。田里的庄稼,播种、收割,施肥、喷药皆是机械,已不需他们操心。
豌豆娘和丈夫当年看园子的两间老瓦屋还在,断壁残垣。水池和抽水泵上的瓦房顶倾斜、坍塌,像一处遗址。曾经,我每天下午来机井上挑水,都能看见她家十多口人在旁边的院子里忙碌,说笑,饭菜飘香。早晚来机井上挑水、拉水的人川流不息,大呼小叫,热闹如赶集。田野上到处是忙碌的人……
岁月一闪而过,那些曾经的人间烟火,如远去的云朵。多么寂静,村子里没人,田野里也不见人,那些喧嚷之声都去了哪里?沉睡的巨大气息笼罩着房屋、村庄、树、田野,像那些屋角生锈、破损的农具,无声无息。
四
几十年的军旅生活,使我养成雷打不动、按时早起的习惯。太阳还未从地平线上升起,我独自在村里闲转,一阵难听的咳嗽声,剧烈、干澀、苍老,将我的目光与一个瘦削、单薄、低矮的模糊身影连在了一起。
七十六岁的桐子娘比我起得更早,正跪在门前的黄花菜地里干活。
她身后的院落,院墙坍废成若有若无的矮坎,一排瓦屋倒了一半,没倒的,屋顶上是一片一片凹陷的窟窿。她栖身的家,是一间简易板房。
没人知道,三十年前,她身后高墙大院里的瓦屋,像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一样引人注目,高大、敞亮、美观,人人羡慕。
悲剧像一颗闷雷,倏然间落进了她家。一个雾气浓重的早晨,因被骗而背上沉重债务的丈夫突然下落不明。消失前,他已做好了不为人知的盘算,大张旗鼓地和儿子分了家。
他走后不久,儿子也带着妻儿去城里打工,留下她一个人在困境里挣扎。
门前几棵高大苍老的核桃树,正在忙碌的半亩黄花菜,就是她一年的经济来源。
看到我,她停下手里的活儿,双膝跪在地里,一脸惊讶:“你啥时候回来的?”
“回来几天了。”我大声说。她的耳朵有些背。
一垄一垄的黄花刚探出嫩芽。她双手撑地,吃力地挪动身体,然后,将衰老的身子慢慢移到地塄上。腰比月牙儿还弯。
她的衰老让我惊诧:眼窝凹陷,嘴唇萎缩、凹削,腮帮子瘪着,沟壑般纵横的皱纹里,隐藏着人生的繁密沧桑。因为哮喘,她边说边咳,喘息急促,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让我心里不安、紧张,瘦弱单薄的身体,似乎一股风就会带向远方。
黄花的花蕾早晨开放,傍晚凋谢。太阳即将露脸,黄花头天采摘过的茎秆上,一夜之间,又会挺立起一簇簇细长如指的黄色花筒。
太阳还未升起,花蕾上闪着晶莹的露珠,她和女儿小丫准时出现在自家的黄花地里。那时,她不到四十岁,小丫十四岁,两个身着蓝色白花衫子的漂亮女人,提着竹篮,挽起裤腿,葱段儿似的手指在弥漫着香味的花蕾上欢快、娴熟地舞动。
这是她和女儿留在我记忆里如一段油画般美好的乡村图景。但眼前的她,几乎让我落泪。
她和我母亲关系好,常来串门,但四五百米的距离,对她是极其艰难的一段路程,要走近半个小时。
她的右腿患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不能动,只能靠左腿和拐棍,拖着半边身子一点一点往前挪动。
她来了,母亲会给她洗一个苹果或梨。她掏出生锈的刀片,一点一点削成薄片吃,一边慢慢咂味,一边跟母亲说闲话。有时,会让我跑水果生意的五弟帮她在街上买一点止痛片、盐或者醋。
她跪在地里干活,咳得厉害,我蹲在旁边说了几句闲话,心被巨大的悲伤、苦涩揉搓,一种难言的痛逼得我不得不转身离开。
我是回家前在城里偶然碰上桐子的。黄昏,我在泾河边散步,他和妻子牵着一只纯白、肥大的牧羊犬迎面而来。递烟,寒暄。从隔膜、简短的说笑里,我知道他是五家连锁超市的老板,大儿子上大三,小儿子和女儿即将高中毕业。
谁能真正读懂旷野上一棵树的孤独与坚守?
走出很远,我回头望脖颈上金链子比筷子还粗的桐子背影,心想,若他手里牵的不是一条肥狗,而是她母亲骨节粗大、衰老无力的手,或推着她的母亲在河边散步该多好。
五
小六像一只大虾,抱着膝盖坐在地塄上,妻子小莲埋头在地里忙着。
“种啥呢,地里一点墒都没,种下去能出来吗?”我问小莲。
“种洋芋呢,今年天旱的劲大(方言,天旱得厉害),种下等雨嘛。”
小六抬起头说:“是他碎爸吗,你咋回来了?”
小六七十三,也许七十四岁,但村里人仍像小时候一样喊他小六。
他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回老家跟小六碰面的次数很少,他竟能从我与小莲的说笑里听出我是谁。
“我瞎得光光,啥啥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他说。
“你儿有钱在城里买商品房,没钱给你做个白内障手术?”小六双眼患白内障五六年,没钱做手术,有人不信,老拿这话逗小六。小六头低到胸腔上,一声不响。
三年前,小六眼睛瞎了。但听觉极灵敏,隔老远,就能听出村里人的脚步声。
小六说:“我现在啥都要靠老婆子,她不在,我就饿死了。”
小莲去场院,去田里,去磨面坊,小六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脚步沉重,佝偻着腰,像一个蹒蹒跚跚跟着大人的孩子。妻子跟人聊天,他怀里抱一根棍子,默默坐在旁边。妻子在田里干活,他坐在地塄上,在无限的寂静里听鸟声、风声,听庄稼在风里拔节、喧哗。与那些没有心灵世界的人相比,小六有别人看不见的辽阔世界。
他说,生活好了,人心瞎了,好东西都被钱毁掉了。都不愿吃苦种地争着去当城里人,吃什么,喝西北风?以前地里啥野物都有,年年往里弄化肥农药,连只兔子都见不到了。天天吵吵着搞什么振兴,靠我们这些半死不活的老人和娃娃,能干个啥,得想办法让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来……
他絮絮叨叨,平静、隐忍,像自言自语。他黝黑、粗糙,皱纹如沟壑的脸膛上,看不到阴郁与焦躁。他在黑暗的世界里聆听、注视大地和万物。
我坐在宝峰家院子里,跟宝峰七十四岁的老母亲说闲话。宝峰的丰田越野车忽然刷啦一声,停在了院门口。
太阳快落山了,我以为宝峰夫妻俩会在家陪他母亲一宿,帮着收拾一下卫生,洗洗衣服什么的,没想到,他急匆匆卸下一堆吃食,前后不到半小时就一阵风似的离开了。
老伴过世后,据说宝峰娘在城里跟着两个儿子生活过半年。后来就死活不去了。
她身上的衣服看上去已几个月没洗过,衣服前胸上是一层层的脏污,厚实、发亮,裤子几乎看不出颜色。她腿痛,站立困难,不洗衣,也不做饭,吃完儿子带回来的吃食,就是开水泡馒头。馒头没了,就托人从集市上买些。
村里的老夫妻,不管有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几乎都跟儿孙们分开单过着。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村里独居老人的生活,像一道道利器,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着芜杂、粗粝、尖锐的光。是什么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隔在了幸福的岸边?
他们曾看着我从一个懵懂毛孩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我离开村庄时,他们都还是四十来岁的人,正当壮年,一边甩着汗瓣子忙农活,一边扶养老人和孩子。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刚包产到户不久,许多家庭日子还普遍艰难着,但忙碌、艰辛里,脸上都洋溢着欢喜。在耕讀传家的传统文化里,家家都是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一起,有欢喜,也有争吵,受亲情道德伦理约束,老人是家里的尊者,不管大人小孩子,孝都皆为大。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金钱、欲望膨胀下人伦道德的断裂、塌陷,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阵痛?抑或人心、人性从来如此?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的胡思乱想,像南方潮湿的龙舌兰,交织,攀缘,混乱得理不出所以然。
我相信,在他们漫长人生的种种滋味里,最难熬的也许不是曾经的贫穷和劳苦,而是晚年的孤独与寂寞。
米兰·昆德拉说:“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人都会老的,这是自然法则,生命轮回,谁也逃不过。
六
村庄仍然朴素、宁静,大地辽阔,万物生长。
我像一个游手好闲之人,每天在乡村古老、缓慢的时间里闲转。我知道有些消失永不再现。
在村口,我碰上明强,他戴着草帽,拉着架子车刚忙完田里一点农活往家里走。
明强是手艺人,可以出门挣大钱,但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这片辽阔的田野上,几乎没出过远门。
明强父亲去世时,他母亲五十多岁。那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毛孩子。
兄妹五个,明强排行老大,他母亲是“三寸金莲”,生活的重担主要压在他肩上。除了在近处揽些木工活挣一点钱,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里忙碌。
我离开村子时,村里许多青壮年已开始潮水般往外涌。明强有文化,会木工,能搭脚手架、砌砖墙,去做建筑工,是会拿大工工钱的。
他说:“家里有老人,走不开。”
有一年我回家休假,去他家拉闲。他九十一岁的母亲跌倒摔断了三根肋骨,卧床不能动,脾气来了拍着炕沿骂:走开,我不要你们陪,我知道你们都盼着我死……她任性,固执,焦躁,痛哭。他握着老母亲的手,温言细语,小心翼翼。
“妈,下午想吃点啥?”做饭前,他和妻子总是先问母亲。饭菜上桌,母亲不动筷子,他和孩子不端碗。
他在母亲房间里搭一张床,地里农活也撂下了,不分白昼地陪护着。七十二岁的明强满头白发,背有些驼,他吃力地、颤巍巍地把母亲抱出抱进,抱着喂饭,晒太阳,擦洗身子。母亲在床上躺了近一年,身上竟没出过一处褥疮。
寒风吹彻的冬天,他九十三岁的母亲,突然像个倔强的孩子,要吃西瓜。
他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在城里跑遍大街小巷和商场,没寻见西瓜,又转车往西安跑。两天后,他一路辗转,从远路上用棉大衣包回一个大西瓜。
他用儿子的爱与温暖,呵护着母亲苍老的身体与灵魂,一直到九十四岁安然离世。
站在路边跟明强聊天时,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世界上无论什么荣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薯。”
我家屋后的扁头,是搞室内装修的,他带着妻子在城里搞了近十年装修。五年前,父亲病逝,他放弃装修,带着妻子回到了村里。
他的母亲八十二岁,但身体还硬朗。我在村里常看见她拄着拐杖遛弯,跟老人坐在一起聊天。到了饭点,扁头七岁的孙女跑来拉着她的衣角说:“太太,回家吃饭。”她笑呵呵起身,牵着曾孙女的手慢慢回家。
扁头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城里打工,几个孩子都留在他身边。他带着大孙子在地里栽花椒树,我逗他:“人家都在外边挣大钱,你在地里刨啥呢?”
他抬头看着我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其实,他比我还小,也就四十多一点。这几年城里楼市火爆,正是他装潢挣大钱的时候。他干活精细,口碑好,手上活儿常年排着队。回来几年了,还时常有人打电话找他装修。
扁头娘是一个活在体面与温暖里的老人。每次碰面,我都会站着和她说一阵闲话。她的宽厚的笑容里有从容、自在、惬意。她不操心家里任何事情。
每个老人都是一座孤独的花园,他们青春的花朵和记忆在寂静里枯萎、凋谢,像黄昏的花园,明亮、炽热、喧嚣已经散去。她们把自己一生的美丽、健康、力量、虔诚、慈爱、温暖……都献给了家庭和儿女,即将油尽灯枯,像故乡苍凉的原野,在无限的寂静里等待黑夜的笼罩与降临。
在老家待了半个月,我在一种难言的惆怅里,离开我亲切而陌生的村庄,重返自己漂泊的河流。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