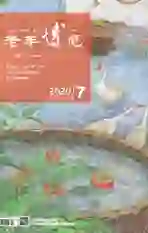院士陈薇,“与毒共舞”29年
2020-07-20王媛媛
王媛媛
陈薇,1966年出生于浙江兰溪,1991年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同年4月特招入伍,199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现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少将军衔。
2020年3月16日,陈薇牵头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几个小时前,陈薇在新冠疫苗临床研究注册审评会现场完成了答辩工作。在答辩现场,陈薇一头干练的短发,头戴迷彩帽,身穿迷彩服,虽然戴着口罩,声音依旧干脆利落:“6个月以后加强一针的话,(防护)作用可以达到两年。”“我们按照国际的规范,按照国内的法规,已经做了安全、有效、可控、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正式开展临床试验的所有准备!”答辩结束后,陈薇接受采访。她说:“我们身在地球村,我们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时代。疫苗是终结新冠肺炎疫情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武器如果由中国率先研制出来,不但体现了中国科技的进步,也体现了我们的大国形象。”
在新冠疫苗的研制上,我国兵分五路,同时进行了灭活疫苗、mRNA疫苗、重组蛋白疫苗、DNA疫苗、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研发。其中,陈薇院士团队和天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合作开发的重组病毒载体疫苗是进展速度最快的。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的原理,就是把致病病毒A的部分基因植入不致病的病毒B里,重组成新病毒C。这个病毒C拥有A的外形,但致病性和B是一样的。我国的第一个病毒载体疫苗就是陈薇团队研制的腺病毒载体疫苗。2014年,他们就是用这种技术开发了我国首个、世界第三个进入临床的埃博拉疫苗。
埃博拉病毒是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第四级病毒,人们熟悉的非典病毒、艾滋病病毒都只是第三级病毒;它是目前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病原体之一,感染后死亡率高达90%,在非洲被称为“人类生命的黑板擦”。
埃博拉病毒出现以来,全世界都在研究相关疫苗。陈薇说:“第一,我们要做原创的疫苗;第二,要做高效、安全的疫苗;第三,要做能在现实中大规模应用的疫苗。”
美国同期研制的疫苗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它是液体的,需要在-80℃到-60℃的环境中储存。非洲烈日炎炎,低温保存是个极大的挑战。陈薇记得,“我们去的时候,不说别的,电都要靠自己发”。陈薇团队成功地把疫苗做成了冻干制剂,“在2℃到8℃常规条件下能保存两年,37℃环境下能保存3周”。
2014年,西非暴发大规模埃博拉疫情。更为致命的是,病毒发生了变异,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疫苗均针对1976基因型埃博拉病毒。当年12月,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在这个严峻的时刻,陈薇团队研发的2014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获得临床许可,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新基因型疫苗。2015年5月,陈薇团队走进埃博拉疫情肆虐的非洲国家—塞拉利昂,这是中国科研团队制作的疫苗首次在境外进行临床试验。陈薇团队抵达后,塞拉利昂的街道上常常能见到排起的长队,那是等待注射疫苗的人们。
2015年11月10日,塞拉利昂中日友好医院门前,十几名塞拉利昂小伙子把陈薇抛向空中又接住—他们之前都在这个医院接种了疫苗。就在此之前3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在塞拉利昂终止”。“大家一脸灿烂。他们很灿烂,我也很灿烂。”陈薇笑着谈起那次“礼遇”。
陈薇爱笑,笑声爽朗。她走路步子大,手甩起来,无论穿着军装、白大褂还是便服,都是英姿飒爽。这样的性格让热情的塞拉利昂朋友感到很亲切。
曾有人问陈薇:“你们为什么要去非洲?”
一个原因是要保护境外的中国人。另一个原因,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我们和病毒之间,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陈薇说:“若非洲的疫情没有控制住,携带病毒的感染者,特别是在潜伏期没有被发现的人,乘飞机来到中国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生物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
一身白衣,长发飘飘,骑着单车徜徉在落满黄叶的清华园里—读研究生那会儿,陈薇是个文艺青年。她会唱歌、爱跳舞,还是校刊的副总编辑,常常参加周末学生食堂的舞会。1990年,她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取抗体时,忽然产生了到这里工作的强烈愿望。从清华大学毕业前夕,陈薇放弃了深圳一家著名生物公司的高薪职位,选择穿上军装。此后,这个在清华园跳舞的女生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2003年非典肆虐,陈薇37岁。她带领课题组连夜进入生物安全三级负压实验室研究非典病毒,到广州一线医院采集非典病毒标本,与尚无治疗方法的病毒零距离接触。最终她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能有效抑制病毒的重组人ω干扰素,这成为健康人群的预防用药。
2008年汶川地震,陈薇42岁,担任“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卫生防疫组组长。为了预防灾后疫情,她赶赴第一线指挥。在废墟上工作了两个月后,紧接着她又投入了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竭尽所能生产疫苗?购买他国的疫苗是否可行?陈薇对此有过深度思考。“我们将近14亿人的一个国家,经济能否承受得起?即便我们国家承受得起,全世界的产能足够供给中国用吗?”陈薇说,现在我国97%的疫苗都是国产疫苗,它们支撑着我们的防疫体系。
另外,疫苗的背后是国家安全问题。“正如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不管出多少钱,别人不再提供疫苗怎么办?”再进一步,进口疫苗一定是安全的吗?
195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特实验室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时灭活病菌不够彻底,导致活体病毒出现。但在安全测试中,这个问题没有被发现,很多孩子因此瘫痪或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美国因为这一惨痛的教训,对相关法律进行了完善,将监管水平提得更高。”
研究病毒的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2014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当年塞拉利昂疫情的病毒基因序列文章,这对埃博拉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文章有55位作者,其中5位在发表时已去世,原因就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陈薇从进入实验室到现在已有29年,这是小心翼翼的29年。“您天天跟病毒打交道,怕過吗?”曾有个小姑娘这样问陈薇。陈薇的回答是:“要说不怕,那可不是真心话。但我想,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去做好个人防护,做好他人防护,做好环境防护。如果我们承担了更多的‘怕,小姑娘,你和其他人可能就少一点儿怕了。”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7期,千百度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