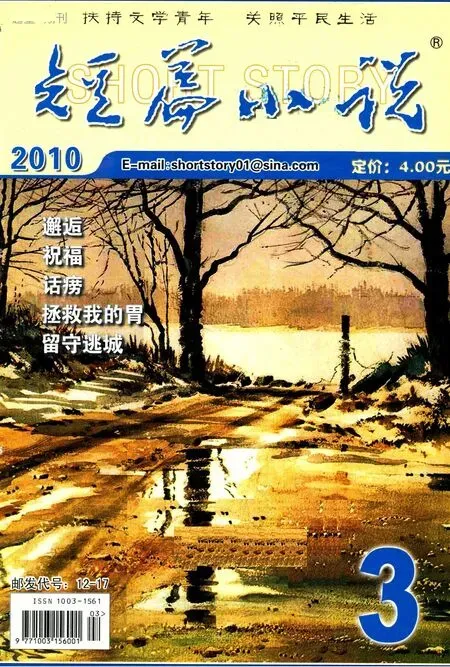双重舞台上的别样人生
——我写“戏中人”系列
2020-07-14岑燮钧
◎岑燮钧
2014年最后一期的《短篇小说》原创版上,有我一组《戏中人》,其中第一篇《祖师婆》,正是我这一系列的开篇之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写好些年,积有三四十篇的规模,仍觉意犹未尽。它是开放的,并没有结尾。
时隔五六年,不意又在《短篇小说》上有了这一组。
我之所以会写这一系列,乃是因为我是一个戏迷。我从小喜欢听戏看戏,能品出其中三昧,惜乎不是梨园中人,否则,似乎还可写得更多更好些。我在写这一系列时,积我半生之功,倾我全身之力,意图为梨园画出众生相。我不仅要画出梨园的横截面,更想画出它的纵深感。
上个世纪,是一个大开大合富有戏剧性的时代。这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我说的剡剧,杂糅了江南的众多剧种。演戏的大多是穷苦女孩,她们从底层演起,闯荡江湖,汇聚于十里洋场,争奇斗艳。梨园又是名利场,在这时代的漩涡里,怎样进退,怎样周旋,都是比舞台更加逼真的活生生的戏剧。她们的人生,就是一台台精彩的戏文。当她们在舞台上歌哭之时,她们也是“积半生之功,倾全身之力”。但是,人生的舞台,无疑比戏台更复杂,更即兴,更幽微。这正是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兴奋所在。我努力想写出双重舞台上这些“戏中人”的别样人生,幽微人性。
江南的戏文,无疑是美的,无论昆曲也罢,越剧也罢,还是各种滩簧。在这么美的舞台上,演着这么美的人物。他们往往至情至性,不计名利,或者历尽坎坷,饱尝炎凉,正所谓“人世间的千般情结,万般感慨,述之不尽,乃舞之蹈之,歌哭之”。而伶人就是舞台上的诗人。诗人是以诗唱戏,伶人是以唱戏做诗,抒发的都是一己之怀。虽说伶人流的是自己的泪,唱的是别人的戏,但那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她们在戏内是一种人生,在戏外,又是一种人生。这两种人生,有时是合一的,有时却又背道而驰。人性的复杂,即在于此。她们在戏里戏外,进进出出,一方面浑身是戏,一方面却又浑身是伤。她们深深知道,做人,路只能走个七八分,再往前就要碰壁了;演戏嘛,沿着这七八分,又何妨来它个十来分呢。这便是舞台上的袖子为何要加长两三尺、五六尺的隐喻所在吧——长袖善舞嘛。所以,她们的人生比起普通人,更多了戏剧的意味,无论是喜剧也罢,悲剧也罢。
我曾以诗自题“戏中人”系列小说,道是:“满纸烟云假作真,人中戏比戏中人。谁人歌哭氍毹上,泪湿青衫更一春?”我在散文《戏之梦》中这样说:我常想,天若赋我一副好嗓,又有俊朗的外貌,挺拔的身材,我必去做一个艺人,唱戏,唱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可惜,我一样都没有,只能白白地做梦。这一系列的小说,或许就是做梦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