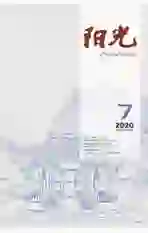铜川印象
2020-07-09秦人
我虽然是陕西人,但在二○一○年前一直没有去过铜川,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去铜川的次数多了,经铜川矿务局的同志介绍和翻阅资料,对铜川的了解也就多了些。
铜川老市区位于南北川道里,发展受到限制,因此开发了新区;铜川没有铜,历史上不同年代叫铜官、同官,一九四九年七月改称铜川,时为县治,一九五八年四月撤县建市,治域时有变化,名称沿袭至今。铜川是个煤城,因煤而生,因煤而发展。
据考证,铜川产煤的历史很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煤,汉代开始用煤冶铁,唐代开始用煤烧瓷并作为生活燃料,元代开始开采煤窑,清代开始大量开采煤炭,民国时期开始引进机械开采。一九三五年大兴、民益等煤矿在铜川开办,开始使用蒸汽绞车、卷扬机,产量逐渐攀升,一九四○年官办铜官煤矿开办,一九四九年实行解放军军管,归郑州铁路局西安分局领导,一九五五年九月成立铜川矿务局。可以说是先有铜川矿务局,后有铜川市,一九五八年建市后矿务局局长兼任市长,之后隶属关系时有变更,二○○四年改隶陕煤集团。
回顾过去,我发现铜川矿务局的历史是辉煌的,曾有两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到矿务局视察工作,朱镕基总理欣然为铜川矿务局题词;还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铜川矿务局视察过,说明铜川矿务局在中国煤炭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也是无法代替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铜川矿务局是陕西乃至西北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铜川是西北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为陕西省乃至新中国的能源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去过王石凹、金华山、徐家沟、鸭口和东坡等煤矿,这些煤矿大都是国家“一五”和“二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如今已经关闭或濒临关闭,这些为新中国建设出过力的煤矿,和那些当年流过汗的煤矿工人一样,已经垂垂老矣。这些建在山沟里的煤矿,是几代煤矿人的家,如今他们从泥瓦房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矿区资源却枯竭了,煤矿工人大部分分流到陕北、彬长的其他煤炭企业,他们大都来自五湖四海,已经有两三代人在这里定居了,在他们把铜川矿区当作家乡的时候,却要背井离乡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王石凹煤矿,这个煤矿是国家“一五”期间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之一,由前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提出初步设计方案,西安煤矿设计院承担技术设计,一九五七年开工建设,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建成移交生产,设计能力年产一百二十万吨,最高产量达到了一百六十六万吨,是铜川矿区煤炭生产的大型骨干矿井之一,也是当时我国西北地区第一座最大的机械化竖井。这个煤矿现已关闭,当年热闹的王石凹镇的经济支柱轰然倒下,经过铜川矿务局的努力,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王石凹煤矿列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经过改造后,将成为人们参观煤矿的工业遗址公园,也是人们了解煤矿的窗口和活教材。
二○○二年我下过王石凹煤矿,因为这个矿井已经开采了六十多年,从地面到工作面相当远,估计有十公里左右。我们先要换工作服,穿上雨靴,然后扎上腰带,别上蓄电池,再戴上头盔,头盔上有矿灯,还要在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我们一行人坐罐笼下到矿井,罐笼是一次可以乘三十人左右的提升机,类似电梯。下到井下后,要乘坐猴车到达井巷,猴车上面有滑道,伸下来一根钢管,离地面四五十公分有一个像自行车座的座位,人坐在上面,手抱着钢管,由绞车带动猴车在滑道里循环转动,可以转进去,也可以转出来。我想它之所以叫猴车,大概就是人抱着钢管像猴子一样坐在座位上面吧。到达井巷的一个平台之后,在这里换乘小火车,小火车类似我们常见的观光小火车,铁黑色,一米五左右高,带着十几个车厢,把人拉三四公里后放下,剩下的路程要靠步行。我们就在巷道里走,感觉路越走越长,走得我腿都疼了,可是大家都在坚持着,我也不能认?,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到工作面,一个单程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一个来回要三个小时,这说明煤矿工人上下班特别辛苦,要提前一个半小时下井,然后在指定时间去交接班。
我看见很多煤矿工人腰里别着一瓶矿泉水,怀里揣着两个馒头,在地下三五百米的地方,冷风飕飕,他们啃个馒头喝口矿泉水就算是一顿饭了。现在有的煤矿提供统一的送饭服务,有些有条件的煤矿还有井下休息室,有热水和方便面,可以吃点儿热乎的东西,也可以喝杯茶或者咖啡。井下是绝对禁止抽烟和喝酒的,所以他们出了井后就使劲抽,几乎所有的矿工都喝酒,酒量比一般人要大。我所知道的煤矿领导酒量都比较大,大多数人都是一斤以上的量,个别有二三斤的量。我听一个煤矿领导说,当年计划经济的时候,他们出去卖煤,电厂的领导指着平时大家用来喝水的玻璃杯说,你们喝几杯白酒,我们就买几车皮煤,他一连喝了七八下,最后真的就卖了七八车皮煤。风水轮流转,后来煤炭紧张的时候,电厂的领导来煤矿买煤,也是这个办法,电厂领导喝几杯白酒就卖给他们几车皮煤。
很多人對煤矿的印象就是脏乱差,到处堆着煤,一刮风整个矿区煤粉飞扬,矿工身上都是黑的。那也许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象,如今的现代化煤矿是看不见煤的,不仅地面上看不见煤,巷道也看不见煤。煤炭从工作面采下来后,经过溜子和皮带传到地面煤仓里,所以地面上没有煤,在地下有煤,地下就是煤海,但是地下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机电、运输、通风、防瓦斯等系统,只有工作面和运输大巷可以看到被采下来的煤,其他地方的煤被锚索、锚杆和铁丝网固定着,被支护系统管理着,所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煤墙、煤柱和煤的巷道。
只有深入到井下,才能知道煤是怎么被采下来的,才能知道煤矿工人的辛苦。煤矿工人是很难见到阳光的,白班天没亮就下了井,出井时天已经黑了,夜班工人白天出井后洗个澡吃完饭后就去睡觉,他的白天其实也是黑夜,他们的世界除了黑的煤,就是黑的夜,他们把青春乃至人生都贡献在煤矿,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他们不仅是最可爱的人,也是最应该受到尊敬的人。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上对煤矿工人却是鄙视和轻蔑,因为他们脸上和衣服上经常是黑的,工作危险系数大,而且又脏又苦又累,生活黑白颠倒,他们找不到对象,大多数人只能在老家农村找对象。铜川矿务局在一九八三年在册职工人数最多,达到六万五千零四十六人,也就是说,大约有五六万煤矿工人从事采煤工作,这个队伍是庞大的,加上职工家属,整个铜川矿务局养活了二十万人,所以说铜川是一个煤城,也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因为有一个英雄的铜川矿务局。
在深入了解了铜川之后,我认为铜川的煤矿文化在全国应该是最出名的,比如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的演唱,很快流传全国,几十年久唱不衰,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歌曲之一。著名作家路遥曾兼任铜川矿务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鸭口煤矿体验生活,在陈家山煤矿医院会议室写出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书里的“铜城”就是铜川,“大牙湾煤矿”指的就是鸭口煤矿,“安锁子”的原型就是其本人,他被原名原姓写入了小说之中。我在参观鸭口煤矿“路遥纪念馆”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珍贵史料,路遥的照片和生活痕迹历历在目,人却已英年早逝。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铜川就吸引了很多作家和诗人,如田汉、冯至、贺敬之、魏钢焰、李若冰等人,他们写下了很多关于铜川的诗篇和文章;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也多处写到刘志丹在铜川地区的革命活动;著名作家贾平凹到铜川后写了散文《陈炉》和《宜君记》,并以陈炉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古炉》,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就是在耀县桃曲坡水库完成的。从铜川走出的作家也不少,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朱文杰、刘新中、黄卫平、钟平、芦苇、秦凤岗、李祥云、郭建民等人,有六七十年代的唐云岗、刘平安、吴川淮、吕俊涛、王宏哲、王维亚、安黎、第五建平、劉爱玲、王可田、王成祥等人,他们是目前铜川文学界的中坚力量,有的人现在省级文化机构任职,在全省有一定的影响。
铜川矿务局有一支六十多人的管乐团,水平相当了得,曾获得过全国第八届非职业优秀(交响)管乐团队展演银奖。我曾在西安音乐学院演出大厅观看过他们的演出,乐团阵容强大、服装整齐,演出震撼人心、精彩纷呈,各位团员紧密配合,奏响了十几支中外名曲,曲声悠扬、跌宕起伏、优美动人,让我有人间天籁般的音乐享受。我想,我们的煤矿工人能把管乐演奏到这个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铜川矿务局能有这样一支管乐队伍,说明我们煤炭系统人才济济,煤矿人不仅能挖煤,还能写作、绘画和演奏音乐。
每一次去铜川,我都有不同的感想,每一次都有新的认识,铜川在不断地发展,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环境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靓丽。铜川是陕西最年轻的一个地级市,建市六十年整,但它在陕西煤炭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忽视的,它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如陕西第一家煤矿、第一个千万吨煤炭企业等,为陕西省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的情况下,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资源型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社会转型发展,“一黑二白”(一黑:煤炭,二白:水泥、电解铝)现象得到很大改善,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现在铜川新区的建设已成规模,新的产业在布局发展,可以说铜川是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个范例,一个新的铜川正在崛起,“渭北明珠”的称谓依然响亮。
秦人:本名张春喜,男,1970年出生,陕西武功县人。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文学》副主编,陕西省文化厅“陕西文学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者,鲁迅文学院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榆林学院兼职教授。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篇,获得第四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第六、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文学奖项四十余次,作品被选入三十多个选集,出版个人作品集六部,主编教育类图书四部,发表长篇小说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