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文献 未名湖畔 10年不倦
2020-06-19高虹飞
高虹飞

今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一条“北大中文,生日快乐”信息,霸占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大家在世界各个角落,“云庆祝”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不觉想起2010年9月自己入学时,适逢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转身之间,已然十年。何其有幸,在未名湖畔,读书不倦。
中文系严肃的面庞
北大中文系的梦想,是很早很早就盛装在我心的。
很小的时候,爸妈教我识字、念诗、背成语。我喜欢在交织的诗词文句中,感受文字无穷尽的精妙组合。随着年龄渐长,亦喜欢在纷繁的小说世界中,放任自己流泪欢笑,还喜欢以空白的纸页与Word文档为画板,将文字尽情涂抹。喜欢文字、喜欢阅读、喜欢写作,所以我很早就决定,大学要念中文专业。
学中文,哪里能比得上北大中文系呢?小学时,我们就在语文课上,在田晓菲《十三岁的际遇》中,得知那里有湖光塔影,秘籍琳琅。念中学时,我们用的语文教材,好巧是北大中文系参与编制的。我特别喜欢那套教材的编排与选文,比如其中一册,第一单元课文为《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囚绿记》,第三单元是《兰亭集序》《赤壁赋》《游褒禅山记》。这些古今山水游记、景物散文名篇,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感觉天光水色满纸,山川风物喜人。就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愈发向往北大中文系。
很幸运,我的梦想照进了现实。十年前的夏天,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翩然而至。然而,当我来到北大中文系的课堂,我发现,它和我的想象不一样。
可能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中文系是优哉游哉的“养老院”,学生的作业就是读读小说。我虽然做好了刻苦用功的思想准备,但对未来的学习生活,也颇有几分风花雪月、诗酒年华的浪漫想象。然而,初入燕园,迎接我的,是中文系严肃的面庞。
大一上学期,我们的必修课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古代汉语的课堂上,先生写着潇洒漂亮的竖版繁体板书,带着我们一字一句地细读古文,探求字的本义。《精卫填海》《蝜蝂传》《王子坊》……先生会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甲骨文的字形,问我们是什么字。那时的我,好多繁体字都不会念,只能用力低头,生怕被先生看见。在古代汉语的世界面前,高中做文言文阅读题积累的那些知识点,简直是沧海一粟。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弱小。
那么,现代汉语课会轻松一点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一开始,我为默写音标、分析“小雨伞”的连上变调而头痛,随后,语音、词汇、语法三座大山,一山更比一山难。“挖深了”“挖浅了”其实不同,“鸡蛋”“鸭蛋”也有所区别(一个是词、一个不是词)……那时的我还不能理解,学习现代汉语知识的意义所在。我只是粗浅地觉得,平时交流、写作,似乎也用不上这些,所以学得漫不经心,成绩也颇为惨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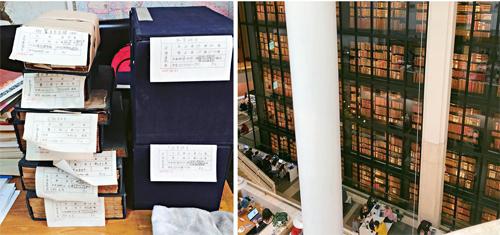
到了大一下学期,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之外,我们的必修课表上,又增加了文献专业的《论语》选读、中文工具书,以及文学专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越发清晰地看见中文系严肃的面庞。它隐藏在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层层叠叠的书架之后,让我在查字典、翻年鉴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屏息凝神;它活跃在一篇篇令我费解的、艰深晦涩的作品里,即使我在课下争分夺秒地阅读,也跟不上老师的书单;它更浮现在历代学者的《论语》注疏等研究成果中,无声地嘲笑我的自以为是,此前我还以为,《论语》浅显易懂。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那种我曾经误解的“用不上”,正是学术与实际生活之间必要的距离。那种无助的弱小感,是因看见了学海无涯。那严肃的面庞,正是学术的模样。中文系的学习生活不是风花雪月,它恰恰与浪漫相反,要求严谨、求实、理性、客观。进入中文系,也不意味着你从此拥有了五色笔,各类文书手到擒来,小说戏剧倚马可待。写作需要灵感,也需要坚持与磨炼。但另一方面,正如十年前刘震云在中文系百年庆典礼上所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是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于他的路能走多长,是非常重要的。”在中文系学到的专业知识,在老师的引导下阅读的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成为我宝贵的写作滋养。
“蝴蝶本”,瞬间心动
然而,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这些。大一、大二两年,我很茫然。总是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羞赧惶惑,不知道将来是要继续读研,还是直接工作。不知不觉到了大二尾声,我需要做出进一步的专业选择。与国内其他高校不同,北大中文系本科,细分为中国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以及面向留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五个专业。大一、大二时,大家共同学习基础课,从中了解、体认各专业特色。大二末确定专业后,大家便分专业学习更为专精的课程。对于各专业人数,系里没有什么限制,充分尊重大家的选择。
我首先排除了语言专业。通过两年的学习,我深知自己兴趣不在此,此亦非我所长。于是,专业选择变成了文学、文献二选一。我喜欢古代文学,然而大学兩年,我的文学专业课大多成绩平平。而在文献专业老师的课程中,我却数次拿到高分。这不禁让我开始思考此前从未想过的另一种可能。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文献专业,我提前阅读了《古典文献学基础》等教材,请教了这个专业的师兄师姐。至今仍记得师姐微笑着说,在文献专业的“版本学”课上,可以看到“蝴蝶本”。这个美丽的名字,瞬间打动了我。后来我了解到,它是古籍的一种装帧形式。在当时的阅读与交流中,我获得了很多像蝴蝶本这样的有关文献学的细节。此前,古典文献学总给我以神秘高冷的印象,似乎只有家学深厚、熟习四书五经的学霸才有资格攻读,然而这些细节,让我感到亲切与踏实。我喜欢一叶叶艺术品般的古籍书影,我想要学习更多相关的知识。我发现自己对文献专业有兴趣,对未来的学习也有期待、有信心。
就这样,我确定了文献专业的选择。进入大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专业课,果然令我乐在其中。比如在版本学课上,我们的一项作业,是为明清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撰写小传。小时候,我就在《文化苦旅》中读到范钦天一阁的故事。在此次写作过程中,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学着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查找比传记更为原始的史料,如行状、墓志等。与儿时在散文随笔中被动地接受知识不同,此刻的我,感到自己正在书山探险,主动地搜寻他们留下的踪迹。毛晋、黄丕烈、瞿镛……伟大的藏书家们对书籍的挚爱,令我深深感佩。至此,曾经犹疑的问题,也有了坚定的答案:我要继续攻读文献专业研究生,我希望留在这里。
经过大三一年,以及大三暑假的学习、备战,在大四之初,我幸运地通过了保研考试。由于在考试成绩位列专业第一,我还获得了本科起点直接攻读本专业博士的资格。
且行且欣
获得直博资格后,我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导师。老师是研究明代文献与文学的专家,明朝也正是我最感兴趣的朝代。我的家乡在天津的建城,与明初“靖难之役”等史事密切相关。是以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朱棣、朱允炆,甚至在脑海中搭建小剧场时,故事背景也总是设置在“明永乐年间”。最终,老师同意了我的申请,让我得以忝列门墙。

大四毕业,开始读博。尽管专业还是古典文献学,但我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本科阶段,虽然也要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但我的角色是“学生”,主要任务是上好基础课、专业课,了解、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而在博士阶段,尽管也有学分要修,但我但角色变成了“研究者”,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研究、撰写论文。在这身份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我常困惑,也会沮丧。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导师的悉心指导,亦在研究生课堂上,在阅读学术论著中,在与其他研究者的交流里学到了很多。
随后,我尝试着围绕自己感兴趣的人事,撰写小论文。2016年是明代著名作家汤显祖以及英国文豪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其时,我正好在读汤显祖与友人的尺牍。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我利用“中国方志库”“大明实录”等数据库,查考到不少材料。借助这些材料,我进一步考证了数十封汤显祖尺牍的交游对象、写作时间等问题。论文写完之时,正值昆曲《牡丹亭》在学校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我坐在讲堂,听着数百年前汤显祖创作的作品,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我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在阅读与考证的过程中,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某种感情吧。
就在这样一次次练习、修改、打磨小论文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地进步。论文的发表,亦为我带来新的乐趣。当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分享自己的研究时,当我看到论文被喜欢的学术公众号转载,并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时,当我看到自己佩服的学者转引我的论文时……那些时刻的开心,都是开展学术研究带给我的独特体验。
我也越发喜欢考据,感觉爬梳文献、搜集史料、考证问题的过程,就好像侦探举着放大镜,收集蛛丝马迹,推理断案。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对古典文献学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文献学的知识,令我特别重视版本形制、源流问题,而考辨书籍的编刻过程、校勘版本,又让我愈发理解传世文本的复杂性。我想,作为古典文献学核心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知识,对于研究古代文学、古代史等学科的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写作小论文过程中收获的经验,为我书写学位论文提供了重要帮助。我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是明朝洪武、建文、永乐时期出版与文学的关系。在我看来,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我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度,书籍出版事业源远流长,出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在明初这一特定时期,出版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出版产生的作用。
在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个身影:王逢的友人朱显忠赠予他四万钱,用以助其别集出版;富商陈宝生要为高启出版其作,却被高启拒绝;宋濂提笔作诗时,想到自己的诗文集将远销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两鬓斑白的傅若川,埋首校勘、编次其兄傅若金的旧稿;许中丽坐在环翠亭,琢磨着总集里该选入自己的好朋友几首诗……在深入考察一位位作家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愈发强烈地感受到,出版意识对作者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这次研究,也让我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思索。正如田晓菲《尘几录》所说:“无论手抄本文化,还是互联网文化,其实都是人类处境的寓言。”当前,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媒介,正在不知不觉中,以极强的力量影响甚至塑造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一篇学术论文,可以在微信朋友圈刊载,收获“转发”与“在看”,一场严肃的学术报告,也可以在B站直播,被弹幕与礼物刷屏。新媒介是否干扰了我们自身的表达,我们又应如何与新媒介相处?我的研究提醒着我,要努力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年前,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能够用几年的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毕业后,我在系里做博士后,繼续修改着自己的博士论文。我想,论文写作是不断精进、精益求精的过程。我们不停地向上攀登,然而前面总有更高的山峰。或许,这种无止境的追寻,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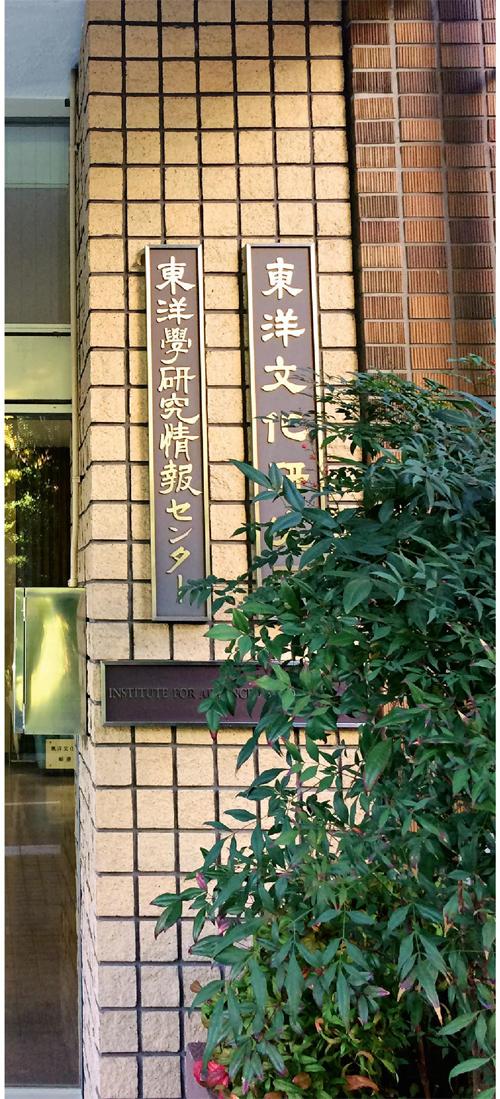
兔走乌飞,十年流转。如今,我依然在北大中文系,亦仍然迷恋这一片湖光塔影。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的幸运,然我相信,在北大中文系获得的滋养,定将助益我的工作,即使那份工作与学术无关、与写作无涉。
责任编辑:曹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