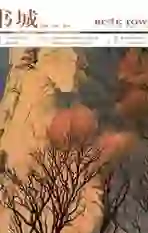假如翻译欺骗了你
2020-06-09Violaine
Violaine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好诗有过无数“续貂”之句,如“不要难过不要悲伤,反正明天也是一个样”,等等。那么,假如翻译欺骗了你呢?难道不能想象被翻译欺骗,更不敢想象其后果吗?其实翻译的“欺骗”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而且是必要的。比如,高端会谈中一方爆出粗口,口译员可以随机应变地告诉另一方:“对方讲了一个不可翻译的笑话,现在请跟我一起哈哈大笑。”于是,不明就里的一方,跟着译员和另一方一起爆笑。这是联合国译员教程关于谈判场景的一个教案。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不是那种临场发挥的翻译技巧,也不是通常所说的错译问题,而是翻译研究者所谓文化与意识形态隔阂造成的“翻译欺骗”。当然,“欺骗”一词不妨打上引号,确切说是因翻译而导致误解的意思。比如有专家认为,我们用“个人主义”“封建主义”“进化论”等概念表示译入的对应语,以及中文“韬光养晦”一语的译出,都存在语言译入译出造成的误读现象,乃至出现歧义与深刻误解。再如,某些人名地名的旧译,亦见有褒贬色彩,尤其是某些国家译名,就多少带有“西学东渐”时期的主观认知,如英吉利、美利坚、德意志、义大利,俨然由汉字传达出某种高大上意味。反之,像危地马拉、厄瓜多尔之类,则不免取字欠佳。虽说音译撇开了表意功能,汉字本身却给人带来二度想象。
“异化”与“归化”
翻译者都明白,严格的翻译伦理是一回事,落实到每一桩案例,则又是一回事。除了某些伦理困境,翻译的优劣与否还受到另一重考验:遇到二者难以兼顾的情况,翻译应该更倾向源语言还是译入语?

比如一个翻译作品,对原文忠实度颇高,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皆严格对应,那么这是否可称得上是好的译作?对于许多译者来说,这正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可是在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看来,这还不够,他可能要问这篇译作是否考虑到译入语文化的因素,是否考虑到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如果没有,或者考虑较少,那么这就不是一篇佳作。勒菲弗尔是欧美翻译学界一大牛人,是促使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旗手之一。其专著《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必要改写。此书在论证过程中,引用了多国历代文学名著的翻译实例,分析研究它们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人改写的过程。这些实例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和时代性。
勒菲弗尔阐述翻译改写之必要,所举的一个典型案例是英国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的《鲁拜集》。菲茨杰拉德翻译(或重写)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旧译莪默·伽亚谟)的作品,使之风靡世界,被认为是成功的翻译案例。海亚姆的诗作几个世纪来似乎默默无闻,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一八五九年菲氏不署名整理发表了《奥马尔·海亚姆之柔巴依集》(共101首),把这本诗集译介到英语世界,才使他闻名于世。菲氏的翻译属于意译,但是保持了原诗的韵律形式,后来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即世人所知的《鲁拜集》(Rubaiyat,四行诗集)。但世人不知道的是,译者菲茨杰拉尔德认为波斯人“生性笨拙”,觉得自己应该在译文中“展现自由”风采,同时也使之更符合当时西方文学的规范。《鲁拜集》在中国有二十多个译本,许多名家如郭沫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都根据菲氏的英译本做过转译。郭沫若比较过几种英译本和据说是完全忠实于波斯文本的日译本,不由赞叹说:“翻译的功夫,做到了费慈吉拉德的程度,真算得和创作无异了。”(《鲁拜集·小引》)
那么问题来了,这算是翻译还是创作?
赞同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人大多认为,译文的表述或多或少要受到譯者所处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让翻译作品在自己所处文化环境中变得更宜于接受的做法,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是必要之举。再者,当意识形态体现为赞助人和权力人的意志时,译者如果违背此种意志,可能会得不到资助,失去生意或生计。很多人做翻译首先是为谋生。这只是一个行业,并非人人都志存高远,潜心学术。

舒乙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老舍在美国》,其中谈到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英译引起的一场风波。一九四五年,《骆驼祥子》由伊万·金(Evan King)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英译本书名改作《洋车夫》(Rickshaw Boy),译文与原作也有很大出入。伊万·金为了迎合战后美国读者对祥和生活的期待,不惜对原著情节做了大幅改动,原来的悲剧结尾被改成喜洋洋的大团圆结局—祥子找到了小福子,并把她从白房子里救了出来,最终两人喜结连理,幸福地走到了一起。这个译本当时在美国竟引起意想不到的反响,获得商业与专业两方面认可,成为颇受欢迎的畅销书,并入选当年纽约著名读书俱乐部的“每月一书”。舒乙说老舍对这个译本非常不满(也有说老舍挺喜欢这个《洋车夫》英文版的,不知究竟如何)。伊万·金初尝成果后一发而不可收,一九四八年又将老舍的《离婚》译成英文,照样依己之意大改大删。按舒乙说法,老舍无法再忍,另请一位郭镜秋小姐翻译《离婚》,并辗转托人为自己的中文版权在美国应享的权利做了公证,迫使伊万·金的《离婚》译本不能进入图书市场。可是,老舍为保护自己著作权益所做的努力,却无法改变英语世界对译本的评价和要求。
那么问题又来了,通常认为翻译作品忠实于原著是达标的基本要求,可是我们该怎样评价一部不那么忠实甚至改变和扭曲了原著内容,却受到译入语读者欢迎的译著呢?

自安德烈·勒菲弗尔以来,翻译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应该是被称为“文化转向”的翻译界定。提出“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标准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维度。是否忠于原著不再那么简单直白,而是有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内涵。翻译研究者们要关注的是译作与原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这也成了翻译批评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不过,勒菲弗尔所谓操纵和制控,并不都是一味向译入语靠拢。比如,伊万·金翻译老舍作品颇受争议的另一个原因,据说是他的“抗阻式”译法,即处理原著中俗语谚语、地名人名、方言切口等语词,并非译成英语中现成的对应词或相近的意思,而是将中国语言的文化意象、情感倾向等“硬生生”嵌入译本的英语中,让译入语不那么顺溜,反而呈现某种异腔异调的风格(在这一点上,倒是符合鲁迅提倡的“硬译”,如今汉译外国文学亦往往如此)。问题是伊万·金本人并非精通中国文化,这种“硬译”造成的错讹就很明显,不像意译往往能蒙混过关,这是争议的根本所在。伊万·金将这种“抗阻式”译法付诸实践,显然是为了凸显异域文化特质,以吸引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此,一些翻译专业人士称之为“异化与归化的统一”。许多评论者认为,伊万·金这么跌跌撞撞搞下来,客观大效果竟还不错。无论如何,中国文学中的世俗风情,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生活,就这样进入了美国普通读者的视野。总之,伊万·金的重述和抗阻,恰是从归化和异化这两方面影响了日后的翻译发展。
关于异化与归化的翻译案例,最典型的,也是最容易直接拿来说事的,应该是那些跨国公司投放世界不同区域的商业广告。一桩著名的案例是“欧莱雅”的化妆品广告,它于二○○二年投放亚洲市场时,为了淡化欧美社会中女性特立独行的公共叙事及其影响,那著名的广告词由“我值得拥有”改为“你值得拥有”。最初,这广告词是该公司一位美籍女主管以女性自我激励宣言为灵感而产生的创意。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广告词都张扬第一人称。然而,“在中国遇到了文化方面的问题,因为这广告词被视为个人主义意识太浓”,所以就改成了第二人称。这一改,微妙的变化就出来了:它既隐蔽了个人的张扬,又借出众的代言女明星表达了价值珍贵的愿望。于是,“我”的价值就成了“你”的。
“忠实”与“不忠”
当今翻译的忠实与否的争议中,文化含义与意识形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某些案例经常被一些学者视为强势文化(直白说就是英语文化)凭借翻译而仗势侵入。尤其是文化与政治方面的翻译。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Mona Baker)所著《翻译与冲突》(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就是一部揭示翻译中因语言“霸权”而使真相蒙蔽于世的翻译理论专著。书中举述诸多案例用以说明翻译是文化冲突的一部分,甚至就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在翻译界,最早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只是语言活动,至多是包含了文化的内容而已;后来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翻译作品对译语社会可能产生各种影响。在蒙娜·贝克看来,翻译不仅仅是与文化有关,而且还参与创造文化。当然,在她的语境中,创造文化也就意味着建构强势文化语境以遮蔽和压制弱势。
此书副标题为“叙事性阐释”,是作者对翻译的一种定义。确实,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它当然也是一种叙事性的阐释。参与政治场合的翻译者,并非仅仅是参与了政治,而是“翻译即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翻译还“创造”了政治。同理,文化场合下的翻译也参与了文化的创造。翻译者是有着社会文化属性的人,所以不可能做到翻译的完全中立。作者认为:“传统的口笔译研究,对于同时代的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一向采取回避态度,因为这些问题必然会使该领域从事翻译实践的理論研究人员注意到译者面临的道德困境。之前,人们坚持一种天真的理念,以为翻译,尤其是口译,是完全中立而纯粹的语码转换,不存在译者个人思想的介入。相信译者对现实的叙述能够‘完好无损地传递语言以及其他符号信息。”不过,贝克教授的质疑基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立场,显然是完全将翻译作为某种主观叙事。
在当代翻译研究者看来,“忠实”是一个很有回旋余地的术语。即便是在实打实的商务谈判中,某一方以几个百分点为底线否则免谈的强硬立场,也可以因翻译转换时的语气表达而使局面发生微妙变化。所以人们对翻译“忠实与否”的担忧确有道理:总有一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流失或改变。但是,任何优秀的译者都会认真告诉你,“流失”或“变化”的风险绝非“不忠实”的借口。恰恰相反,就是这种风险塑造了译者的纪律和警觉,推动着译者在翻译中实现最大的“近似值”。所以,与其追究这是不是正确的翻译,我们不如去问:这个译本是不是正确努力的结果—是不是高度自觉、高度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实践之后的结果?
这种方式的翻译批评必须要追溯至语言本身,还原到话语形成的环境,正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话题:“权力像病毒一样隐藏在每个单词里面,在每一句话里自动生成、扩展。语言的网络就是权力的网络,我们都在不自觉地充当权力的爪牙,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压迫别人。”根本上是关切权力的起源,福柯更进一步是在论述话语(discourse),他认为话语就是权力,因此他认为要在历史研究中去这样分析话语,也正是在这样的考古学研究中,才能理解我们现在可以拥有的知识(文学、历史、哲学、思想等)是怎么形成的。这让我联想到作为一个译者的知识与想象、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给许多翻译者留下的一个难题是,翻译的权力究竟该有多大?如果翻译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权力,在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考证它的原始出处和多重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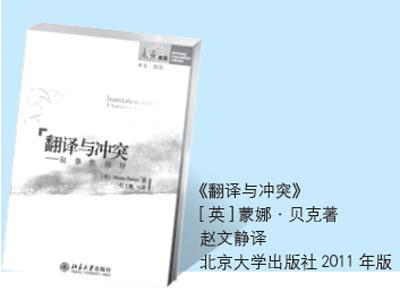
《翻译与冲突》一书显然想让人们对“知识即权力”引起足够警觉。她的绪论中说:“翻译是主要变量,能够影响并维持战争叙事的传播及合法化。”所以,书中所举案例特别指出了对某些国际知名组织的质疑,比如“无国界译者” (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作为一个志愿者翻译群体,“无国界译者”给许多知名机构提供免费翻译,工作性质与“无国界医生”“无国界记者”等组织相似。作者介绍说:“在专业的翻译领域里,无国界译者完全不同于其他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翻译组织……是一个非营利的协会机构,旨在以人道主义精神提供公益性的无偿的翻译服务。”
但是,《翻译与冲突》作者恰恰通过这个组织的口译实例对其译员提出严重指责。二○○○年,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设立办事处,对科索沃难民进行甄别。那时,阿尔巴尼亚局势已极其恶劣,许多从未涉足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为了逃离国境都声称自己是科索沃人。为了确定每位难民的身份,联合国办事处把面谈程序变成甄别过程,他们设定了一套严密的程序,让一线工作人员和口译员遵照执行,重点审查申请人的口音、衣着和对科索沃地理、习俗的了解情况。这个案例中申请者为一名年轻女性,她说自己曾遭遇塞尔维亚士兵抢劫。口译员问她,那些塞族士兵的军装是什么颜色?申请者说是绿色。但口译员知道塞族士兵一律着黑色军装,于是口译员就对联合国官员说,她在撒谎。
书中批评这名译员只凭这一点就断定申请者撒谎,不再听她后面的陈述。于是,作者做出这样的结论:“拒绝考虑她的本体叙事,她的故事成了‘阿尔巴尼亚人为了获准进入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而蒙骗联合国官员。”
接下来书中展示了另一个著名口译案例,即“二战”后盟军法庭对纳粹嫌犯约翰·德米扬鲁克(John Demjanjuk)的审讯。法庭上口译员多次纠正证人关于战争过程以及犹太人在集中营的处境的陈述错误,却并未建议法庭不采信证人的证词。口译员这样的“宽厚态度”,自然被作者作为翻译“不可信”的根据。
这两个作为主观叙事的例子,是翻译问题,还是权力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呢?贝克教授显然认为,文化背景、道德倾向和政治立场决定了翻译是否可信。
“偏心”与“偏见”
贝克教授以“叙事性阐述”为基本理论,对翻译并非中立而展开的学术论证,本身就带有某种预设性立场。撇开那些“话语”“建构”“范式”“符号”等专业名词,可以看出作者对翻译可能投合强势文化的偏向极为警觉,甚至有诛心之嫌。书中说到美国当代语言协会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它的年会上发布广告招募语言教官一事,引用乔治敦大学一位教授的抗议信,认为语言协会应秉承真理与正义的理想价值观,拒绝合作。可是,如果价值观与译员感情立场的问题尚在翻译文化的讨论范畴之中,那么所有对译员的“诛心”质疑难道不会被反向质疑吗?
比如,那个阿尔巴尼亚妇女申请难民身份的案例,批评译员有“偏见”,那么反过来,假如译员对申请者持有“偏心”的照顾,那是否就成了政治正确的翻译呢?至于德米扬鲁克的译员未建议法庭不采信证人的证词,与其说是译员“偏心”,毋宁说是作者将译员与法官、律师混为一谈了,译员在翻译中有责任核实证人陈述事实的准确性,至于是否采信证人的证词,那根本就不是译员的职责。
在贝克教授的书中,翻译的背后始终有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
当然,这不是说翻译活动中并不存在立场、情感或是人格因素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的长篇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翻译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列出的中方通事名单中,有一位“疑为汉奸”的鲍鹏,在两广总督琦善和英方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的一次谈判中,充当了“通事”。根据英方一名军事人员所做的现场记录,这人形象举止之猥琐,就是从他谄媚式的英语中表露的。后来他回到澳门探望鸦片烟商的老东家和旧日的同事。人家拿他“士别三日”后的身份来开玩笑。他马上跳起来,揎拳裸臂,大叫大喊:“You thinkee my one smallo man? You thinkee my go buy one catty rice, one catty foul? No! My largo man, my have catchee peace, my have catchee war my hand, suppose I open he, make peace, suppose I shutee he, must makee fight.”记录者J.艾略特·宾汉姆(J. Eliot Bingham)在引文后加了按语:此公形态,难以言传,欲知真相,只能目睹。上引鲍通事的那几句英语,有齐思和的中譯:“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小人物吗?你们以为我去买一斤米、一只鸡吗?不是,我是大人物啊!我的手中抓着和平,抓着战争,要是我打开它,那就和平,要是我合上它,一定打仗!”确实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
就词语本身而言,记录中“thinkee”
“catchee”和“shutee”这类“拖尾巴”英文确有故意丑化的成分。不过话说回来,宾汉姆也不能仅凭偏见虚构出这样一个人物。
只要有人类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存在,意识形态和情感文化就会被带入翻译与阐述中,我们需要警觉其中的偏见与谬误,但许多问题并不是翻译本身的问题。实话实说吧,假如翻译“欺骗”了你,不必吃惊也无须沮丧,因为明天也是一个样。或许明天不一样,明天该由AI来翻译?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