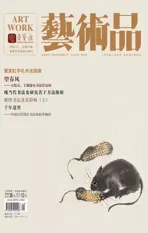黄宾虹手札书法探微
2020-06-04史可婧
文/史可婧
黄宾虹是近代艺术史上一位“不能仅以画史目之”的学者型艺术家,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他的艺术历程中,书法与绘画是不可分割的,以书养画与以画养书交融在黄宾虹的研究和创作中,是黄宾虹在书法创作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因素。黄宾虹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金文篆书和行书,而其行书多见于手札书信中。其手札古朴自然,具有一种美质于内的书卷气息,字里行间都给人清新脱俗、风规自远之感,是为无意于佳乃佳之作。同时黄宾虹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功底对其书法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书写意识和观念,还是笔法和墨法都深深体现出金石学的滋养。
一、黄宾虹手札中的自然潇散之韵
手札作为一种具有久远历史和高度实用的书法形式,相比于卷轴、楹联、匾额等书法形式更为自由随性,在书写过程中具有一般书法创作所不具备的随机性,并不需要刻意计较工拙,因此书写者往往能在一种最惬意的书写状态下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水平,因此也最能体现书家的才情和修养。黄宾虹一生对金石的研究以及晚年对笔墨的锤炼使其在日常书写中表现出对笔墨超高的驾驭能力。苏轼在《评草书》中便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黄宾虹的大量手札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书写的,无论是与友人互通书信,还是诗稿画稿,亦或是一些绘画题跋,相比于精心创作的作品包含更多自然萧散的韵味,充分体现了他终于一生所追求的“内美”理念,这些不经意而为之的笔触和线条,所展现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一)手札书法作为日常书写的特性
手札书法具有比其他任何书法形式都自由随性的书写空间,有学者指出:“由于尺牍为互通音讯而作,故书写时意在表达心境,直抒胸臆,而不在书法之艺术表现,是以笔法线条无需雕琢刻画,结构行气毋庸布置安排。在这种无意求工的情况下书写,呈现出的却是‘无意于佳乃佳’的真率自然与潇洒随意,此即尺牍书法与其他形式之书法大异其趣之处。”1书家在手札书写中往往任情恣性,不计得失,更为真切地展现出作者的真实水平和情感,实现真正的“下笔或无意,兴合自妍捷”。
王澍《论书剩语》曰:“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烂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书法史上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奉为高不可及的理想,遂有“书不入晋,徒成下品”之说。晋人之韵,本于心性,在乎天成,故欧阳修言:“予尝谓法帖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2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魏晋书法“初非用意”的肯定,他认为当时人写字皆是“施于家人朋友”,是“逸笔余兴”之作,所以“初非用意自然可喜”,而今人“弃百事”“专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是不可取的。由此可见,古人对书写的状态和心境尤为重视,往往“偶然挥运”方可实现“自成神妙”的境界。
事实上,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往往就是这些不经意而出的手札,如锺繇的《荐季直表》,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十七帖》《丧乱帖》和《奉橘帖》,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和《祭侄文稿》,怀素的《食鱼帖》,米芾的《珊瑚帖》,等等。苏轼在《评草书》中便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3到了《宣和书谱》中,便充斥着大量对这种无意乃佳的艺术现象的极力推崇,如:“作行草尤妙,初非经意,而洒然痛快见于笔下。其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4清代傅山在《散论》中云:“吾极知书法佳境,第始欲如此而不得如此者,心手纸笔,主客互有乖左之故也。期于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有一字之天。神至而笔至,天也;笔不至而神至,天也;至与不至莫非天也。吾复何言?盖难言之。”5正如傅山所言,如果写信札需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描摹和苦心经营一番,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行为。
(二)“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状态
黄宾虹自言:“我的行书借鉴于唐太宗《温泉铭》,因存晋人书肇自然风貌,吸取笔意,不袭其貌,形成自然风格,故此我的书法胜于绘画。”6由此我们可知,晋人行书“书肇自然”之风貌是黄宾虹所追求的。黄宾虹少年时期从唐楷入门,勤于临习“二王”法帖,并深刻领悟魏晋书法的风雅韵味。为能临池晤对,探究画法,他还不惜重金购得若干晋唐遗迹,这些遗迹对他行书品格的形成和绘画用笔的总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身处“碑学”大兴时代,虽受时风熏染,但不像包世臣、康有为和陈介祺这样的名家崇碑贬帖,而是将碑的古朴凝重,帖的自然流畅都化为己有,不断加深对笔法的认识和对“内力”与“内美”的追求。加之他一生钻于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究,篆籀书体的雄峻奇肆、天真烂漫、苍茫古朴的意态,逐渐深入他的意识中。黄宾虹自言每日晨起都会观古人画作,用粗麻纸练习笔力,几十年从未有间断,这些都是他得以实现“信手而书”的基石。伴随着他在金石文字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书法取法愈发高古,审美格调愈发高雅;同时以金石笔法入画,绘画也不断为其书法注入活力,可以说以书入画与以画养书交织在黄宾虹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提升着他书画创作的境界。随着年岁的增长,心性的成熟和趋于平和,加之书法技艺的纯熟和书学理念的不断沉淀,其书法也臻于妙境。
我们由此来看黄宾虹的手札作品,有些行书的结字中融汇了篆隶的用笔和结体,在最后一笔上往往会尽情宣泄而显得夸张,潦草之处更接近于“一笔书”,但却不会因为失控而轻浮,笔力依然雄厚,这都得益于他金石文字的功底,其手札的艺术价值和魅力正在于这种雄强放肆与自由不拘中。以黄宾虹1938年致陈柱尊的一封信札为例,通篇行笔流畅,结字紧凑,行气几乎没有间歇和停顿,字与字间的联系紧密,尽显魏晋自然消散之气象。最突出的是其中用墨的特点,一眼望去形成浓淡缓急不同的几个块面,墨色变化丰富,通过墨色的干枯浓淡来调节着通篇气息,可谓精彩。清张庚言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类。”“发于无意”正是强调当求无迹之气韵,此即“无意于佳乃佳”。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黄宾虹之所以可以如此自然随性地书写出这些作品,是因为其已经具备了深厚的书法素养和艺术心理定势,具备了驾驭毛笔和控制情感的能力,这些无意产生的杰作是在无数次有意的书法锤炼下诞生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无意求工,不存在任何刻意的经营设计,“偶然挥运,自成神妙”,这正是黄宾虹手札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
他晚年的行书线条流畅奔放、浑厚古朴,结字生动,可谓人书俱老。如与陈柱尊的书信,表面看似略不经意,实则蕴含着对笔高超的驾驭能力,用笔力透纸背,起笔有锋,转折有波澜,收笔收得好,古朴中见飘逸,凝重中见流动,尽显魏晋风韵。再如致汪孝文书信,整体呈现出一种逸笔草草,潇洒散漫,不疾不徐,字与字之间不会牵强引带,真切展示出黄宾虹书写的真实状态。他不会小心谨慎地刻意安排,也不会遵循正规的格式,不囿于一切形式的安排和造作,而是随心所欲地书写。从信封中可以看出黄宾虹用笔遒劲有力,笔力上厚重处有如高山坠石般有力,干枯处又如万岁枯藤般遒劲,这正是黄宾虹所追求的“书肇自然”之境界,整体上给人一种自由散漫的气息,可谓达到了神采为上的艺术境界。
二、“字如其人”在黄宾虹手札书法中的体现
中国书法史中的一个核心品评标准—“字如其人”,自古被用来评价一个人的书法与其道德、品性、情感等方面的相互映射,后世学书者和书论家在选取师法对象和品评书法作品时,当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参考这些书写本体以外的价值标准,这关乎到书家个人品位和作品格调。
(一)书家人品、性格与书法创作
中国自古有“知人论世”的传统,作为一种文学鉴赏方式,是指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应当充分考虑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由此返观书法鉴赏中就是“由书及人”,出现了“知人论书”的鉴赏原则,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品人”的价值标准。品人,不仅要考虑书写者本人,更是社会或书学界对书写者的认知和认可程度。项穆言“有诸中必形诸外,观其相可识其心”7,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的人品胸怀、品德修养、气质气魄的高低优劣,决定着作品所达之情的高低优劣,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作品的生命和价值8,因此古人云“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大凡被后人追崇的艺术家,人、文、艺多是三位一体的,可以说“画品”“书品”“诗品”都根源于“人品”。
赵壹在《非草书》中言:“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在手,何强为哉?”9孙过庭在《书谱》中也提到:“质直者刚挺不道,刚狠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动者过于刽迫,孤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赛钝,轻琐者染于俗吏。”10这就是说不同性情之人创作出的作品也具有不同风格。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言:“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颐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11此中“人品”,即是指人的气质、德性、精神追求等综合而成的品格,“依仁游艺”的高雅品格是作品“气韵生动”的前提。12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提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只有心无杂念,胸怀大义的书写者,写出的字自然带有超脱世俗的高雅,即“人由心正,书由笔正,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13。可见,古代书家早已知晓书法风格与创作者本体之间的关系。
黄宾虹认为,书法艺术创作不仅要把握好书写技巧和规律,同时也要展示出人的性情和心境。他强调书法是精神的载体,在创作时要萧散简逸,一任自然,不能刻意地因书法而为之。14所谓“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15,所以书法不单单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功能,抒发情感、表达性情才是更重要的。他在给夫人宋若婴的信中说道:“来信字迹强硬,无温和含蓄之气,阅之令人生畏。无论字画,皆要有舒和润泽,可以见胸怀之静雅,情性之温顺。为人之道,让则生,争必伏有杀机,观字迹可见亦如此。”16这里,他把书写者性情的“静雅”“温顺”“温和”“含蓄”与书迹的艺术质量联系了起来。他在《文字书画之新证》也提到:“学者志道据德,依仁游艺,通古而不泥古,非徒拘守矩矱,致为艺事所束缚,人人得其性灵之趣,无矫揉造作之讥。”17由此可见黄宾虹的艺术观念即为抒发“性灵之趣”,而非“拘守矩矱”和“矫揉造作”。所以,好的书法作品一定会透露出书写者的价值观念、精神面貌甚至脾气秉性,这不仅仅是通过作品的文辞内容来展现,更是通过书法中每一个字体的取势开阖、点画的处理、章法的布局安排来展现,都是书写者独一无二的表达。我们由一幅书法作品看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内容,更是背后的“人”与“文”,正所谓“得之象外,超以寰中”。黄宾虹的书作表现出“古厚雄沉”的同时不失“流动舒展”,两者的完美融合使作品不入于呆滞板重。他最忌线条轻滑柔媚,一如其为人质朴谦和、温文尔雅,气象自然是常人无法达到的。加之黄宾虹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深厚的学养,以及对艺术本质纯粹的追求,使其落笔自然不俗。他在给夫人宋若婴的书信中,言辞质朴亲切,字迹温和内敛,一反他平日里手札大开大合、狂放任性的书风,他对于家庭所表现出的那种心性的成熟,皆化为纸上志平气和的文字。
(二)黄宾虹人品对其书法的影响
书法艺术体现的是一个书写者的人品和书艺的双重魅力。在黄宾虹看来“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18。黄宾虹在《论中国艺术之将来》一文中将人的品格与创作直接联系起来:
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自然凑合。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污慢之工争巧拙于毫厘。急于沽名嗜利,其胸襟必不能宽广,又安得有超逸之笔墨哉?19
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始终被后人尊为学习的楷模,原因就在于“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20。而宋代书家蔡京,其书法在当时也备受追捧,而经过历史检验之后却被除名于“宋四家”,其作品流传甚少,原因就在于“其悍诞奸傀见于须眉”。书法史上一直对颜真卿的为人和书作有很高的评价,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忠肝义胆的人格和刚正不阿的品行。美国学者倪雅梅(Amy McNair)在其近期发表的著作《中正之笔—颜真卿的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中就特别指出,关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这件未经精心处理和雕琢的手迹草稿为何备受中国古代文人的欣赏和珍视,除了其深厚功底支撑下而即兴迸发出的超常表现力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符合了古代文人在道德上和书法品评中对“巧”与“拙”这组对立概念的认识。我们看颜真卿的楷书“中正浑厚”一如其为人“正直坚韧”,所以作者认为正是颜字的“圆”“拙”“中锋用笔”以及不加修饰等因素,使得历代文人认为其是“善良品德的纯粹表达和自然流露”,于是其书“似其为人”。21
关于黄宾虹的人品与性格,我们可以从傅雷1962年为汪己文编《宾虹书简》一书的前言中有所认知:
(宾虹先生)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凡此种种,既为先生故旧所共知共仰,于书信中亦复斑斑可考。22
其实,从黄宾虹数十年如一日地在书信中传达着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殷切希望,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将自己的艺术心得诉诸学生,都可看出其为人。如题学生朱砚英的山水册页,这是一篇钢笔书写的小稿,写于黄宾虹七十八岁时,书风同其毛笔手札一般不激不厉、含蓄内敛、饶有风规,文辞内容殷切真诚,结尾表示自己虽已衰发,仍然期待其学业有成,足以见其对弟子“循循善诱无倦色”的品德。
黄宾虹认为“缘古人以画为游艺,不求名利,乃修养之道尔”,由此可见其“依仁游艺”的创作心理。他作画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更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通过自己的笔墨实践,来为中国传统艺术寻求在新时代新文化嬗变的时代里立足并使其重新获得生机。如此崇高的人生理想和谨慎务实的秉性使他的艺术创作不流世俗,并不会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或者对世俗风气趋之若鹜,他“黑乎乎”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受大家推崇,而他自己都知道要到五十年后才会被认可,但他仍然坚守本心,笔耕不辍,这种超前的艺术观念和志坚气浩的心境是同时代书家难以企及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黄宾虹的书法取法高古,追寻一种“大美不雕”“美至于内”的艺术境界,作金文书法作品取字唯“奇”、唯“古”,肯定傅山“四宁四毋”的美学观,从而其书法“骨格坚正”“格调高雅”。他的手札不会给人一种精心制作的端正齐整,在他看来那是娱人感官的工匠之字,因此他往往会在书写时融入更多主观的性情,反其道而行之,使作品变化丰富,在虚实关系、墨色浓淡、行笔缓疾、枯湿燥润等方面的处理都别具匠心。如黄宾虹晚年致陈柱尊一书称得上是表现力极强的手札,通篇用笔丰富多变,顺逆笔锋交替,有纤细之线条亦有浑圆之笔画,墨色枯湿浓淡结合,有“疏可走马,密不阻风”之感,结字多显大胆夸张,却从不涉于“狂怪”。方势独字用多后突然出现圆势独字或反之,字形较小的字节后出现字形较大的字或反之,这些不经意而为之的笔意给人以静中寓动、爽中有涩的对比,耐人寻味。正如陆明君所言:“书法立格,当以雅正筑基。雅而能附守于大美,得乎大众通感;正则具磊然振迅之资,而通乎骨气洞达之境。”23这种境界正是甘于淡泊、心境清虚的人才可以达到的。从留存的大量关于画史、画论的文字都表现出黄宾虹审慎度事和孜孜以求的学术心态,在历史转折的关键处,酝酿出了集其所有艺术思想于一体的“内美”主张,饱含了他对艺术本真的追求。
注释:
1 徐力恒《米芾书札管窥—以书信文化和书法为主的考察》,《北大史学》,2016年。
2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下册,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
3 苏轼《苏轼文集》,323页,中华书局,1986年。
4 潘运告编《宣和书谱》,138、222、260、32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5 傅山《傅山全书》,卷二十九《字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张桐瑀编《中国书法艺术大师:黄宾虹》,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
7 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515—53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8 张鸿翔《试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美术界》,2011年第06期。
9 赵壹《非草书》,《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54页,杭州出版社,2016年。
10孙过庭《书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76页,杭州出版社,2016年。
11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59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
12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上,344 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年。
13崔尔平《明清书论集》,28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14黄卓《黄宾虹书法艺术笔墨思想的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15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20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6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17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40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18张公者《学养与书画》,《名作欣赏》,2012年10月。
19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20李瑞清《清道人遗集》,黄山书社,2011年。
21〔美〕倪雅梅(AmyMcNair)《中正之笔—颜真卿的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22汪已文《宾虹书简》,2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23陆明君《书坛藻鉴》,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