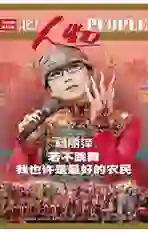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是是非非
2020-06-01木匠
木匠
在历史剧《清平乐》中,范仲淹是被当作一个道德标杆来塑造的,吕夷简也是被当作仁宗朝数一数二的能臣来塑造的。但这两个人并不对付,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范仲淹因何会被称为“大宋第一君子”
范仲淹向有“大宋第一君子”之称。何谓君子?就是襟怀坦荡、不畏强权、刚直不阿、严于律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他也的确是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
范仲淹,字希文,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出生于武宁军(今江苏徐州)。当时,他的父亲范墉正在武宁军节度使的幕中做掌书记(相当于军长官的机要秘书,属于下层官吏)。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顿之中。母亲谢氏在将丈夫的棺材运回丈夫的老家吴县(今苏州)后一年,就为生活所迫,改嫁了时在平江府任推官的朱文瀚。同时也让他改姓了朱。朱家虽不富裕(推官的级别还没有掌书记高),但对他们母子来说,也算是有了一个吃饭的地方。
范仲淹(朱说)自幼酷爱读书。继父待他也还不错,至少是很支持他读书。但天有不测风云,他十一二岁时,继父又去世了。继父这一走,朱家人对他们孤儿寡母的态度也逐渐起了变化,为了供他读书,母亲不得不更加的精打细算。而他为不用整天看朱家人的脸色,同时也为得到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就自己搬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座山上、里面已经没有了和尚的小庙中住。每次他到这里,都只能从家中带来少量的米,然后,就自己在寺院中烧火做饭。为了节省粮食和时间,他都是在夜晚,一边读书一边熬粥。粥熬好了,才去睡,第二天一早,锅里的粥结成了团,他会用刀把粥团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下午吃两块,一日两餐。就的菜,都是他从寺后山上采来的野菜———将野菜切成细末,再加一点盐搅拌一下,便大功告成了。野菜的细末叫“齑”,所以后人就把他这种清苦读书的生活称作“划粥断齑”了。
23岁那年,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伤心不已,毅然决定要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离家时,他对母亲说:“十年之内,我必会考上进士,等我做了官,就会回来接您。”
在应天府书院,他学习更加努力,五年竟没脱过衣服睡觉。当时,和他一起在书院读书的应天府留守的儿子见他过得实在是过于清苦,就要送他一些好吃的。但却被他婉言谢绝了:“我吃粥已经习惯了,如果突然吃到这种美味,再回过头来吃粥,一定会觉得难以下咽,所以,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粥吧。”
还有一次,宋真宗来应天府拜谒祖庙,排场搞得很大,大家都去看热闹了。唯独范仲淹不为所动,仍然坐在那里静心读书。有个同学要拉他一起去,他说:“以后面圣的机会有的是,又何必急在这一时。”可见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早就把自己当作是以后的朝廷重臣了。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范仲淹终以“朱说”之名考取了进士。之后,便被授予了广德军(治今南京)司理参军。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母亲接来侍养。随后,又上疏真宗皇帝,请求恢复范氏宗姓,并很快就得到了恩准。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范母去世,时任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令的范仲淹回到应天府为母丁忧。时,在应天府做知府的晏殊一向都很欣赏范仲淹的人品和学问,于是,就把他请回了应天府书院,任主讲。他在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经常教导学生读书当以“从德”为目的,而不是以科举仕进为目的;读书人当严于律己,崇尚品德,忠君爱民,敢为天下先,并非常善于以身示教,应天府书院在他去了以后,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了。
刚正不阿,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
天圣七年,范仲淹丁忧期满。因此前,他曾给朝廷上过一道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撤冗员、安抚将帅,得到了宰相王曾的称赞。当时已被调回枢密院任职的晏殊,便不失时机将范仲淹作为一个人才推薦给了宋仁宗。晏殊曾做过仁宗的老师,仁宗也一直对他比较尊重,所以他的话,仁宗还是愿意听的。且仁宗当时已经19岁了,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且并没有要还政于仁宗的意思。仁宗要想亲政,就需要让一些既有能力,又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进入朝堂。于是,就把范仲淹召进了京,给他在秘阁安排了一个校理的职位。
谁知,范仲淹一进京,就干出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是年冬至,仁宗准备率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而范仲淹却认为仁宗的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于是,就给仁宗上了一道奏折,说:“皇帝固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是和百官一起在金殿之上参拜太后,势必会有损皇帝威严。”
据说晏殊在得知了范仲淹上了这样一道奏疏后,不由大惊失色。要知道刘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而是当时帝国的最高执政者。且仁宗虽然对太后一直把持着朝权不肯放手有所不满,但与她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范仲淹这道疏一交上去,万一惹恼了太后,或者是皇上,不仅他自己的仕途完了,弄不好还会连累到他这个举荐人。于是,晏殊就急忙将范仲淹叫了来,批评他不该如此莽撞,但是范仲淹却很不以为然,从晏府回到家后,还意犹未尽地给晏殊写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细地向他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并再次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凡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定当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好在,范仲淹虽没能阻止仁宗率百官在金殿上给太后行礼,但也没有因此而被追责。
这事本来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范仲淹他还不干了———自请离京为官!于是,仁宗便把他安排到河中府做了个通判(通判是州府中,负责掌兵民、钱谷、水利和诉讼的官员,并对州府的长官负有监察之责,是以也称“监州”,权力还是不小的)。其实,仁宗对他还是很欣赏的,做出这种安排,也是出于对他的保护,同时也有让他到地方上多历练历练的意思。一年以后,范仲淹又被调到更大的陈州任通判。
此后,向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仍不改其本色,又多次上疏朝廷。今天说朝廷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是“劳民伤财”;明天又说朝廷应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后天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等等。他的这些上疏,虽均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还是打动了仁宗。
与吕夷简的三次冲突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一亲政,即将范仲淹召回了京师,任命他为右司谏(属于高级言官)。群臣为了讨好仁宗,多爱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为政之失,独范仲淹却以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是以对太后的过失,朝廷应当加以掩饰,以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诏令朝廷内外,不得再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这也是刘太后死前留下的意思)。又是范仲淹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说:“频立太后,会给天下百姓造成皇帝不能亲政的错觉。”仁宗也马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取消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其实,这事儿我怎么看都像是仁宗和范仲淹串通好了,演的一出戏:仁宗想立杨太妃固是出于孝心,毕竟杨太妃是他的养母,可要说想让杨太妃参与军国大事,当不太可能。他可是盼亲政盼了好多年了,奈何,刘太后生前,一直借口他还年轻呢、还不够成熟,而不肯撤帘。现在,刘太后终于走了,难不成他还想再找个太后来,管着自己?
好了,在大致了解了范仲淹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吕夷简。
吕夷简,字坦夫。跟范仲淹不一样,他出身豪门,他的伯父吕蒙正是宋太祖时的宰相;他的父亲吕蒙亨也曾官至光禄寺丞。他是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进士,初授通州通判。不久,就因治水有功,而被擢升为了知滨州(今山东滨州)。他在滨州期间,深切地感受到当地农民的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于是,便上书朝廷,要求免征“农器税”(当时,农民种地,不仅每亩地都要交一斗米的田税,这已经不少了,但随着朝廷“三冗”开支的日益增长和每年都要向辽、西夏输送大量的岁银,竟又规定了农户使用农具也要上税,这个税就是“农器税”,此税一出,很多农民因不堪重负,都转行做别的营生,竟致出现了土地大片撂荒,甚至官逼民反的现象)。他的上书得到了真宗的首肯,就下诏取消了“农器税”。他也由此成为了百姓心中的好官。
范仲淹入朝时,吕夷简已当上了大宋的宰相。其实要说起来,范仲淹能顺利入朝,被拜为右司谏,他也是出了不少力的。召范仲淹回朝,固然是皇上的意思,但他毕竟是首辅,如果他不看好范仲淹的話,也不会授给他一个像右司谏这样重要的官职,这说明他对范仲淹其实也是很欣赏的。可让他万没想到的是,范仲淹在入朝后不久,就跟他发生了冲突。
吕、范的第一次起冲突,是因为“废后事件”。时,郭皇后嫉妒成性,心胸狭窄,行为蛮横,且立后九年,未能生子。于是,仁宗便有了废后之意。吕夷简因为与郭后有矛盾,所以他是极力赞成废后的,而范仲淹则是反对废后的,甚至还联合了十几名言官,跪伏于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敢见,就派吕夷简出来解释。他们便与吕当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直到把吕辩得是理屈词穷,无以为对。史家多以此视吕为奸臣,而认为范刚直不阿,是个英雄。但就结果来说,吕为仁宗推荐的新皇后———曹氏(也就是剧中曹丹姝),除了样貌不如郭后,几乎样样都比郭后要好得太多了。可见他的舍弃郭后,而力主以曹氏取而代之,不仅满足了仁宗的废后要求,也更符合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仁宗和曹后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而就抹杀了吕的良苦用心,更不以此就判定他是一个奸臣。
而且,吕夷简也并没有因为范仲淹在废后问题上,挑头跟自己作对,就对范严厉打击。只是把他出为了权知开封府事。开封也就是汴京,是北宋的国都,他这个新职务(大约就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的重要性,其实要严格地说起来,比右司谏还要更高一档。
范仲淹也是不负众望,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京城的官僚机构,剔除弊政,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使开封府“肃然称治”了,甚至当时在开封府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谚:“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吕、范的第二次冲突,发生在景礼二年(公元1035年)。是年,范仲淹因有感于吕夷简选拔官吏多出于其私门,于是,就向仁宗上了一幅《百官图》,指出吕相有用人唯亲,意在朝中广植党羽之嫌,并进一步指出“进退近臣,须当由皇帝自己把握,不能全权委于宰相”。据史书记载,吕在看到这个《百官图》时,很是生气,但仍隐忍没有发作。其实,我以为吕夷简是提拔了很多和他关系好的人,虽然不能说他一点私心没有,但我总觉得,换谁坐在他那个位子上,大概也是一样。关键还是要看他提拔的那些人,是否称职。只要大部分都称职,那就没什么好指摘的。总的来看呢,吕重用的人,大部分也还是称职的。不然,又哪里来的“仁宗盛治”?再说,他把你范仲淹放对了权知开封府事的这个位置上,难道也错了?岂不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吕、范的第三次冲突,发生在景礼四年(公元1037年)。是时,西夏人南侵的野心已显,范仲淹主张迁都洛阳。仁宗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则表示范不过是一“迂阔而不可信”之人。范仲淹闻之,又写了“四论”攻击吕“专权徇私,阴窃人主之柄”。这下,终于把吕夷简给惹毛了,于是,他便以“越职言事”的罪名,把范仲淹贬为了知饶州,又阴使让人上书,请求在朝堂上,挂一个“朋党榜”,将范仲淹和支持他的那些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使人引以为戒。其时,梅尧臣还曾作了一篇《灵乌赋》送给范仲淹,劝他以后还是少说话、少管闲事为好。没想到范仲淹马上就回了他一篇《灵乌赋》,强调自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但由于范仲淹当时在士大夫中的声望极高,在他被贬后,很多士大夫都站了出来,接连不断地为他辩白,不久,吕夷简也落职为了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许州。
吕、范二人的最终和解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攻宋。范仲淹又以知永兴军的身份,被调到了前线,抗击西夏人,吕夷简也再次拜相。因为范仲淹在前线的表现相当突出,仁宗于是有了让他官复原职的想法,但又怕吕相不同意。没想到,吕在了解了仁宗的心思后,竟主动对仁宗说道:“范仲淹,乃是当世贤臣,官家要用他,怎能只让他官复原职呢?”仁宗听了,十分感动,认为吕不愧是一忠厚长者。于是,便任命了范为龙图阁直学士兼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地位相当于副相)。后来,范仲淹在听说了吕夷简对他的评价后,亦十分真诚地向吕表达了感谢之情:“先前因为公事触犯了相公,没想到相公竟然还会这样奖励我、提拔我。”吕亦表示:“我怎么敢再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
庆历元年(公元1041的),范仲淹又兼任了延州知州,继续抗击西夏。不料,一次处事的失当,竟被人扣上了一顶“私通敌国”的帽子。又亏得有吕夷简为他说情,并坚称以自己对他的了解,他绝无可能会私通敌国,将他保了下来,只受到了官降一级的处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吕夷简因为年事已高,自觉已无法再胜任宰相一职,遂向仁宗提出了辞职,并向仁宗推荐范仲淹、韩琦和文彦博入朝辅政。仁宗答应了,最后,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在成为参知政事以后,就雄心勃勃地推行起了他的改革。吕夷简曾诲汝谆谆地告诫过他,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步子迈得太大……
可惜,范仲淹并没有听进去,一年以后,他的“庆历新政”终于还是因操之过急,步子迈得太大,而告失败。他也又被降为了河东陕西宣抚使。在去上任的路上,他又去看望了已病入膏肓的吕夷简。此时的他,似已对吕夷简当年很多所作所为都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感悟,言谈之中,颇有“悔语”。不久,吕夷简病逝。范仲淹当时正在边关,闻讯后即撰文说:“得公遗书,适在边土,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所以综上所述,吕、范的确不是一类人,但他们说话、办事的出发点,还都是为了大宋,争斗也是很激烈,但总的来说,还是“明争”而非“暗斗”,可谓“君子之斗”,就像后来的王安石与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