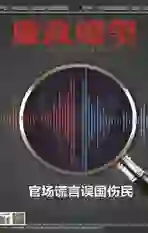年关,那些关于新衣服的企盼
2020-05-25张翎
张翎
儿 时在老家过年,印像最深的不是年夜饭,也不是压岁钱,却是新衣。母亲爱漂亮,又是个极其好强的女人,日子过得再紧,吃上可以马虎一些,头脸却必须是光鲜的。所以岁尾年终之际,一家人的新衣,便成了必置的年货之一。
从小跟在母亲身边,自然很早就有了关于美的朦胧意识。一到腊月初,母亲就拎着一个装了布料的网兜,领着我和哥哥穿过长长的凭票供应的年货队伍,拐进丁字桥巷一爿门上贴着“金剪裁缝”招牌的小店铺。
我积存了一年的耐心,便在缓慢的路程中零零星星地丢了一地。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吩咐裁缝,裁得长一些,宽一些,明年还能穿。而我却只能踮着脚尖,用几近哀求的眼神暗示裁缝,短一些,紧一些呀。
裁缝极为精明,剪裁出来的新衣,总是落在母亲和我设想的那个尺寸的中间。
在那个色彩和线条都很匮乏的年代,母亲最离谱的想像,也只能停留在一条红色的领边和几个盘花扣子上。但这却已是我关于过年的全部企盼了。
几天后,母亲捧了新衣回家,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仔仔细细地叠平了,压在枕头底下。夜里躺下了,却睡不着,脸颊感受着枕头底下那一层薄薄的柔软,觉得自己与新衣是如此地近,却又是如此地遥不可及。
一整个腊月,就在这样细雨一样连绵的等待中缓慢地逶迤着。直到大年初一,当我终于穿上那一套带着生硬压痕的新衣,和母亲走在拜年的路上时,我和新衣之间,却已经有了一层久别重逢的陌生。
对过年和新衣的企盼,如同一条细软却柔韧的丝线,穿起了我散珠般无章无序的童年和少年岁月。后来我渐渐长大,离开了故乡,去上海求学。大学毕业后,又去北京工作。
再后来,就离开北京,来到加拿大留学。一次又一次离家,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对过年和新衣的记忆,便渐渐地消蚀在求学和求职的环节中,变得遥远而模糊起来。
记得初来加拿大的第一年,在地广人稀的卡加利城读书,一切都是陌生而寒冷的。寂寞如雨前的天空,低矮却又无所不在地罩住了我的视野和心情。
那时的电话费极贵,四加元一分钟。我舍不得打电话,只能一封又一封地写信回家。郵期一来一往就是一个月。待那一纸的凄惶终于飘过一汪大洋抵达那岸,而母亲的慰抚又飘洋过海地回到我手中时,早已时过境迁了。
那年的除夕夜,我打了第一通国际长途电话。家里那时还没有装电话,我只能打到邻居家,让她喊母亲来听电话。母亲的喘息声隔着一条电话线遥遥地温热了我的耳朵,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母亲也哽噎着,两下都说不出话来,却听见父亲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你说话,你说话呀,电话费贵着呢。”
父亲后来终于忍耐不住地抢过了话筒,问:“你妈给你做的新衣,国际邮包寄出去两个月了,赶上过年了吗?”我想说早收到了,嗓子里却堵塞着一团噎也噎不下去的柔软。
回头一算,去国离乡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世事发生了许多变化,国际长途电话费已经变成了数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月租,微信一跃而上成为了隔洋沟通的新宠。
我父亲在七年前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的母亲则很是垂暮了,自然也寄不动过年的新衣了。即使她还寄得动,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我早已受周遭环境的影响生出了与她迴异的审美观念。
在她的眼光里,我的衣装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而且领口总是太低。甚至颜色,也似乎总是在隐隐地违拗着她的规范。
我现在隔几天就打电话回温州和母亲聊天,信却是再也不写了。在我定居的那个叫多伦多的城市里,每一个角落都住满了中国人。过年的喧闹几个月前就开始出现在报纸电视和电台的广告上。
然而关于新衣的企盼,早已被岁月的积尘严严实实地压在记忆的最底层,虽然不曾彻底忘记,却是极少想起了。我心里却比从前更加明白:过年不过是长长的岁月里的一些句逗,把日子分成一个一个的段落,好叫我们借机告诉亲人和朋友们:在这个段落里,我们活着,平安,也思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