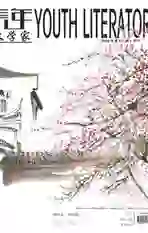试论《哈吉穆拉特》的艺术特色及史诗建构
2020-05-06郑巧
摘 要:《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一部不太为人注意的史诗性中篇小说。《哈吉穆拉特》的独特文学价值在于它是的散文和史诗兼备的历史小说,在平淡的叙事中却彰显着人性的张力,体现了托尔斯泰繁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哈吉穆拉特》;哈罗德·布鲁姆;散文小说;史诗
作者简介:郑巧(1994-),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2
引言:
《哈吉穆拉特》[1]讲述的是高加索鞑靼人哈吉穆拉特的英勇的事迹。他本是反抗沙俄统治的高加索穆斯林派领袖沙米里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副帅,因沙米里嫉妒他,要杀他,并监禁了他的家人,他被迫无奈向沙俄投诚。为解救家眷,他又私自逃离沙俄军营,沙俄以为他叛变,在与沙俄的追兵斗争中,他陨殁了。哈罗德·布鲁姆对《哈吉穆拉特》推崇备至,评价这部小说时说:“它成了我衡量小说崇高性的一块试金石,是世界最佳短篇小说,或至少是我读过的短篇小说中最好的。”[2]《哈吉穆拉特》的卓越的成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篇小说,它也是一篇散文,一部史诗,托尔斯泰用不紧不慢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冲突的魅力。
一、散文特色
《哈吉穆拉特》不仅仅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更是一幅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的散文。《哈吉穆拉特》小说的散文之美,正体现在托尔斯泰对风景的刻画、对风土人情的描摹这两个方面。
(一)风景的刻画
从小说的引子部分开始,托尔斯泰就为读者铺开画卷。以“万紫千红、百花斗妍”的仲夏晚归图为开端,带领读者接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花的海洋之中。托尔斯泰不遗余力地渲染着花的颜色,“红的”、“白的”、“粉红的”、“黄色的”、“淡紫的”、“蓝色的”等等各种颜色轮番上阵,各种颜色之间争奇斗艳。故事的叙述进程仿佛被中止,情节的进程被人为地打断,小说一开场就具有散文般的“绘画美”。
接着托尔斯泰的大笔开始收束,画面逐渐缩小,最后聚焦于一朵“盛开的牛蒡花”。这朵花不仅是全篇小说的中心意象,也是哈吉穆拉特的隐喻。与前面开头的花海中描绘的“毛茸茸”“娇嫩”的花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别名叫“鞑靼花”的牛蒡花,“刺手”,“粗犷”,“不驯”,“我”与花“搏斗了五分钟”才将其折断。接着托尔斯泰又用夸张的手法写了这朵花被碾压又顽强地挺立着:
“好像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了五脏,砍掉一条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消灭了它周围弟兄们的人,绝不低头。”
托尔斯泰的笔调冷漠近乎残酷,可以称之“残酷写作”的模范,充满了暴力与血腥。这与前面的浓郁的抒情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读者读完,顿觉不寒而栗。但是熟悉托尔斯泰小说艺术风格的读者会想到,什克洛夫斯基曾在《作为手法的艺术》提出了“陌生化”的创作理论来分析托尔斯泰的小说:“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在于,他不用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初次发生的事物,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名称,而是像称呼其它事物中其它事物中相应部分来那样称呼。”[3]因为如果托尔斯泰只是简单的去写“我”与一朵花的“斗争”,那么,无论怎么写“我”取花的艰辛,都无法令读者达到“震惊体验”的效果。唯有将花进行“陌生化”的处理,赋予花以人的品格,并利用读者的“艺术共情”的心理体验,才能让这朵牛蒡华的形象从众多平凡的花丛中以“陌生化”地方式突显出来,以达到延长读者阅读体验的效果。
(二)风土人情的描绘
《哈吉穆拉特》不仅在自然风景的描写上处处体现着化小说为散文的叙述笔调,即使是在描摹风土人情方面,也极具散文化的特点。小说中插入的很多山歌、民谣以及童话传说等,一方面既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又延缓了故事的叙述节奏,使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
例如,在第19节,沙米里得知哈吉穆拉特投诚沙俄了,立即威胁哈吉穆拉特的儿子优素福,命令他写信给哈吉穆拉特,如果他不投降,就要杀了他儿子。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担心着哈吉穆拉特前途未卜的命运。但在紧接着的第20节,托尔斯泰的如椽大笔突然一撇,转而大篇幅的引用歌词,尤其山歌中的這一段:
“枪弹,你激烈,你夺去人的生命,但当我忠实的奴仆不也是你吗?黑色的土地呀,你埋葬我,但是我的马蹄践踏的也是你吗?”
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托尔斯泰有意地的利用民歌的插入将故事叙述的节奏减慢下来,打破了情节叙事的连贯性,使小说的整个叙事显得“节外生枝”,较为的随意和散漫。
从22节之后,小说更是随处可见各种民谣和山歌,以及充满象征意味的夜莺的歌声,使得小说的散文化倾向非常明显。另外,小说中随处可见的通俗口语、大量的语气词,如沙米里虽然唱着造反之歌,但大多都是语气词,“嗒啦——啦——哒哒”;以及哈吉穆拉特回忆童年时母亲的歌谣;候鸟之歌;骑兵之歌等等,也使得小说的叙事性的节奏不同程度地被减弱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歌谣、口语,使小说生动活泼,富有音乐感。散文之歌铺成的历史小说,淳朴自然,天然去雕饰,小说的情节的紧凑无意间被这些歌谣给冲淡了。所以评论家在评论《哈吉穆拉特》的艺术风格时候就说:“托尔斯泰对艺术散文中富有表现力的新手段所作的长期的探索,在《哈吉穆拉特》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家所追求的,就是叙述明快,朴实,简练,情节集中而有结尾;广泛依靠民间语言及其丰富的词汇和成语。”[4]厚重的历史感被隐匿在一阵阵柔和平淡的歌声之中,“夜莺婉转的啼叫声、苍凉悲壮的歌声、霍霍的磨刀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曲动人的乐章。”[5]我们在这歌声中,净化了自己,深刻体验到一种审美的尊严和崇高的情怀。
二、史诗建构
《哈吉穆拉特》除了是具有明显的散文化性质的小说之外,还是一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型的史诗性质的小说。这使《哈吉穆拉特》呈现出崇高的精神价值。前文我们分许了“花”被四分五裂的过程,而哈吉穆拉特的死,是与花的消亡极其相似的:
“几声枪声,他身子一晃就倒下了…但他们(敌人)原以为死去的身体忽然动起来。……加治阿加(敌人)第一个跑到他跟前,拿一把大短剑向他的头扎去,他还以为有人拿锤子敲他的头,但他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敌人踩他,砍他……阿治阿加一只脚踩住尸体的背,两刀就把头割下来……鲜红的血从颈动脉涌出,黑色的血从头颅里直往外冒,洒在草地上……全体民团,像猎人围着打死的野兽那样围着哈吉穆拉特和他的卫兵的尸体……快乐地说说笑笑,庆祝他们的胜利”。
上述这段引文,极其残暴与血腥,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是极少见到这样“暴力”的场景的。通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它既具有古典时代的“野蛮式写作”特征,因为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联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描写赫克托尔之死:
“他(阿基琉斯)把赫克托尔的双脚从脚踝到脚跟的筋腱割开穿进皮带,把它们系上战车,让脑袋在后面拖地,赫克托尔拖曳在后,扬起一片尘烟,黑色的鬈发飘散两边,俊美的脑袋,沾满厚厚的尘土。赫克托尔的脑袋就这样在尘埃里翻滚。”[6]
这一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早就指出过:“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艺术家,像托尔斯泰那样,身上所存在的荷马的不朽的史诗因素那么强烈,他的创作中栖息着一种史诗的天然伟力。”[7]《哈吉穆拉特》里的主人公与《荷马史诗》里的主人公一脉相承的特点,也被哈罗德·布鲁姆揭示出来了:“哈吉穆拉特生与死都像个古代的史诗英雄,他融合了奥德修斯、阿喀琉斯和埃涅阿斯的长处于一身却不在他们的任何缺点。”[8]确实,在小说中,哈吉穆拉特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但是也是一个充满悲剧性色彩的人物。然而托尔斯泰在情感的表达上似乎更加令人感到惊诧,在一阵血雨腥风的恐怖屠杀描写之后,他的突然笔锋一转,用了极尽温柔的延续了散文的诗意笔调:
“战火纷飞时鸦雀无声的夜莺,现在又开始鸣唱;先是近旁的一只,随着是远处的齐鸣。”
这一悲壮残酷情感的高潮,读者还来不及宣泄,小说到此突然戛然而止。英雄之死的恐怖让人窒息,荡气回肠的壮歌之后的抒情小调却又是绕梁之余音,绵延不绝于耳。然而,在夜莺的歌声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挽歌的悲凉之音。在史诗般的死亡结局之后的散文化的收尾的叙述方式,着实令人感到惊奇,托尔斯泰不再执着追问形而上的逼近上帝的真理,也不再以上帝的视角俯瞰着芸芸众生,进行着喋喋不休的议论,只是如其所是的在记录一个人的死亡。
其实,通读文本,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哈吉穆拉特的悲剧在于,他是英雄的同时又是自然人,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无法对抗命运,因为他唤不起任何神明的帮助;另一方面,他无法对抗社会历史,他在沙米里的要挟和沙皇派的敷衍之中艰难挣扎,无能为力。所以,在他快要走向死神之前,插入了一个很具有暗示性的童话故事:
“一只鹰被人捉住,在人间住了一阵,然后回到山上伙伴那里。它回去时带着脚绊,脚绊上系了个银铃,别的鹰都不肯接纳它。它们说:‘飞吧,飞到给你带上银铃的地方去吧。我们这里没有银铃,也没有脚绊。鹰不愿离开家乡,就留下来。但别的鹰都不肯接纳它,最后把它啄死了。”
这段话其实就是哈吉穆拉特的命运的真实写照。他是英雄,是领袖,甚至是半神,但他就是不是真正的神。在整个大的环境中,他是渺小的存在之物,他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对抗沙米里,更不用说是沙皇的军队了。尽管“哈吉穆拉特有着赤子般的善良心肠,但同时又坚强,灵巧,有着罕见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他是个行动坚决精力旺盛的人”。[9]但是,高加索鞑靼人民眼中非凡的英雄、母亲眼中伟大的儿子、妻子眼中深情款款的丈夫、儿子眼中屹立不倒的榜样,他身上肩负太多的使命和太多的责任,他伟岸的身躯也经不起这么多的重量,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太多了,唯有死亡才是永恒的安息。
三、结语
纵观整部《哈吉穆拉特》,约计有大小人物六十多个,出场的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刺点”和“趣点”,极具艺术表现力。小说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高加索附近的山野军营中,时间主要集中在英雄哈吉穆拉特临死的那个时间段,也就一周左右时间。但却将爱恨情仇,生死欲望,家仇国恨,王宫大臣,贩夫走卒等一系列情感和人物熔于一炉,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描写都有条不紊,可以看出晚年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表现力已经炉火纯青、举重若轻,在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截取一个时间点,并用诗意的史诗手法将历史向读者娓娓道来。托尔斯泰用《哈吉穆拉特》这一小型化史诗对整个艺术创作生涯作了一次返璞归真式的回归性的总结,为其史诗性的创作历程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用小说均出自:(俄)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4卷),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3](俄)扎挪·明茨,(俄)伊·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王薇生编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4](俄)米·赫拉普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刘逢祺,张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5]王洪猷:《豪华落尽见真淳——论<哈吉穆拉特>的艺术特色》,载《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6](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1页。
[7]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89页。
[8](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9](俄)贝奇柯夫:《托尔斯泰评传》,吴均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