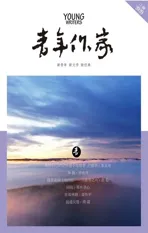我们去坐游艇
2020-05-01谢京春
谢京春
张茂拉着我去海边玩。那是四月里的一天。水很凉,还没有人敢真正下到海里去。只是有几个女孩子脱了鞋、提着裤脚沿着海岸走,旁边有她们的好朋友在给她们拍照,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水面被太阳光照得闪闪发亮,这正是拍照的好时候。我们坐在沙滩上一直看她们变换着姿势拍照,张茂没说带我来干什么,我们一到海边就在这里坐着。
还没到旅游的季节,海岸上人很少。在我们左边大约五百米的地方就是出租游艇的一家游乐场。老板举着招徕顾客的牌子懒洋洋地在海滩上踱步。要是没有生意他大概会在天黑前离开这里。张茂问我为什么没有把苏菲带来。他不知道,苏菲已经走了,我不知道她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他这个消息,于是我对他说,苏菲回了老家。其实苏菲的老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张茂问我,是不是跟苏菲吵架了。我说没有。张茂说我应该好好对待苏菲,因为除了她,再没有人能对我这么好了。我并不赞同张茂的话,但我还是点点头。很多人喜欢把将来的事情过早做出最坏的打算,希望以此来说服自己在此刻能多受点委屈,张茂的观点无非也是这样。我现在不想就此跟他展开一场辩论。
我承认苏菲很好。那时候她在市中区一家连锁的大药房上班。早在认识苏菲很久以前我就有失眠的坏习惯。有一阵子张茂曾拉着我去看中医,老医生给我开了一服祖传的秘方,里边有二十多种草药。我跟张茂说,吃中药太麻烦了,还要去买药锅自己煎。张茂拉着我去老医生诊所的里屋看,里边有一台专门煎药的机器。真空包装好了的草药汤从机器出口里递出来,就像一包又一包的袋装可乐,上边还清楚地印刷着老中医的名字和防伪标志。我当时对张茂说,这太棒了,我可以买回去放在冰箱里。可惜的是,这药我坚持吃了很久最终也没什么效果。后来草药汤没有了,我觉得冰箱里空落落的,就买了很多瓶装可乐放进去。后来又过了一阵子,社区里组织我们体检,体检报告上说我的胃不好,医生问我是不是经常喝饮料。我说是。我问医生,这会死人吗?医生说,不好说。但我觉得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不想把可乐戒了,因为那样我就得重新布置冰箱。本来我的房子里就空荡荡的,没几件像样的家具,但好在我的冰箱里一直塞得很满。
后来我在那家连锁药店里碰见了苏菲。那药店叫什么名字我一直都没记清楚,这些药店从外边看起来都太像了。但是苏菲在的那家药店的位置我记得十分清楚。我问苏菲我常常失眠,能不能吃药治疗一下。她要我多运动。我说我不喜欢运动。她说少用电脑手机。我说这不可能,我每天要按时敲击五万个左右的字符。她说要健康饮食要规律作息。我说不可以吃药吗,比如安眠药?最后苏菲给了我一盒灵芝片。我记得之前张茂带着我去找中医,老医生开的方子里也有灵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药的功效十分明显。我睡过好几次安稳觉,这其中当然也有苏菲的功劳。我跟苏菲之间发生的事情张茂并不全都清楚。尤其是后来有一次苏菲半夜来到我家,张茂至今对此一无所知。
我跟张茂坐在海边的沙滩上各自心怀鬼胎。为了找点乐子,我说我可以把那三个拍照的女孩子叫过来。张茂不同意。张茂并不是不想,他只是不敢。在很多时候我要比他自己更了解他。于是我站起来朝那三个女孩子走过去,此刻她们也正好来到了我的正前方。我大声地向她们喊了一声:你们好!那时候的海边并不嘈杂,风很小,浪一小波一小波地涌到岸边,冲洗着其中两个女孩子的小腿。她们其中一个人的裤脚被水打湿了一截。我已经走到了她们面前,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她们三个人也同样清楚地观察着我。我笑着问,可以一起玩吗?左边的那个女孩子稍微弯着腰提着自己的裙子,听见了我的邀请,她咯咯咯地笑起来。右边的那一个看起来要更高兴一点,她很痛快地说,没问题。紧接着另外一个替她们拍照的女孩子放下了相机,她问我,玩什么。我说,什么都可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坐游艇。我左手指向那家无人问津的游乐场,那个男人也向我们看了过来,他摇了摇手里的广告牌,好像我已经事先跟他约定好了一样。那三个女孩儿非常开心。在走向张茂的短暂路程中,我试图把胳膊放在其中一个女孩儿的肩膀上,就是刚才提着裙子的女生。离开海水,现在她已经可以把裙子放下来了。我的手刚刚搭到她的肩上,她就继续咯咯咯地笑起来,这一次比刚才更大声。另外两个女孩子扭过头来看向我俩,我则趁机提高了嗓门大声喊着张茂的名字,我说:我们去坐游艇!
张茂从地上爬了起来,车祸发生时他的右胳膊率先着地,现在血顺着他的小臂流向手背继而从手指尖滴下来。幸运的是,我毫发无损,尽管当时是我在前边骑着摩托车驮着张茂。那辆白色货车从右边的路口突然冲出来,还没来得及刹车我就撞了上去。货车司机跑到车屁股旁边一探究竟,那时候张茂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我的二手摩托车还倒在花坛里轱辘朝天。司机问我们,怎么回事。张茂很生气,他抬起右手指着司机的脑袋一顿破口大骂。但他的胳膊流血越来越多,他不得不让右胳膊垂下来才能缓解疼痛,所以骂了没几句张茂就停下来了。
货车司机继而把目光转向我,可以看得出他受了张茂的侮辱所以显得很不高兴。他并不高,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皮肤很黑,在阳光下反出油亮的光。我也有一件跟他相似的背心,那是我哥哥从部队里寄给我的,是07A 制式背心。我非常爱护它。看见司机我就想起我的哥哥,于是朝着司机嘿嘿地笑起来。他问我,你怎么没事。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是我骑的摩托车。司机说,你没长眼吗?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当时骑车的速度并不快。平时我一个人骑车的时候可以跑到80 迈,很多拉了货的农用三轮都追不上我,它们只能突突地冒着黑烟消失在我的反光镜里。但是那天我骑车驮着张茂,速度并不快。张茂冲到司机面前想要给他一拳,我知道这时候张茂的拳头一定没有多大的力气。司机不屑一顾,他环顾了一下自己的车屁股,没有多大的问题。司机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呢?司机说,不然拉你朋友去医院看看吧。我突然觉得这个司机人很好。我说,不用了,我可以带他去。听见这话,货车司机转身走向驾驶室,我听见他的嘴里嘟嘟囔囔说了几句话,但是我听不清楚,觉得那应该不是什么好话。张茂把一口唾沫吐到了小货车的后牌照上。那口唾沫遍体通红。司机很快打着火沿着路离开了,烟囱里冲出来的汽油味很香。我们从花坛里把我哥哥的那辆二手摩托车翻过来。我继续驮着张茂往前走。张茂说,慢一点。这时候我才发现摩托车的反光镜摔坏了,我看不见张茂坐在车后座上的样子了。我跟他说,我们去找苏菲。
苏菲很快帮张茂处理好了伤口,他的肘部磕掉了一整块肉。为了避免伤口裂开,苏菲用一块卷式夹板把他的胳膊固定起来,这样张茂的右胳膊就再也不能弯曲自如了。苏菲问我,这是谁。我说,这是我的朋友。苏菲说,这是怎么搞的。我说,我们撞了车。她说,你怎么没事。我说,我不知道。我又补充说我当时骑得并不快。苏菲不信。她还问我最近睡眠怎么样,我说有时候好一点。苏菲跟我说可以试试中药,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爷爷是个老中医。我说喝中药太麻烦了,还要煎。苏菲说不麻烦,现在卖的中药都是煎好的,有真空包装,就像喝可乐。我说我知道,但我还是不想喝中药,那一点用也没有。我用手指弹了一下张茂的胳膊,他没有很大的反应,看来他伤得并不严重,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值得庆祝。那是张茂唯一一次跟苏菲见面,他们彼此都留下了好印象。一直到张茂带着我到海边玩,他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张茂看见我们走过来也变得高兴起来。我的一只胳膊还继续搭在那个女孩儿的肩膀上,脸上却眉飞色舞。我们五个人一起朝着那家冷清的游乐场走过去。我很快就挑好了一艘最大的游艇,可以轻松地盛下我们五个人。老板扔掉广告牌很熟练地跳进去启动游艇。我们也紧跟着跳进去,然后按照老板的指示穿好救生衣。我跟张茂坐在一边,另外三个女孩子坐在一边。我们朝着大海前进,那时候天色已经快要变暗了,那个穿裙子的女生又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问老板,可以走多远。老板说,你想走多远。我说,能走多远。老板说,跑到公海转一大圈没问题。听了这话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没去过公海。我跟老板说请尽量开得远一点。老板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说快要涨潮了,到时候浪会很大。这时候游艇突然加速了,三个女生跟着尖叫起来,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害怕。马达的声音震耳欲聋,海水被游艇分成了两部分,白色的浪花紧跟在我们后边升起来。我趴在张茂的耳朵边上跟他商量着分开坐,这样就能跟女孩儿挨在一起。张茂听不清我说了什么,他一直大喊,什么,你说的什么?我就不再跟他说话,而是看向中间那个喜欢咯咯笑的穿着裙子的女孩儿,现在,数她尖叫的声音最大。我用手拍拍身边的座位,示意她坐过来。她一边尖叫一边忙着用手捂住飘起来的裙子,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邀请。帮她们拍照的女生使劲摇了摇她的胳膊,于是她终于向我看过来。我一边拍得更加用力,一边朝着她咧开了嘴笑。但是她抿起嘴朝着我摇了摇头。我觉得是张茂坐在我旁边的原因,才让那位女孩儿不敢靠近。我们就这样继续坐着又往前走了很远,海岸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马达的声音与海浪声搅拌在一起,让我眼前一阵眩晕。于是我再次想起苏菲。
苏菲敲开了我家的房门,楼上电钻打孔的巨大声音戛然而止。苏菲特地跑来看我,她买了很多东西,还给我带了两盒灵芝片。因为我之前告诉过她,这药对我很有用。我请她留下吃饭,她没有拒绝。我只会简单地炒青菜,苏菲从外面又点了好几份外卖,我们摆了满满一大桌。我说,开瓶酒吧。我的床头柜里还放着一瓶红酒,是张茂拿来的,我还没有喝。冰箱里塞满了可乐,我几乎从来不喝水,可乐维持了我的生命。有一段时间,我妈来这里住,她每天去楼下买大桶的纯净水,我跟着她喝了几天,但她一走我就继续从超市里买可乐塞满冰箱。那一阵我哥哥从部队回来了,他也来我这里住了几天。我哥哥从来不喝饮料。没当兵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酩酊大醉,但是现在他连酒都戒了。他在我这里住了没几天,没去楼下买大桶的纯净水上来,我不知道那几天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关于他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不过后来我又去省立医院做过一次全身体检,我的胃越来越不好,它有点下垂,应该还是喝可乐的原因。但我的胃口却并没有差,我甚至觉得我的胃的消化功能有增无减。我并不担心它。
我跟苏菲打开了那瓶红酒。我喝不习惯,觉得很涩,但我忍着没说,我怕扫了苏菲的兴。苏菲一杯接着一杯,她喝得很快,我都有点跟不上了。我就不停地说,不着急不着急。但是苏菲的速度一点都没有变慢。我们很快就喝完了一瓶。苏菲坐在我的对面,她变得越来越大,她手里的杯子也越来越大,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杯子,里边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我问苏菲,我们是喝的可乐吗?苏菲笑着点了点头。我跟苏菲说,冰箱里还有很多可乐,我昨天去超市买了很多,我往家里拿的时候在楼梯上不小心磕破了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抱着那箱可乐的时候晃得太厉害了,可乐溅了我一身,还有三楼楼道的白墙上也有,你来的时候看见了吗?苏菲说她看见了,我其实不信,但我还是点点头。
后来苏菲扶着我躺到床上。我跟苏菲说,我最近睡得一点也不好。苏菲说她会按摩,她要我脱了鞋反过来躺。我一下子就把我的两只鞋全甩掉了。我的目光渐渐清晰,看见那晚轻盈的月光,它们从窗子外边透进来照在苏菲的身上。月光下的苏菲晶莹剔透,她的外套薄如蝉翼,她的手指修长,她的手腕上有一粒通红的珠子。那粒珠子在黑夜中闪闪发光。我闻到了苏菲身上的味道,那味道又甜又香,但是里边还夹杂着一点凉凉的消毒水味道。我知道这就是苏菲的味道。我甚至听见了苏菲的心跳,它的频率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大。苏菲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游艇的马达突然之间安静了下来。老板回过头跟我们说公海已经到了。我们才意识到已经离开了岸边很远。但是自从海岸线消失以后大海开始变得无聊。周围没有任何一点东西,我知道即使再往前开一个小时也不过还是这样。所以尽管已经到了公海,我却没有感到任何一点惊喜。
我对那个会拍照的女孩儿说,帮我们拍张照片吧。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坐到游艇的另一侧。那个女孩儿摇了摇头,说她来的时候把照相机放在岸上了。我只得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此刻,太阳正变得越来越红,游艇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我们靠在座位上,手可以伸进水里:海水冰凉,就像女人身上丝滑的绸缎。
张茂正忙着给女孩们讲笑话,老板坐在前边看着我们。这期间那个穿裙子的女孩儿问我,我和张茂是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的哥哥。张茂笑着点点头,他说他刚刚退伍回来。另外一个女孩儿立马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张茂转头看了看我,我马上把话接过去说,他受不了那里的苦。看起来这样的回答并不能让女孩儿感到满意,她对张茂说她不信。张茂说,其实是他不想待在那里了。我感到有些生气,对张茂说:不要再找什么别的理由了,你就是没有胆量继续留在那里。张茂不甘示弱,说:真应该把你送进去。我说:为什么不呢,我肯定比你要好得多。张茂气得满脸通红。但是这时候那个会拍照的女生突然弯着腰坐到了张茂的身边。她两只手捏着张茂的胳膊,问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瘦弱。张茂的脸更红了。我则趁机重新坐到了对面,跟那个穿裙子的女孩儿又挨到了一起。
周围什么也没有,几个女孩儿也不再说话。我才发现,一旦船关闭了发动机,那么海上的旅行就立马变得不再有意思。所以当我们短暂地停了一会儿就要立刻赶回去时,我觉得这将会是个好主意。但是那个穿裙子的女孩儿问老板,能不能再待一会儿。我不知道这里究竟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我说,还是回去吧,还是岸上有意思。
游艇加足了马力按照原路返回。天已经黑了,浪变得很大,我们坐在游艇上一句话也没有。海岸线已经看不清楚,但是出现了零零星星的灯光,我知道离岸边已经不远了。这时候那个穿裙子的女孩儿突然伸过脑袋问我,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不会。但是海浪的声音完全把我的回答吞没了。女孩什么也没有听见。我不想很大声地喊我不会,那会让我很没面子。女孩又把脑袋靠过来,她冲我喊:我们去游泳吧!她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我有些失神。其实当时我完全可以拒绝她,但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女孩一下子从船上跳进海里,所有人都惊呼起来,连老板也回过头来看。我看见她落水的位置已经被我们远远甩在了身后。我想都没想就跟着跳了下去。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变得鸦雀无声。我觉得应该往前游一下,没准能找到那个穿裙子的女孩。她的裙脚本来沾了水,但现在她肯定全身湿透了。我想往前走一下,我知道海水的浮力很大,可我却一直下沉。我刚才真应该告诉她,我不会游泳。如果我这样说了,她是不是就不会跳下去了。她长得那么好看,她身上的那件裙子我从来没有见别的女生穿过。我觉得就算有别的女生穿了那件裙子也肯定不如她穿起来好看。我真后悔带她们来这里,我应该陪她们在沙滩上坐着。那没什么不好的。我跟张茂两个人坐在沙滩上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在,我就要死了。我可真是后悔。
我被人从海里打捞上岸。张茂说我当时眼神涣散如同一只落水的母狗。我睁开眼第一句话就是问那个穿裙子的女孩被救上来了吗?张茂说,就是那个女孩儿把我救回来的。张茂说真应该要一个她的电话。我当时想的却是,这辈子再也不要碰见她了。
我的失眠越来越严重。药店的灵芝片再也起不到丝毫作用。我无数次感到内疚,觉得自己那天真不该邀请那三个女孩儿出海坐游艇。更让我觉得难过的是,在我生命濒临死亡的最后一刻,脑海中关于苏菲的记忆却荡然无存。但我似乎记得有天晚上苏菲躺在我的身边,她对我说她就要走了。她说出的话香气四溢,已经让我双耳失聪。她还说了很多,可惜我全都没有听清。我只是觉得开心,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好。那天晚上我酩酊大醉,躺在席梦思的床上就像掉在了海里。我很想往前走一下,我知道海水的浮力很大,可我却一直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