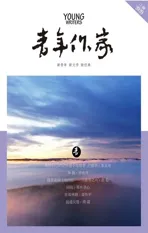田埂上的兔冢
2020-05-01张圣华
张圣华
那天快放学时,我悄声对孬说我在车枉地抓了一只野兔。他不信。放学后,一出校门我就跑,孬追上来问我怎么抓到的?我不说话,径直跑。孬一直随我到家。我指着兔笼让他看,孬惊呆了,那确实是一只野兔。
“我去车枉地采草药,刚跨过地上水渠,就看见它在渠沿下趴着,我一把就按住它了。”
孬的眼里发出了光芒,“我回家取篮子,咱们去车枉地。”
那是四年级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放学时,午气刚下去,太阳还高高的。
我和孬挎着篮子来到车枉地,地里并没有别人。刚刚收过玉米,地还闲着,没有犁起,亮亮堂堂,风来风去的。大多野菜野草开始变蔫,过不久就要种冬小麦了。
“就是在这里抓住的兔子。”我站在渠沿上,用脚指了指下面。
孬呆了半天,说:“这肯定是只傻兔子。”
“你可以在这里等另一只傻兔子来啊。”我笑着说。
“守株待兔!哈哈哈!”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刚刚学的成语,还热乎着。
我们沿着地上水渠拔野菜,这是当年最后一茬野菜了。很快篮子就满了。把篮子往渠沿一放,我们俩四仰八叉躺在地里。
“很快就要冷了,你看天都高了。”孬若有所思地说。
云彩并不多,棉花似的,被阳光一照,披了一层霞光,缓缓向南。
“把眼睛闭上,你会听到虫子爬动的声音。”我闭上眼睛说。
真的听到了马梢子快速移动的声音,有一只甚至爬到我的脚上,停了停,又迅速离去。突然,孬惊叫起来:“你看你看!”
我看见东北方向有一人,拄着双拐,一蹦一蹦在往这边移动,头发长长的,随风飘扬。在我俩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这样走路。
“老水!”我和孬兴奋地叫道。
我们挎起篮子向他跑去。
“两位兄弟!”老水老远就看见了我俩,也高声叫道。
老水不是我们村的,好像是二十多里外杨柳村的。他是个瘫子,三十几岁,平常只能拄着拐慢慢移动,想快也可以拄拐蹦着前行,那就是他的“跑”了。他把双腿向前摆出去,重重落下,再迅速把双拐挥向前面,这样一下、一下,移动速度竟也不慢,只是动静太大,也很累。从我记事起,他每年来我们村乞讨一阵子,跟孩子们混得很熟。他的到来,让我很兴奋,因为他会讲故事,我心里好多事要问他。
“两位兄弟,在这里研究什么大事呢?”他和蔼地说。
我俩赶上去,卸下他背上破破的背囊,抬着走。
“咋这么沉?里面还藏了好东西吧?”孬问。
“有!里面藏着我刚到手的一套‘三国’。”老水说。
太阳已经在正西了,我们三人一路说笑着,往村里走去。
一进村,老水不断热情地打招呼,嘴里响亮地叫着“大哥忙活呢”“叔叔硬朗着呢”。人们都热情地回应着他。我知道,人们其实大都在敷衍他。他只不过是个乞丐。
不一会儿,老水身后就跟了一群孩子。经过生产队的饲养股时,见有大马车停在那里,老水高兴地说:“我就下榻在这里。”他指挥我和孬把他的铺盖卷放在马车底下,这里晚上可以避露水。然后他挪到孬家的山墙下,一屁股坐在那里,喊道:“瘫子到家了!”抬头望见街对面郭蛤蟆家的屋顶,木蝉正在迎风飞转,欢快地叫着。我不屑地哼了一声。
“蛤蟆家的木蝉是谁做的?”老水问道。
“他爸呗,还会有谁。”我酸酸地回答。
这时,孬妈端出一碗水给老水,他一饮而尽,大声表示感谢。
我一直蹲在他旁边守着,好奇地看着他,希望他多说话。他说话时嘴不能张大,好像被人捏住了嘴角,吐字也不圆润。我觉得好玩儿,时不时模仿一下。
我看他不断地捶打腿,就说:“老水,我家有一套按摩腿的方法,我告诉你。”老水高兴地点点头。
我在他的腿上指点起来,老水认真地照着按摩。一会儿工夫,他额头上竟冒了汗。
“好像感觉松快了。唉!我这腿,就是我的命。”
天渐渐暗了,各户纷纷把剪刀、菜刀、镰刀之类的拿来给老水。老水自诩是磨刀大将。大家来取刀时,会带个窝窝头、咸菜什么的,或一碗粥,家里吃什么就送老水什么。
“大嫂,看来日子不错啊。”郭蛤蟆的妈送来了两把菜刀,老水夸了一句。
“哪有什么不错啊!”蛤蟆妈高兴地说。
“两把菜刀,必有肉吃。”老水肯定地说。
正说笑着,黑黑壮壮的郭蛤蟆走来。他比我大两岁,连续两次留级,结果就与我一个班了。他左手拿着一块白馍,右手握着一根大葱,指缝里还夹着一根猪肠子,正吧唧吧唧起劲地嚼着。
村里小孩都怵他。他见孩子们围住老水,也想占一个好位置,就一屁股把我挤开。他把馍叼在嘴里,伸手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大白馍,递给老水。小孩们羡慕地看着。老水立刻挡回来:“哪里就送馍呢?给块窝头就行了。吃了白馍,别的就不好吃了。”蛤蟆不依不饶,非要给他。蛤蟆妈在旁边看着,变颜变色。
老水一再推辞,蛤蟆妈讪讪地说:“收下吧,收下吧,都拿来了。”老水也就不再推辞。
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天已经黑了。我得回家喂兔子了。
家里已经点起了油灯,正准备吃晚饭,依然是地瓜面窝头和玉米粥,就腌咸菜。我没有什么胃口。我跟爸妈说老水来了。爸妈顺着我的话头说起老水的事情。
爸爸说那一年,老水家的枣熟了,他晚上守枣林,没有扎窝棚,露天睡觉,腿被露水打了。先是全身疼,后来腿就不听使唤了。
“不能治好吗?”我问。
“除非有神仙。”爸爸说。
我装模作样做作业,心里却在琢磨老水的事。我仿佛看到了一大片枣树林,红枣累累,一个像我一样大的少年睡在枣树下。他就是老水吗?后来又想起了自己数次没有做成的木蝉,已经有了一根合适的木条,还需要有一把很锋利的刀来削成两个错落的平板,中间要钻一个眼,工具很难找,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要有根铁条,两个以上的铁片或铜钱……风一吹,木蝉飞转,连狗都会好奇地看,羡煞伙伴们……蛤蟆,你的算什么,哼!猛然间我想到一件事:老水一个人在街上睡,该多孤单害怕啊,万一有坏人呢。再说,那大车下也不干净。我越想越不安,便悄悄出屋,取了扫帚,往外面走去;刚出大门,又返回,取了兔笼才走出家门。
老水刚刚磨完成堆的菜刀剪子,正缓缓向大车移动。我摸黑把大车底下扫了一遍,觉得不放心,又扫了一遍。老水默默站在旁边,等我扫完,说:“华,谢谢你。我要是太干净,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得凑合,才能活下去。”我不太明白他的话。
“我把兔子放在这儿,跟你做个伴儿。”
老水笑着问:“你真舍得?”
“嘿嘿,我昨天刚刚给它洗了澡。它不咬人的。”我怕家里大人发现我出来,赶紧回家了。
早上,孬照例叫上我一起去上学。我俩出门走到大车下看老水,车架上面罩了一块透明的塑料布,他还蜷在里面呼哧呼哧睡着。我特意看了一眼他的腿,也看不出什么,只是发现他的腿很细。这时,听蛤蟆妈在家嚷:“这啥时候是个头啊!遭这个罪,天天这样。”然后就听到蛤蟆憋足了劲的哭声。
学校在村子的西南角。我们家住在村子的东北角。先往南,下坡,几十米就是老庙。老庙坐落在南大湾北岸,由此往西,上一个坡,再几十米,就是学校。学校的南面是浓密的古梨林。
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老水的妈是后妈。”
“啥?”我心里一惊。
“我妈说,老水小时候妈妈就病死了,他爹又给他找了个后妈。上七年级的时候,家里就让他退学了。”
我一时没明白这事该怎么理解。
孬又说:“昨天看到郭蛤蟆在吃一种东西,吃得津津有味,再往下看,看到他挖鼻孔,往嘴里填,原来是在吃自己鼻屎。”我说:“恶心死我了,你又在瞎编蛤蟆的故事。”孬指天跺地发毒誓。我说:“老天才不管你这破事。”
我和孬一路打闹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
那天上午,算术课讲的是“四则混合运算”应用题。蛤蟆照例迟到。
教算术的是郭浩老师,这是一堂比较难懂的课,也是我记忆当中特别专注的一堂课。郭老师讲得非常投入,我眼睛紧盯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落下,甚至能把他讲的话全部复述下来。临下课,郭老师嘱咐道:“听不懂一定要问啊,这节课的确很难。”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觉得眼睛好累。
老师刚离开,听得有人高声喊叫:“啊——”我一回头,见是郭蛤蟆。他掐着腰,脸沉着,喘着粗气,莫名其妙地瞪着大家,又用手咣咣咣地拍着课桌。同学们吓得不敢说话,纷纷躲闪。
放学路上,孬说:“蛤蟆要疯了,这堂课听三年了,还是没有听懂。”我并没理会,疾步往回走。急着去与老水厮混。
老水气色不错,正在与几个老头抽旱烟说话。我迟疑着是否走近,老水喊我:“华,你过来。”说着,就在面前的一堆锅碗瓢盆菜刀等东西里,找出一件东西。是木蝉!那木蝉削得光滑、精巧,固定在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柄上,柄后坠了红色的布条。
“看看!我做的!你拿着跑跑,看转不转。”老水满脸和蔼地说。
我把书包递给孬,擎着木蝉的柄,使劲往北跑。那木婵转得欢快,红布条刷刷地往后垂放,煞是精神。我兴奋地跑回来:“转!转得飞快!你手艺不错啊!”
“送给你的。”老水说。
我以为他是闹着玩的,拿着木蝉不知所措。
“我去年就发现你在琢磨木蝉!”老水得意地说。
一旁的孬说:“对对对,他一直在折腾这事,没折腾成。”
此时,我觉得老水是我最亲的人,自己嘴笨得都没有说句感谢的话。我暗下决心,等我长大学医成功,一定要给老水治腿。
回到家,我立刻找了根木杆子,把木蝉安装在杆子上端,可以360 度旋转。我把木杆子固定在房山墙上方,走在街上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刚刚装好,一阵风起,木蝉欢快地旋转起来,屋檐上的麻雀和鸽子们闻声飞起,直冲蓝天。让他们羡慕去吧!你有我也有,蛤蟆你还牛?
那天,家里蒸了一锅白面馍,妈妈说是给小姑姑送米的馍馍,一个也不能少!特意叮嘱不让我和弟弟妹妹们动。小姑姑嫁到十里地外的簸箕刘家,一个月前生了个女儿。按风俗,娘家人要在满月时去送米。通常,送米要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满满地装满白面馍或油条或鸡蛋。在缺吃少穿的岁月,这就是重礼。
第二天放学时郭老师宣布之前的考试成绩。蛤蟆又考了0 分,被郭老师当着全班的面狠狠训了一顿。蛤蟆磨磨蹭蹭上台把卷子领了,看也不看,往桌上一推,双手抱住了头。
老师沉了一下说:“我们班只有一个满分。”我立刻心跳加快,因为只有我没有领到卷子。
“华,你上来,举着你的试卷,绕教室一圈。”老师大声说。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奖赏,虚荣心大为满足。我举着那张纸,像在云中漫步,肆意享受着同学们的羡慕,却故作害羞地低着头。经过蛤蟆桌旁时,我特意向他晃了一下试卷,昂头走过。
“所有不及格的,明天早上提前一个小时来学校补课!”老师“啪”地一拍桌子,走出教室。
同学们吵吵嚷嚷走出教室。我也赶紧收拾书包准备走,身后蛤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还能牛到天上去?!”我听了,后脊梁发凉。赶紧拉了孬走人。
我们匆匆走到老庙,听到有人咚咚地追上来,不用回头也知道是他。
“站住!”蛤蟆恼怒地喊。我回头见这厮眼睛通红,满脸杀气,知道不好,扭头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他窜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我早就看你不顺眼!”我使劲掰他的手,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越揪越紧,我喘不过气来,抬脚就踹他,并把手里的书包向他甩去。这厮躲也不躲,手一使劲,同时腿往我腿后一别,我顿然倒在地上,他用膝盖压住我,双手锁住我的双手。我挣扎不得,大声骂道:“郭蛤蟆,你家要死人了!”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拉架。这个时辰,大人们还都在地里干活。我心想,孬啊孬,你这个胆小鬼,你去了哪里,也不帮我一把。
“你也敢有木蝉?你看看这南北街上,除了我谁还敢有木蝉?”蛤蟆一说话,臭气熏人。我被压在身下,简直是奇耻大辱。
“蛤蟆!你就是个笨蛋!弱智!”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郭蛤蟆甩手就打了我一个耳光,脸上顿时火辣辣的。我借机抽出右手,也打了他一巴掌,却换来他左右开弓的连击,我感觉鼻子出血了,嘴里不住地叫骂。
“住手!”我头顶上一声炸雷。蛤蟆也僵住了,露出了怯怯的神色。是老水来了,他用拐轻轻把蛤蟆推到一边。我一骨碌爬起,扑向蛤蟆,被孬一把抱住。
我和孬陪着老水缓缓往回走,看着他拄着双拐,一点儿一点儿挪步,明白刚才他是一蹦一蹦跳着过来救我的。老水说我和蛤蟆这事得想个解决办法,他让我动动脑子,最好找蛤蟆谈一谈。
那一夜我睡得不好,反复想蛤蟆的事,最终决定冒险一试。
半夜时,我悄悄爬起来,从已经盖好的篮子里拿了一个馍,塞进了书包。
第二天我起得早,并没有等孬来叫,背上书包就走。出门先走到大车旁,见老水还在睡,就掀起塑料布,把馍塞到他的脖子旁。他被惊醒了,睁眼看是我:“华,你这是干啥?”
我说:“我家蒸了很多白馍,给你一个。”我想他一年到头也很少吃到白馍。
他使劲坐起来,说:“华,这怎么成,拿回去!”
我转身跑了。我要在校门口截住蛤蟆。
在校门口,看到同班的同学都纷纷提前到校了,他们要补课。孬也来了。
“你怎么这么早?去叫你,扑了个空。”孬埋怨我。
“我要在这里等蛤蟆。”
“你要干啥?”孬惊奇地问。
这时蛤蟆远远地跑来,喘着粗气。
“站住!”我走几步迎上去。
蛤蟆吓了一跳,这出乎他的意料。但很快就恢复了牛哄哄的架势。他不屑地继续往校门走。
“我知道你为啥每天迟到!”我低头恶狠狠地说道。
他果然转过身来:“你咋知道?”
“你拉不下屎来!”我肯定地说。
“你找我妈了?”
“你知道女孩子为啥不喜欢你?因为你口臭!”我大胆地说。
“你咋知道?”他一脸懵懂地问。
“我还知道你每天嘴里苦,老想喝水。”
“是啊!是啊!”他认真地说,“这是为啥呢?”
“你干的坏事太多了。你打一次架,你体内的毒就会多一次。”我毋庸置疑地说。
蛤蟆眼睛直了:“我才不信你胡说八道!你又没有办法。”
“有办法也不会告诉坏蛋。”
我在衣服上擦了擦满手的汗,走进学校。
放学时,我与孬拿起书包就走。蛤蟆紧跟在身后。快到老庙了,蛤蟆忍不住说:“老华,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你还动不动就牙疼,睡觉满床滚。”我淡定地说。
“是的!真是这样。老华,你真有办法?”蛤蟆已经完全上道了。
从老庙往左拐,一眼看到坡上站着拄着双拐的老水,他定定地往这边望来。
“老水来接我们啊?”孬喊道。
老水看到我们三个小子说着话,一路走来,很惊奇。
我明白,老水是怕昨天的戏重演。
回到家,妈和弟弟还没有回来,妹妹却哭红了眼说:“哥哥,兔子死了。”
我决定把兔子埋在车枉地。老水与孬和蛤蟆,陪着我往车枉地走去。我是在地上水渠的沿下发现兔子的,但老水说,不能埋在这里,水来了一冲,就毁了。
“埋在这里吧。”他用柺指了指旁边最近的田埂。蛤蟆帮忙挖开田埂,再往下挖了一个深坑,把兔子放进去,土培得与田埂一样高,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这样兔子可以长期住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和蛤蟆在微风吹拂的古梨树林里采摘了很多牵牛子。
“这叫黑丑。”我说。
“和我一样。”蛤蟆说。
“所以治你的病。”我俩都笑了。
“不能乱吃啊,这个有点儿毒。要炒了磨粉,每次吃一点。”
我们又挖了一棵大大的地黄,让他当时就吃了。蛤蟆像吃生地瓜一样大口咬,使劲嚼,一通呱唧,“没想到还挺好吃。”
回来的路上,蛤蟆突然局促起来。
我诧异地望了他一眼:“你咋了?”
“老华,你能帮我讲一下算术吗?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大题我就是他妈的不会做。”他竟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好!”我爽快地说。我知道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解决了。
月亮出来了,经过大车时,我看见老水似已经睡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不用去学校,我睡了个懒觉。
起来吃早饭时,蛤蟆来了。
“华,你真神,一大早我就拉屎了,拉了很多。”他欢天喜地,比比画画。
我颇为得意。他又压低声音道:“老水走了。”
“走了?去哪里了?”我一下还转不过弯来。
“我哪里知道啊,我找了,没有找到。以前都是住十多天的。”蛤蟆失望地说。
我赶忙拉着蛤蟆,跑到外面的马车旁,见车下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的眼泪一下溢出眼眶,觉得很伤心。老水,你怎么不辞而别?你太不够朋友了。
伤心了一会儿,我抬头望了望房顶的木蝉,见木蝉垂头丧气、爱转不转的样子。我突然若有所感:“走!去车枉地。”
我俩来到掩埋兔子的地方,果然见到些动静:兔冢被人用什么工具捶打得更结实了。肯定是老水又来过了。
回到家,一大早出去捡柴的爸爸回来了。
“华,看,有宝贝给你。”爸爸从大门后取出一个布包。布已经很旧很旧。
我打开一看,竟然是老水的那套《三国演义》。我不解地望着爸爸。
“一大早出门,老水让我给你的。”
天啦!我心里想,老水可就这套书还算是财产。
第二年春天,车枉地种了大豆。我拉着孬和蛤蟆,特意去察看了兔冢,看上去似乎没有被破坏,上面长满了绿绿的草芽,异常茂盛。“这是什么草?长得好旺。”孬问道。
“菟丝子,这是兔子最喜欢的食物。”
八年后,我在三十里外的县城读高中。孬和蛤蟆都没有考上县中。
那是秋末的下午,放学后,我去街上买咸菜。那时每天窝头就咸菜,没有咸菜,窝头无法下肚。其实,兜里也只有买咸菜的钱。
买完咸菜回校时,见校门西侧聚着一群乞丐,忍不住多瞄了几眼。突然有个乞丐喊:“华!是你吗?”
我定睛一看,一个又老又瘦的乞丐,胡子拉碴地躺在一个残破的平板车上,立起上半身,目光浑浊地盯着我。天哪!
“您是老水吗?”我小心地问。
“华,是我老瘫子啊!我算着你该上高中了,我都在这里等你好几年了。”
我觉得心头发热,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他的双手好凉好凉啊。
“您的柺呢?”我的眼里猛地盈满了泪水。
“早不能用了,腿软得站不住,只能躺在这破车上,兄弟们天天拉着我。”他拉着我的手,看样子恨不得抱我一下。
“兄弟们,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华,上高中了。在这个世上,我一个瘫子一个要饭的,还曾经有人真心对我好过,为我挨过打。”说着,老水泪流满面。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老水,我们以后可以常见面了,又近了。”“华,你要好好读书,你可是我的念想。”我点了点头。
“老水,你的脚冷不冷?”我问。
“冰冷冰冷的。天天睡不着觉。华,我估计活不了几天了。”
“老水,别这么说。会好起来的。”我嘴里安慰他,心中却感到不祥:筋骨已废,阳气衰微,老水命将不久。一阵凉风吹来,有木蝉飞转的声音。有只木蝉被细心地固定在车后面的挡板上,像车的螺旋桨。
老水用手抹了一把脸说:“华,见你一面,我就心满意足了,说明我没看错人,没有白等。以后可别来找我,一个高中生总来找一个要饭的瘫子,让人家看热闹,对你不好。”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下午放了学,我拿了几个窝头出门找老水。那群乞丐已经不在了。又找了几个地方,见到了几个乞丐,问起老水,他们都摇摇头。后来多次寻找未果,从此竟再也没有见到老水。看来老水又躲着我了。
再后来,我离开县城读大学、考研、工作。蛤蟆去县城开了个大饭馆,孬办了几个养鸡场。村里的土地已经包产到户,车枉地也被分给了几十户人家,田野被彻底修整,再也没有兔冢的影子。我请蛤蟆和孬多次打听,竟一直没有老水的消息。这么一个瘫了的叫花子,存在与消失,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