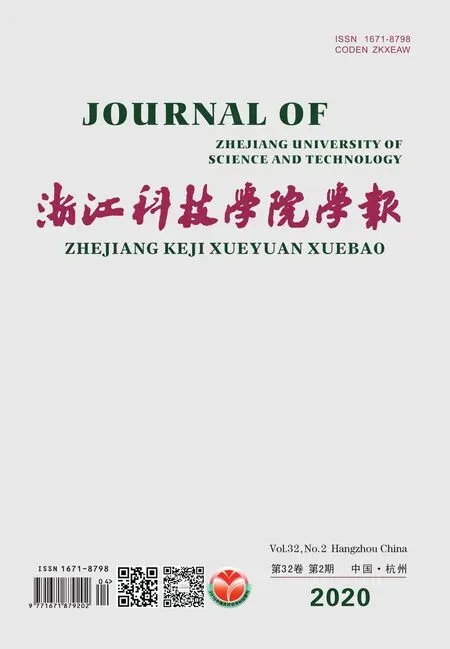本土外来词“科学”的本土存在理据研究与思考
2020-05-01陶绍清
刘 超,陶绍清
(浙江科技学院 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杭州 310023)
葛本仪[1]认为,外来词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重新改造和创制的过程。由此可见,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是两种语言的碰撞与融合。基于这一认识,研究者在对外来词尤其是意译外来词进行研究时,往往对其内部的演变规律尤为关注。其中,以“科学”为典型代表的日源意译外来词,由于其演变规律的特殊,更是成为研究重点。史有为[2]先给这类词定性为“特殊的外来词”,强调其“借音借义的分析过程也应特殊对待”,随着近几年对外来词研究的逐渐深入,日源意译外来词的理据也更加清晰,高名凯等[3-4],从词源角度对其出处进行了精确探查,罗常培[5]、史有为[6-7],从语用方面对其功用与文化意义做了脉络梳理。高燕[8]认为,这类外来词比一般的外来词更有渊源,理据性也更加充足。因而,探究“科学”一词的创制与发展,也是在窥探日源意译外来词消长的演变历史。
1 “科学”词源的本土融合过程与对比
张博[9]提出“外来概念不等于外来词”的主张,由于概念和词语并非完全对应,因此很多外来词的“形音义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变成了中式”,被划分为特殊的一类,“science”就在其列。这个词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3]54(以下简称《外来词研究》)里被归入了“先由英语吸收而被改造成英语的外来词,再由英语转传入汉语而被改造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分类。通过“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inese Linguistics PKU)”(以下简称“北大CCL语料库”)的检索,“科学”词条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分别出现了48条和500条,“赛因斯”则出现了5条。由此可以梳理出“科学”一词发展的4个阶段:独立释义—多义接触—系统接纳—正式融合。以下语料均引自北大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
清末之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处于独立释义阶段。《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提到“又应文藻流誉科学擢第”,可推断“科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且释义与科举制相关;发展到北宋时期,朱熹所著的《朱子语类》中提到“祖宗是有《三礼》科学究,是也”,用“科学”二字来通称“三礼”是“义理之学”;清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也提到“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以“科学”代指西汉之后荒废的经文讲学之道。由此可知,在具有拉丁文含义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前,“科学”被赋予的含义是完全“本土化”的,具有独立的释义。
维新变法开始到民国建立初年,“科学”一词的发展处于多义接触阶段。西学派将“格致”用作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后来经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传播,“科学”一词以新的涵义从日本引入,被用来扩大“格致”思想。据王良杰[10]所言,“中日甲午战争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自己的文章中大量使用日语新词,这些词通过留日学生和被翻译的日语著作不断传入中国,形成了汉语外来词中比较独特的‘日源外来词’”。清代章炳麟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缪》中提到:“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赋予其“理性”释义;无垢仙人在所著小说《八仙得道》中提到“外人所讲,则完全属于科学”,赋予其“技术”释义;《张文襄公事略》中提到“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与专制对比,赋予其“开明立宪”释义;《清代野记》中提到“科学仪器之属,而好古之士,日见寥寥”,赋予其“发明”释义;民国向恺然所著《留东外史》中提到“英语是主要科学”,又进一步补充了“课程”释义。由此可知,此时引入的“科学”虽不成体系,但涉及“科学”的不同方面,多种涵义同时与本土接触。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科学”的运用进入了系统接纳阶段。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追求“全盘西化”,胡适撰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掀起了西方名词的使用浪潮,“科学”的直接音译形式“赛因斯”也开始大量使用;但与此同时,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旧派学者坚决反对这样的西化,他主张“中国现在需要西方的赛因斯,但世界未来最终会走向中国之路”,此时进入“科学”与“赛因斯”的并行阶段。新文化运动开展以后,这种对立的局面被逐渐中和,陈独秀摒弃了“赛因斯”的用法,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democracy”与“science”的直接翻译结果加以修饰,亲切地拟作“德先生”和“赛先生”,可见当时中国对“科学”的认识已经逐渐清晰,多种释义的散乱使用也开始集中起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科学”一词进入正式融合阶段。董乐山[11]认为,赛先生采用外来语后逐步以现代汉语替代,是社会语言约定俗成的趋势所致。杨霞[12]认为,“英汉混杂的形式,主要是汉英语码的混用比较普遍,也利于外来词的大量地快捷地转化、吸收,但有些外来词语在汉语中已存在很准确、简练的表达形式,若再夹杂其原形词反而显得画蛇添足”,显然“赛因斯”的表达不够精练。范铁权[13]引用了中国科学社发表的倡议书,“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刘敏[14]也提到“科学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可见“中国科学社”中“科学”的内涵,是以国际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现状;范铁权[15]引用周铭对“科学”的看法,“一切学说之枢纽,吾人不能任意命某名”。因此,中国科学社让“科学”一词彻底被人们接纳,“赛先生”因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主观命名特征,只是一个过渡名称,它的消亡与“科学”的确立,是前三个阶段整合而成的结果。
故“science”的本土融合过程从纵向来看经历了“英—日—中”的流转历史,横向来看经历了“独立成义—全面换新”的融合过程,正因为深厚的本土基础,适当的时代助力,加上丰富的词源历史,“science”最终才能与本土完全融合,形成独特的存在理据。相比之下,纯音译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sandwich”“hamburger”,显然都缺乏足够深入的语义背景作为本土融合条件。它们被《外来词研究》[3]40归入“纯粹英语来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作为从西方引进的食物名称,虽在制作原理上也有与本土相关的部分,但语义浅显,且混用名称影响较少。“hamburger”的两种称呼形式“汉堡”“汉堡包”,属于使用时的音译省略情况;广东地区因方言因素将“sandwich”称为“三文治”,归因于使用区域的差异,均无法影响其表达效果。故“hamburger”“sandwich”等都无法通行本土表达,只沿用直接音译的结果。由此可得结论,在词源的本土融合过程中,“科学”一词比纯音译的现代汉语外来词有更深入的融合条件和更复杂的融合过程,这是本土表达“科学”存在独特理据的原因之一。
2 “科学”创造方式的本土融合理据与对比
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是语言融合的过程,语音不能单独被吸收,必定要和语法、词汇形成一个整体的融合规律。史有为[16]也提到“现代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大凡有十端”,其中“四为明层次”,“五为审构成”,提倡区分层次和审查外来词的构成方式或词内整合模式,具体而言即“音形义”。
2.1 语音的创造方式
《外来词研究》[3]149-154中提到“英语的原词有重音,无四声,相应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则无重音,有四声的区别”“英语原词的齿音s在其相应的现代汉语外来词里一般做s”“英语原词里的元音,在其相应的现代汉语外来词里可做i”“英语原词的鼻音收尾-n,在其相应的现代汉语外来词里也应该是一个带有鼻音收尾的音节”。据此分析“science”的音标[sans]可得,“赛因斯”的翻译理据为将“saI”结合英语重音与汉语声调的转换规律合成为汉语语音中的“sài”,将“”与“n”译作了“yīn”,并以“sī”结尾。但是因为“赛因斯”发音的轻重音格式为“中·次轻·重”,且“sài”的韵尾和“yīn”的韵头相连会导致语流音变发生同化作用,所以读起来会弱化“yīn”的发音。肖轶瑾[17]认为“多音节外来词素在音节形式上缩减,正能反映出汉语词素系统对于外来词素的汉化发展。”故将其摒弃也是为了顺应“多音节外来词素的单音节化发展”这一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science”的翻译形式由日本转传,日语的“science”读作“kagaku”,相比于借用英语发音,使用同源的日语发音区分效果更佳,也和语义更契合(详释见本文2.3)。故从语音上分析,放弃“science”的直接翻译形式,改为“科学”的理据更加充足。

故从语音的创造方式来看,由“science”直接音译得来的“赛因斯”因其违背语言发展趋势,比其他纯音译形式的外来词多了转换的步骤。
2.2 词语的创造方式
《外来词研究》[3]163中提到,“在创造外来词的过程中,人们是把原词的意义范围加以改造,来适应自己的语言词体系的”。但这样的改造是有条件的,如果生搬硬套,就很容易造成两种语言词体系的使用不对等。肖轶瑾[17]认为,“外来词素的发展,构词能力的增强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science”可以构成众多延伸义项,如“science-park(科技园区)”“science-fiction(科幻小说)”,但在现代汉语里不能将其直接译为“赛因斯公园”“赛因斯小说”,这源于“语素化程度的高低”。孙道功[18]认为,外来词进入现代汉语时,需要“降格语素化”,“科学”降格为语素后,就可以大量生成新词短语,如“科学课”“科学家”“科学书”,语素化程度提高;“赛因斯”的语素化程度则明显偏低。苏新春[19]认为,“复音类音译词的语素化发展模式”即“单音节式简化—独立运用—重复构词—语素化完成”,其中可重复构词的能力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人们舍弃了“赛因斯”,选用复合双音节词“科学”,利用它的“词根+词缀”的构词形式灵活与其他词语相结合,让“science”进入现代汉语之后构词能力更强,使用范围也更广。
对比纯音译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sandwich”,语义范围则较为狭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20]只收录了两项与“sandwich”有关的延伸词汇,分别为“sandwich-board(夹板广告牌/三明治式广告牌)”“sandwich-course(工读交替制课程)”,虽然也出现了翻译不对等的情况,但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与其他词语组合,组合时可以以比喻义出现,或者直接构词。因此照顾到词意本身,并不需要强行换成本土表达方式。辛荣美[21]认为,“在词汇色彩义方面,词的色彩意义依附于词汇意义而存在,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由于外民族和本民族文化背景、认知习惯、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外国的风格色彩,在使用过程中进行保留,这样会更加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接受。”故“sandwich”沿用纯音译的形式更为方便。据此分析可得,将“science”附加创造方式,将纯音译外来词的再造过程省去,更能适应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则。
2.3 语法的创造方式
孙道功[22]认为,“语法制约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音译词语素化时的词性改变或词性功能的转化,即形成的新语素和原词的词性不同。二是功能变化,即新语素出现了新的语法功能或语法意义。”“赛因斯”在使用时只能作为名词,无法涵盖所有情况的使用,但“科学”既可以用作名词,如“科学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如“老张的算法很科学”。因为词性开阔,功能也随之拓展,故对比之下舍弃音译形式是必然结果。《外来词研究》[3]167中提到,“现代汉语在把外语的原词改造成本语言的外来词的时候,往往要受到现代汉语构词法的支配,外语的原词是依照现代汉语的构词法规律而被改造成现代汉语的外来词的”,并将其分为三种方式,其中一种是“外语原词的构词法词尾或词头往往要被改换成现代汉语的构词法成分”,前文已经论证过“科学”一词古已有之,只是释义有所不同,“science”可切分为“sci(表理性)”和“ence(表性质)”,与“科学”的古义有所关联,故人们在寻找更精确的表达时直接将已有词改头换面,加速了“science”的本土融合。以“科学”现在的解释来看,它的存在不仅是因为语言创造的省力原则,更是因为它充足的理据:“科”与日语中“科学”的前半部分发音“ka”相似;《说文解字》[23]里有“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程品等级,含有规范之意)”的记载。“学”表示学科、领域,可以同义替换表性质的词尾尾缀“ence”。可见,“科”与“学”都分别作为自由语素将词义延伸开来,赋予“science”更深的内涵。这样既不曲解词义,又能凸显出词语的定中结构。
“science”之所以改换名称,是因为之前“赛因斯”在语法上受到制约,此时添加构词法便可以梳理结构,但若将构词法用在纯音译外来词如“montage”“toast”上,则会适得其反。由“montage”音译过来的“蒙太奇”,以及由“toast”音译过来的“吐司”均属于单纯词,且使用范围较为狭窄,若要凸显现代汉语构词法而分别译作“拼贴剪辑手法”“切片面包”,词性和功能不仅没有完善,反而受现代汉语构词法的限制,不再简洁,因此保留直接翻译形式更符合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由此可得,在语音和词汇的本土创造方式的共同作用下,“科学”的语法创造方式能与本土的构词法规则相融合,形成不同于纯音译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存在理据。
3 “科学”所占比重的本土重视程度与对比
曾小燕[24]认为外来词的演变途径主要包括“以需求为导向;以交际为驱动力;以感知为途径;以频率为生存条件;以汉语特征为内部机制”几大类。可见社会需求是外来词被引入的重要原因,不同的社会需求,以及需求重要性的大小,导致外来词翻译形式不同。《外来词研究》[3]129中将现代汉语里一般的外来词按其所指的事物或概念,由高到低进行了领域比重的分类排比,可得结论,排在前几位领域里的外来词绝大多数都是本土表达,如第一位政治领域中,除“脱党”“托派”等少数外来词的本土融合特征不明显,其余均是本土表达;而后几位的领域里纯音译外来词明显增多,如排在第七位化学领域的“阿司匹林”、排在第十三位物理领域的“卡路里”。“科学”一词被划入排在第四位的哲学领域。由此可推测,外来词所在领域的比重大小也是影响“science”翻译理据不同于纯音译外来词的翻译理据的一个因素。
“science”在日本的哲学表达中被称为理学,清末西学派将其引入后,又归入基础技术范畴。可见“science”的内涵是哲学与技术的糅合,属于哲学领域的“科学”,可以归入中国本土的哲学理念中。“哲学”一词虽从日本引入,但“哲”的思想古已有之,尤其是墨家思想最先将“哲”的理性思想与自然科学并行研究。除了哲学,墨家思想还研究时间、空间、力学等多种自然科学。“science”与“格致”含义相通,且古已有之,只需要改换释义,因此本土表达更容易进入社会生活。属于饮食领域的纯音译外来词“巧克力”“可可”,情况则不尽相同。“西食中传”的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及哲学,近代“西食中传”的影响又不及古代。古时的“西食中传”从市场、流传范围、饮食文化等与中国本土相结合,故金相超[25]提及的外来词如“安息香”“苜蓿”等的内部结构早被赋予了中国本土的色彩。而近代被引入的“巧克力”“可可”,更像是旅居在中国文化里的异域文化,外来的烙印还很明显,并不能充分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故保留了纯音译的形式而没有转为本土表达。由“科学”所在领域比重影响其本土融合程度的现象可知,现代汉语外来词所占比重受能否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影响,而能否与之相结合,就直接关系到外来词能否转换成本土表达。
4 “科学”使用的本土规范原则与对比
将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多种形式并行使用,很容易造成表达上的困难,因此,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出发,《外来词研究》[3]178中提出了“三一”原则:“一词,一音,一字。”即同一个外来词的词义、语音、书写形式都要求唯一,正好与现代汉语所要求的一一对应原则相适应。李彦洁[26]认为,外来词的规范使用主要表现在“一词多形情况的改观、词形选择淘汰的机制”两个方面。《外来词研究》[3]178-181中将其细分为6个原则,本文选取了通行、简易、语义3个原则进行阐述。
4.1 通行原则
通行原则指在初创的几种方案中采纳一种最合乎社会要求和语言发展内部规律的方案,将其固定下来,立为规范。前文已经论述过,“science”在转传入中国之时,背景复杂,因而出现了纯音译形式“赛因斯”与本土表达“科学”混用的现象。但词汇作为现代汉语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部分,所具有的能产性,也带有优选的属性。“赛因斯”和其他翻译形式作为初创时的方案,必得经过考验,选用一种社会最为接受的形式。“科学”相比于“赛因斯”,理据更充足,也更符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自然要将其固定下来,立为规范。纯音译外来词“尼古丁”“凡士林”则并无混用现象,广东地区将“三明治”另称为“三文治”也只是源于方言差异,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在现代汉语外来词使用规范里,纯音译的外来词不具有独特的理据,通常只有一种形式作为通行表达。
4.2 简易原则
简易原则是就同一事物的不同书写形式而言,只选取其中书写最简易的一种形式,选取原则是“以简易为准”[3]179。纯音译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在书写时已经使用了最简的汉字,表达最直接的含义。如“迷你”“培根”“沙发”,也无复杂的笔画,且没有其他形式相混,故没有必要将其分别换做诸如“简便轻巧的”“烟熏肋条肉”“多座位软垫椅子”的本土表达,纯音译就是最简易的形式。从字形和笔画上来看,“赛因斯”书写繁杂,“科学”字形简洁,语素精练,因此从“三一”原则的“简易原则”出发,理应把“科学”确定为规范表达。
4.3 语义原则
语义原则是选用其中一种表达式,将语义实用与否因素也考虑进来。《外来词研究》[3]180中提到“每个现代汉语的词素都包含它所特有的意义”,在加工外来词时,“音义兼顾”即最优选择。杨霞[12]认为“语码混用”现象是指“一种语码成分被插入另一种语码中,另一种语码处于主导地位,被插入的语码成分处于从属、补充的地位,不能作为完整的语言单位起独立作用。”“但有些外来词语在汉语中已存在很准确、简练的表达形式,若再夹杂其原形词反而显得画蛇添足”,因此从语义原则出发,“science”翻译形式的变革势在必行。但这不意味着对纯音译外来词也要强行套用语义,如“coffee”的真正语义表达在于凸显其与中国茶文化不同的西方特色,而不在于其制作过程的原料与原理,若改换成“经过烘焙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反而会“因义害词”,将“coffee”真正的语义掩埋,故“science”在语义上具有转换为本土表达的充分理据。
5 结 语
外来词的翻译形式融入或消失,取决于它在构词能力、使用功能、规范程度等多方面是否顺应语言发展的趋势,是否具备与本土使用环境相融合的能力。“赛因斯”的兴亡过程,也体现出词汇发展过程中,正常呈现的短暂逆发展,这种逆发展在当下多表现于新兴的网络用语上,时常会出现诸如“因垂斯汀(interesting,有趣的)”“哦可(OK,好的)”这样本来有标准翻译形式而另外使用音译形式的网络用语。严格地论,这些另类的表达方式并不符合使用规范,受众虽广,出现却短暂。但这种短暂的语言混乱现象也恰恰证明了外来词进入本土的发展模式是动态的,只有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外来词才能被固定下来,这也正是“赛因斯”只能流行一时而被“科学”代替,“三明治”却依然沿用至今的理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