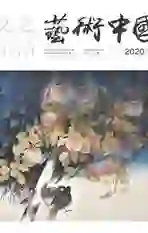中国现代木刻应取法古典
2020-04-27肖伊绯
肖伊绯
三十余年前,沈从文逝世后不久,黄永玉于1988年8月所写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表叔沈从文》一文中,曾经提到: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书信往来。……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黄永玉所言非虚。如今,翻阅《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那卷帙颇丰的书信卷(第18—26卷)中,仅收录了一通沈氏写给黄永玉夫人梅溪的信,却无一通写给黄永玉的信。看来,那一段特殊历史留下的遗憾,着实令人无奈,再也无从弥补。
“烬余”遗珍,长信一通曾摘录千字发表
然而,笔者近日闲坐故纸堆中,却偶然翻检到一通沈氏致黄永玉的“佚信”,实在是一份弥足宝贵的“烬余”遗珍。当然,这并不是通信原件,而是曾经发表在1947年8月28日《东南日报》之上的摘录文本。为披露史料计,亦为便于考述,笔者根据报刊原文,酌加整理(原文中加有括号者为沈信原注,“上略”与“下略”两处为编者原注),转录全文如下:
中国雕刻的风格——给永玉的信
沈从文
(上略)关于木刻古典作品好的还多,如汉六朝报十七孝图,曲水流觞图,和明清方法完全不同,黑白对照,极有意思,古拙处带图案性,极动人,可惜上海不易见到。墨谱也有可观的,精细中有拙处,设计巧得很。宋磁影青越窑划花设计,也有极巧的。漆器剔红及精巧单纯不可想像,给人深刻印象。……总之,可师法参考的多不可数,一般人眼和心得不到好处,即无法吸收。……以木浮雕,如戏台前透花阑干或石桥上半圆形雕阑干而言,好处亦多不可数。……一切创造多由综合传统而来,因另一时另一地人的热情和幻想或信仰,实已留下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東西,到处可掇拾,重新综合成为一种新的表现也。
笺谱(如十竹斋笺谱),本草(彩色套印),芥子园画(开花纸精印彩色套版),均分浓淡,全凭印者手艺;尽管手艺高强,两份总不能尽相同。又唐诗画谱,有些极好,拙中有飘逸。又日人印敦煌画有极好的,设计伟大巧妙,尤令人心折。中国营造学社,桥上阑干浮雕拓片即有上万拓片。中研院则有拓片拾万以上,真是取用不尽。现在二三弄雕刻的,只知仿希腊或文艺复兴作家群,挤人一堆,全不知中国式从武梁石刻,后晋石报,到宋明石刻,多重分布,留出空间点缀树石花鸟,别有从容处。又如浮雕,气魄极伟大重厚的,有霍去病墓前人熊抱子图,大至二丈,只作一母一子,圆浑壮丽,极可取法。我想汉人石刻有许多可转到木刻上,因为注重黑白对比,注重分配,线条强壮而单纯,拙中有斌媚。瓷器(宋瓷)暗花则设计巧妙温雅,移之于木刻,亦必可另成一格局。
晋六朝报则最可注意点为人像黑白法,以及置人物于山中水石之间法。树木叶片尚对称如图巡查,在画中则洛神图尚有此式,树木均对称具图案美。似乎极拙,可斌媚之至。这个法则一直到明清工匠石刻还保存。所以从石桥雕装饰人物看,还可以学许许多多!铜器则铜镜可以学甚多,线刻如龙虎四兽镜,浮刻如海马葡萄镜,刀如手掌,常有大气魄。商周镜则重矩形花纹比称,生物用蟠虁,亦不甚重象形,只重图案。彩陶有种可改作木刻的,十字布扣花亦有可取法为彩色木刻的,尤其是十字布与同类扣花。彩色多混合综合成一矇眬眬虹彩,稚弱天真中有生命流动;用于新木刻,让此色重叠于彼色之上,可产生真正的新意义,值得一试。
对于中国画,有极多伟大到不可形容作品,将来必有机会看到,且有些亦可使木刻影响的,如唐人画小景,木屋拙重厚实,于小院中配以点点花木石栏,却用淡彩相晕染,看来起种奇感。宋人如林椿作花鸟,夏青溪山晴远卷子,赵子昂拟徽宗墨画秋江叠嶂,用墨神奇到不可思议。钱舜峰则于用色淡韵与人物风致相称,均了不得。又咫尺小幅作千里景物,收纳江海楼观外,还能在海岸小船上写家庭生活,用心之深,均可师法(下略)。
上述1100余字的文本内容,可能摘自沈从文1947年8月间致黄永玉的一通信件。摘录者,自然应当是收信人——黄永玉本人。摘录时,掐头去尾,将信文内容集中在“中国雕刻风格”这一主题之上,即付诸发表。
概观这摘自通信中的“千字文”,不啻为一篇缩微版的“中国古代雕刻史”,亦不妨视作“中国现代木刻”如何取法“中国古代雕刻”的一纸研讨书。这里边既饱含着沈从文有意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的个人志趣,更有其对表侄投身现代木刻事业的真切关注与热切期冀。仅就摘录部分即达1100余字的篇幅视之,此信全文篇幅颇为可观,乃是一通下笔千言、真情洋溢的“长信”。
“佚信”背景解读:汪曾祺初晤黄永玉
值得一提的是,刊发此信的《东南日报》第七版为“长春版”,1947年4月至10月期间,黄永玉的木刻画作经常刊印于此。而且,这个版面还经常刊登研讨或评述“中国现代木刻”的文章,几乎每期都会刊印新近的木刻画作,俨然可以称之为“木刻艺术版”了。
无独有偶,不单单是70余年后的笔者对此版有此观感,早年有此观感且就将此“长春版”径直称之为“艺术版”者,竟还有汪曾祺。且汪氏此说,乃是出现在1947年致沈从文的一通长信之中,此信又间接透露了当年黄氏行踪及其与“长春版”的密切关系(此信收入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汪曾祺全集》)。
原来,这一通长信,乃是汪曾祺受沈从文委托与黄永玉见面后,次日(1947年7月15日)即向其“汇报”相关情况,主体内容是对沈氏表侄、已为木刻家的黄永玉的初次印象与大略评价。显然,当时沈、黄叔侄二人都还尚未见面,各自尚在北平与上海两地。
汪信中言及黄永玉近况时,称其之前“到福建集美学校教了一年书,去年冬天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穷了半年”。
汪信中提到的“张西厓”,应当是章西厓,只不过因发音相近而将“章”误作“张”了。据考,章西厓(1917—1997),乃是著名的中国现代装饰画家、木刻画家,曾于1939年创办《刀与笔》期刊,与张乐平等编绘《星期漫画》副刊。1947年曾出版中国现代第一部装饰画专集《西厓装饰画集》,1948年作品入选《中国版画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汪信中还提到了所谓《东南日报》的“艺术版”,即章西厓负责主编的《东南日报》“长春版”。汪信中称,黄永玉因章氏“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至于怎么“闹翻”的,因何“闹翻”的,汪信中没有详叙。不过,据查证,直到1948年底,章氏作品及其极富特色的版头装饰画,仍在《东南日报》的“长春版”上刊印发表,或者竟没有“闹翻”,或者后来竟又“和好”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期间,黄永玉的木刻画经常刊印于《东南日报》“长春版”之上,与章西厓的版头装饰画交相辉映,颇有相得益彰的意趣。虽然未能继章氏接手“长春版”,可在这个版面之上,黄氏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屡有出现的;可以揣想,章、黄二人的交谊,或许并未因前述汪信中所言与报馆“闹翻”事件受到影响,二人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罢。
汪信中提到,黄永玉原本“想到杭州接张西厓的手编《东南日报》艺术版”,这里提到“杭州”,可当时的《东南日报》却是在上海印行的,依常理而言,黄永玉应该直奔上海才对,何必又绕道杭州,再因“张跟报馆闹翻了,没有著落,于是到上海来”呢?这样的状况,后世读者恐怕不容易明白其中缘故,难免一头雾水,以为是不是汪曾祺误记了。
说到这里,还是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当时《东南日报》总社在上海、分社在杭州的历史背景。《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更名为《东南日报》。1937年11月中旬,因日军即将侵占杭州,《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刊,“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成为分社;“南平版”则迁到上海,作为总社。可以看到,抗战前后,《东南日报》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战之前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与总社所在地,抗战之后杭州却成了分社所在地。
当时《东南日报》“长春版”副刊,由总社陈向平任主编,但具体的编辑工作交由杭州分社章西厓负责。所以,汪信中提及黄永玉先至杭州,再去上海,是符合历史实情的。而黄永玉将沈信摘录后,发表于《东南日报》“长春版”,报纸本身虽则是由上海总社印行的,可是稿件最初应当还是“绕道”杭州,交由当时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章西厓来办理的罢。
汪曾祺“身家作保”,沈从文“留心扶植”
至于沈信中何以大篇幅地论及“中国雕刻风格”,一方面固然极有可能黄永玉曾主动去信对这一问题有所研讨;另一方面,从这一通1947年7月15日的汪信中,就可以看出“诱因”与话题之“预设”。事实上,初晤黄永玉,汪曾祺对其印象极佳,对其作品也激赞不已。在致沈从文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他想找一个民间不太流行的传说,刻一套大的,有连环性而又可单独成篇章。一时还找不到。我认为如英国法国木刻可作他参考,太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掏汲恐怕很费力气,这个时候要搜集门神、欢乐、钱马、佛像、神俑、纸花、古陶、铜器也不容易。您遇见这些东西机会比较多,请随时为他留心。
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
不难设想,收到汪信之后,沈氏必定会“随时为他留心”,在“中国旧有东西中淘汲”方面,对黄永玉有所指导与建议。可以假设,即便远在上海的这个表侄,当时还没有致信与之研讨“中国雕刻风格”方面的话题,就是仅仅以汪氏“身家作保”的激赞之辞,沈氏也必定会有所关注与表达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