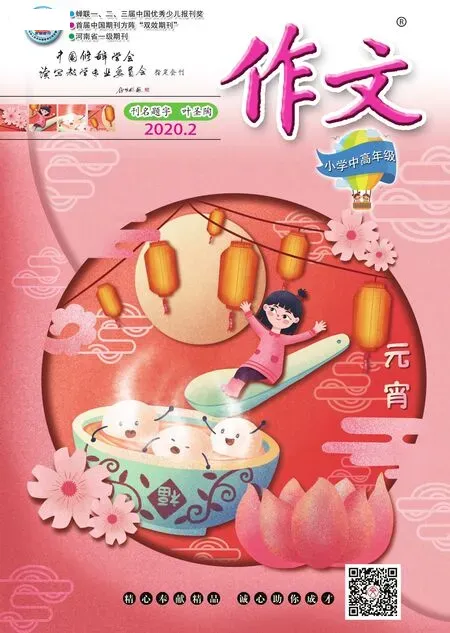画画与作文
2020-04-18郝月梅
●郝月梅

上小学时,作文是我最喜欢的课。虽然语文老师一直不怎么喜欢我。
语文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上课爱画画。而他是班主任,对纪律要求得近乎苛刻。所以,此刻我写起他来,脑海中浮现的依然是一张不苟言笑的“猫脸”。这张猫脸一出现在教室,总有一种“一鸟入林,压倒百鸟不语”的威慑力,学生见了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我敢在他的课上画画,的确是对师尊大大的“冒犯”。
其实,那时我是个很乖的女孩,胆子很小,小到老师丢一个脸色,就要流一节课的泪,老师批评一句,就一上午趴在桌子上抬不起头的程度。但不知怎的,我就是改变不了自己在课堂上画画的习惯。因为上课爱画画,虽然我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却没有被评上过“三好学生”。所以,几十年后小学同学聚到一起,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的画。
今天回想起来,我画画,实际上也是一种作文。因为我画的基本上是连环画,有故事情节。我是在用画面传达一个故事,讲一个笑话,显现一种幻想。在思维方式上,画画和小学阶段的作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形象思维。小学阶段的孩子主要凭借形象来思维,所以这个阶段的作文应该从具体可感的事物写起。
但我的语文老师是不懂这一点的,看到我在课堂上画画,只认定我是违反纪律,轻则没收本子,重则罚站。惩罚最重的一次, 是我画一个男生上课睡觉,梦到深处打起鼾的画面。我把这个细节画下来,就有了夸张的成分,画这个男生的鼾声过响,把教室房顶的瓦震落,烟囱震塌……同桌看了忍不住笑出声。我被老师逮住了,在办公室反思了一中午,没让吃饭,下午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作了检查。自那时起,我觉得语文老师从骨子里轻视我,见了他我就两腿发抖,患了严重的“语文老师恐惧症”。
治愈我这个症状的,是毕业前的一篇作文。
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非常时期,所谓的作文基本都是空喊革命口号,毫无感性内容。尽管语文老师讲得滔滔不绝,嘴角冒白沫,学生们依然很难爱上作文,每次交上去的作文大都是照报纸抄来的,而且抄的基本都是社论,空洞无物。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作文,老师布置的依然是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作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了完全不同的一篇。
作文写的是毕业离校的一种心情。写时,我很投入,只感到在这所简陋的小学平平淡淡地待了两年,临离开时突然有了一种不舍,这种不舍我没有空洞地写出来,而是把它凝于一幅画中。当然,这画面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
村头一棵百年大槐树,一座高高的山坡,山坡对面是我们的小学。夜幕降临,走在高高的山坡上,我不觉回望学校。学校的两排教室沐浴在朦胧月色中,西头的办公室闪闪地亮着灯光。我在心里默默说,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我的老师……
作文交上去后,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了,读得同学们都低下了头,沉于离别的情绪中,有的女生竟哭出了声。我用文字画的那幅画,被老师用红笔在下面圈了许多圆圈。遗憾的是,我并未拥有这篇作文,毕业的时候老师把它留下了,说是给下一届同学看看。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我得庆幸那时狂热地爱着画画,是它发展了我的形象思维和编故事的才能,使我能够在毕业时,自然地写出了这篇独特的作文。这篇作文不仅把我从“恐师症”中解脱出来,也让语文老师记住了我。
几十年过去,不知那所小学是否还在,我那篇留给下届同学看看的作文是否还在,我的老师是在的,据说身体结实。我在此向他祝福,谢谢他的红笔圈圈,让我找到了作文的自信。
(选自《100位作家教你阅读与作文》,有删改)
郝月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麻烦人儿由由”系列、“王闹一定有办法”系列等儿童小说。作品获山东省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