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事
2020-04-14
初阳台,那么美
何霆(浙江杭州,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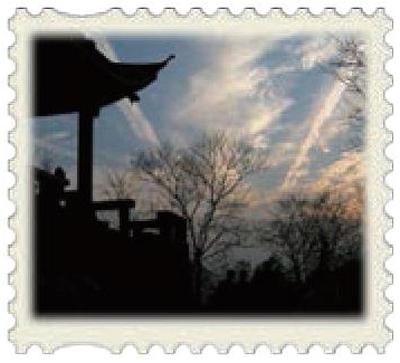
春依然来了,忽然很有兴致去一下葛岭初阳台。
今年特殊,因为疫情。戴上口罩下了楼,开车到葛岭脚下,便上了山。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山中已能感受江南特有的春的温润。
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很是温和耐心,一路和十几岁的儿子说着话。忽然听到儿子在问父亲:“爸爸,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它最终会怎么样?”父亲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儿子,你觉得人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到哪里去?”
儿子想了一下答:“好像有很多种答案,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
“关于探求事理极限的问题,研究问题本身比寻求答案更有意義。”父亲答道。儿子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听着父子的对话,行走在葛岭之中,自然想起了奇人葛洪。葛洪是晋代道家名士,亦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亦即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却认为,急病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所致。如今我们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葛洪著作《肘后备急方》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是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为普通百姓也能用得起的药。由此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
许是在山上的缘故,抑或是很久没有出门。到了初阳台,感觉阳光出奇地好。据说,每逢农历十月初一,登初阳台可观日月并升之奇景。现在虽是春天,依然想起了南宋诗人董嗣杲《初阳台》中的名句“日月光华含吐异,云萍踪迹往来空”。
少时至今,初阳台上观景,已不下百次。初阳台为无数杭州人见证了古城的沧桑巨变。虽在抗“疫”之际,我感觉,杭州,依然那么美。
回想十七年前
张锦渭(上海,摄影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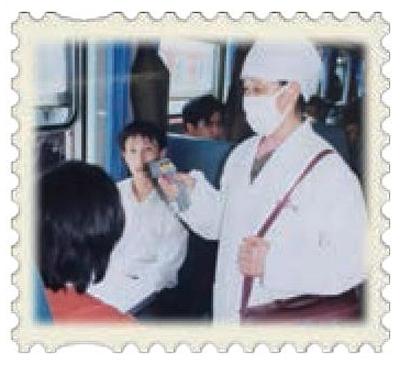
当年抗击非典的北京小汤山医院重新启用。宅在家里的我,翻翻相册,17年前拍摄的照片,又一次展现眼前。
2003年4月3日下午,我乘坐14次特快去北京。途中得知广州、北京的非典已有扩散,上海也已采取措施做好预防工作。
第二天返沪后,看到上海地区铁路各部门已行动起来。上海列车段防疫人员对停放的上海至广州的99/100次,上海至北京的13/14次及1462/1461次列车进行消毒。接着我身背相机来到旅客进出集中的公共场所上海站。发现在车站南进口大厅已安装检测设备。
当时女儿和同事都告诉我:“你不要去冒险,万一传染到怎么办。”当时,还没人去车站采访、拍照。作为党员,作为摄影师,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记录。
当来到铁路行车公寓时,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打扫和消毒。因这里住宿的,是来自全国各局到沪的列车乘务员和机车司机,每天进出的人数达1000多人次。广州是发生非典的重灾区。当走进上海开往广州的99次车厢时,三组列车长介绍说列车上已配备应急包。列车开车前,乘务员还对卧铺房间、厕所、走廊进行消毒。开车后,用广播对旅客进行通风、个人卫生宣传。上海开往北京的1462次是逢站必停的绿皮车,旅客上下频繁。上海站放客前,列车长对立岗的列车员进行测温。医务人员身背药箱,在车厢内给旅客测温和了解情况。在站台上,志愿者从到沪列车员处了解车内旅客情况,进行登记,防疫人员对站台上的行包进行消毒。行李房职工将防非药品装上14次特快列车,支援北京。
5月21日,由广州开往上海K48次列车上,一名列车员确诊为上海第8例非典患者。为检查诊断收治他,与其接触的铁路12名医务人员,车站两名职工,全部在上西大酒店隔离14天,直到6月5日结束,我还给他们拍了一张合影。回看昔年,再看今朝,相信这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也要挺过去,走向胜利!
我居然在年前去了武汉
陈立群(上海,出版社编辑)

一月上旬,出差北京。我是周二中午到的,估计待大半周,准备周末返沪。不巧的是,有几个想见的人临时有事,碰不到。还是想在周日回沪,正好赶上周一上班。这样一来就多出来一天。去天津还是武汉,有点犹豫。北京西—汉口和北京南—上海高铁最快的班次都差不多4.5小时左右,直接去武汉比回沪后再去省了一个单程。
当时网上已有武汉发生不明肺炎的消息在流传。北京的朋友劝我,武汉最近情况不明,还是不去为好。
我还是稍微有点纠结。武汉的彭老师已经联系上了,原来就准备年前去一趟。致电同济医学院的朋友,了解当地情况。他告诉我,只要不去医院等人流密集场所,应该问题不大。犹豫了两天,还是去武汉。
11日周六,晚上7点,北京西—汉口。一路正常,中途在河南下去很多人,抵达汉口前,车厢里没几个人,空荡荡的。这个时候想起了武汉的情况不明,因为没口罩,还是有点害怕。
23:30,车抵汉口。出站的人稀稀拉拉,毕竟半夜了。这里每年来,应该有点熟。出站了,广场上黑乎乎的,原来的通道被出租车道拦住了。费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出了广场,入住附近的一家连锁酒店。半夜了,水不热,龙头开了很久,还是不热,没法洗澡。和总台联系,答应给换一间房。我当时已脱了衣服准备洗澡,也懒得换房间了。不久来了一个师傅,调了一下龙头,没用。说是到楼上看一下房间里热水是否正常,再告诉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电话来。龙头的水还是不热,肯定洗不成了。已经不早了,赶快睡吧。这个时候发现空调的遥控器居然打不开。被子不够厚,没有办法,只能将就着睡了。
醒来已过8:30,赶紧洗漱,吃早饭。结账离开,马上打车去彭老师家。先到了荣东小区。进了小区大门,在里面转了差不多半小时,还是没有找到要找的楼栋。这里的编号完全没有规律,只能再打电话。彭老师的妹妹让我原地等,她来接我。一会儿她来了,陪着我去姐姐那里。到那里已经过10点半了,中午只能在她家吃饭。彭老师的妹妹说,昨天已关照阿姨准备了。她就回去了。饭后才开始进入正题,聊抗战时期内迁四川李庄的高校的情况。彭老师记性很好,很多细节都还记得。其间联系两个当地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上。下午3点左右,突然想起这里离同济医学院不远。我给金士翱老师打电话,准备去看看他。金老师今年98岁,当年在李庄考入同济医学院。我想好了,从那里出来,穿过一条小巷就是青年路地铁站,可以直达天河机场。
与彭老师告别时,她非常客气,非要让他们家阿姨送我出来。走在荣华街上,金老师家的阿姨来电话了,告知春节前不要去了。武汉的情况看来还是紧张。
街上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稍微有点不自在。索性直接去机场吧,尽管有点早。我在路边稍微站了一会儿,没有看到空出租车。不远处就是武胜路地铁站。还是坐地铁吧。周日下午,地铁里人不少。进站一如平常,车厢里大概有八成满,好像没人戴口罩。那个时候真紧张:你不知道周围的人是否传染。中间在常青花园(下一站就是金银潭,这个地名后来经常出现在新闻里)换乘2号线,到了天河机场。时间17:10。
机场一切照旧,虽然人不少,但人流密度比地铁还是小很多。19:10,航班正常起飞,21:00不到降落浦东机场。我回来了。
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如果回沪后再来武汉,就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