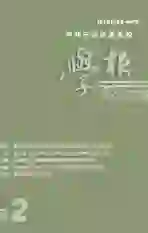王阳明与“楚中王门”
2020-04-07陈寒鸣
陈寒鸣
[摘 要]黄宗羲《明儒学案》标立有“楚中王门”,但所列人物和录载资料均甚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楚中王门”的研究亦十分欠缺。但事实上,王阳明曾在湖南有两次为时颇长、参与人数较多的大型讲学,他门下亦有些湖北籍的亲传弟子;可以说,他不仅在楚地播下了心学思想火种,而且亲自为“楚中王门”培养了中坚力量。至晚明,耿定向及“天台一派”崛起,李贽(卓吾)又长期在湖北生活讲学,更因深受卓吾影响而有公安三袁,“楚中王门”达到了发展高峰。而发生在荆楚之地的耿定向与李贽之间的长期论争,则不仅是晚明王学,而且是当时思想文化界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耿、李“和解”及不久天台的去世,以及因耿、李之争余波而形成的对李贽新一轮更加猛烈的迫害并导致卓吾不得不永離麻城龙湖,宣告了楚中王门的终结。
[关键词]中晚明;王阳明;“楚中王门”
[中图分类号] B24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2-0058-12
楚中地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即荊楚(湖北)和湘楚(湖南)之地。中晚明,阳明心学在这里有很大影响,逐渐形成起“楚中王门”。“楚中王门”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慧眼独具地首次归纳概述出来的,但他仅录记了佥宪蒋信(道林)和孝廉冀元亨(闇斋)两人,显然很不完备。这就有必要详考史料,对王阳明与“楚中王门”予以析述。
一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楚中,“当阳明在时,其信从者尚少” 。在《楚中王门序》中除了蒋信、冀元亨、刘观时,他据徐爱《同游德山诗》,又列出王应奎、胡鸣玉、刘德重、杨礿、何凤韶、唐演、龙起霄。但事实上,王阳明亲传弟子中出自楚中者并非只有这几位。兹先述阳明在湖南的讲学活动。
正德年间,王阳明往返贵州时曾两次途经湖南。第一次是正德三年(1508)早春,谪戍贵州龙场驿途中,由江西萍乡入湖南。过醴陵,宿泗州寺,游靖兴寺、龙潭,探访李靖遗迹,有诗咏怀;至长沙,因病齿留居八日,与提学陈凤梧、参事吴世忠、佥事徐守诚、太守赵维藩、推官王教交往,由府学生周金陪同游岳麓并谒朱张祠,多有诗咏唱酬;过洞庭作赋吊屈原,过湘阴栗桥作诗吊易先墓;过沅江阻泊于天心湖,过武陵欣游桃源洞,作《去妇叹》五首自叹谪臣命运;过溆浦和辰溪,遂入贵州境。钱德洪《年谱》说“先生赴龙场时,随地讲授” ,或即指这次途经湖南在长沙留居八日时事,其时有所交集者或向阳明问学,而长沙人、府学生周金在陪他游岳麓时更执弟子礼,对他十分敬重,故他有诗曰:
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谈诵。之子特相求,礼殚意弥重。自言绝学余,有志莫与共;手持一编书,披历见肝衷;近希小范蹤,远为贾生恸;兵符及射艺,方技靡不综。我方惩创后,见之色亦动。子诚仁者心,所言亦屡中;顾子且求志,蕴蓄事涵泳。孔圣固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閧。知子信美才,大构中梁栋;未当匠石求,滋植务培壅。愧子勤倦意,何以相规讽?养心在寡欲,操存舍即纵。岳麓何森森,遗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贤迹尚堪踵。何当谢病来,士气多沈勇。
但此时赴谪途中的阳明,“情绪低落,与道友相会,多半也是强打精神,很难说有讲学传道的心思,钱德洪所称的‘随地讲授,实有臆测之嫌” ,所以,述论“王阳明与‘楚中王门”,似可对这次途经湖南所交集者不作多析。第二次是正德四年(1509)十二月阳明离贵阳赴江西庐陵知县任,次年春途经湖南溆浦、辰州、常德、长沙 、醴陵等地。他这次途经湖南,有两次重大讲学活动:
一是在辰州,居龙兴寺,与辰中诸生静坐讲学,语学者性体悟入之功。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七十六《金陵答问》记:
往时阳明先生在辰州龙兴寺讲学,时世隆与吴伯诗、张明卿、董道父、汤伯循、董粹夫、李秀夫、刘易仲、田叔中俱时相从,每讲,坐至夜分。一夕讲及好色者,众咸曰:“吴伯诗、张明卿恐难免此。”先生曰:“若一向这里过来,忽然悔悟,亦自决裂;若不曾经过,不能谨守,一旦陷入里面,往往多不能出头。尝见前辈有一二人,平时素称不饮酒,不好色,后来致仕家居,偶入妓者家饮酒,遂至倾家资与之,至老无所悔。此亦是不曾经过,不能谨守之故也。以此知人于此须是大段能决裂谨守,乃可免此耳。”
同书卷七十七《金台答问录》又记:
隆问阳明先生曰:“神仙之理恐须有之,但谓之不死则不可。想如程子修养引年者,则理或然耳。”先生曰:“固然。然谓之神仙须不死,死则非神仙矣。”隆闻此语时,先生年已三十九矣。
吴伯诗问阳明先生:“寻常见美色,未有不生爱恋者,今欲去此念未得,如何?”先生曰:“此不难,但未曾与著实思量其究竟耳。且如见美色妇人,心生爱恋时,便与思曰:‘此人今日少年时虽如此美,将来不免老了,既老则齿脱发白面皱,人见齿脱发白面皱老妪,可生爱恋否?又为思曰:‘此人不但如此而已,既老则不免死,死则骨肉臭腐虫出,又久则荡为灰土,但有白骨枯髅而已,人见臭腐枯骨,可复生爱恋否?如此思之,久久见得,则自然有解脱处,不患其生爱恋矣。”
这几则不见载于《传习录》的珍贵资料,为亲聆阳明讲学,故可称为其亲传弟子、后又为湛若水门人的王世隆所记,由此可见阳明在兴隆寺与辰中诸生讲学之况。阳明稍后对他此次龙兴寺讲学所以教诸生“静坐密室,悟见性体” 、“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作解释道:
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得诸友,何幸何幸!方以为喜,又遽尔别去,极怏怏也。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实德未成而先揭标榜,以来世俗之谤,是以往往坠堕无立,反为斯道之梗。诸友宜以是为鉴,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著实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分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著力处,既学便须知有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学要鞭辟近里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谦受益”、“不求异于人,而求同于理”,此数语宜书之壁间,常目在之。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只如前日所约,循循为之,亦自两无相碍。所谓知得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也。
阳明殁后,“门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邹守益作《辰州虎溪精舍记》说:“阳明王夫子自会稽谪龙场,道出辰阳。辰阳之胜,曰虎谿山寺,世称二十六洞天。因宿僧舍弥月。有古松甚奇,大书其轩曰‘松云,复留诗于壁。一时从游诸彦,如唐柱史房诩、萧督学璆,千余人切琢正学,剖剥群淆,若众鸟啾啾获闻威凤鸣也。嗣是大酉王宪副世隆题所寓曰‘思贤堂。东桥顾中丞璘载诸通志。年来山麓产紫芝,光丽异常,识者曰:‘兹其文明之祥乎!”众所周知,阳明极重讲学,尝谓:“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钱绪山称他“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习,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圣贤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 。而像这样在龙兴寺讲学弥月,千余人参与,可以说是阳明一生中唯一一次人多时长的盛大讲会。即使后来居越,弟子环立,其况亦不如此之盛。
二是在常德,居武陵潮音阁,讲学二旬,蒋信、冀元亨、文澍、刘观时、杜世荣、王文鸣、胡珊、刘瓛、杨礿、杨禠、何凤韶、唐演、龙起霄、龙翔霄等众多武陵士子皆来受学。
尽管一到武陵,阳明就因恐弟子由静坐而入禅寂,故特致信辰中诸生,说其所以令“静坐”乃“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但此时“诸士来谒,论知行异同,纷纷辩告。先生曰:‘兹来与诸生寺中静坐,使自悟性体。因题《雨霁》诗,有云:‘沙边宿鹭寒无影,洞口流云夜有声。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王阳明全集》卷十九《霁夜》诗曰:
雨霁僧堂钟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边宿鹭寒无影,洞口流云夜有声。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问津久已惭沮溺,归向东皋学耦耕。
束景南据此而谓“阳明在‘龙场之悟后仍教人静坐入定、悟见性体” ,这是合乎事实的。案:洎乎北宋初叶,受佛、老二氏影响,周敦颐始明言:“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程颢、程颐兄弟继之而起,亦认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程氏经说》卷一)“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故曰动、静一源。”(《程氏粹言》卷一)又以“静”为入德之始基,认为“静”能养德,“静坐”为心性修养之最佳途径,唯有善“静坐”者方堪称“善学”。二程弟子后学也多重视静修的作用,如杨时好言“静中体认”;时之弟子罗从彦“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从彦之弟子李侗(朱熹的老师)既以“静”为进学之功,又以之为养心之要。稍前于阳明的程敏政熟知儒学史,对南宋时期朱、陆纷争的历史公案极为了解,更对他身处的“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現实学术文化氛围深有体察,所以,他直溯周敦颐和二程兄弟(尤其是程颢)竭力强调“静”的意义。敏政说:“定而后静,曾子之所受于孔门也;定而主静,周子之说太极也;静定而动亦定,程子之答横渠也。盖必究心程子之说,而后至善之地、中正仁义之指可窥也。夫静定之义大矣!”(《篁墩文集》卷十九《静定山居记》)他不仅以“‘静学之言,实洙泗绪余”,视之为孔子开启、曾子所受,而又为历代“大儒君子每有取焉”的儒门固有传统,而且更进一步从价值作用角度确认“静定之义大矣”,说:“人之为德也,静然后可以制天下之动,故求人德者,学必自静。夫静则心恬而不兢,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应万变,有所恃而不舛礼。”(上书卷二十九《静轩序》)这样的“静定之义”,“推而极之,积而不已,则其体天德,其用王道。用有小大,而吾之所养者殆无施不可也”(上书卷十八《徽州府婺源县重建庙学记》)。陈献章提出:“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并以“静”为“心学法门”(《陈献章集》卷一《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又力主“为学须静坐中养出端倪方有商量处”(上书卷二《与贺克恭黄门》),认为:“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作圣之功,其在滋乎!”(同上《复赵提学佥宪》)当然,宗信陆学、“以自然为宗”(同上《遗言湛民泽》)的陈献章,其论“静”之用心与以程朱理学为理论背景、学术立场来讲论静修之学的程敏政有很大不同,但在开启中、晚明“主静”思潮这一点上,敏政和献章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对于王阳明来说,他在湖南这两次讲学过程中,之所以要令弟子“静坐”,除了承受宋以来儒学传统,尤其是在当时篁墩、白沙已启明儒的“主静”思潮背景下,欲使弟子通过习“静”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外,大约还与他曾有过“静坐”以修身养性乃至进而获悟至道的亲身体验有关。早年阳明因病而对道教养生之术有所实践,且颇收奇效,如弘治十四年(1501)公务繁剧兼通宵苦读患了虚咳之疾,不得不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 。至其被贬贵州龙场驿,“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为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以求诸静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以所记忆《五经》之言征之,一一相契,独与晦庵注疏若相牴牾,因著《五经臆说》” ,所谓“端居默坐,澄心精虑”,即白沙“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他在武陵讲学后过沅江晚泊江思湖,静坐悟天机,有数首感怀诗,如云:
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港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同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
江日熙熙春睡晚,江云飞尽楚山青。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
总之,他于“静坐”中获益甚多。明乎此,我们便不能理解刚至贬所归返的阳明何以要令弟子“静坐”了。当然,“龙场悟道”后的阳明已俨然“为思想界之巨子,其人坐而论道,起而能行,他虽重视‘静处体悟,但也不遗却‘事上磨炼,因此其思想体系虽倾向‘主静,却未偏言‘主静” 。这正是他此番湖南讲学时,既令弟子“静坐”,又要申言“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的原因。
王阳明的这两次讲学,不仅在湘楚之地播下了心学思想火种,而且培养出了以刘观时、王嘉秀、萧琦等为代表的辰州弟子群和以蒋信、王应奎、冀元亨、胡珊、刘瓛、杨礿、杨禠、何凤韶、唐演、龙起霄、龙翔霄、文澍、刘观时、杜世荣等为代表的武陵弟子群。关于这些湘籍弟子,王兴国有专文考述 ,故兹不赘言。楚地本有深厚的道家(道教)文化传统,阳明赴谪途经湖南时已有所感受,如其《与沅陵郭掌教》云:“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诸生问业冲星人,稚子拈香静夜焚。世事暗随江草换,道情曾许碧山闻。别来点瑟还谁鼓?怅望烟花此送君。”而他令弟子静坐,恰与此传统相契合,有些楚中士人或即因此而追随阳明,这使他不得不作诗申明自己的思想理念:
王生兼养生,萧生颇慕禅;迢迢数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学亦匪仙。坦然由简易,日用匪深玄。始闻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镜,暗暗光内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烛媸妍。世不如剪彩,妆缀事蔓延;宛宛具枝叶,生理终无缘。所以君子学,布种培根原;萌芽渐舒发,畅茂皆由天。秋风动归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彦,往往多及门。临歧缀斯语,因之寄拳拳。
王生即王嘉秀,善画且好仙学。阳明讲学滁州时,又特前来受学。阳明《书王嘉秀请益卷》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古之人所以能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人之不善则恻然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见善而妬其胜己,见不善而疾视轻蔑不复比数者,无乃自陷于不仁之甚而弗之觉者耶?夫可欲之谓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见恶于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凤翔麟,人争快睹;虎狼蛇蝎,见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见之必恶,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见恶于人者,虽其自取,未必尽恶,无亦在外者犹有恶之形欤?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于隳堕断灭之中,而自任以为无我者,吾见亦多矣。呜呼!自以为有志圣人之学,乃堕于末世佛、老僻之见而弗觉,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学者所吃紧。其在君子,则犹对病之良药,宜时时勤服之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夫能见不贤而内自省,则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矣,此远怨之道也。”谆谆告诫他严明儒释之辨,远离佛老,依归正学,涵泳体认仁者一体之怀。他和“慕禅”的萧琦终于信从了阳明心学,成为楚中王门中坚。至于阳明本人则通过讲学,“一方面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另一方面还使其对圣学与佛道间的关系有了更透彻、全面的把握,从而为建构逐步走向成熟的思想体系作了极好的理论铺垫” 。他后来在作于正德十年(1515)的《见斋说》中写道:
问于阳明子曰:“道有可见乎?”曰:“有,有而未尝有也。”曰:“然则无可见乎?”曰:“无,无而未尝无也。”曰:“然则何以为见乎?”曰:“见而未尝见也。”观时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则明言以教我乎?”阳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子未观于天乎?谓天为无可见,则苍苍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未尝无也;谓天为可见,则即之而无所,指之而无定,执之而无得,未尝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风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见也。”曰:“然则吾终无所见乎?古之人则亦终无所见乎?”曰:“神无方而道无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是有方体者也,见之而未尽者也。颜子则如有所立,卓尔。夫谓之‘如,则非有也;谓之‘有,则非无也。是故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故夫颜氏之子为庶几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见,斯真见也已。”曰:“然则吾何所用心乎?”曰:“沦于无者,无所用其心者也,荡而无归;滞于有者,用其心于无用者也,劳而无功。夫有无之间,见与不见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顾切切焉,吾又从而强言其不可见,是以瞽导瞽也。夫言饮者不可以为醉,见食者不可以为饱。子求其醉饱,则盍饮食之?子求其见也,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见之道也已。”
这里依据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之论而发挥性阐述的在慎独中体认有与无之别、在真有、真无、真见中探求至道等观念,是阳明以前未曾谈论过的。这表明在培育湘楚弟子过程中,他的思想向成熟化、体系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阳明亲传湘楚弟子,当以蒋信和冀元亨最为重要,黄宗羲《明儒学案》即以他们为代表而录载于《楚中王门学案》。限于篇幅,兹不述论,姑待日后为文专析。此外,除了阳明亲自为楚中王门培养了中坚力量外,徐爱、钱德洪、季本等阳明重要弟子也都在湖南讲过学,对王学在楚中的传播与发展作出过各自贡献。
二
王阳明一生讲学足迹遍布十余省,但他并未亲履湖北讲学,黄宗羲盖据此而谓“阳明在时”,荆楚之地“信从者尚少”(《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案语》),以至现代学者有“楚中王门发展不均”之叹。
不过,阳明亲传弟子中也有荊楚士子。如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记正德九年(1514)五月,阳明到南京任鸿胪寺卿后,郭庆、吴良吉自湖北黄州来受学。而据《邹守益集》卷七《阳明先生书院记》:“阳明先生官滁阳,学者自远而至。……中丞方近沙任,旧学于予也,谋于诸缙绅曰:‘阳明公归自贵阳,诸生郭庆、吴良吉辈及门受学,请尸祝公为矜式。” 郭庆、吴良吉原为师徒,因闻阳明倡道东南而特从湖北徒步至江苏,拜阳明为师。光绪年间所修《黄州县志》卷十九《儒林》说:
郭庆,字善甫。正德丁卯举人,质方力学。时,王守仁倡道东南,庆徒步往从之。三年始归,充然有得也。授清平知县,有冰檗,称勤于抚字,捐俸给贫民牛种。后乞休归,民不忍舍,为立祠祀之。家居不治垣屋,澹泊自守。戚里有困匮,辄赒给焉。耽吟咏,每诗成,常自削稿,故著述不多见云。
吴良吉,字仲修,号石梁。师事王守仁,讲良知学。家贫,授生徒,榘矱嶷然,而纯粹可掬,学者暱就之。作诗歌,有邵尧夫风。孟津宰黄冈,延之书院。有暮夜怀金请问者,力却之。及卒,耿定向借棺敛之,为作传。知府瞿汝稷志其墓。著有《居湖集》。
《问津书院志》亦记郭庆“闻王阳明倡道东南,徒步往,从之三年。讲学问津,充然有得” 。但县志和书院志说郭庆等此次从学阳明“三年”,并不确切,因为阳明《赠郭善甫归省序》明言:“郭子自黄来学,踰年而告归。”兹将阳明作于乙亥年(1515)的此序全录于下:
郭子自黄来学,踰年而告归,曰:“庆闻夫子‘立志之说,亦既知所从事矣。今兹将远去,敢请一言以为夙夜勗。”阳明子曰:“君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种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时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种之是忧也,而后可望于有秋。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辩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尝见子之求嘉种矣,然犹惧其或荑稗也;见子之勤耕耨矣,然犹惧其荑稗之弗如也。夫农春种而秋成,时也。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至于秋矣。巳过其时,犹种之未定,不亦大可惧乎?过时之学,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犹或作辍焉,不亦大可哀乎?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子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
郭庆到滁阳后不久,阳明即有升南京鸿胪寺卿之命,他遂随侍阳明往南都继续受学。其时,来求学者渐多,阳明《与顾惟贤》说:“向在南都相与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马明衡、兵部主事黄宗明、见素之子林达有、御史陈杰、举人蔡宗兗、饶文璧之属,蔡今亦举进士,其时凡二三十人,日觉有相长之益。”钱德洪《年谱》录载阳明南都讲学弟子中即有郭庆。关于郭庆从学阳明的情形,薛侃据其亲见而在《研几录》中记道:“昔者郭善甫见先生于南台,善甫嗜书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余月,无所事,复告之曰:‘子姑读书。善甫憨而过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庆以废书而静坐,终也为庆以废坐而读书。吾将奚适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郭庆显然与那些“放言高论”、“渐背师教”的“自滁游学之士”不同,是位谨守师教而勤学苦读之人,故而后来阳明亲题“泉石不知尊爵贵,乾坤何碍野人居” ,以嘉其志。嘉靖元年(1522)暮冬,郭庆致书阳明问安请益并述思念之情,阳明遂即复书云:
朱生至,得手书,备悉善甫相念之恳切。苟心同志协,工夫不懈,虽隔千里,不异几席,又何必朝夕相与一堂之上而后快耶?来书所问数节,杨仁夫去,适禅事方毕,亲友纷至,未暇细答。然致知格物之说,善甫已得其端绪。但于此涵泳深厚,诸如数说,将沛然融释,有不俟于他人之言者矣。荒岁道路多阻,且不必远涉,须稍稔,然后乘兴一来。
接此复书,郭庆思师之情更加迫切,次年春正月,他就携吴良吉前来绍兴,再次向阳明求学。他们途中讨论学问,意见参差,颇不相合,故一到绍兴见到阳明就赶快求证。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记之曰:“黄冈郭善甫挈其徒吴良吉走越受学,途中相与辩论未合。既至,郭属吴质之先生。先生方寓楼饘,不答所问,第目摄良吉甫再,指所饘盂语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饘,此案下乃能载此盂,此楼下乃能载此案,地又下乃能载此楼。良吉退就舍,善甫问先生何语?良吉涕泗横下,呜咽不能对。已,良吉归而安贫乐道,至老不负师门云。”郭、吴二人在绍兴就阳明受学至少月余方归,邹守益春二月作《同郭善甫、魏师颜宿阳明洞》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其时学习、生活的状况:“躡足青霄石万寻,谢墩何处更投簪?云穿草树春亭静,水点桃花洞口深。屋漏拂尘参秘诀,匡床剪烛动幽吟。千年射的谁能中?莫道桑蓬负壮心。”从目前所见资料看,敦朴笃行的郭庆,在思想上对阳明心学并无多少发挥,且其已无著述传世,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他们心学造诣,但善甫不仅对阳明有很深的感情,而且讲学乡里,接引后生,在荆楚之地传扬阳明心学自亦有功。耿定向《先进遗风》卷上说“余里中郭孝廉庆,字善甫者,敦朴笃行人也,从先生(阳明)游最久。既归,则以其见闻诸先生者接引里中后生” 。
嘉靖年间阳明居越时,八邑彦士纷纷来学,而荊楚士子前来绍兴就学的有:黄冈人蒋月涇,后入南雍与湛若水(甘泉)游,终身不仕,教授生徒,岁至数百人,著有《易经肤说》三卷。麻城人毛凤起,德性和易,志行高洁,弃举子业而从阳明学,归后授徒于乡,作《心学图》、《致知说》阐扬师说,知县陈子文为建道峰书院居之,传播阳明心学,就教者甚众。黄冈人朱守乾请学而归时,阳明特书“致良知”三字赠别:
黄州朱生守乾请学而归,为书“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守乾由此而获悟阳明“良知”教精意。应城人杨绍芳、继芳兄弟,均受学于阳明,深契良知之旨;绍芳是嘉靖二年(1523)进士,从学阳明时为上虞知县,《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说他“复堤塘,浚壅塞,往来者便之……”,《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说他“好兴剔利蠧,改运河,拓学地,修筑海塘,治绩甚著”,可见其治邑颇有政声,又在上虞县北龙王堂建水东精舍以传播阳明心学,后升御史,任江西按察副使,年四十卒于官。安陆人杨汝荣,从阳明游归后与继芳等一道研习践行“良知”之学,省心饰行,为乡里表率。通山人朱廷立,字子礼,号两崖,嘉靖二年(1523)成进士后任诸暨知县,究心政事,常至绍兴向阳明求教,《王阳明全集》卷八《书朱子礼卷》:
子礼为诸暨宰,问政,阳明子与之言学而不及政。子礼退而省其身,惩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恶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趋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蠧,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举。叹曰:“吾乃今知学之可以为政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为学,阳明子与之言政而不及学。子礼退而修其职,平民之所恶,而因以惩己之忿也;从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欲也;顺民之所趋,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蠧也;复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叹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为学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政与学之要。阳明子曰:“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礼退而求至善之说,炯然见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这“‘问政的故事说明,在王阳明的良知学逻辑中,所谓大学之道,就是为政之道。而政道之要,就在‘明德、亲民、止至善三纲领。为政的根本在明德,德是道之体,其见之于实践便是亲民,亲民是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亲民的根本旨要和终极目标。这个‘至善便是‘良知,‘止至善便是‘致良知。所以,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是与其良知之学密不可分的,是其良知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当时王门弟子中,朱廷立实为能问能思,善学善行者。在为政实践中切实践行了阳明“明德亲民”之教,并因此而契悟“良知”,优入至道之域。他为知县则爱民礼士,勤于职守,治称第一;晋河南道御史,任两淮盐政,巡按顺天,督修河道,又起补北畿辅学政,倡正学,精藻鉴;迁升南京太仆寺卿,勤于牧政,寻以老母忧去;忧除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升大理寺卿,后终因蒙忌而以礼部右侍郎谢事归。归家,或闭门著述,或坐炯然亭赋诗论学,著有《盐政志》、《马政志》、《家礼节要》等行于世,另有《两崖集》、《清朝疏》藏于家。
毫无疑问,上述获阳明亲传的荊楚诸子都是楚中王门的主要成员,惜乎均失载于黄宗羲《明儒学案》。显然,钱明将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讲学于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崇正书院,才使“湖北阳明学气候”“由此而生” ,并不很确切。当然,阳明弟子曾才汉采辑《阳明先生遗言录》并初刻行于湖北荆州,以及钱德洪这次在蕲州崇正书院的讲学和他讲学期间依据《阳明先生遗言录》修订为《传习录下》并由黄梅县令张君刻于蕲州,这些对阳明心学在荆楚之地的传播以及楚中王门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故特录载钱德洪《〈传习录〉下跋》: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以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去年,同门曾才汉得洪手抄,复旁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今年(嘉靖丙辰)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益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今吾师之殁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三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将耿定向归入泰州学派,《楚中王门学案·案》中称:“楚学之盛,惟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这是认为由泰州心斋王艮之学而开启了自己学说思想的“耿天台一派”的崛起,使楚中王门得以兴盛。但他同时又说“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世称天台先生,湖广黄安(今湖北红安)人。其仲弟定理(1534—1584),字子庸,号楚倥;昆弟定力(1541—1607),字子健,号叔台。耿氏三兄弟以及天台的门生弟子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一些同道朋友,大体构成了黄宗羲所说的“耿天台一派”。关于此派的学说思想,黄宗羲说是“自泰州流入”。检索天台资料,可见其为学无常师之人,他在思想上倾慕邹守益、罗洪先,更自谓私淑王艮,又称受到罗汝芳、胡直、史惺堂和王庐陵的影响,而实际上,子庸对其思想影响最大并最为直接。当然,定向、定理间论学亦时有不合,楚倥与天台兄弟二人,一个崇佛,一个尊儒;一个出世,一个用世;一个守定‘未发之中一言,一個恪守‘人伦之至一语。其矛盾自在其中” 。子庸是李贽的知己好友;万历五年(1577),李贽擢任云南姚安知府, 赴滇途经团风,舍舟登岸,直抵黄安看望他并其兄定向,《耿楚倥先生传》说时“有弃官留住之意。楚倥见予萧然,劝予复入,予乃留吾女并吾婿庄纯夫于黄安,而因与之约曰:‘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楚倥牢记吾言,教戒纯夫学道甚紧。吾女吾婿,天台先生亦一以己女己婿视之矣”(《焚书》卷四)。卓吾之外,定理又与被定向称为“三异人”的方湛一、邓豁渠、何心隐最为相契。因此,尽管“无论问学师从还是学术取向,耿定向都是王门中较为特殊的人物,很难简单地把他划入哪一派、哪一门” ,但总体上看,黄宗羲说他的思想“自泰州流入”或深受泰州学派影响,还是有道理的。总之,“天台思想尽管具有某种复杂性,但是就其思想的本质而言,无疑属于阳明心学” 。故以天台一派出而使楚中王门得以兴盛,这应该是合乎史实的。
傅秋涛在其《〈耿定向集〉点校整理说明》称:“耿定向属于官僚兼学者型,而以政治职业为主;他不尚空言,以学问作为从政为官的必要的修养。”这是符合儒家传统的,因为不仅孔子有“学而优则仕”之教,而且《大学》更倡修齐治平,遂使为学为人成为为政的必要前提。这也是符合阳明心学精神的,因为阳明在回答后学者之问时就已借“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曲折地表达出了他“政学合一”的思想倾向:
有一属官,因久听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煩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 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其后,阳明后学中,虽用语不尽相同,但大都有此论。如邹守益说:“学与政匪异辙也。” 欧阳德说:“政学本非二事。”又说:“无政非学,无学非政。”王艮说:“学外无政,政外无学,是故尧舜相传授受,允执厥中而已”王艮弟子林春亦发挥说:“古人即政是学,即学是政,只於自身上反求,自然得力,亦有滋味。”王畿更专作《政学合一说》,云:“君子之学,好恶而已矣。赏所以饰好也,罚所以饰恶也。是非者,好恶之公也。良知不学不虑,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是非之则也。良知致,则好恶公而刑罚当,学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学》之道,自诚决以至于平天下,好恶尽之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之诚也。好恶无所作,心之正也。无作则无僻矣,身之修也。好恶公于家,则为家齐,公于国与天下,则为国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学在其中矣。昔明道云:‘有天德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独知无有不良,能慎独,则天德达而王道出,其机在于一念之微,可谓至博而至约者矣!”就此来看,黄宗羲说“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并不妥切。
对于耿定向来说,他是持守着一种“不容已”的学术宗旨而成为官僚兼学者而以政治职业为主的人物的。定理本有“吾学以不容已为宗”之言,而定向则把“不容已”视为“千圣学脉”,并对定理所言“不容已”解释道:“盖仲子之所揭不容已者,从无声无臭发根,高之不涉虚玄;从庸言庸行证果,卑之不落情念。”又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古人继天之不已者以为心,虽欲自已,不容自已矣”;“古人原从根心不容自已的道理做出,所谓天则,所谓心矩是已。此非特不可不依仿,亦自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也” 。他不仅“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虽欲坚忍无为,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虽欲任放敢为,若有所制而不敢” ,而且更将这种“不容已”的为学为人宗旨自觉转化为强烈的“卫道”意识,身处晚明之世,目睹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出现的种种“异变”现象,深感危机而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二0一《管佥宪》称天台“有实见实力,又勇于卫道,确然迥澜之柱也”。其弟子焦竑在《天台耿先生行状》说:“先生……目无流视,坐无倚容。孝友忠直,出自天性。若好学不倦,若火之必热,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学,先后凡累变,大都以反身默识为先,以亲师取友为助,以范围曲成为征验。一言一动,皆足为学者法。至于微言渺论,第以开端启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诐之词、诡异之教,则排斥之不少假借。盖国朝理学开于白沙,大明于文成。文成之后一再传,而遂失之。承学后进,窃其管窥筐举,穿径而穴焉。以至发堿抉樊,受衍于荒淫之陂,而失其大宗。先生重忧之,为坊甚力。”
天台一派的崛起,使楚中王门在晚明兴盛了起来。而李贽弃官后于万历九年(1581)至黄安依耿定理,并自此长期在楚地生活讲学,受其思想深刻影响而有“公安三袁”的出现,更使楚中王门发展至高峰。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与李贽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相识的,其时,卓吾漫游楚中至公安,住在柞树林里,且以“狂禅”之貌出现在集市上,当地人讶称他为“柞林叟”。熟知历代狂士怪诞人格的年轻的三袁兄弟听说后,立即前去拜访:
柞林叟,不知何许人,遍游天下,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庚寅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宗道)时以予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再访之,遂不知所在。予仿佛次其语,以传于后。(袁中道:《珂雪斋集》“附录二”)
“公安三袁”兄弟一见到李贽,就提出许多问题请教,李贽一一作了回答,如问“圣、凡同异之分”,答:“不必论圣、凡同异。公且指何者为圣,何者为凡?”问“《六经》”,答:“《易经》真是圣贤学脉,《书经》则史官文饰之书,《春秋》则一时褒贬之案。”问“太史公何如人”,答:“天下大侠!当时李陵降虏,陇西之士皆耻出其门,马迁独救之,非独枯木寒灰,无势位之可附,亦且负不忠不义之名,救之而无以自解于清议者也。无恩无名,而又有不可测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于意气,非后世矜重名义之流可比。” 问“王心斋何如人”,答:“也是一个侠客。所以相传一脉,为波石、为山农、为心斋,各有杀身不悔之气!波石为左辖时,事不相干,挺然而出,遂以死,肉骨糜烂。山农以行船事为人所恨,非罗近溪救之,几至以死,不但谪戍而已。心隐以言忤人,遂死于杀人媚人之手。盖以心斋从来气骨高迈,亢不惧祸,奋不顾身,故其儿孙都如此!所谓龙生龙子,果然非虚。”问“何心隐何如人”,答:“这样人,甚么人?好轻易!”谓宗道曰:“公如何只在枝叶上求明白?纵枝叶上十分明白,也只是枝叶。”强调“学问须“要有些真实受用。不然只在道理上缠缚,如何了得?”并向他们专门介绍罗汝芳的思想,说“渠是为己的学问,不求一人知的”,又将之称为“根器”,释曰:“根器即骨头也,有些骨头者方可学道。”如此等等。(袁中道:《珂雪斋集》“附录二”《柞林纪谭》)“公安三袁”大感获益,惊叹为“大奇人”,并从此愈益敬慕李贽,与他结下深厚情谊。而再去村落野庙拜访时,他却已飘然而去,不知漫游到何方了。袁中道后来把这次拜访李贽的经过写入《柞林纪谭》。李贽与“公安三袁”的这番遇合,对他们有很深刻的影响,袁宏道即坦承卓吾之学对自己的人生观起了改造性作用:“仆少时于小中立基,枯寂不堪。后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门户始得自在度日,逢场作戏矣。”(《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徐冏卿》)后来,李贽将新印出的《焚书》寄赠“公安三袁”,袁宏道作诗《得李宏甫先生书》,云“似此瑶华色,何殊空合音” ,备致倾倒之意。“公安三袁”“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卓吾)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 ,“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 。可见他们十分珍视李贽的《焚书》。“公安三袁”自此以卓吾为师,而他们兴起的性灵派文学思想无疑深受卓吾之学的影响。至于“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在晚明文化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已有众多析论,兹不赘述。而亦因此故,笔者以为,李贽长期生活、讲学于楚,使“楚中王门”发展至高峰并形成全国性的深远影响。至于发生在荆楚之地的耿、李论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谓:定向“因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故每每以实地为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带水,于佛学半信半不信,终无以压服卓吾。乃卓吾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唯先生与江陵(张居正)厚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先生之讲学友也,斯时救心隐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表面看来,是由于对待禅学的态度导致了耿、李反目乃至论争,而实质乃是维护文化专制与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的歧异。这是晚明思想界格外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论者多有研析,限于篇幅,兹不赘述,要之,因为这场论争而最终导致卓吾不得不离开他本想终老并安息的麻城龙湖。这实际宣告了楚中王门的终结。至于后来卓吾进而被下诏狱并自颈于狱中,则宣告了晚明阳明学派讲学运动的落幕。
【注 释】
《明儒学案》卷二十八《楚中王门学案》,上册,第6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九《长沙答周生》,第6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说“或许是急着走马上任之故,这次阳明没有再住长沙”,但据《王阳明全集》卷十九《三山晚眺》,他这次由贵阳往庐陵赴任途中,还是到长沙,并在鹅羊山道院住了一晚的。
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552-5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5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第13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四《与辰中诸生》,第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六《年谱·附录一》,第13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七,第397页,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第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第194页,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刘球《皇明泳化类编》卷四十五《王阳明先生》,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5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5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阳明先生行状》,第140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同上,第1408-1409页。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夜泊江思湖忆元明》,第9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睡起写怀》,上书第9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姜广辉:《主静与主敬》,引见姜氏《理学与中国文化》第3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王兴国:《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湖南的活动情况略考》,载《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第7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门人王嘉秀实夫、萧琦子玉告归书此见别意兼寄声辰阳诸贤》,第7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嘉秀尤精擅画山水,阳明《题王实夫画》:“随处山泉着草庐,底须松竹掩柴扉。天涯游子何曾出?画里孤帆未是归。小酉诸峰开夕照,虎溪春寺入烟霏。他年还向辰阳望,却忆题诗在翠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第739页)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八,第2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吴光等編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2---26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7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37-2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阳明其时多以“立志”诫勉弟子,如其弟守文来学,亦“告之以‘立志”,曰:“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劳苦无成矣。……”(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9页)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第9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7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23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引见杨正显:《王阳明佚诗文辑释》,第24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与郭善甫》,第9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卷十三,第53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关于此事,《传习录栏外书》亦有记载,参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5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第1308页,南京:鳳凰出版社年2007版。
转引自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1512-15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八《书朱守乾卷》,第2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28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吴光:《论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引见《国学新讲-吴光演讲录集粹》,第397---39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第196-197页,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第193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4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吴光等:《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第94—9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东廓邹先生文集》卷二《虔州申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册65,第620页。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答方三河》,20页下,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三《答王仁仲》,4页下,明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与林子仁》,第14页下,民国元年袁承业编校本。
《林东城文集》卷下《答林巽峰》,民国九年海陵丛刻本。
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八《政学合一说》,第195-196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卷八《汉滸订宗》,上册,第30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卷四《与李卓吾·一》,上册,第162、161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卷四《与李卓吾·三》,上册,第16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
傅秋涛点校:《耿定向集·附编五》,下册,第906-90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
《袁宏道集笺校》,第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一五。
《袁宏道集笺校》卷五《李宏甫》。
责任编辑:郭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