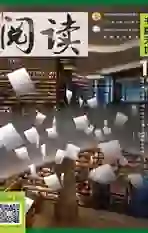第三件毁了我父亲的事
2020-04-06雷蒙德·卡佛
〔美〕雷蒙德·卡佛



我父亲这辈子有三件事让他很受打击。第三件事是傻蛋,傻蛋死了這件事。第一件事是珍珠港事件。第二件事是搬到温纳奇附近我祖父的农场,我父亲在那里结束余生,虽然他的余生或许在这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我父亲把傻蛋的死这件事怪罪到傻蛋的老婆身上,然后他怪罪鲈鱼,最后他怪罪到自己身上,因为是他把《田野与溪流》杂志后面的那张广告拿给傻蛋看,上面写着他们可以运送活鲈鱼到美国各地。
傻蛋拿到鱼以后,他开始变得怪里怪气。那些鱼改变了傻蛋整个人,我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知道傻蛋的真名,如果有人知道,我也没听说过。他以前就叫傻蛋,现在我只记得他叫做傻蛋。他像个小老头,秃头,个子很矮,但手脚却很有力。如果他露齿而笑,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嘴唇会往后卷,露出黄褐、残缺的牙齿:那让他有一种狡猾的表情。当他听你说话时,那一双水溜溜的眼睛牢牢盯住你的嘴巴——如果你不是在说话,那双眼睛就会游移到别处,在你身体上打转。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聋了,至少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聋。但他的确不会说话,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不管他是不是聋子,傻蛋打从一九二〇年代起就是锯木厂的工人。这里是属于华盛顿州亚基马市的“卡萨卡木材公司”。我认识傻蛋的那些年,他是个清洁工,那些年来我从没看过他有不同的打扮。一顶毛帽、一件卡其工作衫、一件丁尼夹克、一条吊带裤。在衣服上面的口袋,他每次都放几卷卫生纸,因为他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打扫厕所并且补充厕所里的用品。这工作让他很忙,因为夜巡的工人在绕过工厂一圈后,离开时总是会在午餐盒放一、两卷卫生纸夹带离开。
傻蛋带着一只手电筒,即使他上得是白天班。他也带了螺旋扳手、钳子、螺丝起子、绝缘胶带……所有技工会带的工具。就这样,他们为此取笑傻蛋,因为他总是带了那么多工具在身上。卡尔、泰德、强尼,他们是取笑傻蛋的人里最恶劣的。但傻蛋毫不介意,我想他已经习惯了。
我父亲从不取笑傻蛋,至少据我所知是如此。爸爸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留着小平头,双下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肚子。傻蛋总是盯着那肚子瞧。傻蛋会到父亲工作的磨光室,当他用磨石轮打磨木材时,傻蛋会坐在一张板凳上,看着我爸的肚子。
傻蛋的房子和别人的差不多。
那是一间贴满焦油纸的房子,在河流附近,距离镇上约五、六英里。房子后面半英里的地方,在草坪的尽头有一个大石坑,那是州政府为了铺设附近道路挖出来的坑。原本是三个大洞,过了许多年,三个大洞都积满了水。然后慢慢地,这三个池塘就变成一个池塘。
那池塘很深,看起来很阴森。
傻蛋有房子,也有老婆,年纪比傻蛋小很多,据说曾经和墨西哥人鬼混。父亲说讲这种话的人真是爱管闲事,像卡尔、泰德、强尼那些人。
她是个矮小的胖女人,一双骨碌碌的眼睛。我一看到她,就看到那双眼睛。那次我和彼得在一起骑着脚踏车,在傻蛋家门前停下要一杯水喝。
当她开门时,我说我是戴尔的儿子。我说:“他和傻——”然后我马上改口,“噢,他和你先生一起工作。我们骑脚踏车,想来这里要杯水喝。”
“在这里等。”她说。
她两手各拿了一只小锡杯回来。我一口就喝光了。
但她没有帮我们多倒一杯水。她看着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当我们开始骑上脚踏车时,她走到门旁边。
“哪天你们两个小家伙有一辆车,说不定我可以一起兜兜风。”
她笑了。她的牙齿和嘴巴相比,看起来太大了。
“我们走吧。”彼得说,然后我们就走了。
在我们这一州,不是很多地方可以找得到鲈鱼。在一些高山溪流中大多数是彩虹鳟,一些河鳟和红点鲑,在蔚蓝湖和环石湖里还有银鱼。大概就是这些鱼,除了在秋末,有些河里会有海洋鲑鱼回游。但是如果你以钓鱼为生,这里的鱼足够让你忙的了。没有人钓鲈鱼,我认识的很多人从来没看过鲈鱼,除了在照片上。但是我父亲在阿肯色州和乔治亚州长大,他以前看过很多鲈鱼,傻蛋的鲈鱼和他有很大关系,因为傻蛋是他的朋友。
鲈鱼送来的那天,我跑去市立游泳池游泳。我记得我回家后又出门去拿鲈鱼,因为老爸要去帮傻蛋的忙——从路易斯安那州巴顿洛吉寄来的三大箱包裹。
我们坐上傻蛋的小卡车,老爸、傻蛋和我。
那三大箱包裹原来是三个大桶子,放在木条箱里。它们放在车站库房后面的角落,要我爸和傻蛋两个大男人才搬得动一只木箱到小卡车上。
傻蛋很小心地开车穿越镇上,也很小心地一路开回家。他没有停下来就直接开过他的院子,一直开到距离水塘一英尺才停下。那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所以他戴上了头灯,从座椅下拿出铁锤和工具,然后他们两个人把木箱拖到水塘边,把第一个木箱拆开。
里面的桶子用粗麻绳包捆着,桶盖上有一个铜板大小的洞。他们把桶子打开,傻蛋拿起手电筒往里面照。
那看起来像是一百万条小鲈鱼在里面游动。那真是非常怪异的景象,那么多活生生东西在里面瞎忙着,像是从火车运来的一座小海洋。
傻蛋在桶子边舀了一勺水,然后倒出来。他拿起他的手电筒,往池塘里面照,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我们可以听到青蛙的声音,但只要天色一变黑,随时都可以听到它们的声音。
“我去拿剩下的箱子,”我父亲说,然后他伸手要拿傻蛋外套上的铁锤。但傻蛋往后退,摇了摇头。
他自己一个人把剩下的木箱打开。他拆木箱时割伤了手,在木条上留下几滴褐色的血迹。
从那天晚上开始,傻蛋就不一样了。
傻蛋再也不让任何人靠近他家。他在草坪四周搭起了围篱,然后用通电的铁丝网把水塘围起来。人家说他为了那些铁丝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当然,在那件事之后我父亲就再也不理傻蛋了。傻蛋把他从水塘边赶走,并不是因为禁止他钓鱼:别忘了,那些鲈鱼还只是鱼苗而已。傻蛋把他赶走是因为不准他看鱼。
两年后有一个晚上,老爸上晚班,我帮他送饭和冰茶罐,我看到他站着和技工席德在聊天。就在我走进去时,我听到老爸说:“照他那种方式,你会以为那个笨蛋娶了那些鱼。”
“从我听到的谣言,”席德说:“他最好在他的房子周围也搭起铁丝网。”
此时我父亲看到了我,然后我看到他用眼神向席德示意。
但一个月后我老爸终于让傻蛋让步了。他的方法就是,他告诉傻蛋为了大多数的鱼着想,他必须除去一些瘦弱的鱼。傻蛋站在那里拉着他的耳朵,看着地板。老爸说,没错,他明天会去做,因为这件事应该马上办。傻蛋没有说“好”,事实上他只是从来不会说“不好”而已。他又拉了拉耳朵。
当老爸那天下午下班回家,我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我把他那老旧的假饵钩拿出来,用手指试试看锚钩坏了没有。
“你准备好了吗?”他从车子跳出来,对我说:“我去上个洗手间,你把东西放到车上。如果你想开车的话,可以让你开。”
我把所有的东西丢到后座,然后试了试方向盘,这时老爸戴了他的钓鱼帽出来,用两只手拿着一块蛋糕吃着。
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很瘦,金发盘绕在脑袋后面,用假钻发夹固定。我在想从前那些快乐的日子,她到底有没有离开家到处走走,或者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我把手刹车放下。母亲看着我推动排挡,然后还是没有任何笑容地走进屋内。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我们把窗户摇下来吹风,我们驶过莫克西桥,往西转到石板路。路的两旁是一片紫花苜蓿田,更远的尽头是玉米田。
老爸把手伸出窗外,让风吹着。他很兴奋,我可以看得出来。
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傻蛋家。他戴着帽子走出屋子,他老婆从窗户往外看。
“你准备好煎锅了吗?”老爸对傻蛋叫着,但傻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车子。“喂,傻蛋!”老爸喊着。“喂,傻蛋,你的钓竿呢?”
傻蛋前后晃了晃头,把身体重量从一只脚放到另一脚上,看着地面,然后看着我们。他的舌头放在下唇然后他把脚踏入泥土。
我用肩膀背着鱼篮,把老爸的钓竿递给他,然后拿了我自己的钓竿。
“我们可以走了吗?”老爸说:“喂,傻蛋,准备好了吗?”
傻蛋拿下帽子,然后用同一只手,在头上抹了抹他的手腕。他很快转身,我们跟着他走过松软的草坪。每走大约二十英尺,旧田沟的草堆中就冒出一只鹬鸟。
到了草坪的尽头,地面渐渐开始下坡,变得很干而且很多石头,到处都是荨麻灌木和矮树丛。我们切到右边,跟着一条旧的轮胎痕迹,穿越一片到腰部高的草丛;当我们穿越草丛时,干的蝗虫壳在草茎上嘎嘎作响。这时候,我只能从傻蛋的肩头看到湖水的反光,而且听到老爸喊,“老天,真棒!”
但傻蛋的速度慢了下来,不停地用手前后移动头顶上的帽子,然后他就停下来不动了。老爸说:“怎么样,傻蛋?还有更好的地方?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哪里钓?”
傻蛋抿了抿下唇。
“你怎么回事啊,傻蛋?”老爸说:“这是你的水塘,不是吗?”
傻蛋往下看,从他的吊带裤上挑走一只蚂蚁。
“管他的,”老爸吐着气。他拿出手表,“如果你觉得没问题,我们应该在天黑之前到。”
傻蛋把手插在口袋里,然后转身回到水塘。他又开始走了,我们在后面跟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片水塘了,不断窜起的鱼在水面掀起阵阵涟漪。不时会有一只鲈鱼从水面跳起,溅起水花再落下。
“老天!”我听到我父亲说。
我们走到水塘边一处开阔的地方,一片碎石滩。
老爸要我往前,然后蹲了下来,我也蹲了下来。他在我们面前,眼睛盯着池水里瞧,当我看着水面时,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做。
“老天!”他轻声地说。
一群鲈鱼在游着,二十、三十只,没有一只小于两磅。它們转了一圈,然后改变方向又游回来。池里面挤得不得了,它们像是彼此在互相推挤似的。我可以看到它们游过时,厚厚眼皮的大眼睛看着我们。它们一下游开,然后又游回来。
那是它们自找的,不管我们蹲下来或站起来都没有差别,那群鱼根本不在乎我们。说真的,那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我们在那里坐了一阵子,看着那群鲈鱼天真地游来游去,从头到尾傻蛋都在拉他的手指头,四周张望好像在等某人出现。在水塘里到处可以看到鲈鱼游到水面上吸气,或跳出湖面再落下,或露出背鳍靠近湖面游来游去。
老爸用手势比了一下,我们站起来准备钓鱼。老实说,我因为兴奋都发抖了起来,几乎没办法把鱼饵从钓竿的鱼漂儿上拿下来。当我准备拿出鱼钩时,我感觉到傻蛋的大手抓住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傻蛋用他的下巴朝老爸的方向指了一下。他表达得很清楚了,只准用一根钓竿。
老爸把帽子拿下来又戴上,然后走到我站的位置。
“你继续,杰克,”他说,“没关系,儿子——动手吧。”
我拿出钓竿之前看了傻蛋一眼。他的脸变得很僵硬,下巴上有一条细细的口水痕。
“如果它想挣脱,收线时要用力。”老爸说,“这些龟孙子的嘴巴很硬。”
我把线轴转松,然后手臂往后挥,我挥了整整四十呎远。在我还没来得及收线之前,水面就开始动了。
“用力!”老爸叫着,“用力!逮住它!”
我用力往后拉,拉了两次。我钩住它了。钓竿向下弯,来回不断震动。老爸一直叫喊着。
“放松!放松!让它游一下!放多一点线!现在收线!收线!不好,放松!太棒了!你看看!”
那条鲈鱼绕着水塘舞动。每次她跳出水面,就使劲地甩着头,我甚至都可以听到鱼饵震动的声音,然后它又继续游。我一次又一次地让它筋疲力尽,让它越游越靠近。它看起来很大,大约六磅或七磅。它侧躺着挥动着尾巴,张大着嘴,鱼鳃一张一合。我觉得膝盖发软,几乎都站不稳了。但是我把钓竿拉了起来,收紧钓线。
老爸走下水塘,水面超过他的鞋。但是当他捉住那条鱼时,傻蛋开始咕咕哝哝,摇着头,挥着手臂。
“你到底怎么回事,傻蛋?这小子钓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大的鲈鱼,他才不会把它放回去,想都别想!”
傻蛋仍然继续朝着水塘指手划脚。
“我不会把这孩子的鲈鱼放回去!你听到了吗,傻蛋?如果你以为我会那么做,那你就错了。”
傻蛋伸手要拉我的钓线。此时,那条鲈鱼又恢复了一些力气。它翻了身又继续游。我大叫一声慌了手脚,开始卷线。那条鲈鱼最后一次奋力想游走。
就在这时,钓线断了,我几乎摔个四脚朝天。
“拜托,杰克,”老爸说,然后我看到他拿起他的钓竿,“拜托,该死的笨蛋,看我怎么逮住它!”
那年二月河水涨洪。
十二月的前两个礼拜降雪很大,到了圣诞节变得非常冷,地面都结冰了,积雪还在。但到了一月底,西南风开始吹起。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强风猛吹着房子,潺潺的水声从屋顶传下。
强风吹了连续五天,到了第三天,河水上涨了。
“已经涨到十五英尺了,”有一天晚上我父亲看着报纸说,“还差三英尺就要淹水了,老傻蛋的宝贝要泡汤了。”
我想去莫克西桥看看河水到底涨得多高,但我老爸不准我去。他说洪水没什么好看的。
两天后河水溃堤,然后开始消退。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上,欧林、丹尼和我骑脚踏车到傻蛋家。我们把脚踏车停下,徒步穿越傻蛋家旁边的草坪。
那天的天气阴湿,风很大,被吹散的乌云在天边快速移动。地面还有点湿湿软软的,我们在草堆里一直踩到小水洼。丹尼才刚开始学会骂脏话,每次一踩到水洼,他就把刚学会的所有脏话都骂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草坪尽头的高涨河水,水位依然很高,而且河道也改变了,河水绕过树干,吞没了河边的土地。在河的中央,水势又大又急,有时候还看见一团树叶或一株树从河面上漂过。
我们走到傻蛋的铁丝网旁,发现一头母牛被缠在铁丝网上。她的身体肿胀,皮肤看起来又亮又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死尸。我记得欧林拿了一个树枝,戳了戳她睁开的眼睛。
我们沿着铁丝网走到河边,我们很怕靠近铁丝网,因为担心它可能通电。但是当我们走到一条看来似乎很深的河道旁时,就没有铁丝网了。路到这里变成了河水,铁丝网也没入水中。
我们跨了过去,沿着这条新河道走。这条新河道直接穿入傻蛋的土地,直通到他的水塘,流入水塘,又从另一头钻出一个出口,然后蜿蜒前进与更远的那条河汇合。
不难想象傻蛋的鱼多半都被河水带走了,就算没有被带走的,现在也可以自由进出。
然后我看到了傻蛋,看到他着实让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告诉另外两个家伙,我们全部趴下来。
傻蛋在水塘的另一头,靠近水道的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我从没看过这么哀伤的人。
“我真替老傻蛋难过,”几个星期后,老爸吃晚餐时这么说,“虽然那家伙是自找的,但还是没办法不担心他。”
然后老爸开始说,乔治看到傻蛋的老婆和一个墨西哥大个子坐在酒吧里。
“还不止这样呢——”
母亲用锐利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然后看着我。但我只是继续吃饭,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老爸说:“该死,碧雅!儿子已经够大了!”
傻蛋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了很多。他再也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没有人想开他的玩笑;自从上次因为卡尔把他帽子弄掉,他拿着木棍追赶卡尔之后,就没人想开他的玩笑了。但最糟糕的是,傻蛋现在每个星期总有一二天没来上班,工厂有谣言说他被资遣了。
“那家伙快要完蛋了,”老爸说,“如果他再不小心点就会疯了。”
然后就在我生日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老爸和我在打扫车库。那天的天气很暖,飘着风,空气中可以看得到灰尘悬浮着。母亲走到后门说:“戴尔,你的电话,好像是维恩。”
我跟着老爸进房里洗手。当他讲完话后,把话筒放下,转过身面对我们。
“傻蛋他,”老爸说,“他用铁锤杀了他老婆,然后自己淹死了。维恩刚从镇里听到的消息。”
当我们抵达时,到处都停满了车。通往草坪的大门敞开着,我看到轮胎痕直直通往水塘的方向。
纱门被一只箱子顶着半开着,门口站着一个干瘦、扑克脸的男人,他穿着松垮长裤、运动衫,戴了一支手枪皮套在肩膀上。他看着老爸和我走下車。
“我是他的朋友。”老爸对那个人说。
他摇了摇头。“我不管你是谁,除非你是警察,否则全都得离开。”
“找到他了?”老爸问道。
“他们正在拖出来。”那个人调整了一下他的枪。
“我们过去看看可以吗?我和他很熟。”
那人说:“你可以试试看,但是他们会赶你走,别说我没警告你。”
我们穿过草坪,走的路线和那天来钓鱼时差不多。水塘上有一些汽艇,一些废弃物漂浮着。先前涨起来的湖水已经吞没了地面,冲走了树木和岩石。两艘船上都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们来回划动着,一个人驾驶船,另一个人拿着绳索和钩子。
救护车就在我们钓鲈鱼的碎石滩上等待着。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背靠着车,抽着烟。
有一艘船熄火了,我们都抬起头。船后面的那个人站了起来,开始拉他的绳子。过了一会儿,一只手臂浮出水面,看起来钩子已经钩住傻蛋的侧面。那只手臂沉下去,然后又浮起来,跟着浮起来的还有一大堆东西。
那不是他,我在想。那是别的东西,已经在里面好几年了。
船前的那个人走到后面,两个人一起把那个滴着水的东西拖到船边。
我看着老爸,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好笑。
“女人,”他说:“杰克,这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
但我觉得老爸并不是真的相信他说的,我觉得他只是不知道应该责怪谁,或该说些什么。
就我看来,在那件事之后,父亲的日子便越来越差了。就像傻蛋一样,他也变了一个人。那只在水塘上上下下的手臂,就像和好事说再见,向坏事招手。因为自从傻蛋在那座黑水塘自杀以后,日子就千篇一律了。
朋友死了以后,就是这样?他把厄运都留给朋友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珍珠港和回到祖父家这两件事,对我老爸一点好处也没有。
(摘编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一书)
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 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并被誉为“新小说”创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