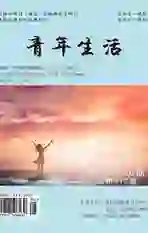国家认同的情感模式
2020-03-28吴浪
吴浪
摘要:情感模式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有效地运用在灾难的处理之中。灾难在认同的图景中是戏剧的再现。情感模式在灾难中发挥着在空间上的情感动员、时间上的追忆与再现以及灾难叙事上的情感教育作用来深化国家认同,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
关键词:情感模式;国家认同;灾难
一、问题的提出
认同问题是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说,其重要性体现在现代国家的成长必须要克服认同性危机,否则不足以称之为现代国家[1]。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就面临着认同危机的挑战不容忽略。然而,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是伴随着国共两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成长起来的,并且是以中共夺得了政权建立新中国为现代国家确立的节点。同为列宁主义的现代政党,在革命的动员问题上却分享着不同的工作模式。在以往的历史-结构研究的基础上,裴宜理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时指出:国共两党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是大于其差异性的,而在唤起普通群众的情感上,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革命过程中的激进理念和形象要形成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不仅仅需要外部的结构性因素作为支持,更重要的是,领导者何以在追随者身上实施情感工作,以将革命的宏图现实化,这一有效性的工作模式被称之为情感的工作模式。在裴宜理看来,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2]
革命的情感动员经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之中仍然被延续,既是历史-结构上的路径依赖,也是在面对改革后日益壮大的社会自组织性发展的有效回应手段。在获得政权以后,领导者与追随者两者都在新的国家里面获得新的合法身份,追随者成为新的国家的现代公民,而如何将具有破坏性的革命激情组织为建构国家认同的力量,则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情感是比政治性意识形态更为广泛与普遍的因素,它是每一个人形成认同的基础,而将认同塑造为国家认同则意味着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当中,始终需要关注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革命时期情感模式主要是把人们组织起来,以团结的方式进行斗争,而在新的历史建设时期,自然灾难(外部的强大的敌人)同样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感模式发生作用的契机,对于灾难的处理将重新演绎为一种“戏剧”。本文试图在指出情感模式作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建构方式,并结合一个关于自然灾难的案例,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认同的情感模式。
二、国家认同与情感模式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认同的范畴,而政治认同则要回答身份政治的问题。身份认同是构成稳定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身份认同是比较稳定的,基于具体角色的自我理解和基础[3]。现代国家认同是个体在接受、参与并分享国家制度体系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国家制度体系及其决定的自我身份(公民身份)的认同[4]。然而,认同本身就具有多重性,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认同才能发挥作用。现代国家对于认同危机的解决并非是要摧毁地域性的或者族群性认同心理,而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其形成对于新的、共同的独特对象所形成的认同。国家认同整合了多元的个体认同,帮助个人在国家事务上形成统一的选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则是以将民族主义比作一个“特殊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成“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5],这一范式也主导着人们对于现代国家思考的认知图景,即国家认同是通过组织力量塑造公民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对于建构国家认同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它超越了内部的多样性,为生活方式不同的公民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可感知的统一性,因而可以为具有多种身份的公民提供共同的认同对象;二是它表明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标志,能够使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明确区分开来,所以,一个国家的公民可以基于此形成独特于其他国家公民的国家认同;三是国家的整体性特征相对稳定,能够为保持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供一种情境化的基础。其实,个人就是在对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形成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将国家的整体性特征内化为个人心中的一种认同信念,即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国家认同[6]。
三、自然灾难:情感模式的切入点
长期以来,灾难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会内部本身的问题。2001年,克雷普斯对灾难提出新的定义:“灾难是在社会内或较大社会子系统内(比如地区或者社区)发生的非常态事件,这些事件来自于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受到损害和干扰的综合作用”[7]。灾难发生的地点以及灾难发生之前与之后的时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域,它不仅为国家及其组织提供特定的话语空间,而且还可以成为政治资源为国家及其组织所利用。然而,這一模式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是谁”的回答,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每一次灾难化的叙事其本身乃是对于国家认同的回应。这一模式在以下三个维度呈现出其特性。
1.空间上的情感动员
国家认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于灾难的叙事层面,在最实际上人员物资的调配之上体现出了跨越空间的情感动员。这一空间内划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政治空间,这些救援的主体则被报道二分为官方—民间,自发—动员的两类。一是代表国家意志的解放军战士奔赴第一线,形成庞大的救援景观;二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救援组织,被“众志成城”所鼓励和引导。灾难总是发生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受灾的也是特定的人群。然而,对于救灾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被一体化的救援者。在抗灾之中,构成了一副整体化的救灾图景。不同地域的人在地域上是不同的,却因相同的情感而结为一体,而这个一体化最终会指向国家。国家的意志作为引导者和督促者,既成了地域互助的原因,也成了地域互助的结果。
2.时间上的追忆与再现
作为政治认同的国家认同必须要面对的解释过去的问题,而人们对于灾难的记忆又相对容易遗忘。“一个人对事件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延续的意识,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对该社会制造的这种延续之形象的意识。”[8]故而,不断地再现和重复对于灾难的某些特征,也成为获取国家认同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是试图唤起人们的情感,把一种集体式的、过去的情感内化到个人的情感结构之中。一方面它是对于集体记忆的追溯以来加强对于政治体的认同,但更进一步,这种关于灾难的追忆与再现更是服务于未来的。我们只有在一个统一的记忆框架之中,才能获得对于预期的统一的期许。
3.叙事中的情感教育
媒体作为灾难叙事的讲述者和建构者,却是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来进行的。媒体的叙事策略,乃是对于国家意志所需要达到的对于情感教育理念的具体化体现。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媒体的灾难新闻生产呈现出感动模式和问责模式的分野,在具体的事件场景中,二者还形成竞争和博弈关系。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迁,在“多难兴邦”话语和维稳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感动模式”已逐渐占据主导位置,并固化为“悲情”和“英雄”两种叙事策略。而对于马航MH370事件的回应,更加能够看出这种模式被运用到极端化的体现[9]。
四、结论与讨论
国家认同所展开的问题是纷繁而复杂的,本文试图从对于自然灾难的处理视角上来理解情感模式在其中在空间上的广泛动员,时间上的记忆与再现以及叙事的情感教育,最后导向国家认同的这一价值基础。对于灾难的处理是把私人化的情感公共化的处理,最终的结果则是将其政治化成为一种更深厚的内含于国家认同的情感。
面对如今高发的社会风险,私人化的情感的公共化潜能具有爆炸性。如何在分疏的情感之中建构统一的认同如同“与恶龙缠斗过久”。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现代国家在维系统治基础依据其强大的公共管理职能实现。情感模式只能作为深化国家认同程度的方式,而非认同的基础。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应是以提升其公共管理职能为目标。
参考文献:
[1][美]鲁恂·派伊:《政治发展的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裴宜理:“重訪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方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8辑.
[3]阎小骏:《当代政治学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4]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第27页.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7]转引自 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5期,第114页.
[8]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黄月琴:“‘心灵鸡汤与灾难叙事的情感规驯——传媒的社交网络实践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5期,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