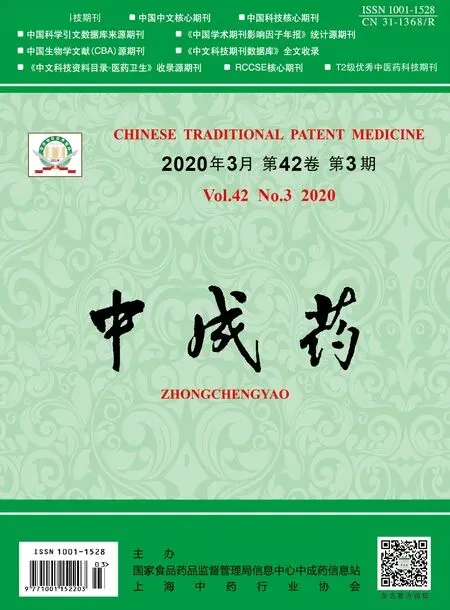逍遥散过度应用情况分析
2020-03-27晔胡
熊 晔胡 琛
(上海中医药大学门诊部,上海201203)
1 背景调查
1.1 文献 2016 年,梁 媛等[1]基于CNKI 数据库,对2005 至2015 年有关逍遥散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共发现2 940 篇,并且呈上升趋势(图1),学科领域中以精神病学最多,其次为消化系统疾病、肿瘤学等。仅2017 年相关文献就超过400 篇,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耳鼻喉科、神经科,以及精神代谢、心理、亚健康等各领域学科病种达57 种,可见具有一定广度,并已形成系统性,对后续研究有很强的拓展潜力和空间,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同时也看到了逍遥散目前应用的局限性和滥用性。很多临床研究仅定位于治疗“肝郁脾虚证”一环,不能体现甚至误导“和法”的临床价值[2];同时又有大量研究仅针对某一类明确诊断的疾病进行治疗,甚至没有体现任何辨证论治的过程,停留在单一辨病层面,脱离了整体观念[3-5]。

图1 2005 至2015 年有关逍遥散文献的分析
1.2 药品说明书 以某厂逍遥丸说明书为例,适应症及主治栏中标注“疏肝健脾,养血调经。用于肝气不舒所致月经不调,胸胁胀痛,头晕目眩,食欲减退”,可见“肝气不舒”在无形中成为了该方仅有的“标签”。临床应用中但凡遇上肝郁气滞之证,甚至只要见到情志不畅、心烦不舒者,即用逍遥方治之,所谓“用其名而未用其方是也”。实际上,应用逍遥方时仍应在精准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分清标本缓急,从而发挥该方真正的作用。
2 经典考据
2.1 “用”逍遥方的广泛应用并非近现代才开始的,清代高鼓峰在《医宗己任编》中就指出:“逍遥,治肝胆两经郁火。无论六经伤寒,但见阳症悉用此方;妇人郁怒伤肝致血妄行,赤白淫闭……俱宜此方,风以散之,此方是也。”
2.2 “不用”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第五十五篇《肝郁用逍遥散论》中写道:“今人见肝郁,佥用逍遥散,效者半,不效者半,盖不知有仲景新绛旋覆花汤、缪仲淳苏子降香汤之妙也。盖经主气.直行,属阳.逍遥散中之柴胡,直行,为纵;络主血,横行,属阴,新绛等汤专走络,横行,为横。治肝宜横而不宜纵,盖肝之怒气直冲上行,岂可再以柴胡直性上行者助其势乎?其间有见功者,肝喜条达故也,或有阴邪伏陷故也。肝主血.络亦主血,同类相从,顺其势而利导之,莫如宣络。再肝郁久则血瘀.瘀者必通络,岂逍遥散气药所能治乎!”
2.3 “用与不用”高氏以“肝胆两经郁火”为辨证要点——用则郁火散,不用则阳症不除;吴氏认为,在“治肝宜横不宜纵”的治法比较中主气则用逍遥散,主血则宜宣络[6]。由此可见,“用与不用”的选择在于精准辩证,以及脏腑、病证、用药的属性,这才是属于中医药特色的精准医疗。
3 方论
公元1078 年,逍遥散诞生之初——逍遥散方首见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第九卷之治妇人诸疾中第13 篇方剂,原文为“逍遥散治血虚劳倦,五心烦热,肢体疼痛,头目昏重,心忪颊赤,口燥咽干,发热盗汗,减食嗜卧,血热相搏,月水不调,脐腹胀痛,寒热如疟;又疗室女血弱阴虚,荣卫不和,痰嗽潮热,肌体羸瘦,渐成骨蒸。甘草(微炙赤)半两,当归(去苗,剉,微炒)、茯苓(去皮,白者)、芍药(白)、白术、柴胡(去苗)各一两。上为粗末。每服二钱,水一大盏,加烧生姜一块(切破),薄荷少许,同煎至七分,去滓热服,不拘时候。煎服”
不难看出,逍遥散之创方本意并非如今教科书上的和解肝脾方剂,由于证属“血虚劳倦”和“血弱阴虚,荣卫不和”,故治在血在阴,并被列于《第九卷之治妇人诸疾》中,专用于妇人阴血虚证。原方借用《逍遥游》“借力”之说,仿效《伤寒》炙甘草汤,以炙甘草(国老)为君——益气健脾,生血养心,不用人参而借当归之力——生血,而非补气,借茯苓白术之力——健脾养血,至此方已成,功已备;更妙在又借白芍柴胡之力——敛阴疏肝,引药入经渗络,使肝得以柔,血得以藏,并使血有归处,补无后患;再借煨姜薄荷柴胡之力——温凉,入里透表,以解如疟之寒热,羸弱之骨蒸,进而入营,出而达卫。最后,君之炙草统调荣卫。全方药药相扣,相借为用,贵在温凉施补,无攻伐之弊,故后世称其为“妇科圣药”。
4 后世应用
后世应用逍遥散并未受限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如妇科经典《妇人良方大全》和《傅青主女科》[7]。
4.1 古代 南宋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大全》中善用逍遥散,应用该方或加味方就达123 处。施用时惯与归脾、八珍方合用,而且常朝用归脾,夕用逍遥[8],可见此时医家已意识到逍遥散在用法上有气血之别;明代《傅青主女科》中鲜有使用逍遥散这一“妇科圣药”,仅“青带”一篇使用该方加减治之,并明确提及“夫逍遥散之立法也,乃解肝郁之药耳”[9]。从《妇人良方大全》到《傅青主女科》,这600 年之间的转变即是中医对“郁证”“和解剂”的认识演变[10]。以和解之法解肝郁之证可追溯到东汉《伤寒论》,而金代成无己则首先从理论上提出“和法”[11],清初汪昂著《医方集解》首纳逍遥散为和解剂用以退热调经[12],但此时和解之法尚未完善,直至50 年后程国彭撰《医学心悟》才首次明确“和法”概念[13]。
4.2 现代 经过历代医家临证摹方,对逍遥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立法之初,这不仅丰富了方证,扩展了治疗领域,更使该方灵活运用于临床,并被广泛接受。时至今日,逍遥散其证被总结为由肝郁血虚导致肝体失养;脾弱不运,气血生化乏源;木不疏土,引起土壅木郁,适用于肝郁血虚脾虚证,方中柴胡为君药,疏肝解郁;当归、白芍为臣药,养血柔肝;白术、茯苓、甘草、烧生姜、薄荷均为佐药,其中白术、茯苓、甘草益气健脾助运,烧生姜温胃和中,薄荷助柴胡疏肝而散郁热,诸药合用,气血生化有源,气机调畅,本方肝脾同调,以疏肝为主;气血兼顾,以理气为重。
5 医案分析
若认为逍遥和法因药性平和,调和表里,便可以肆意滥用的话,则完全不符合中医提倡的辨证施治。
5.1 不效(2 则)案一[14]:一女子因正值经期与他人发生口角后,月经闭止,诊断为肝郁化火,治以加味逍遥散加减,。3 剂后,病情似有缓和,继服病势加重,至第6剂经血如崩,面黄如纸,血红蛋白450 g/L;遂改投归脾汤加味,同时西医以输血及止血类药物。治疗3 d,血量反多,小腹剧痛,舌暗苔薄白,脉细涩,重审其证,与血瘀胞宫,寒凝不散相关,选用桂枝茯苓丸加味,1 剂后下血较多,但腹痛已止,血块减少,续服3 剂后血止经停。后改八珍汤10 余剂,又连服归脾、六味等2 个月,情志调养半年而愈,1 年后随访月经规律,余体健康。由此推测,可能与片面根据始于“郁怒”,一味补气固涩,加重血瘀滞涩,瘀血停留有关——而初服似有缓和,正应验了吴氏“有见功者,肝喜条达故也”。
案二[15]:一女子27 岁,经前腹痛,乳胀连胁,腰酸少寐,胸闷眩晕;面色萎黄,舌正红苔薄,脉缓,当时考虑其多郁,婚后3 年未孕,抑郁寡欢而起,遂从肝郁气滞着手,以疏肝解郁和血为法。但5 剂后未有转机,月水延期43 d 始潮,腹痛不减,乳胀反增,继用原方后经期错后48 d,初经行腹痛外,又见口干不多饮。经进一步询问病史,乃知其母现已72 岁高龄,患者年近三七天癸方至,系先天不足,腹痛悠悠喜按,得热熨则适,故修改原先诊断为先天不足,精血亏耗;肝体损于前,用亢于后,法宗滋水涵木。四诊时汛期仅错后19 d,量仍少,但腹痛减半,乳胀仅1 d,遂效方大其制。五诊时月水延期8 d 而潮,腹痛乳胀几近于无。7 个月后,据无不适故停药,后得知其停经64 d,厌食泛哕,经查为早孕,乃妊娠恶阻。
观误治之例,不乏为女子多郁的“俗套观念”所累,被经前乳胁胀痛之厥阴表象所惑,忘记了“理气需防阴伤”“香燥易化成胀”之谶,而致辨证失误之谬。
5.2 有效(2 则)不可因和法药性平和而轻视逍遥散疗效,导致仅视其为解郁手段,止步于情志调养,而不解躯体病症。
案一[16]:一男子39 岁,因勃起不坚伴早泄,甚至不能勃起,服用温肾壮阳之右归汤加减近半年,初服改善但早泄频发,近1 个月来不能勃起而不能完成性生活,性欲正常,因妻子时常埋怨而心情压抑,无腰酸腰痛,喜叹息,头晕口苦,胸脘不适,食少便溏,舌质红、苔薄白,脉细弦。病属所愿不遂,肝气不舒,气血郁滞,宗筋失养,而致阳器不用。治以疏肝理气,调和气血,佐以益肾。治以逍遥散加减,3 个月后性生活正常,精力充沛而停药。
案二[17]:一女子24 岁,妊娠60 d 阴道出血,诊断为胎漏,用寿胎丸化裁。3 剂后,流血未止,少腹胀痛,方知此乃激经误治之坏病,治以逍遥散加减。5 剂后,腹痛已除,出血全无。后足月分娩一男婴,体健。
由此可见“和法”作为“八法”之一并非虚有其名,逍遥散也并非可有可无之方。
6 辨证论治
应用逍遥散时可解肝郁脾虚,亦可养血调经,除烦去(气分)热。用以补养肝体而调肝用,健脾利湿,化生气血。
6.1 适应证
6.1.1 肝郁血虚脾弱证 血虚不养肝者,可用;脾虚而致肝郁者,可用;情志不畅而肝独郁,或致土虚血少者,可用;
6.1.2 半表半里证 半表半里或热在气分有欲陷里者,可用;气郁化火未入血分,腹痛得矢气减者,可用。
6.2 非适应证 但凡非“6.1”项下适应症所诉,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肝郁血虚脾弱证者,或久病兼有实证者,皆应慎用。
6.2.1 逍遥证为标(即假逍遥证,应治本求因)非凡肝郁者皆可用逍遥方,应审因求证,精准辨证方可施治。肝郁可由多种病因引起,逍遥之力可达者,效之;不可及者,效也勿施。
暴怒伤肝者,慎用。暴怒者,气机上逆,逍遥散中柴姜薄荷均可助其升散,虽有归芍之缓、炙草之调,难免有助纣为虐之嫌。《难经》曰:“损其肝者缓其中”,故慎用。
水不涵木肝郁者,不可用。肝郁因肾阴亏虚,母病及子,而肝肾阴虚,逍遥治之,久则伤阴化燥,变为坏病。《难经》曰:“损其肾者益其精”。
阳郁不达之热厥,非肝邪犯脾之四逆证,不可用。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一味疏肝理气,厥阴太阴之外无以解之。
肝脾不和之腹痛下利等症,不可用。此乃脾虚致木乘,肝旺克脾土,脾之升降失司。治宜抑木扶土,法当痛泻要方。
6.2.2 兼有实证者 邪在肌表未入少阳,或已入里,阳明热盛者,不宜和解。肝脾未及,不宜和解。在肝在络者,慎用。
气滞不通,胸腹胁痛,咽干无津,舌红无苔脉沉细者,不可用。
气失统摄,血热妄行者,不可用;湿热内蕴者,不可用。
虽无湿热内蕴,却进一步郁热,进一步血虚,或外感者,不可用。
血瘀证者,慎用;
少阳合阳明者,不可用。
气阴两虚,虚中夹实者,不可用。
气郁湿阻,湿浊壅滞,阳气升发受遏者,宜芳香、燥湿、淡渗。
肝郁气滞兼痞满闷胀食不消者,宜越鞠;兼血瘀轻症者,宜四逆;兼化热者,宜丹栀;兼寒者,宜暖肝。
邪郁少阳者,宜柴胡桂枝。……
6.3 禁忌症 阳虚不耐柴胡升疏者,禁用。
年老体弱,阴虚火旺,出血倾向者,忌用;《本草正义》中提到:“柴胡其性散……邪实者可用,真虚者当酌其量”。
7 小结
逍遥散创方一千多年来,经历了数代医家们的临床总结,该方不再局限于妇科单一领域,并被归于“和法”范畴,灵活运用于临床。当今,对逍遥散临床研究已具有数量和广度上的优势,但也应看到其实际应用的局限和过度应用。只有在精准辨证的基础上,方能发挥逍遥散药效;“用与不用”取决于四诊和参而得的病证分型,不能因其药性平和可调养无伤而随意施用。目前,逍遥散广泛应用于由肝脾本脏致病或七情内伤所引起的肝郁血虚脾弱证,症见两胁作痛,头痛目眩,口燥咽干,神疲食少;或往来寒热,或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脉弦而虚者。但对继发于心肾阴虚暗耗营血等其他脏器病证,或外感六淫邪实而引起的继发性逍遥证者,若单独使用逍遥散则只可祛标,无法治本,或无效,或病情反复迁延难愈;病久出现食湿痰火瘀等变证时,大多属实证范畴,则需慎用逍遥散。
另外,医案分析中举例的参考文献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导致其说服力和连贯性有限,但这也是全网搜索仅得的4例可用医案。由此,从侧面反映了目前逍遥散应用面虽广,但对其应用深度的研究有所缺失。
临床用药时,应严格辨证论治,审因求证;标本兼治,准确拿捏,既要辨明患者体质,也要熟悉了解药性。逍遥散用于治疗肝郁血虚脾弱证,和法虽有调和表里阴阳偏胜的作用,但不可因其药性平和而肆意滥用。《医学心悟》云:“有不当和者而和者……轻则为疟,重则传入心包……而借此平稳之法,巧为藏拙,误人匪浅”。
如今,有关逍遥散的论文(而且不限于此方剂)广泛存在过度应用的趋势,病与证分离现象严重。从《伤寒论》 六经辩证开始,精准辩证、精准治疗就一直引领着传统中医药不断前行和进化。本文在此并不是指出现代应用存在错误,而是旨在提醒大家不应忘了中医本源精准辨证施治的精髓[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