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疫疾的抗争千百年从未停止
2020-03-23肖瑶
肖瑶

油画《阿什杜德的瘟疫》
疫情席卷,城市像座荒岛。人人自危的底色之上,潜伏着恐慌与顽抗。无数人意识到那来自自然不可抵抗的力量与人类的渺小。
2020年冬春,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它身上遍布的伤痕,将成为我们反思与重建的标记。
千百年来,疫情之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字。它们以不同的学科角度、叙事手法,描绘了人类对疾病的共同记忆。以下五本书,将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疫疾在历史与当下的非常意义。
《瘟疫年纪事》
丹尼尔·笛福 著
关键词:人间百态
多灾多难的时候往往尽显人间百态。曾作《鲁滨逊漂流记》的英国作家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描绘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广泛蔓延伦敦的“黑死病”。这场1665年的瘟疫带走了超过8万人的生命,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1/5。
《瘟疫年纪事》的叙事,建立在详实而系统的数据、轶事之上。读者多数把它当作历史回忆录,而非一本非虚构小说。笛福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写了那场瘟疫的惨象,还原了疫疾中穷人和市民的迷信、恐惧、匮乏、冒险和忧戚。
伦敦市民在瘟疫到来前的反应,更像是个体对于死亡的某种认知。而瘟疫到来之初,人们开始疯狂逃亡,一切变得混乱、盲目。随着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恐惧一触即发,幸存的人面临着全面的精神崩溃,整个城市弥漫着哭泣的声音。
看到伦敦长街瘫痪、荒芜凄凉、基础设施奄奄一息,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40天,伦敦就要灭亡了。”从人到城市,都染上了瘟疫,它不仅侵入人的身体,更攻占人心。
疾病的扩散将死神的威慑具象化,它神秘莫测又令人惊骇万分、猝不及防。无形的瘟疫之手,不只伸向了人们的身体,也伸向人们的精神。当人们发现寄托于上帝和神不再管用的时候,人性的劣根开始明目张胆,罪恶开始橫行,抢夺,偷窃,甚至谋杀……
瘟疫的隐喻,从笛福的作品中延续下来。直到现在,现代大都市的芸芸众生都处在某种健康和繁荣的幻觉之中,而非带着历史的教训和记忆生活。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理查德·普雷斯顿 著
关键词:“大自然杀手”
病毒炸开人体,炸开冰山与海洋,侵蚀了整个人类社会。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采用非虚构手法,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记叙了1967年至1993年间埃博拉病毒为祸人间以及人们顽强抵抗的一段历史。该书普及了埃博拉病毒的特性、传播方式,同时,其表达方式并非以空洞的数据、高深的术语构成,而是将悍戾的血腥味溶解在了跌宕的情节中。
在作者看来,人们无法预防不可医治的病毒,是因为“地球启动了对人类的免疫反应”。人类无限的扩张和恶意的虐杀,极有可能破坏整个生物圈而导致大灭绝,但“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
因为“大自然的自我平衡的手段”,也许它正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而人类自诩为主宰世界的生灵,所欠缺的正是对生命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尊重。

《鼠疫》
阿尔贝·加缪 著
关键词:本能和良知、精神和意志
瘟疫象征着人性之恶,象征着人类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可避免的苦难。
正如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鼠疫》中小说人物塔鲁所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行为,避免把灾祸传染给别人。
起初,加缪通过神父布道之口,表达了人应当听从上帝旨意的观点。痛苦是上帝的愿望,人应从灾难中学到教益。然而,在灾难面前,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某种本能和良知可以被激发出来。主人公里厄在小说中以行动为证,对待鼠疫,本能地想要抗争;面对荒诞,不需要争辩、讨论,唯有接受,然后在接受后保持抗争,直到战胜。
人们无法预防不可医治的病毒,是因为“地球启动了对人类的免疫反应”。
自人类有历史的那一天起,瘟疫就一直在参与和改变历史。
瘟疫横行,带走大量生命。疾病固然是难以战胜的,但“荒诞是在人类的需求和客观世界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即便结果未料,我们也别无选择。精神的坍塌、肉体的放弃,都是向瘟疫低头的表现。
最后,鼠疫终于结束,城门打开,久别的人们又重逢。他们如痴如醉,忘却了身外还有世界存在,似乎战胜了鼠疫。他们忘却了一切痛苦,忘却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
死亡与时间让人们记住痛苦,却也忘记痛苦。人类循环往复的生与死,正如疫情一样来之无兆、去之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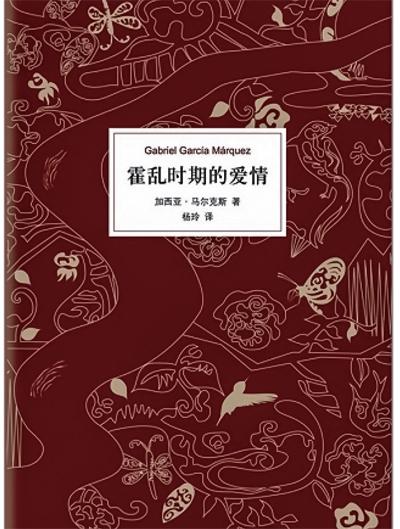
《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关键词:爱情
在马尔克斯的笔下,“霍乱”成为一种策略性修辞。他用爱情比喻霍乱,同时用霍乱类比爱情。爱情与霍乱有相似之处,令人痛苦,时间和死亡皆作为转折点,需要信心和毅力,需要“熬”。
当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时,马尔克斯用冷静、残酷的笔调,撕开爱情该有的温情、浪漫。最终,两位主人公阿里薩和费尔米纳走到一起,间隔了半世纪的拉锯徘徊,却也让这场相逢变得充满了感伤和孤独。在他们的故事里,霍乱是底色,爱情也是。而漫长的等待、难熬的思念,神魂颠倒的春去秋来,期待半生的爱情就像一场梦,甚至是一场笑话。
《霍乱时期的爱情》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更在斗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生命的宏大背景下,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疾病加重了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心理距离加大。
如果说,用医学术语来诠释疫疾过于枯燥,那么,用人人都经历过的情感来比拟,似乎更在现实主义之上添了一层理想主义。爱情与疾病,或许都让人的一生面目全非,却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意识到人类个体的微渺孱弱,意识到战争、瘟疫带来的悲惨,从而记住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并为之付出一生。

《瘟疫与人》
作者:威廉·麦克尼尔
关键词:历史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以编年手法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结合,探讨了自史前时代至20世纪前半叶间,传染病如何肆虐地球几大洲,如何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特色,又如何深刻影响文明的发源与存续。
在这本书中,麦克尼尔为解释人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角度。人类、动物和微生物都是自然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文明的进程不停止,自然生态就不会停止对人类造成影响。但这种动态又并非一种绝对的平衡,而是在平衡和失衡之间波动。换言之,自人类有历史的那一天起,瘟疫就一直在参与和改变历史,而人类的活动则给瘟疫制造了更多机会。
历史早期,生产者通过生产超过自身维生所需的谷物和其他粮食生存了下来,进而提升了其他技能,部分人参与对外战争或掠夺。这种优胜劣汰的固定模式是一种试错法,它或许的确能建立起某种平衡,然而,作为庞大自然界的一环,人类在与瘟疫抗衡的过程中必然处于弱势。
书中还提到,在穆罕默德时代,疫病不仅是阿拉伯半岛的常客,还成为了一种生活指南,促使人人接受训诫。其中,诸多严诫的核心要义之一便是:“当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但如果它就发生于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要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