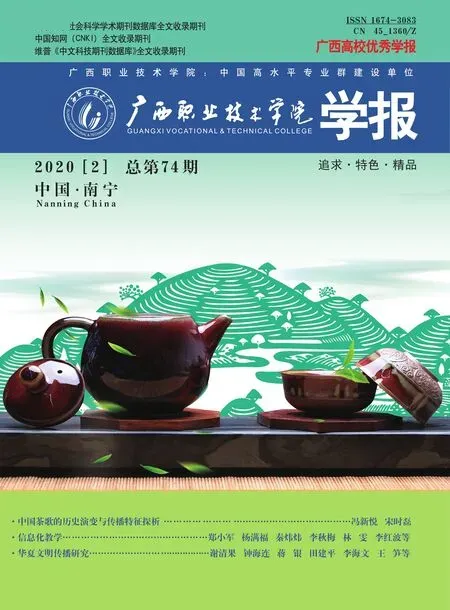论周作人对日本茶道的接受
2020-03-15高健欣
高健欣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谈起茶,绕不开自号“苦茶上人”的周作人。周作人的居住之所名为“苦茶斋”,他的散文也多与茶相关,如《北京的茶食》《喝茶》《吃茶》《苦茶》《煎茶》等,还有以茶为名的文集,如《茶话》《苦茶随笔小引》《苦茶庵笑话选序》等。1906 年,清政府派遣一批海军学员前往日本留学,周作人便是这批学员之一。留日期间,他多次在日记和文章中直言对日本的喜欢,甚至视日本为第二故乡。他颇喜欢看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也关注此书展现的日本茶道所蕴含的禅思想及文化意义。受日本茶道影响,周作人最后走向了自己构筑的独特“趣味”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化的生活。
1 茶道文化要素:对审美化生活的向往
日本的茶是从中国传入的。[1]据《日吉神道密记》记载,公元805 年,赴唐留学僧最澄和尚由中国带回茶籽,并种在京都比睿山的日吉神社,由此形成日本最早的茶园,这是日本栽种茶树的最早记载。此后“饮茶风”逐渐在日本的皇室、僧侣、上层社会中兴起,种茶、制茶、饮茶方法均效仿唐朝,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照搬《茶经》。中国的茶文化来源于平民的日常生活,而日本的茶文化却是自上而下传播的,茶道首先被当做一种高贵典雅的文化流行于上层阶级,甚至在《吃茶养生记》的影响下,日本人将茶视作养生之法,快乐之源。在上流社会的带动下,茶的需求量增加,茶叶种植高速发展,饮茶活动遂逐渐走入民间。因此,日本的茶道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日本室町时代,茶农们为了对茶叶评级,效仿中国举行“斗茶”活动。他们将从中国引进的茶道礼仪本土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茶室,这种茶室被称为书院式建筑,定期开展的茶会便成为“书院茶”。将品茶视为高尚精神活动的日本人将点茶、饮茶发展得更为精致,对于茶味、茶人、茶器、茶室这四个茶文化要素,极力追求规制上的严谨和精致,无论物件大小,一定要体现出美感,在生活的细节中追求美学性与艺术化。可以说,“日本的茶道不只是追求感官的愉悦和享受,而是通过茶让人们懂得茶的礼法,了解茶道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2]
周作人对日本茶道美学的接受可以从上述茶味、茶人、茶器、茶室这四个要素中管窥到,他在《喝茶》一文中提到了自己理想的喝茶方式与状态:“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同饮,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尘梦”[3]54,这一句话囊括了茶味、茶人、茶器、茶室这四个日本茶道所追求的茶文化要素,这样的喝茶环境与中国市井中的茶楼和茶馆极为不同,暗合了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和敬清寂”之精神。周作人不仅追求这种生活美学理想,也将这种美学理想日常化,他讲究的以茶待客方式让很多人记忆深刻。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详细地描写了与周作人在家中喝茶的情境,“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4]199-200
茶食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中茶食叫做“茶菓子”。“茶菓子”作为茶的装点而存在,不可太过花哨、甜腻而喧宾夺主,无论是味道还是形状都有仔细的考量,要与喝茶的整体氛围相融合。周作人十分赞赏日本的茶食,认为“优雅的形式,朴素的味道,很合于茶食的资格”[3]28。而对中国人喝茶时将瓜子作为茶食的做法,便觉不妥,瓜子配茶,好像将下里巴人强行融入了阳春白雪,冲淡了雅味,增添了市井气。
由此可见,在茶味、茶人、茶器、茶室、茶食五个方面,周作人都受到了日式茶道文化的影响,并认同其背后的文化美学,有意识地吸纳日本茶道文化的要素,并成为其超越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个人化、艺术化的“生活之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部分。他所坚持的“生活之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的便是这样一种超越现实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打破了审美救世的功利观念,通过审美的超越性而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以审美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生活,对现实进行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把握。
2 茶道精神:追求禅意与“苦味”的生活态度
在《喝茶》一文中,周作人以徐志摩和胡适之的茶论情景开篇。他心中的喝茶之道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人生观,即“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忙里偷闲”与日本茶道的禅意有一致性,“苦中作乐”与日本茶道的“涩味”可相互观照。
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对日本茶道进行了阐释:“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5]267可以看出,周作人从日本茶道中找寻构筑自身理想生活观的依据。日本茶道已经成为他内心所追求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理想生活观的一种来源和外化表现方式,茶道与人生之道和谐统一于周作人的人生观中。
对日本茶道进行追根溯源的禅僧荣西所著的《吃茶养生记》是日本茶道的早期文献之一;村田珠光创建“四叠半茶室”,确立“清心”的观念,从而基本形成了日本茶道[5]34-36。在此基础上,武野绍鸥提出的“茶禅一体”和千利休提出的“和、静、清、寂”等都深化了日本茶道的精神内涵,一直流传至今。茶道何以成熟于日本呢?周作人在为方纪生翻译的《茶之书》所作的序言《茶之书序》中给出了答案:“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即日本的禅僧将中国的饮茶种茶之风引入日本,将禅宗精神与饮茶方式相结合而逐渐形成茶道,追求茶禅一体,从而有别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周作人看来,禅宗之于日本茶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将日本茶道观与人生观统一起来的周作人看来,他的人生志向与文学表达也是禅宗式的,比如他在《志摩纪念》中写到:“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以心传心得境界,……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由此,周作人追求的是禅意,是心境相通、豁然开朗之感。
禅宗作为佛教的一派,主张清净寂寥,远离尘世喧嚣,禅寺和禅僧一般都幽居深山,于丛林之中求宁静,于修行中使心灵静谧,参悟人生的真谛。日本茶道便融入了禅宗幽闲静谧的精神。茶室在闹中取静,布置素朴而典雅,每一位进入茶室参加茶会的人带着“一期一会”的感情,暂时放下尘世的忧虑,坐在宁静清洁的茶室中,静待清水煮沸,看着茶师们优雅而颇显礼法的点茶姿势,体会难得的片刻宁静,体会人与人互敬与平和的情感,体会“和敬清寂”的精神境界。禅与茶道的关系正如日本著名的禅学家铃木大拙所说:“禅与茶道的相通之处,在于对事物的纯化。这种纯化,在禅那里是靠对终极实在的把握来完成的,在茶道那里则是靠以茶室内的吃茶为代表的生活艺术而实现的。 ”[5]89日本茶道闹中取静的禅宗精神与周作人“忙里偷闲”的人生观十分契合。
周作人认为日本茶道区别于中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武士之用。武士在古代日本是等级较高的阶级,诞生于战乱时期的日本茶道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阶级性,蕴含着反思乱世的沉重感。因而日本茶道所生发出的“涩味”不仅是茶之苦涩,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感,这与周作人的“苦味”“苦中作乐”相一致。
如果说,周作人前期爱喝“清茶”,可看作他对清淡闲适的生活追求,而后期对“苦茶”的热爱则体现了当他面对不完美的人生时,他要苦中作乐,追求并享受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这一生活哲学。1933 年他以“苦茶庵”替代了之前的“苦雨斋”,这一变更既表达了周作人彼时矛盾而苦闷的心境,也表明了与日本茶道颇深的渊源。“庵”承载着人隐居在独乐的小天地中对清贫而自由生活的向往,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就曾住“芭蕉庵”“无名庵”等。以“庵”代替“斋”,显示出周作人希望饮茶避世的心境。
周作人思想观和文学观出现转变是因为他提出“生活之艺术”之时,正值五四退潮期,他精心构建的“蔷薇色的梦”破灭了,这促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社会、文学等问题。这一转变是他立足于个人生命体验所进行的选择,“在饮茶中所获得的片刻精神愉悦,便成为周作人应对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并又被其提升为一种用以抵抗生活之苦的安然自在的生活态度”[6]。他不再“浮躁凌厉”,而是由叛逆走向恬淡闲适,走向自我返归;他主张贵族化的平民文学,开始大量创作平和冲淡的小品文,表现自己所喜欢的“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隐逸自由生活;他还提出了“生活之艺术”的艺术观,主张个人化的生活艺术。无论是精神态度、文学表达还是生活观,他都选择了自我回归的道路,追求恬静闲适的人生。
3 茶道美学:“平和冲淡”的自然状态
中国历史上文人骚客的生活和艺术离不开茶,“茶添话语香”“清谈煮茗不论杯”一向是文人士大夫的嗜好,诗人才子为茶吟诗作赋,使得茶文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茶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美、追求超脱世俗的怡然自得的淡泊之美、简朴平易的简约之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之美。中国的茶道美学建立在文人的主体意识之上,强调在实践中感知和领悟审美主体,实现精神上的升华。
周作人身上散发着浓郁的书生气质,他选择冷眼旁观人间世事,而非热情介入的态度与观念。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他向往“清茶闲话”的隐士生活,将“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视为人生快事。这种喝茶与生活方式,就是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的气质所现。读书、吃茶、会友、写作成为他向往的生活的全部内容。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还生动描写了周作人在北京创办《雨丝》杂志时,常常在茶馆喝茶闲话,伴清风品清茶的场景,他将其称为“语丝茶话”。
周作人终其一生,一直都在做一件事——将茶与文学打通,“我平常觉得读文学书好像喝茶,讲文学的原理则是茶的研究。”[7]126周作人爱茶,打通茶与文学的关系,以茶入文,以文观茶,话语恬淡一如清茶。
日本茶道美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茶”,强调体会自然的妙味。日本茶道从茶中确立了人生和宇宙的美学,又融入禅宗,成为一种审美的宗教。于“苦茶庵”隐居,以“老僧”自处,周作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与日本茶道的悠然自然的美学追求相一致。在日本茶道中,周作人感受到的是日本的禅宗精神,隐逸生活的情趣,自然清寂的美学,这些内容对周作人形成自己“生活之艺术”的生活观产生了影响。“读古书,看花……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写楹联,买书,考古,印古色古香的信封信笺,刻印章,说印泥,说梦,宴会,延僧诵经,搜集邮票,刻木板书,坐萧萧南窗下。”[8]28这种带有传统士大夫情调的生活方式与日本茶道的审美追求是相通的。可以说,周作人将中国传统美学与日本美学结合于一体,构筑起自身“平和冲淡”的自然审美人生观,以审美的眼光观照社会,并以之勾勒自己的理想世界和救国之途。[9]
中国茶道美学与日本茶道美学的共同点在于追求自然、和谐以达澄明的审美状态。而周作人也把“自然”与审美的结合提高到艺术本质的层次上,追求艺术本身的和谐状态。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曾如此阐述其文学观:“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10]7-8。他所说的“浑然”即是“自然”。周作人认为,“为人生”或者“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总是不自然的文学,而自然是生命的状态,是生命力的体现。通过自由与节制的和谐,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然状态,通过“任其自然”的追求,才能达到文学的“纯真”性。这实际上便是周作人超功利的“平和冲淡”的审美观的体现。
周作人将中国茶道美学的精神与日本茶道美学的精神相结合,追求“平和冲淡”的自然审美状态,更加肯定生命力的自由表现。
4 结语
“半是儒家半释家”“只欠功夫吃讲茶”是周作人的写照。由“清茶”到“苦茶”,由儒士的积极入世到“厌世”再到回归本初,重视生活与内心的安宁,周作人茶文化观的转变与他人生轨迹的变化是一致的。周作人对日本茶道充满兴趣,从日本茶道中,周作人吸收了“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观与审美情趣中,形成了自己“冲和平淡”的文学气质,使其在繁华中保持着一份孤独者的气质和精神。
周作人对日本茶道的接受和研究为我们了解周作人的文学转变与人生轨迹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研究近现代中日的文学关系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