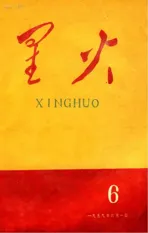暂居者漫记
2020-03-13李晓君
○ 李晓君
在雨季
在雨季,贤士花园像一条船,陷落在连绵的雨水中。记得苏东坡写过:“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这里是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属于“夏炎冬寒”的典型城市。与东坡先生贬谪的湖北黄冈气候差不多。雨季闷热、潮湿的天气给南方人带来了烦恼。湿漉漉的地面、墙壁,拧得出水来的家具,雨后无尽生长的霉菌,深受其害的电器,以及永远不得晾干的衣物,让人不断诅咒这天气。贤士花园作为老城区旧建筑群,仿佛这样一幅图景的代言人,雨季给人带来不便和烦恼的一切,它都有。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一个电影观众,或小说读者,南方的雨季可能是某种诗情画意最集中的体现,是南方世俗民情,特别是在一些小城市,生动而浪漫的布景。南方人精致的生活、邻里之间的人情世故、友善温暖的诸多细节和景致:小心翼翼地撑着伞在街巷行走、放学的孩子顽皮地踩水、苍老的巷子窗棂上青葱翠绿的植物、阿婆背着竹篓跨过拱桥、英俊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在雨中疾驰、咖啡馆里一双细嫩修长的手搅拌热气腾腾的饮品、邻居递过来一把香葱茴香、鱼儿在小溪里欢快畅游、二哈明亮乌黑的眼睛、楼上的钢琴声、招牌上乌亮的仿宋体字、校园围墙外疾走的年轻夫妇、汹涌的城市内河、焕然一新的柳树、一个女作家笔下的文字—“南方那种与自然和群体关系密集的居住结构,让生活十分便利,让人保持对季节以及细节的兴趣。那时他们做什么都是喜气的,即便喝一碗绿豆汤,也会由衷地赞不绝口。对食物有着格外细腻热诚的心意……”(安妮宝贝)—所有这一切,与居住在贤士花园里的居民所感受到的:由于潮湿,墙纸从墙上脱落下来,下水道驱之不散永远难闻的气味,电视机一经打开朦朦胧胧泪眼婆娑的画面,因积水而停留在单元门口心急如焚的上班族,在雨中滑倒的电动车—诸如此类,似乎隔着两种画风,不在地球的同一个区域。
没有谁比一个居住在贤士花园里的老太太对雨季更有发言权。雨,形成了她们性格中的一部分,影响了她们的口音、味觉,深入到她们的作息习惯和内心世界。雨水加重了建筑物的重量,对于那些阔叶植物、香樟树和竹类来说,同样如此。在雨季,贤士花园的人说话的声音都是“嗡嗡”的,舌头仿佛在青苔上打滑。橡胶套鞋成为又憎又爱的对象。伞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有人站在地铁、学校、商场门口兜售雨伞(20元一把)。少女们开始忧愁头发。人们从雨中钻出来,来到商厦屋檐下,跺着脚,互相尴尬地一笑。这是适合吃米粉肉的季节,某种绿色蒸制食品(青团)开始上市。没有谁比大街上的清洁工更怨愤这季节—满街香樟树开始落叶子,推陈出新,不知不觉中树冠已被刷了一层绿漆似的—翠绿得让人不敢相信,黄黄绿绿的叶子落得满地都是,它们粘在地上,在雨中、风中,病毒似地到处扩散。大街上,没有哪一刻,会比现在显得更加混乱。潮湿的空气又闷热又寒冷,“二四八月乱穿衣”,收进衣柜的厚衣服又被翻出来,也有人穿着短袖,趿着拖鞋满街乱跑,从人们的着装上来看,分不清季节。主妇们对居室的被褥、床单忧心忡忡,伸手摸进被子,湿漉漉的。建筑物的楼顶上现在一片空荡,只有满是锈迹的、冰冷的铁丝,像几道蛛网无辜地暴露在雨水中。屋顶形成了许多水洼,雨水溅落下来,开花、消逝。有时,竟然会有阳光突然从雨中照射过来。雨水加重了事物的重量,延长着寂静的时间,使人们内心的迟疑持续扩展。雨水是书本的天敌,一个读者站在青苑书店门口—手中新买的书被雨打湿,纸张黏连在一起,字迹浸泡在一片狭小的水的沼泽中—这是一本崭新的读物,这是最让人心烦的一刻,被雨水浸泡过的纸张无法再回到它挺括、光洁的过去,这忧愁加重了内心的疲倦,诚如印在书封上的文字—“超越一个人本身的疲倦,宇宙的疲倦,树上耷拉的树叶的疲倦,突然好像流动不畅的河流的疲倦,慢慢褪色的天空的疲倦”(彼得·汉德克《试论疲倦》)。
一个城市小区在雨季似乎也获得生长的力量。如同山上的竹笋,在暗中拔节生长。雨水涤荡了身上的尘埃、污垢,使窗户变得明亮,让沥青地面显得更黝黑光亮,一个在雨水中“洗过澡”的小区,像一个突然长结实了的男子,向你迎面走来—这也可能是你的一个幻觉,事实上没有比在雨水中泡过的建筑更让人觉得沉闷。雨水加速了它的衰老,在毁坏它的墙面,朽烂它的门板,让霉菌在房间内无处不在地生长。老人们拿出瓶瓶罐罐,摆满了床头、餐桌、茶几,只要一进门,就能看到。这些药丸躺在一个个玻璃瓶、塑料盒或白色长方形纸盒里,似乎在提醒她的儿女们,重视她加重的病情,为忽视对她的关心感到内疚。一颗粉色药丸摧毁了一个家庭的和谐,考验着伦理和亲情。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的母亲每到雨季肩膀和膝关节就隐隐发痛,风湿和关节炎折磨着她的暮年。她躺在14楼某个居室床上,为不吵醒酣睡中的我们,疼痛难忍半夜她自己用手撑起微胖的身躯,给肩膀张贴药膏。楼下的麻将桌早已支起来,雨季也摧毁了这项娱乐,使老人们变得更加无所事事。那些挺过严冬考验的高龄者,携带身上的病灶和日渐衰竭的器官卧在床上,轻易不迈出家门。从早到晚,他们不知厌倦地听着雨水“滴滴答答”地歌唱—那虚无的、隐形的歌唱家,从虚空处来,遁迹于虚空处。
雨季使北门后面的玉带河猛涨,像一根不堪重负的肠道在吞噬、排泄,那些从暗沟流出来的废水,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它的污浊。一些来历不明的柳枝和水藻漂浮在上面。水的刻度不断上涨,几乎快要与路面齐平(洪水退后,新砌的花岗岩上留下深重的水渍)。贤士湖新种的菖蒲和其他叶片狭长植物,全部浸泡在水中,清淤泵和增氧机在勉力工作,罗茨鼓风机将空气压到水里,几条鲫鱼浮在水边的菖蒲丛,反射着微白的光,一动不动。闷热潮湿的天气,让蚊子大面积繁殖,蛙鸣混合着雨声,在夜晚进入人们的睡梦中,带来初夏意味。雨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使踏青的计划被打乱。雨季,使一个租住于此的写作者,仿佛看到远在黄州的东坡先生,正苦于雨的烦恼,“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对一个刚刚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浪淘沙·大江东去》的豁达者来说,漫长的雨季也让他写下心灰意冷的诗句—在那诗中:被雨水污泥践踏的海棠花、白发病体、湿冷的灶台、乌鸦、坟墓—种种意象,显示出一个灰暗、颓废的形象。
雨水将逝去的时间与当下的时间连接起来,将不同的区域连成一片。甚至将小说里的时空,电影里的画面,音乐里的形象,勾连起来。雨消弭了真实与虚幻、存在与消逝、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在玛丽·雷内东笔下,雨季让“极地那冰雪和黑夜的混沌之中拔地而起的”豪华旅馆陷入了无边的沼泽地……雨水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催生出一些虚构的故事。雨甚至直接催生了一位诗人—博尔赫斯,这位盲者,他的诗歌仿佛是为雨而生的,随着雨落下,他突然看见“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雨落在一个深夜阅读者的头顶。落在宁波、黄州、格里芬、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漫长的雨季,让人仿佛进入冬眠,也让回忆终于以粗暴者的形象出现。
我的房东们
从我入住贤士花园算起,平均不到一年半时间,便有一次搬家经历。描述这些房东,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有着各自的背景、性格、情趣,虽然我与他们的交往浅尝辄止,远谈不上深入,但从一个自以为善于观察人的角度来看,大致能够对他们有所把握。频繁地搬家,可以看出我性格中某种变动不居的偏好,一定程度上的完美主义、爱挑剔、理想主义乃至易幻想的特征—总觉得会找到更好的房子。回过头来看,这四套房子其实总体上大同小异,在居住的便利性和缺陷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此,我的搬家看起来像是瞎折腾,显得有些徒劳和不切实际。
搬家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些随着时日增加的书籍、衣物、厨房用品等等,在每次搬家的时候,成为恨不得扔掉的累赘。在这期间,我们清理掉多少书籍,是不可计数的。当我面对一堆堆并非“经典”但也来自朋友的馈赠、若干场合偶然所得、一些会议活动的附赠品时,取舍往往是让人痛苦的。我总觉得某本书会作为今后的工具或资料而用,但显然,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它。更重要的是,在搬家时不可避免的负累。我的太太,是个比我干脆和豁达的人。正是她帮助我痛下决心,将那么多的书清扫出我们的书柜,使之遭遇化为纸浆或摆上旧书市场货柜的命运(如果是后者,我内心的愧疚感会轻一些)。我的一大纸箱早期发表作品的样刊,竟也在某次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这是两个高个子、相貌平整、很般配的人。两人都姓郑,而且名字最后都有一个华字,这是让我惊讶的,乍看之下,以为这是一对兄妹。我在他们的房子里住得时间最久,大概有两年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女儿初一下学期搬进这套房子,直到她初中毕业才离开。阴差阳错,女儿录取的高中,又在这片区域,我们又鬼使神差地搬回了贤士花园。基于与原房东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我拨响了郑女士的电话(在他们家庭关系中,她是主导者),遗憾的是,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我们在女儿学校周围找了一圈,临近开学都一无所获。有一天,我在单位接到太太电话,告诉我找到房子了,还是在贤士花园,让我赶过去看下以便敲定下来。这当然是后话。郑氏夫妇,都在证券公司上班,属于哪个阶层不清楚,年纪比我和太太大三岁。从房子原有的装修和格局来看,属于经济上的宽裕阶层,目前他们住在红谷滩新区(是集资房还是商品房不得而知)。这套房子他们此前租过一个客人,我们是第二个租户。显然,他们对以前的租户很不满意,那是几个南大一附院的实习生,共同分担开支,房东嫌她们不太重视卫生。这是一对职业特点鲜明的夫妇,也许工作劳累或者别的,女主显得有些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些—但那份精干、细致(伴随着轻微的苛刻)却是显而易见的。男主看起来年轻一些—他们同岁,只相差一个月,曾经是同学。不是万不得已,我们不会约着见面,那通常是家用电器坏了,或遇到什么难题非得房东出面解决。一般是女主来得多,也是来去匆匆。他们在经济上不算是很大度的人,锱铢必较,理性而严苛,虽然总体上是不错的人。他们是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培养了一个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儿子。我希望,我们家能沾上他们的好运。对这套房子,我比较满意—虽然那沙发摇摇欲坠,是个危险品,厨房和卫生间也不少毛病,电视机完全是个摆设等等,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似乎不该有太多的挑剔,我们做好了长租的准备,一些不足我们准备来逐步完善。
我一直对这对夫妇有一定好感,想来他们人缘也是不错的,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十年之久,孩子在这里读书、成长。C栋门卫看得出来与他们非常熟悉,关系很好,每次他们过来(尽管时间很短),总能看到他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攀谈。
第二个房东,始终未曾谋面。房子是太太通过中介找到的。我赶到贤士花园的时候,只有中介—一位女士,和太太在房子里。房主将钥匙留在中介手上,她是外地人—抚州临川人,不知何故,在南昌拥有这样一套房子。这是一栋八层楼高的二楼,小两室一厅,面积大约只相当于前一套房子的一半,可能不到70平米(我们之前租的房子有140平米)。但这套房子看起来装修得比前者新些,家具电器也更齐备,虽然小,但也紧凑,加上临近开学—再加上我并不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往往是这样,房子在你最急、最需要的时候,是最稀缺的,踪迹难觅;而在平时,在你不在为找房发愁时,菜市场边上的公告栏里,各个建筑物的临时招贴处,那种租房信息比比皆是。我们很快就和中介签了合同,并且住进来了。自始至终,房主未曾见面,只在电话里有过沟通。仅从电话里的交往来看,这是个厚道、实诚的妇女,一言以蔽之,是个好人。我们才住进不久,热水器就坏了,我打电话给她,她二话没说让我们找菜市场旁边的电器修理铺维修,费用从下个月的房租中扣除。我想,如果是前面那位房东—郑女士,尽管我对她印象也不错,但显然的,会有一番核实和交涉的。后来几次因为房子一些问题与房主协商时,对方都很大度,充分信任。这让我对临川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但房子的缺陷,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这时,我的母亲已经完成“保姆”式的陪伴使命,回到赣西那个小县城去了。尽管如此,房子仍让人觉得拥挤。女儿的房间,只摆下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一个小衣柜,就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写字做作业的位置也没有。我们将书桌摆放在客厅,客厅成为我们家吃饭、休息空间外,兼做了女儿书房。高中第一个学年,还不要求上晚自习,每晚女儿在客厅做作业,我则侧躺在靠窗的沙发上—用女儿的话说是“葛优躺”。太太拿着书在卧室里看。这是每晚我们家固定不变的情景。窗外,是两栋楼宇之间的平台,户外的声音纤毫毕现,以前在14楼听不到的老太太们的闲言碎语、楼下电视里的声音、狗的追逐声、风吹起地上纸屑的声音,现在如此逼真地传入耳膜—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最要命的是,那在别的小区、广场和空地都能遇到的,这些年来一种奇怪的健身运动—广场舞,每晚准时伴随着一支乐曲在窗外响起。那是一支奇怪的曲子(我不知道歌名),同时有着奇怪的旋律—现在,只要一闭上眼,那支奇怪歌曲还会在我耳边萦绕—“感觉自己棒棒哒……”那些妇女,大概七八个,每晚准时随着音乐出现。基于此,我到现在无法接受广场舞—也许那时带来的阴影太重吧。我的房东—那个隐身人,自然无法目击和感受到这一切。她是个好人,我们却无法再合作下去。
第三位房东姓刘,是位温婉的女性。我回到了C栋,那么凑巧,我从地宝网上又找到了一套C栋的房子。当我们开车把东西搬回C栋时,我看到C栋门口小卖店罗老板(我通常叫他罗师傅)惊掉下巴的神情—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不快,但仅这一次,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便终结了。我第一次住进贤士花园时,是房主带我还是自己找到罗师傅的记不清了。那时,小区没进行燃气改造,还在使用罐装煤气,我在罗师傅店里代办的煤气使用手续。每次他扛着煤气罐上来时,我们还会交谈几句。他是个热情的人,每次我们交谈都很愉快。我也时常在他店里买些小零碎。在我前次搬离这里找他要回三百元押金时,他要我拿出押金条来。这理由无可反驳,然而两年多时间过去,押金条不知藏身何处。我向他说明,他一改往日的热情,恶狠狠地拒绝了我,料想我们今后将不会再见面。我觉得他脸变得太快,有些不近情理,便忿忿地离开。
房主和我加了微信。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女士时,她穿着一件旗袍,虽然年纪与前面的郑女士相仿(从后来的聊天中,得知她也在证券公司上班),但她的风格与郑女士不同。郑女士是那种精干的职业女性形象,刘女士则带些文艺范。她会在朋友圈里晒她参加古琴学习、焚香、时装秀之类的信息,也会晒一些抄写《心经》、读书会之类的照片。她是几个房主里唯一一个称我“李老师”的人。我的微信偶尔会露出我职业特性的一鳞半爪。既然我们是微信好友,我想她多半也会关注—作为一个谨慎的房东来说,这合情合理。我们的合作关系时间不短,仅次于她的同事郑女士。我们回到了电梯房,回到了高层。我重新拥有了写毛笔字的空间,而女儿则开始了上晚自习。她拥有一个带书桌、书柜的很大的卧室,外面还有一个阳台,每天阳光会照射进来。在那许多个夜晚,我沉浸在写毛笔字中,桌上摊着一大摞字帖:《黄州寒食帖》《蜀素帖》《祭侄文稿》《苕溪诗帖》,地上满是我涂写的毛边纸,一得阁墨水的气息在房间里沉浸不散。刘女士很少过来,微信省去了很多麻烦。但中途也来过几次,每次都穿着不同款式的旗袍。她看起来大约五十来岁,肤白,身材苗条,秀眉长目,也许古典的打扮反而使她显得老相一些,实际年龄可能不到五十岁。解除租赁合同后,自然地,某一天她在我的微信好友中消失了。
至少到现在为止,互信在我和三个房东身上都存在着。我们有时会夸大人的恶意,喜欢听闻人群中糟糕、负面的信息,对于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总是持怀疑态度。我们有时习惯了“他人即地狱”的思维。
我的最后一位房东,是位男士,年纪与我相仿。春节过后不久,女儿即将从杭州返昌。我回到贤士花园,找到大门口的门卫老太太,她带我看了一套房子(她有钥匙),但那房子并不能让我满意。我从网上摘录了一些房子信息—有些不实的信息将我带到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看房是要付费的,大约花了百来块看房费后,我不甘心似的又回到了贤士花园。意外地,我在一个拐角处看到一张A4纸那么大的新贴的租房信息。我拨通了上面留的电话,是一位女士接的,对方让我在原地等十几分钟。迎面骑着电动车过来的却是一位瘦削的男性,嘴上留着小胡子,衣着普通毫不讲究,仿佛正在干活的中途过来,急匆匆,寡言少语。这套房子的陈设,与前面几套大同小异,三室两厅,除了光线稍差—因为我们进屋开灯后,好半天室内才显得透亮一些,那是一栋高层楼的三楼,没有电梯。对于我来说,觉得已经不错了。房主审慎地、沉默地陪着我将屋子转了一遍,熟稔地按着开关,拉开窗帘又拉上。我浮皮潦草地看过后,便迫不及待希望签订合同。他显然有备而来,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有些发皱的纸来。当听说我只租六个月后,他断然拒绝,说那不行,最少要租一年。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此次可能出现的最大障碍。房主收起那两片纸,起身准备离开。他说他很忙,店里还有生意要去照顾。我非常清楚,没有更合适的机会了,因此我请他再考虑下,帮帮忙。我说实在是因为女儿读书就近才来租房,她学美术,刚刚从杭州集训回来,离高考不到五个月时间。他突然眼睛一亮,看了我一眼说你女儿也在实验中学?我说是的。原本不抱指望的心又提起来了。他说好吧,我租给你。原来他女儿也在实验中学学美术,我女儿在八班,她女儿在七班。
此后一切顺利,不仅签了合同,房主还将卧室里坏了的空调换成了新的。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成了我们合作和缔结友谊的纽带。他甚至坐下来,与我聊了下她女儿的学习情况。因此知道她的女儿是在本市某个画室集训,联考成绩比我女儿落后大概千把名。他没有让女儿回学校学文化,而是放到一个培训机构(新状元还是博艺?)学文化。这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他说他还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初中,供养两个孩子读书,成了家里最紧要的事,他们夫妻两个是做小生意的,离这里不远—我脑海里浮现出永外正街那些店铺的形象。王兄—我这样称呼他,对他的负责任的态度表示钦佩。他说,还不是想博一下,为了孩子,做父母的不都是这样?这是个非常朴实的人。我与他之间的信任感,在亮明一个准备高考的家长的身份后,无比坚实地建立起来了。在我离开贤士花园半年后的春节,还收到过他的微信问候和祝福。
过道简史
我对这一画面至今印象颇深,当回忆的触角深入这甬道中,仿佛一束光,照在深邃的海底,我在那深蓝的寂静中看见过去的自己。那时,我意外地来到父亲的工作地,那是南方一个矿区,主要产钨,也产少量的金和银。我像是坐了很久的车才来到这里,其实现在回忆起来不过是两三个小时车程。我和父亲隔膜已久,每次他从异地回家,似乎总是夜晚到达,第二天我们才发觉家里多了个人,而他正坐在客厅里吃母亲用蜂蜜开水冲的鸡蛋。每次,他都是带着相同的东西回家:当归、党参、枸杞。总是那三样。父亲一回来,饥饿的我们嘴里便被母亲塞满了党参和枸杞,她把这个当做我们的零食。我很不喜欢那零食的中药味儿,但不得不含着眼泪把它们吞咽下去。要不就是难得地煮了一只老母鸡,鸡汤里也满是当归、党参和枸杞。我们不是在吃鸡,而是在吃药。母亲说这很滋补,现在我只要吃鸡,口里仿佛还是那中药味儿。
父亲很少回家,在那个年代,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父亲懒惰的天性。他是一个不愿折腾的人。他习惯于待在自认为安全和舒适的范围内,轻易不迈出一步。每次父亲回来,我刚与他混得半生不熟,他却又消失了。我们习惯了父亲消失的生活。我们三姐弟,我,姐姐,和妹妹,像三只小虫围绕在母亲身边,有时母亲也不理我们,她有做不完的事。姐姐像是另一个母亲,她的伙伴是那些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整天跳皮筋、扯猪草,也忙得不亦乐乎;我同时鄙夷妹妹,她太小,好动,一问三不知。我于是习惯了孤独和幻想。因此,有一天,当我坐着班车头昏脑涨地来到父亲的矿区—因为第一次坐班车,不免晕车,对父亲生活在云端感到诧异。那是一个国营钨矿,据说时不时潜伏着特务和破坏分子。依靠开采钨矿,俨然发展成一个小镇,学校、医院、澡堂、影院一应俱全。我和父亲来到一个山脚下,准备登山—他就住在这山顶筒子楼里,准确说,是职工宿舍。这样的职工宿舍,在矿区有好多个,但是像父亲这样家属不在身边的职工,便统一住在这山顶。好像那是一座庙。我勉强拖着沉重的双腿随父亲踏上台阶。父亲穿着蓝色中山装,四个口袋,头发梳得光溜溜的,黑色皮鞋笨拙但铮亮。我似乎还看见他左胸口袋插了一支钢笔。我不知道走了多少级台阶,没有数过。我为父亲每天上下这么多台阶去医院上班感到吃惊。
我和父亲出现在黑暗的筒子楼里,站在黑暗的过道,闻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对父亲的住所感到陌生。过道里放了许多柴火,墙壁因为常年的烟火而变得发黑。一股饭菜味儿冲入鼻底,经久不散。我像是第一次来到这种筒子楼。我的经验里,只熟悉县城老家平房和乡下亲戚家的房子。过道里没有电灯,在印象里,那仿佛是一条黑暗的街道。父亲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打开其中一扇门,在这间小小的居室,数年如一日“囚禁”自己。宿舍简单得像他这个人,仅一床一桌一厨一凳一箱一镜而已。他是真正的“六一居士”。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宿舍,仿佛也是唯一一次。
我已经读了师范,出乎父亲意料。对于学习每况愈下的我他动了将我转入工矿子弟学校的心思。他想得多,真正实施起来少。一贯都是如此。美术老师的母亲与我父亲是医院同事,父亲托她给我带过两回菜—在她来学校看望儿子的时候。父亲这温暖的举动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父亲隔一阵还会与我通信,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毫无抒情和文采可言,而是硬邦邦地有一说一。父亲怀疑和不信任任何抒情的方式,他一辈子认为抒情是矫揉做作扯鬼淡的玩意儿。居然有一个此后以抒情和文辞为职业的儿子。高小毕业的母亲那时居然也给我写过一封信来。那是我进入师范不久,母亲大约担心我适应不了离家的生活,在外吃苦,因而满纸都是愧疚,仿佛那是她的过错。现在还记得信里母亲喜欢用“想必”这个句式。一点不像平时见到超然省心的母亲模样。母亲还坐班车专门来学校看过我一次,晚上睡在女同学的寝室。
美术老师因获得筒子楼里某间宿舍,高兴得唱起齐秦的《九个太阳》。筒子楼就在我们教室后面,那是一栋与父亲宿舍相似的砖房。火车厢似的建筑,楼中间过道同样漆黑和堆满劈柴。家家门口放着一个炉子和简易厨具。我的班主任是个下放的上海知青,她的爱人与她先后担任我们班主任。他们住在靠近沿江路的套房里,那是已婚教职工享受到的待遇,进门客厅挂着一幅西洋女子油画肖像。我和几个同学被美术老师拉到他位于文山路的老宅子搬东西:成堆的画册、油画框、颜料、画纸以及被子衣物碗碟等等,装了满满一卡车。美术老师头戴纸折的帽子,唱着歌儿用石灰将房间刷白,行李悉数搬进归位,充满艺术情调。我是美术老师喜欢的学生,时不时出现在筒子楼过道上,脑子里却想起父亲山顶上的房子—像是复制的一般。美术老师将我们几个,晚上叫到他的宿舍里写生。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待遇和体验。我们已经上了一阵油画课,画过不少石膏像、夹竹桃、花瓶、罐子和水果。美术老师给我们开小灶画人体。模特是我们同学中的一个,一个肌肉结实的男同学。那个夜晚,他在美术老师的指挥下模仿画册中的形象露出脊背给我们画。这样的画册我们已见过不少,但当真对着画布写生的时候,我发现握笔的手在颤抖。那是一次糟糕的不成功的体验,灯光晦暗,我被一种好奇和荒谬感所驱动,无法集中注意力进入状态。当我们陪着“模特”从老师房间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掩面痛哭,像一个失去贞洁的少女。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回宿舍,而是陪着他在学校操场坐了一整晚。
我像是定格在那筒子楼黑暗的过道上。那时,我已经毕业回了家乡,在一个乡村中学当老师。我看起来像在重复父亲的命运。中学也在一个山顶上,四周是荒野,学校因此也像个庙或庵。一样的筒子楼,只是略新一些,砖的颜色由青灰变成了暗红。我站在筒子楼里,感觉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我从腰间解下钥匙开门,另一个我在边上旁观。房间的陈设与父亲的宿舍如出一辙,不多也不少。当第一次出现在学校,被总务带着穿过黑暗的过道时,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我记得那次,虽然已经过了夏天,但父亲还是领着我来到宿舍后面的水泥沟渠里,将身子浸没在冰冷的山泉水中。砧骨的水刺激着让我尖叫,而父亲毫不理会,他自顾在身上打着肥皂,甚至吹起了口哨。许多个夜晚,我在学校山脚下的水井旁,用冷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时,嘴里也发出阵阵尖叫。
那些夜晚,我体会着父亲的孤独。学校里往往人去楼空,唯有我经常住校。在黑夜的筒子楼里,孤独披着黑夜的外衣,它一层一层包裹我,我又像是回到小时候在老宅前坐在门槛上看星星睡着了的情景。我坐在黑夜里,无限怀念父亲母亲。这时,父亲已经提前病退回到家中。我每周一次回去看望他们,其余的时间全部交付这乡间的夜晚。我在黑暗的楼道里伫立,看不清未来,不再画画。我将全部的虚妄和恐惧交给黑夜,像窗外树枝上的猫头鹰,有着金色、不眠的眼睛,和比夜晚更深的孤寂和固执。我开始收到一些刊物,原先我羡慕的名字,现在我列在他们旁边。我抚摸这些分行文字,像是开始孕育一个全新的我—这陌生的形象,在一个个夜晚被煨熟、养大,终将从这平凡之躯中脱离出来。我越来越迷恋筒子楼的黑暗,当我写累了,从房子出来,关上门,隐身在黑暗中,久久地一动不动,谛听自然的律动,银河旋舞像梵高的画作,虫声不绝如诵经的声音。我进入一种思悟和自证中。在山中夜晚,像丢进丹炉里的一颗药丸,在接受烈火煅烧和冶炼。
这样的岁月长久得似乎让人相信不再有任何改变。却意外地,我又经历了数次变动。我以为将告别筒子楼过道的黑暗,却又像是一个符咒,无法摆脱那不可知的命数。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在另一个更大的校园里,筒子楼变成了三层。同样熟悉的过道,黑暗、悠长,像是没有尽头。但那黑暗过道却有我至大的欢喜。我的女儿已经出生,并且上了小学,这是个笑起来充满感染力的女孩,大眼,圆脸,短发。我像是每次在相同的时间守候在过道,看到她从楼梯上过来,看到我,迅速地向我飞奔,在即将接近的时候一跃跳到我怀里,双腿紧紧勾住我大腿,她的笑声像秋天的阳光一般甜美、爽朗,整个楼道充满她的笑声。在此后无数个时辰,我总在一遍遍重温这个场景,感到女儿带着不顾一切的重量向我扑来,我努力去捕捉她的每一个笑声,每一下紧紧勾住我大腿的力度。从她身上去感受一个小男孩对他父亲的隔膜和思念,对他的抗拒与靠近。我将女儿永远定格在那个时刻,在那长长的筒子楼的过道里,她朝我飞奔而来,纵身跃起,让我感受到那千真万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