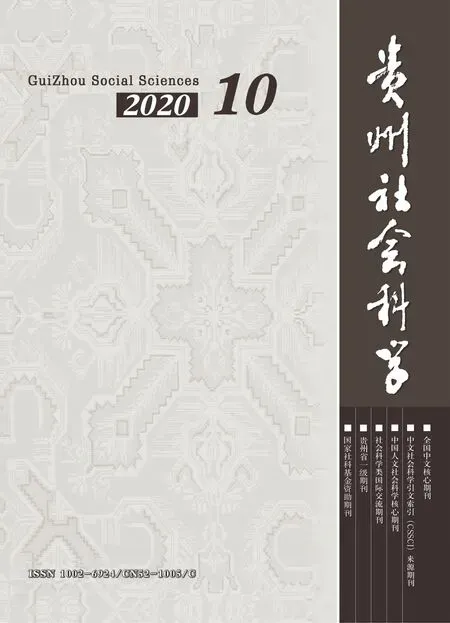欧洲颓废民粹主义与中国别现代主义
2020-03-11衣内雅边沁姚天明
衣内雅·边沁 撰 姚天明 译
(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爱尔兰 高威市 H91TK33)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法国社会学家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的理论。他们的理论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变迁。在其理论基础上,将探讨在这期间,美学、艺术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哪些重要变迁。第二部分,将阐述意大利哲学家佩尔尼奥拉的理论,他的理论围绕知识和社会权力的关系展开讨论。其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当代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颓废心态与民粹主义特征,这一特征已经蔓延到了欧洲学术界和文化界。最后,将对国际上引发热烈讨论的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理论进行探讨。由此展示在对待知识的价值和社会效能方面,欧洲和中国所遵循的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新资本主义精神
在评价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时,阿列西· 艾尔雅维茨(AleErjavec)谈到,“如果说几十年前,西方的文化对抗和竞争主要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之间,那么现在这种两极的趋势已转变为一个四边的较量。我们仍然见证着美国和欧洲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竞争者参与其中,它就是中国。中国正在努力获得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诠释了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观点。”[1]53
艾尔雅维茨的这种观点隐含了一种西方文化处于优越地位的假设,而中国扮演的则是一个在其后努力追赶、希望能够得到承认和重视的角色。事实上,我认为恰恰相反,欧洲和美国的文化界和知识界正走向下坡。在欧洲,知识分子已不再受重视,知识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用;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正日益提升。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近年来,多位学者和社会学家聚焦于西方社会的转型(1)参见Boltanski, L., Chiapello ., 2007,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New York, Verso.Boltanski, L., Thévenot, L., 2006, On Justification. The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Lojkine, J., 2005, L'adieu à la classe moyenne, Paris, La Dispute.Perniola, M., 2000, “La differenza europea”, in galma no. 1, pp. 113-120. - 2002, “Prova di forza o prova di grandezza?”, in galma no. 3, pp. 63-79. - 2012, Da Berlusconi a Monti, Milan, Mimesis. - 2017,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Dangdai Meixu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他们当中,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为了寻找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新方法,提出了一种叫做“新资本主义精神”的视角。这些学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管理学著作。我想谈谈这个所谓的‘新资本主义精神’给当代欧洲文化界,美学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从整体上改写知识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的。
简单来说,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界定了三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他们是如何判断出资本主义是有“精神”的呢?难道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通过表面上看似温和的形式,进行无止境的资本积累”[2]吗?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认为,为了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精神’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他们开创性地提出了三种资本主义的精神。第一种是以资本家、企业家为代表的传统男权主义价值观。然而,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认为,为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资本主义需要反对派,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声音。例如,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倡导平等、安全和社会保障的社会主义运动大潮中,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结构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换言之,资本主义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一成不变的呆板教条,而是一种可以随机应变的社会形态,其指导原则和实践形式可以依照外部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开始逐渐采纳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和诉求,这也标志着第二种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种精神建立在集中化、官僚化的工业化企业架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强悍的工会组织、福利国家、终身聘用制和纵向社会流动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时代。然而,这样一个系统受到了“六八运动”(2)指1968年5月爆发的巴黎学生运动,又称“五月风暴”。及其之后一系列反体制、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倡导自主、创新、真实和个性的新艺术、政治主张的冲击。在强调民众需求、安全以及公正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和艺术激烈批判下,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精神分崩离析。
为了缓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期困扰欧洲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再次战略性地采纳了新的批判和诉求,从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精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一方面吸收动荡时期的艺术主张,另一方面调整九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的专业性分工。不同于之前集中化的工业模式,这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以构建合作网络为运作特点,伴随着以雇佣高流动性的临时工人,承接零散项目为主要运作形式的灵活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这个时期,非主流艺术风潮应运而生,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管理风格则倍受青睐。这种波西米亚式的“放荡不羁,离经叛道特质也迎合着新的资本主义剥削需求”[3]64“就业能力”,“应变能力”和“创造力”成为备受推崇的职场新标签。人们感觉自己似乎处在一个平等、开放、前卫、充满激情的工作环境中。在这第三种精神的资本主义新时代下,那种曾经属于艺术家们的特立独行、自力更生的非主流生活方式,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大众审美。
二、欧洲当下的人文学科
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进行如此明确的社会学区分,目的在于考察在这个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大环境下,知识分子在当代欧洲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或者从广义上来说,学术界在当代欧洲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除了高校,艺术馆和博览会以外,欧洲的大众的文化、审美和日常生活方式又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按照马里奥·佩尔尼奥拉的理论视角,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精神在二十世纪末摧毁了自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发展壮大的学术体系和职业分工系统。用佩尔尼奥拉的话说,自启蒙运动以后,产生了“思想的社会化”[4]31现象。这种现象催生了新闻业、职业分工系统、现代大学以及政党的快速发展。公共舆论逐渐形成并得以传播,为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学,作为由国家担保的学术机构,奠定了职业分工系统的发展基础;政治,则为各党派表达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舞台。这个职业分工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科学的社会化,也就是说科学研究不再是某种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一项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这样,也就形成了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步骤和准则。换言之,科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而职业划分也变得日益科学化。佩尔尼奥拉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化的现象在高校知识分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规范的科学研究和职业分工系统的形成,使得知识可以跨越国界,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当时的欧洲,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思想理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例如,在艺术领域,产生了印象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在哲学领域,产生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等。
佩尔尼奥拉认为,在欧洲,这种相互竞争、砥砺前行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所谓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破坏了知识在社会上获得重视和应用的传统。例如,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运转了近两个世纪的高等教育系统资金短缺。“资本主义不愿意再耗费大量金钱去维持一个昂贵的科学研究和职业分工系统,而更愿意把大学降格为高中,把教授降格为雇员”[3]70。换句话说,佩尔尼奥拉认为,当代欧洲已经无法为教育界和学术界提供一个进行独立研究的良好环境,而大学则更是已经丧失了对社会和政治的知识影响力,这一点在人文学科的衰落上体现得尤为显著。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将不难预见到大学性质的转变。从独立原创精神主导的科研中心,蜕变为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临时性,灵活性,流动性,机动性)所主导的企业。此外,在这种以构建合作网络为特征的新资本主义精神的侵蚀下,建立在大学专业教育上的职业分工系统也面临瓦解。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和快餐文化所主宰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饱受诟病,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返璞归真的朴素生活理念的追求。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和佩尔尼奥拉都表示,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回应了人们对朴素生活理念的追求。资本主义于是‘使追求朴素生活的理念商品化’,一方面去除消费品的商业特征,另一方面“使商品更人性化,以实现‘人性化’服务”[2]442。博尔坦斯基表示,这种商业操作是资本主义对“六八运动”时提出的“小众化”、“差异化”诉求的回应。资本主义的回应方式正是将批评者的诉求纳入其市场服务的范畴,把之前没有的商品和服务种类增加进来。例如,远途旅行、遗址参观,极限运动如荒野探险、蹦极,以及演唱会、艺术家、定制家具等等。这种做法背后的目的,是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购买的并不是流水线上的批量商品,而是一种纯真、独特、不可复制的经历与体验——“资本主义既平息了人们对朴素生活的渴望,又从中赚得盆满钵满”[2]447。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展会、艺术节和研讨会,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艺术正走向民主化、大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艺术走向商业化、娱乐化[4]53。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欧洲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是否还能够产生出有影响力的理论,-isms,或是王建疆所说的主义(Zhuyi)(3)Wang, Jianjiang (2016). "The Bustle and the Absence of Zhuyi. The Example of Chinese Aesthetics". Filozofski vestnik, Vol. 37, 1 (2016).Wang, Jianjiang (2017). "Philosophical Quadrilateral and Bie-modernism. Comments on Aleš Erjavec's 'Zhuyi: From Absence to Bustle Some Comments to Jianjiang Wang's Article "The Bustle or the Absence of Zhuyi"'". Art +Media,volum 13,2017.呢?
职教成[2011]6号中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推动职业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培养大批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它为高职教育指出了行业指导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了“推进产教结合与校企一体办学,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与岗位对接”的指导意见。
三、别现代主义视角
当前笼罩欧洲的颓废心态和民粹主义,与王建疆所提出的中国所处的别现代有着天壤之别。在欧洲政界、学界、以及大众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浓重的阴郁消极、甚至是虚无主义的氛围。用佩尔尼奥拉的话说,那秉承着古典时代光辉传统、在近现代孕育出累累硕果的人文主义的壮丽理想,在今天的欧洲大地上正逐步走向绝望与幻灭。
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科学、人文、文化与知识体系如今正面临崩塌。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预言过一种他称作“欧洲虚无主义”的社会状态,我认为这正是欧洲当前所处的状态。事实上,现在欧洲的权威机构已经不再重视知识的价值,或者说,所谓的价值,其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价值、品质和卓越等概念,已经被数量、排名和等级所取代。
佩尔尼奥拉所描述的景象,象征着一个欧洲的关键转折点。事实上,欧洲近在两个世纪以来留下的历史遗产,如现代性的产生、启蒙运动以及旧制度的废除等,正遭受着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腐蚀。这种腐蚀不仅仅只发生在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也同样发生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断受挫、力不从心,使人们一方面沮丧焦虑、自暴自弃,另一方面也丧失了彼此间的信任和尊重。尽管他们会矢口否认,但是欧洲人其实已经沦为各种形而上观念的俘虏。其原因并不是世俗化所导致的信仰的缺失,恰恰相反,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形形色色价值理念冲击下的迷失和无所适从。”[5]欧洲的这种情况也被恩斯特所指出:“在西方,与社会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优势地位不同,美学与哲学以及其它人文学科一起,被边缘化了。”[1]41
王建疆在他的《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一文中说:“常言道,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术巨匠”[1]41,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欧洲很多伟大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其悠久的古典传统。从希腊美学到地中海经院哲学,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绝对美学、实证主义逻辑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不一而足。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沉沦,是否代表欧洲对于伟大思想的追求已经偃旗息鼓?这种景象,并不代表欧洲已经没有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了,而是意味着当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已经抛弃他们了。那曾经带给欧洲辉煌成就的理想追求在欧洲已日渐式微,却又找不到新的精神寄托,让人们心灰意冷,而这种心灰意冷的背后正反映着学术界、思想界的萎靡不振。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新的理想替代品,而是要认清眼前的挑战,认清学术界、思想界如何在除高校以外更广泛的社会中发挥作用。我认为这才是值得反思的关键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我们不应该回到形而上学或者美学的旧书堆里找答案,而是应该去审视价值理念的传播渠道和利用方法。哪些传播渠道和利用方法提升了或者贬低了某种价值理念?我们应考察价值理念的动态属性,而不是视其为静止不变的。
回到开篇提到的艾尔雅维茨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正在人文领域中努力争取一种与西方平等的“声音”。而我更赞同郭亚雄的观点,在《声音与语言之辩的脱魅》一文中,他指出对于声音和语言的二分法本身就是西方哲学观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化早期译介者的传教士对‘中国哲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被展示为一个政治清明、道德高尚、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国家;另一方面,本诸信仰的立场与传教的需要,耶稣会士们又迫切希望阐明基督教之于中国思想的优越。通过对中国哲学概念极为随意地翻译以及对文本的刻意扭曲,欧洲学者在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又对其做出了混杂不堪,无法理喻的品评。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的译介似乎预示着‘比较哲学’研究的开始与哲学国际化的征兆。然而,此种思想比较却被传教士们演绎为‘言语’对‘声音’的嘲讽与排斥。从表面上看,‘混乱的中国格言’与明晰的西方哲学之间的对照为‘声音’与‘言语’的区隔提供了理据。但就话语运作条件而言,传教士所进行的‘思想比较’却先行奠基于‘声言二分’的观念方能展开。以是之故,凡与‘中国思想是声音”的判断不相符合的话语便不会被传教士纳入比较范围。此种‘哲学比较’并非是一个倾听双方言说的场域,也并未设定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声’与‘言’的对立与中西思想的本然样貌无关,只与传教士(想要)迫使中国皈返(依)基督的策略有涉。”[1]167
此种“声言二分”只不过是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逻辑与非逻辑等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观的老调重弹。而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从道家到儒家、墨家、法家,倡导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人文理念和价值主张[6]。那么用这种声音和话语的二分法去理解独特的中国思想传统,恐怕会无功而返,因为西方的两极对立的哲学观难以囊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声音和话语的二分划分其实是以欧洲学术界作为默认的标杆。我认为欧洲学术界远非处于领导地位,也不应该以欧洲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在世界人文领域中的位置。
王建疆的别现代理论,创建了一个重新思考这些重要的问题的空间。汉语这个“别”字,蕴含着“差别”、“区别”、“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现代性内涵[1]245。用王建疆的话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处在迈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现实仍旧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交集纠结的杂糅状态,边际模糊,很难说它就是纯粹的现代或前现代,更不能说它是后现代,只能说它是别现代。这里的‘别’就有与现代性相分别的意思。别现代主义就是要与这种虚妄不实的现代性做一种分别、别离和切割,从而具备真正的现代性,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与前现代告别而奔向现代的过程。因此,提出别现代就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概括,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是一种进步的价值观。”[1]247王建疆认为,别现代概念的一方面开创了考察中国独特的、原生现代性的新理论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理解和分析现代性所倡导的人文目标在中国发展与实践情况的理论基础。这样,别现代概念的提出,使中国思想研究能够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挣脱出来。
要理解王建疆的理论,首先我们要跳出以欧洲文化和宗教传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直线性时间概念。与西方的断代式历史划分方法(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或者基督教一神论所说的尘世、天堂和救赎的线性时间概念)不同,别现代主义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创新与传统并济、孕育了“非西方现代性”[7]的中国历史。比起直线性的时间概念,空间化的时间概念更适用于中国历史。空间化的时间概念中,古老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历史的发展遵循的是一个回旋而上的路径。王建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也在当代思想上实现复兴。如同恩斯特·曾科所说:“中国美学并不需要运用西方的理论(正如知识的传递是没有定时的一样),关键问题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学方法论。”[1]140
学术思想的复兴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和国际声望上,同样也体现在风俗礼仪、大众品味、精神面貌上;它建立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它反映的是知识与社会效用、权力的有机结合[8]。美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归功于专家学者们的思想贡献,但同时必须找到一个向大众普及的方式[1]105。正因为如此,王建疆建议我们应该采取中国古代“急流勇退”的策略,在实现跨越式发展后进行跨越式停顿,消解惯性,实现一种伟大的突变[1]105。他说:“所谓跨越式停顿就是在事物发展的高级高速阶段,在事业发展欣欣向荣甚至如日中天之际,进行自主性的突然停顿。跨越式停顿的事例我们可以在中国古代的急流勇退和禅宗的顿悟成佛中找到,可以从当今全球无水日、无车日、无烟日的演习中看到……因为它发现经济、技术、军事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不能代替文化传统、自然生态、社会制度的非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已经是对追随式发展的区别和超越,而跨越式停顿却又是对跨越式发展的区别和超越,是区别中的区别、超越中的超越。因此可以说,别现代之别是别中之别。”[1]83与经济不同,文化的发展是有节奏规律的[9]。如果一切以无节制的资本积累为目标,盲目追求数量而非质量[10],关注眼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忽视教育所带来的长远社会效益,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对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日常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欧洲可以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鲜活案例:民粹主义政策加上民众的反智情绪正在摧残着高等教育系统,第三种资本主义精神麻痹着大众的思考能力,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君子上达”的自我要求。新自由主义已经让他们视无知为理所当然[11]。随着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日益缩减,加上消极颓废的民粹主义的日渐抬头,欧洲正成为反知识、反理性、反文化的重灾区。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加入世界哲学四边形(欧洲、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准备? 即使声音与话语的二元区分概括不了欧洲或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学术界也不应该再继续韬光养晦、默默无闻。在保持着自身独立、原创的思想体系的前提下,中国应该推进与西方的交流。王建疆认为:“学术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体现之一,因此实现文化上的复兴也对中国至关重要。学术影响力来自于学术的质量,而非数量。在学术质量的考评中,主义是学术的硬通货,没有主义的学术是难以自立的学术,而由原创性主义统摄的学术才是真正独立于世界之林的学术。”[1]16
四、别现代艺术
别现代风格在现代与前现代相结合的中国当代艺术上的体现尤为明显。接下来将以王建疆的《别现代:作品与评论》中的四位艺术家作为代表,展示艺术与别现代理论的关系。这四位艺术家来自于绘画、雕刻、建筑和一般意义上的视觉艺术。
曹铃:“随着阅历的加深和游历中外的自然景观、文化遗址、博物馆、美术馆,观摩中西优秀作品,我的所思所想通过一幅幅作品展现出来了。王建疆教授‘别现代’的话语创新和该理论构想的具有人类普遍价值认同和力图打造有中国特点的现代性等等,与我的艺术理念和绘画风格堪称不谋而合,这就是,既要有对现实的描述,又要有更新超越;要深入自己的心灵,从传统中、从东西方文化上、艺术上,寻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12]23
旺忘望:“旺忘望的作品体现了别现代艺术的杂糅与冲突并置的特点。这一特点也被旺忘望称作“跨界”。在看似通过拼贴的杂糅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精神与利害之间的冲突。艺术家在对我们所熟知的事物进行解构的同时,建构了对当下社会警醒性和反思性的新体验,从而形成巨大的张力。旺忘望在传统水墨画观念形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艺术手法和思想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形成了跨界的别现代杂糅与冲突。”“《肉山》、《钱山》系列虽然在方法上采用了传统的散点透视法,但是却用肉体、美元的堆叠解构了传统画中最重要的笔墨,同时也解构了传统水墨画的意境,看似是中国水墨画的形,但却是艺术家夹杂着中西方观念的当下体验,其核心已经不再是一种对精神意境的描绘,而是欲望符号的碎片堆积,和在欲望世界中人类的精神以及信仰的丧失。《钱山找神》、《车山找神》等系列也是如此。”[12]32-33
陈箴:“作品中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地球仪,里面充斥着现代社会产生的典型垃圾。旧式马桶隐喻前现代时期,作品中央的一大堆工业垃圾象征着现代时期。……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原初意义丧失殆尽之后,形成了一个别现代空间。”[12]50-51
陈展辉:“凹凸系列是象形文字与阴阳哲学观念及极简主义建筑理念的叠加。属于别现代建筑理念的创新性尝试,也预示着传统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凹凸系列将中国古代道家推崇的五行学说与阴阳对立统一学说相结合,并运用现代设计工艺、材料加工制造而成‘建筑之外’衍生品。从金玉结合的结婚对戒,到凹凸陶器,再到城市的系列设计,多聚焦于室内家具和城市公共空间装置尺度的创作和演绎,不一而足。对于‘凹凸’来说,凹凸不只是装置艺术以及现代家居展品,这一组站立起来的文字也是一组空间感极强的图形、图腾,极具别现代主义意识,这就是立足前现代文化遗产和现代城市生活,在以解构中心为标志的‘建筑之外’,重构以阴阳平衡为标志的凹凸对接。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下最有前沿性和革新性的代表之作。”[12]113
这些艺术家的宣言及其作品评价有什么共通之处?是什么把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工业废料、景观主题、道家哲学和极简艺术联系到了一起?以上的这四位来自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都展现出别现代的风格特质。其作品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传统技艺与当代、后现代主题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艺术的底蕴结合了西方视角和表现手法,在符号、图像、技巧等方面传达出传统、革新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理念。惊艳之处在于,艺术家们没有回避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恰恰相反,他们积极地将这种冲突表现到其作品中去。也正是在这种灵感、视角、技巧和理念的冲突中,孕育了新的独创理论和实践。 如果墨守陈规,为了保持一种臆想的文化纯粹性,而故意将东西方文化传统隔离开来,则将难以激发新的灵感。也正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纯粹性已经不复存在,正是来自各种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技巧相互碰撞与兼容并蓄,诞生出了独出机杼的新颖艺术风格和潮流。这一点的重要性,基顿·韦恩也进行了相关阐释:“在西方对其与非西方世界的他者的际遇作出回应时,前现代就变成了现代。殖民与扩张并驾齐驱。在观望自身之外的非西方文化诸如非洲、波利里西亚和东方后,西方艺术变成了现代。随着西方文化开始自我质疑,它向其他视角敞开了怀抱,与此同时也就削弱了自身传统,尤其是天主教会和君主政体。如今西方信奉许多新构建的叙述:自由民主的优越、资本主义以及进步现代主义的余脉。中国和西方均已成“他者”,均对他们自身的叙述心生怀疑。但在这新的时代,我们必须找到交流和构建有效思想的方式。假如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不提出他们自己与西方不同的主义或者理论,西方将永远也不会对他们自身的叙述——凯旋高歌的现代主义叙述产生怀疑。王建疆已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空间。这个空间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杂糅进‘别现代’,并伴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存在。”[12]304
不过,这种中西合璧的别现代艺术风格并非只是全球化冲击下中国艺术家生搬硬套西方舶来品,被同化的产物,而是一种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态度之体现。尽管按照欧洲人的理解,全球化的进程是欧美模式在世界上的单方面拓殖,但是正如《一个现代神话——以中国为例》所指出的,情况绝非这么简单,他声称“全球化的影响虽然无所不在,但并不是铁板一块”[1]356。尽管西方艺术、文化、音乐和商业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王建疆指出:“当下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审美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现代性的印痕。这些艺术和审美的新变化一般被认为与来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审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流行的歌曲、街舞、发型、服饰、装潢,在不出24个小时就会在对面中国的上海粉丝中流行起来。因此,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对于民族艺术和审美来说,不是承认不承认全球化的问题,也不是回避和拒绝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认识全球化的利弊,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本体,并进而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1]356
王建疆认为,正是在传统东方世界观和当代西方方法论的共同影响下,中国才会发生如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别现代理论也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原创理论。他指出:“有关中国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具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是否具足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现代性自西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而来,其核心范畴和核心价值是社会契约、科学理性、人权保障、博爱精神、社会福利制度、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正是这些核心范畴规定了西方的现代性。与之相比,中国是否具有这种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或者在多大占比或程度上具有这种现代性,就是一个十分需要考量的问题。如果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出发,来考察中国的现代性现状,则发现,与西方的断代式发展不同,中国是一个现代跟前现代、后现代杂揉在一起的社会形态,因此,很难有真正的、纯粹的或具足的(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1]253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对于文化、美学和艺术,欧洲与中国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当前反智情绪和颓废心态笼罩下的欧洲社会,文化和知识似乎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陪衬;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在迎接新的挑战的同时,人们不仅尊重知识,而且也努力使知识充分发挥其社会功用。
颓废心态与民粹主义笼罩下的欧洲,也许应该通过温故知新的方式来寻找出路。通过审视过去,来认识当下。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自己从何而来,才会认清我们将走向何方。让传统的智慧焕发新的生命力,才能帮助我们最终实现伟大的人文理想并将其传承下去。如同王建疆所说:“哲学家首先是一个个我,一个高度精神自由的个我。因此,我认为中国哲学、美学、人文学科要走的路既不是哲学帝国的振臂一呼集者如云,也不是哲学帝国外的对于哲学帝国的亦步亦趋,而是要走自己的路。”[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