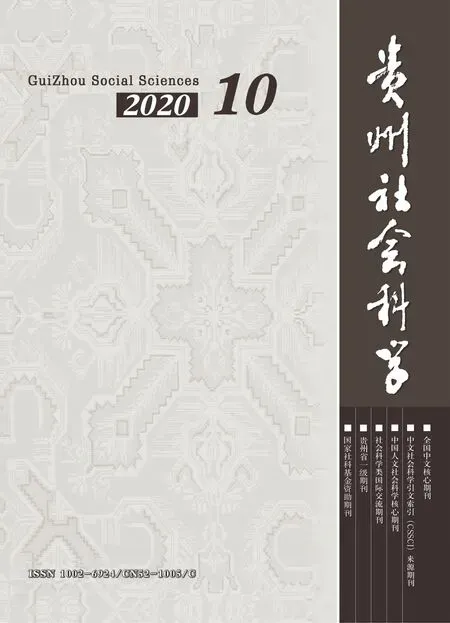欧洲中心假设论的实质和对别现代艺术的误读
2020-03-11基顿韦恩
基顿·韦恩 撰 李 隽 译
(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2.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2)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与盲点
在欧洲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已有很多文章对20世纪早期非西方艺术在形式实验中的运用予以了关注。1906年,马蒂斯、毕加索、弗拉明克、基什内尔等人在巴黎的特罗卡德罗民族博物馆和德累斯顿的民族志博物馆中展示了欧洲殖民事业的胜利果实。尽管这些博物馆的藏品以展示其他文化的艺术成果为名展出,但却将其他文化的人类视为“劣等人”。 植根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思想的构建“高贵的野蛮人”,尽管假装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扮演仁慈的角色,但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剥削手段。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程总会导致赢家和输家、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权力动变。西方现代艺术的历史源于这一战略。随着黑格尔式的进步停滞和文化倒退至审美形式主义,“世界精神”并没有在一种或者若干种新的方式中展现出来。好在矫正的西方“启蒙”文明应运而生,它以创造天才和文化进步自居,蚕食其他“原始”文化。这些相互关系中所潜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证明了西方进步和历史的叙述穹顶。
毋庸置疑,由西方人书写的历史是一纸对西方的控诉书。毕加索之前的一代西方艺术家具有日本风格,更毋宁说早期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埃及风格了。这吸引了梵高、图卢兹-洛特雷克和卡萨特等一批艺术家。怀抱着通过和“原始的”人民生活来恢复能量、拯救被现代侵蚀的灵魂的愿望,高更背弃了西方文明。被科学描绘的宇宙令人不甚满意,死结在于它的可测性上,因为艺术家们需要的是通过灵魂和不可预测的生活去获取更深层的意义。科学的剖析破坏了世界。这一点在高更创作于1897年——他自杀未遂的那年——的一幅绘画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画的标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是一个热烈追求意义的男人的画作。他对意义的追求大于生活的其它部分——那些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被分解为可量化的原子部分的总和。现代物质主义已不足以满足他内心的生活。
毕加索如是描绘自己对于原始的迷恋:“每个人都在讨论黑人对我的影响。我该怎么办?我们都有恋物癖。梵高曾说:‘日本艺术——我们有共通之处。’对我们而言,黑人也是这样。当我去特罗卡德罗时,真感到恶心。跳蚤市场、气味、形单影只。我想离开。但我没有离开。我留下来了。我明白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对吗?(非洲)面具不像其他雕塑。完全不像。它们是神奇之物。但为什么不是埃及或迦勒底人的作品呢?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些都是原始的,但是不是神奇之物。黑人作品是代祷者……他们反对一切——反对未知,危及灵魂。我总是恋物癖式的凝望它们。”[1]
毕加索描绘了一种近乎萨满教式的转变以及出于文明的抗拒。那些假设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判断力和权威性的欧洲艺术家们将文化材料、形式、意象甚至生命能量运用于一种创造性的同类相食中。在毕加索模仿——如果说并非直接抄袭的话——非洲形式的时期,他正在吸收一种新的表现语言,这种语言只能通过模仿来学习。在艺术史的传统中,这项工作从未被视为一种抄袭,而被视为学习新的视觉语言的必要阶段。毕加索的模仿既非不真实的也非拙劣的,而是非洲形式的升华。似乎通过他们的挪用和开发,这些外来形式会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释放全部潜力,达到预期目标。正如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他1912年的论文《立体派画家》中说:“许多年轻艺术家关注埃及、黑人(非洲)和大洋雕塑,他们对各种科学的造物冥思静想,生活在对崇高艺术的期待之中。”[2]对这些欧洲艺术家而言,非西方和所谓的“原始”艺术只是一种朝向更加崇高形式的目的地的方法。从这些艺术中获取灵感的作品从未被称为衍生品或者是被称为对于更为真实和优越的原件的复制。
通过自我定义,西方现代进步文化相信自己早已远远超越了原始文化迷信的世界观。接下来,欧洲艺术家为回应非西方影响而创作的作品将创造出一个大胆的审美新世界,开天辟地,翻开西方艺术史上新的篇章。这是一个被操控的游戏,因为定义早已被确定,特权位置早已被预留。
二、文化反思与创造力和真实性问题
欧洲中心观通过殖民利益广为传播,殖民地国家接受了这种对现代艺术历史和发展的阐释。假如殖民地文化试图参与到西方文化中来,那么他们除了视自身处于宏大的西方叙述内别无选择。这一现象持续至今。而今是否有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正对历史进行漫长的微调?这种现代历史的观点被默认是我们的历史,也是后殖民时代变迁中最坚固的据点。如今历史该被如何诠释?近期的历史该被如何诠释?是谁书写了历史,又是为何而书写的?
别现代理论与这些问题进行搏斗。别现代正在参与多种中国现代现实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它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描绘既引人深思又令人兴奋。北京策展人朱其如是形容这一观点:这是目前“对中国现代性的重新思考”[3]。他还描绘了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史主要由西方人书写的现象。因此,格外强调了对特定反叛艺术形式的关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那些书写新艺术的历史的人“不仅是来自欧美的学者,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他们的写作和话语模式基本上都是欧美风格。”[4]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拱顶朝两个方向弯曲:一个方向沿袭西方的叙事模式,强调艺术对西方式历史诠释中的优越感和价值观遥相呼应的批判和政治功用;另一个方向是一些强调多样性的中国学者所引领的。朱其认为,今天的中国艺术可被描绘为与西方艺术同步的“中国当代艺术”,或者是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展的“当代中国艺术”。
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将欧洲殖民者与非西方艺术的邂逅解释为“文化反思”(1)“Cultural Reflexivity”as I am using the phrase would mean the ability to see your own culture more critically and objectively through the engagement of other cultures.的一种形式。也许我们可以视毕加索和他的同辈们对其他文化中的艺术的兴趣,是一种试图通过反思其他文化的表达来认清自己并超越自身视角局限的方式。即使真是如此,双重标准仍不可避免。当欧洲先锋艺术家运用非西方艺术在抽象艺术上取得的突破被视为具有创造性的突破时,使用西方艺术的非西方文化却总被视为是衍生品或者是缺乏原创性。
批评集中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早期阶段: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它们被认为缺乏原创性,仅仅是对西方当代艺术形式的模仿。泰特美术馆在线肯定了对政治波普的批判:“政治波普的批评者认为,这一运动并非完全(政治性的)参与,它采取通过模仿进行宣传的策略,充满了消费主义话语。这些艺术家也因为迎合西方市场采用刻板模式而广受批评。”[5]
加州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ihwa Ong指出,领军的纽约评论家质疑中国当代艺术“为迎合全球市场,发展了虚假的先锋主义。”[6]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在全球当代艺术的舞台上广为接受,中国当代艺术被认为既非是真正的先锋艺术,也非政治参与,而是一种高端的商品文化。在20世纪早期,欧洲艺术家的“文化反思”促进了先锋艺术的发展,但当中国艺术家采用同样策略时,却被视为仅仅是进入了西方艺术市场。这揭示了欧洲中心观的双标。从“原始的”文化模仿和衍生而来的各种变体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当中国将西方波普艺术视为一种从外部关照自身文化的策略时,却被视为毫无创新的模仿。Aihwa Ong认为这种批评可能是由于“担心亚洲艺术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威胁当代西方艺术”[6]。
三、当代中国艺术发展的两个阶段
这些观点显然是误读了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阶段被压缩的事实。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分层的别现代导致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几乎同时发生。后现代中崭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自我意识推动了雄心勃勃的先锋冲动的发展,但这一发展并没有消除存在于文化深层意识中的前现代的过去,尽管这种前现代的过去曾被近代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所打断。这种“新”的自我观最能体现在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上。西方文化表达体现出的全球性力量显示在消费主义意象和波普艺术的盛行上。这种讽刺性的文化反思表达了一种寻求形式的中国声音。这不是模仿而是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仍在继续。在评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时,可以确定两个不同的阶段。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第一阶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无名画会”。他们游离于官方的学术界外,出于个人的品味和兴趣而非国家的需求而创作。
随着这样那样的发展,中国踏出了诸多第一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打破了自身的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在苏联模式中)。先锋艺术的发展导致本土当代艺术市场迅速扩张,并因为政治波普和玩世主义受到了国际认可。这一阶段可以在王广义、岳敏君、祁志龙的作品中看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弥合了中西方艺术批评家之间的鸿沟,有助于中国先锋艺术迅速取得合法地位。这些艺术家吸收和重新诠释西方形式的能力成为中国先锋艺术获取全球声音的方法。在一个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8年英语的国家里,这些艺术家能够流利地运用西方的视觉艺术语言就不足为奇了。所有人都认为视觉语言比话语容易掌握得多。这些艺术家为绘画领域所做的,包括张洹通过内化克里斯·伯顿的作品重新诠释身体的挑战行为等,强化了作为政治影响载体的个人的身体。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重新融入更深层的中国文化,在新的全球化艺术感受中重建与历史和传统形式联系的阶段。这种对西方形式的偏离表达的不是对意识形态的构建而是对根深蒂固的意义的需求。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包括现在一些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譬如徐冰、谷文达、蔡国强和曹斐等创造了全球影响力的艺术家,他们备受尊重并非仅仅是因为在艺术市场的生命力,还因为作品的质量和深度。他们每个人都表达了别现代的分层现实。他们通过书法、水墨画、烟花和中国历史的具体方面的呈现参与了中国传统。正是通过这些艺术家,西方才得以更好地了解和尊重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影响。这些艺术家也是中国文化最好的大使。
中国当代艺术的短暂历史可以通过若干方法进行概述,并进一步细分为更小的阶段或类别。两个大的阶段是:第一阶段是反思和同化,第二阶段是内化和表达。第二阶段将继续发展壮大。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艺术家会像其他非西方的当代声音——例如加纳艺术家艾尔·安纳祖(El Anatsui)或在英国工作的尼日利亚艺术家辛克·索尼巴尔(Yinke Shonibare)——那样被完全纳入西方的叙述中去吗?到目前为止,这些艺术家已被充分接受和收藏。他们独特的批评声音如今已成为更为包容的后现代西方文化的预兆。但是,如果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或者纽约的MOMA美术馆举办过重要展览便意味着“成功”,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西方霸权。批判霸权的创造性文化被接受,并成为西方历史叙述的一部分,但却不能立于西方叙述之外,保持独立的声音。如果不能保持独立性,那么它将会因为隐形而枯萎饥饿。实际上,任何这些真实的变化强化了西方的历史叙述。艺术被转变为博物馆作品和“历史”或者是商品,散发出社会转型的力量。尽管如此,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可以成为影响力日增的全球性的声音,因为它可以从自己丰富的历史中获得灵感。
四、别现代艺术由思想驱动,没有共同的风格与形式
那些探寻别现代“风格”和“形式”的人被极大地误导了。现代艺术中的形式主义DNA已经随着现代的终结而终结了。即使别现代艺术和西方后现代艺术截然不同,它仍然不会接受某种现代形式为本质核心,就好像它不会用甲骨文来卜卦一样。别现代存在于后现代、现代、前现代的现实中。别现代受到概念的驱动,因此形式是流动的。正如我们所例举的别现代第二阶段艺术家所证实的那样,别现代艺术形式多样,当代艺术家做的仅仅是选择了这一理念。没有可识别的形式的艺术在市场运作上存在困难。它扰乱了品牌推广过程。中国和西方艺术市场如何回应中国当代艺术,可能决定其未来。财务上的成功可能使充满活力的变革思想沦为可量化的利润空间,从而导致其失败。只有当这些艺术家迈向中国独有的历史和文化指涉时,才能从西方手中争夺文化话语权。历史证明,除非是有剥削、剥夺或从他人创作性文化中获利的机会,否则西方从未真正关心过他人的语言、文化、历史或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