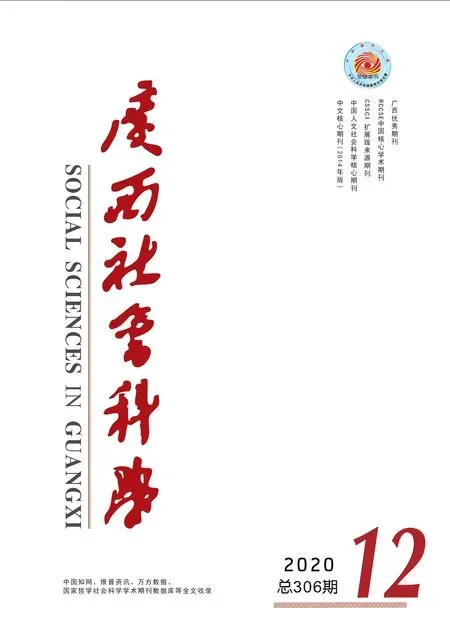从“价值重估”到“文化诗学”
——基于“现场—理论”的当代文学批评审视路径
2020-03-11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与社会文化媒介的多元化发展密切关联,如社会“媒介批评”对当代文学的介入等,都对文学消费以及文学生产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代文学作为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适时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复苏与发展,使当代文学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引领社会思潮、改革的先声。但随着新时期文学逐步失去启蒙话语表达或是转喻的可能性,80年代构建起来的“纯文学”“迷思”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以致90年代之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文论失语”的呼声愈发频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性症候反思与主体性重建同时发生。
一、社会媒介的“当代文学价值重估”与文学评论刊物的策动性参与
21世纪以来,公共舆论场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审视的话语方式与作为言说整体的“当代文学价值”具有同构关系。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辽宁日报》在文化观察版推出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国内外60余位文学批评家、作家或接受《辽宁日报》专访,或以文字形式参与“重估”活动。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认为:“《辽宁日报》选择了自己的参照系统,从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入手,反思创作、批评和文化生产。主要思想基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成长,必须坚持人文理想,弘扬人文精神。因此,从本质上说,这次策划是1993—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续,是媒体对人文精神的再度追问。”[1]
《辽宁日报》的“重估”策划活动是报刊媒介借助具有公共舆论导向的话语方式对当代文学以及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所进行的一次“检视”。在“重估”的过程中注重对当代文学整体性价值具有重大参照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整个过程脱离了常见的文化事件炒作,并因而在学界赢得了尊敬”[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以来的社会媒介仍然对当代文学作为社会文化思潮前驱的“新时期”历史意味抱有理想主义的热情,但是在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杂性话语并置时,我们又很难评定21世纪初至当下的文学批评反思是否具有类似“深化和延续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影响力。虽然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着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等诸多向度所加之于其身的话语负重,尚未建立一体化的阐释机制等问题,但是,社会媒介对当代文学以及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这本身就意味着当代文学的反思活动并未与现实的社会文化脱轨,同时当代文学要阐述的问题又恰是内在于当代社会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之中。
社会媒介尝试参与对当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反思的同时,文学评论刊物也自觉地策动并发起文学批评面向文学现场的批评实践活动。林建法在《批评的转型》中指出,“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建设。如果要反思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学批评杂志的得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作家批评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也是文学批评杂志的基本内容”[3]。稍做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参与并策动21世纪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文学评论刊物并不少,诸如《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及年度论坛,《当代作家评论》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及开设的“批评家论坛”“当代批评家研究”等专栏,《小说评论》的“批评家评论小辑”专栏,《艺术广角》的“70后”批评家栏目及访谈,《长江文艺》的批评家与批评家间的访谈和批评家与作家间的访谈,等等。
其中,《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对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策动是面向当下以及未来向度上的文学批评可能性,其将“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的理念变现为不断策动和参与到文学批评现场之中的指导策略,“通过批评家对自己批评观的言说及其他批评家对他的再批评,批评家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最新成果,同时通过再批评,形成批评家相互间文学观念的交流,文化精神的对话,从而体现文学精神”[4]。2016年11月,《今日批评百家:我的批评观》一书出版,书中集结了1998年至2015年《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的96位批评家的文艺批评文章。在近20年的时间跨度中,《南方文坛》“集成了中国四代优秀青年批评家”,“不同个性的青年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的言说,形成敏感深刻、灵动丰盈的批评文风,不仅再现近20年来文艺批评的争鸣和共鸣,又试图还原历史,更在于描述和激励当下”[5]。可以说,《南方文坛》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历时性发展过程。此外,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学术化,在“由批评而学术”背景下,当代文学批评与学院化的文学研究必然发生关联,而“今日批评家”栏目对文学批评事业的关注也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学术化发展。事实上,文学批评理应和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流派等研究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史研究一道成为较为完整的当代文学学科的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不仅仅是附庸于现时作家作品的评论性写作,其重要性更在于批判立场的当下价值以及对当代文学发展方向、文化思潮的关联性阐释,这当中蕴藏着当代文学的诸多可能性。
二、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热潮兴起。随着西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的文化研究视点传入中国,文化文学研究“用文化学方法来研究文学”或者“借助文本来研究文化”的现象逐渐普遍。王鸿生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批评已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批评经验:80年代中后期的伴随寻根文学而起的‘文化热’;90年代晚期勃兴的‘文化研究’。”[6]“文化热”作为在文学内部寻找文化之根的尝试,传统和民间的视角为人性书写搭建文化学的阐释空间,此时的文化观照更像是当代文学在“85新潮”转向之前寻求自我更新的一次有效尝试。而文化研究的兴起,加之文学批评自身阐释能力所受到的质询,文化研究逐渐被视为文学研究之外的“后学科”。文化研究有着自身庞杂的理论、方法体系,诸如“文本—世界”的批评图式的支撑,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符号学、叙事学、修辞学、人类文化学、传播学等都被囊括到文化研究强大的阐释架构中,学界将其归纳为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或者“隐秩序性”。当代文学批评也不可避免地被文化研究这一“开放的总体性”吸附进来。
南帆曾把文化研究看作继社会历史批评和审美批评之后,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批评方式。他认为,文化研究确实是可以对文学文本提供某种阐释的有效性,“文化研究的明显特征是:对话语的分析、对意识形态的考察,重新回到文学之中。文化研究介入当下社会、从各方面提供分析文学的视角”[7]。但是,当下文学批评一旦将文学文本的阐释价值过度依附于文化研究,文学批评自身也将再次面临危机。“文化研究提供的分析问题的范畴和代码,无法提供判断一个作品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的标准。因此,审美阐释仍不可忽视。”[8]在这里,文学批评的审美属性被从文化研究之中剥离出来。
21世纪以来,针对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二者关系的争论也频频出现。曹文轩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指出,“由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混同以至于文化研究完全取代了文学研究,使文学文本沦为一种社会档案,从而使艺术探讨处在一种停顿状态,并导致文学史写作者错误地写作文学史”[9]。从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整体状况上来看,曹文轩的判断可能存在过于偏激的成分,但他指出了当代文学批评忽视文学自身艺术性而单纯地进行文化社会学阐释有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弊病。在方法和学术体系上,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多有相互观照、启发的互文性,但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不断挤压文学批评的空间。
当代文化研究是一种强调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阐释的批评,这也是其区别于一般的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特质。赵勇认为,文化批评对社会政治活动的介入构成其批判性活力的重要因素,“文化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分道扬镳,而积极介入社会的政治运动。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中走出来,意味着它从此走出了被学科圈定的狭小天地,‘穿越学科边界’的‘跨学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将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标记和主要特征,而政治性与批判性又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传统”[10]。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开始,人的主体性被置于整体的社会框架之中,结构主义的阐释使得文化批评的社会学意味加强。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看似消解了学科边界,使得“后理论”时期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粹的知识操练,理论、意识形态、方法成了关键。陶东风也有相近的观点,“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中只是手段,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文本,也不是对文本进行审美评价。文化批评并不把文本当作一个自主自足的客体,其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这从威廉斯、霍加特等创始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11]。文化研究作为“文本政治学”,与意识形态阐释动机分不开,但是陶东风的论述中有一个前置的话语,即文化研究应用了文学批评的文本分析的方法,换言之,文化研究有着从文学批评之中溢出而确立自身独立性的过程。
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恰恰是从文学批评当中的文本分析获取阐释的有效性。陶东风指出,“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内在’与‘外在’打通,把文本分析、形式分析、语言分析、符号分析等与意识形态分析、权力分析打通,在文本的构成方式(如叙事方式、修辞手段)中解读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12]。这种内部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消解了学科的边界,使得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成为难以区隔的话语言说。实际上,在文化研究日益兴起的21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自身独立的学科属性,很多从事文化批评和研究的学者都是从当代文学批评中转变而来。这一批最早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有着当代文学批评的底子,甚至较为扎实的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基础,他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往往与文化语境有分不清的话语缠绕,文化批评也深受文本分析、语言“编码——解码”的阐释影响。
三、走向融合的诗学阐释:“文化诗学”的理论生成
在文化研究之中的知识和视野的训练一旦返回到当代文学批评,也会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影响。近年来,童庆炳、蒋述卓等先后提出的“文化诗学”的概念正是在以上语境中产生的一种阐释路径。
“文化诗学”是既区别于单纯文本阐释的文学批评,又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它强调融合传统的审美批评与文化视野于一体,走本土化的文学文化批评之路。“文化诗学”产生的背景既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相关,又与文化批评兴起分不开。蒋述卓等认为:“文化诗学理论的生成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以及当时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沦陷。为此,它强调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面向社会现实的文化批判。从文化诗学来要求的话,文学批评家需要成为文化哲学家,要能够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13]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形象思维讨论、方法论热;主体性、文艺心理学的认识以及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后,当代文学批评一贯的“主导”“先导”地位逐渐从社会思想、思潮退居到文学文本阐释的内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失语”。而文化研究在90年代的兴起为当代文学批评的转向提供了契机。“文化批评给文学理论研究重新迎回来文化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将看到一个极为辽阔的天地。因此,文化研究在伸向文化的广阔的领域后,将扩大文学理论的版图和疆界。”[14]童庆炳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指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通往一条既重视文学的‘富于诗意’的‘审美性品格’,又关注文本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的‘文化诗学’之路,成了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15]。“文化诗学”在两代学人的阐释推进下,不断构建起一种具备对话性言说立场、跨学科的互文性视野,注重不同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差异性并确立起自身价值体系的文艺理论[16]。
“文化诗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吸收传统古典文学批评的精髓,在当代文学批评亟须重建自身理论体系的21世纪语境中有着重要的阐释价值。首先,“文化诗学”是一种反对“不及物”批评的文学批评方式。它强调的文化语境、历史语境是避免当代文学批评走向文本空洞言说的有效路径,文学社会学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过于附着政治话语的图解模式已经成为僵化的庸俗社会学,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激活历史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自身活力是当代文学批评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诗学”反对空心化的阐释。蒋述卓等在梳理“文化诗学”的发生语境时都关注到文学批评的伦理化问题,从传统文论上来说,“诗言志”“文以载道”是古典文学的正统,但是当代文学批评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价值立场的缺失或混乱。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反对文学阐释的空心化仍然是当下需要强化的共识。最后,“文化诗学”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找寻到融合的最大可能性。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之间有显在区隔,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何发挥二者在阐释对象时的各自优势,寻找到一个可能的契合点,是当代文学理论亟须解决的问题。“文化诗学”既不拒绝跨越学科边界的开放性阐释视野,又注重构建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其能够整合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达到当代文学批评较为理想的状态。
综上所述,文化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在走向差异化的专业、学科道路;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构建起新的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文化诗学”是富有建构性和阐释性的文学理论,其自身阐释的合理性正在发生深远的学术影响;但是,真正具备阐释有效性的理论方法最终仍要面对当下的文学状况,在当代文学文化历史化的过程中接受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多重的实践与检验。
四、结语
从当代文学批评自身来看,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起着关键性作用。“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文学批评对创作有着一个前置“规训”效应,作家及其创作也正是在文学批评的导向下不断“学习文件精神”“时时刻刻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指示”[17],因而作家常常处于创作版本的修改变动之中。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体制一体化”的进程是同构的,它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越出文学自身嬗变的内部话语,成为一时期政治策略的诠释和注脚。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同样扮演着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导向角色,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反应会对后来的文学史起到牵引作用。比如吴亮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改革文学”的历史语境阐述、对后期先锋文学的文本批评,很大程度上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对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确立的重要参考。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集体反思“文论失语”“批评缺席”的20世纪90年代语境之下,尝试重新树立对文坛乃至文化界热点事件的“制造”和应对能力,试图回归到“当代文学前沿”的轨道当中来。
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自我审视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的现实语境而愈发显现。《辽宁日报》策划的“当代文学价值重估”是21世纪初期不断凸显的当代文学整体性症候的一次集体性反思活动①21世纪初期,针对当代文学整体状况的评价成为一时热议的社会话题,如“垃圾论”“当代文学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当代文学只有高原没有高峰”等。,它仍是内在于“当代”“当代性”的一种“影响的焦虑”,不可逾越的20世纪90年代乃至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和21世纪初期的现实语境决定由社会媒介参与策划的这一场反思所可能呈现的效应。值得思考的是,类似的活动策划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变得越发容易,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对话越发频繁,同一整体性问题审视的话语形态被不断细化、局部化和时间后移所重新组合时,“价值重估”是否成为某种象征性的审视和反思程式?当批评家过于热衷当下“文学版图的拼接”时,21世纪初期所面对的整体性症候的阐释势能是否也将耗尽?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文学评论刊物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策动性参与也具有很强的观照性,可以说成为21世纪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参与和见证者。文学评论刊物所要面对的历史和现实语境是容易为今天的文学批评研究所忽略的,它不仅仅是一家刊物及其主编所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文学评论刊物不断推出的文学批评“新人”以及“我的批评观”所呈现的批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策动了年轻学人不断从学院研究的训练进入到知识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自我反思当中。可以看到,刊物策动对激活当下文学批评现场、构建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积极效应,但是,当置放在整体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之中审视时,“文学批评观”背后所潜在的问题形态又将浮现——批评家所秉持的当下的文学批评观是否在历时性的文学批评话语当中获取了某种更新的可能性?“批评观”能否真正恢复到21世纪初期症候阐释的观照原点,或者仅仅是变成话语程式固化的机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审视的。
当代文学批评始终面临着自身理论化路径构建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历史和现实语境决定“价值重估”以及“批评观”形构的必然性,那么文学批评走向具有历史和现实阐释有效性的理论构建也将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经由两代学人的努力愈发形成本土化的当代文学批评路径,这一理论的内部衍生和实践尚在进行中,可以看到,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在现实语境中不断地在寻求一种合理性阐释的可能性。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诗学”的理论话语背景仍是建立在试图缝合新兴的文化研究和传统的文学批评之间的裂隙,如果当代文学批评始终无法将自身的价值形态剥离开来审视,那么在理论构建和阐释之后能否避免成为多重话语复合之下“当代性”的某种变体是值得思考的。
总之,从“价值重估”到“文化诗学”是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审视的一种路径。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驳杂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尝试着多元的内在建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丰赡同样需要自身进入复杂的文学现场清理时是否具备有效性来进行验证,而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必须经历的历史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