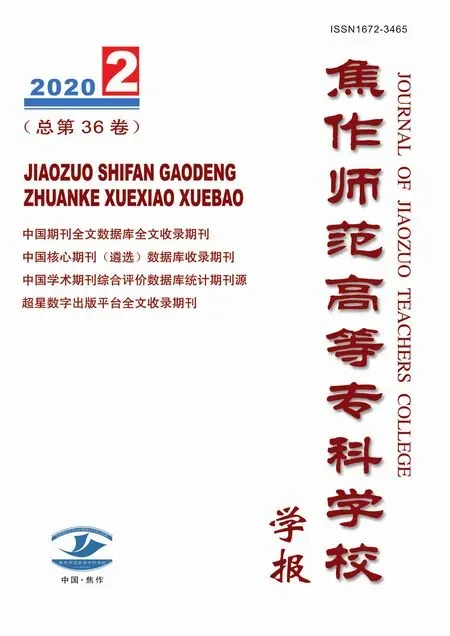《极花》的乡土叙事研究
2020-03-04王彩峰
王彩峰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乡土小说是乡土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小说。20世纪20年代,我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创作乡土小说的热潮,其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城乡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既而成为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关注的对象。贾平凹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就特别重视城乡发展。他的乡土文学叙事,致力于突破传统的乡土叙事模式,长篇小说《极花》为丰富、拓展当代乡土叙事做出了重大贡献。小说通过双重视角即胡蝶的女性视角和作者的知识分子视角,运用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手法,记录了当下农村的现状,反思了互相缠绕的城乡文化。
一、乡土叙事的双重视角
贾平凹的《极花》与《秦腔》《高兴》一样,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但这部小说中的叙事者“我”是一位与另一叙事者(隐含作者)性别不同,且年龄差异很大的青年女性,这种差别悬殊的叙事机制对于贾平凹来说是很富有探索性的。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其文本的形式意义主要受其叙事方法、策略以及由此形成的文体样式影响。作为一种修辞行为的叙事,小说是作者“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通过一个特定的目的给一个特定的人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1]。同一件事从不同的层面出发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经由各异的人看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极花》取材于真实的拐卖妇女事件,通过被拐少女胡蝶的视角以及隐含作者的知识分子视角,叙述了中国当代乡村村民的生存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当代中国城乡发展的重新认知。同时,它也揭示出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乡村的困顿,如“留守”男性的婚恋问题。
(一)胡蝶的女性视角
《极花》由“夜空”“村子”“招魂”“走山”“空空树”“彩花绳”六部分组成。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用小说中被拐卖的女主人公胡蝶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的,蕴含着作家勇于直面现实、敢于探索世界真相和乐于关注人物的真实内心和生存处境的意味。故事开篇就以胡蝶的口吻来诉说自己被拐卖之后的生活日常,包括她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人物和她被拐卖到的圪梁村的地域风情等。
通过“我”和胡蝶的眼睛,我们认识了胡蝶,并了解到她被拐卖之后的真实境遇。她把读者带进了圪梁村,看到这里生活着一群单身男性及他们所存在的尴尬婚恋现状。作为一名被拐卖到乡村的城市女性,胡蝶最初对圪梁村一直充满仇视并伺机逃跑。对黑亮等人也是口不择言、厌恶至极,难以接纳这里的一切。在没有“兔子”之前,她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鄙夷的态度对待这里,她嫌弃乡民的陈规陋习,厌恶他们的衣食住行。直到生了儿子“兔子”后,她才开始学着接受、习惯这个穷地方,并尝试对老老爷、黑亮及其家人转变态度。可对村里其他男性仍然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地厌恶。她鄙视村长那些见不得人的行径,大胆阻止外村拐卖女性事件的再次发生。身为受害者,胡蝶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她可以迅速地与麻子婶、訾米等人不计前嫌地结友交心,但对这里包括黑亮在内的所有男性都一直心存芥蒂。因为受害者的身份,她看不到贫困农村男性面临的严峻的婚姻问题,也不可能对其产生同情心。所以,胡蝶的叙述视阈有其局限性。
通常,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不仅可以参与故事全程,同时又可以跃出作品而面对受述者进行描述和评价,这往往会留下空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极花》作者将叙述视点更多地投放在黑亮的家,也就是主人公胡蝶被拐卖后受拘禁的那个窑洞以及近距离内的生活场景。但胡蝶生活的这个偏远的农村的具体位置在哪,具体样貌又是怎样的,则需要读者在自己的脑海中构建。当黑亮大骂城市不仅将农村的钱、农村的物夺去,还把农村的姑娘全都夺走的时候,胡蝶反问他:“难道农村的男性就不会出去打拼,提高自己的身价后吸引女性,非得像流氓地痞似的拐卖女性吗?”[2]10面对这样的质问,黑亮会转移话题,读者则不禁思索:这些单身的男性为什么宁愿选择滞留贫困农村,宁愿出“巨资”拐卖女性,也不愿出去打拼呢?这样的疑问需要读者自己来建构。帕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指出,在小说的复杂技巧中,视点也就是叙述者与他要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有着关键性的作用[3]。通过对《极花》的研读,足以看出有着特殊经历的“胡蝶”视点在这部小说中对其艺术结构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作者的知识分子视角
根据贾平凹在《极花》后记里的叙述,我们见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胡蝶”。她“是作者相识的一位老乡家里的女儿;她中学辍学后从农村来到城市,与买卖废品为生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事发三年后,公安人员将她解救回来。不料,女孩在被解救的半年后,却又偷跑回那个被拐卖的地方”[2]203-204。听完老乡女儿的遭遇,贾平凹曾说: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里。尽管他在《极花》中主要通过女主人公胡蝶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其中不乏对拐卖妇女这样的恶劣行径进行批判和控诉,但其最终指向却是通过胡蝶的“眼睛”,展现出大批农村男性成了光棍的现实状况,并传达出对这些农村男性的深深同情。同时也凸显了小说背后所隐藏的、作者本人那一双关注当下中国农村男性婚姻难题的眼睛。故而,小说其实还有第二个叙事视角,即隐藏的作者的知识分子视角。
《极花》是作者本着最平常的生活原则,去感悟、去诉说真实的生命体验的乡村。他以批判性的态度,审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引导我们去思考那些几乎被生活遗忘的“人”的生存。作者绕开了对“拐卖妇女”事件的深究性探讨,以被拐卖乡村女孩胡蝶为着眼点,通过其反抗、屈从与回归的行为来关注乡村人的精神变化以及单身男性被异化的生存状态。《极花》是贾平凹站在男性的态度立场来书写的女性故事,是一种对男性有着特殊关怀的女性叙事[4]。这也体现了作者对乡土的人性关怀,他给予乡村这些男性的无外乎是同情,面对自己无力改变的敏感事件,他竭尽所能地做着或多或少的努力——探索现状背后的根由。这部小说是与以第一人称视角的“我”即胡蝶进行着对话,同时更多的也是“我”和众多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的交谈。他在《极花》后记中说:“必须打击那些残暴的拐卖,但在打击的过程中,除了重判人贩,表彰公安,有谁会在乎城市剥夺了农村的财富和农村的劳动力,甚至还有农村的女人?又有谁会在乎那些农村的男性成为了一层开着的没有果实的谎花?也许,他们就是中国农村最真实的代表,也是最后的光棍。”[2]207从这些惹人非议的言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创作动机:贾平凹在故事的结尾将胡蝶留在农村的叙事安排更多地展现了他对传统农业文明的贴近和同情。面对同样的拐卖事件,如果是鲁迅那一代作家,他们必然发出这样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在作者笔下,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对黑亮通过努力获得生活的主动权的认可。他把重心安放在黑亮的勤劳和有商业头脑,对待花钱买来的女性,黑亮有足够的耐心和体贴,甚至是适当的尊重。我们说,贾平凹是在极力塑造一个“理想”的光棍,竭尽全力地挖掘着一个理想的乡村,只有这样,他才能给被拐卖女性胡蝶的归宿找到制衡点。综合作者在小说中的声音可以看出,在胡蝶的生活轨迹中,城市并没有那么可爱,反而是贫困落后的乡土裹带着她应有的温婉和善良。这是一个法理与人伦悖谬的苦涩中带着些许暖意的故事。
二、乡土叙事的特点
对于乡土作家来说,土地和农民一直是他们的创作之源,他们当中有的生长于农村,有的曾经作为知青劳动生活在这片平凡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各种生活体验成为其文学创作的资源。他们以深情的笔触书写乡村,既现实又颇具意蕴。贾平凹曾说过,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写给农村的,或许他的命就是土命,也或许是农村选择了他[5]。作为乡土作家中的一员,乡村始终是贾平凹进行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他对乡村始终怀有一种热情的执念。
《极花》是贾平凹敏锐地觉察到当下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而创作的一部作品,有着很强的现实冲击力。它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议论,其中讨论最多的莫过于:贾平凹在处理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冲撞时的价值观取向问题。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关心的较多的是,城市在肥大的同时农村又是如何的凋敝。”[2]207显而易见,与拐卖妇女事件本身相比,作者关注更多的是引起该事件发生的缘由:随着现代文明都市的迅速发展,贫困落后的乡村到底损失了什么,最终又落得一个怎样的下场。通过主动与被动地感受圪梁村的贫困,我们最大的感触便是无奈和同情。但总的来说,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存在着可取与不可取之处。在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下,作者又借用了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以及独特而丰富的叙事意象,为我们更细致地了解城乡关系做了铺垫。
(一)城乡对立的叙事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多数作品表现了乡村被城市挤压的局面。《极花》是作者运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写出的一部直面现实的作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胡蝶是一个急于摆脱农村身份、一直梦想成为城里人的农村姑娘。辍学后的她跟随母亲来到城里靠捡破烂谋生。她热切地希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所以开始学着说普通话、学习城里姑娘的走路姿势、买镜子、买衣服、染发,学着穿高跟鞋。精心的打扮在得到房东老伯、大学生青文和菜市场大娘的夸奖后变得愈发不可收拾,于是她便谋划着挣大钱,以便能改善生活,彻底摆脱农村身份。然则,在过度追求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她被人贩子诱拐到了闭塞的圪梁村,被迫离开了城市。虽然被禁足在窑洞,但她从未放弃过回到城市的念想。即使在生了儿子之后,她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回城里的愿望。在此期间,她曾通过村长家的电话与城市联系,并在梦境中回到了城市。不过,在梦中最后一次回城后,她却选择了逃离城市。梦境中的“胡蝶”在警察和报社记者的帮助下得以回城,她被许多人“看”,被许多媒体炒作、“消费”,也被许多家长当作教育小孩的“案例”……胡蝶再一次沦为受害者,而且她的“回归”甚至影响了母亲、弟弟和邻居的正常生活。胡蝶再次受到“城市”的歧视和践踏,在充斥着利己主义的城市中,梦境中的她最终选择与城市“不欢而散”,毅然回到了圪梁村。其实,在胡蝶的生活中出现了“兔子”的时候,她已经有意无意地开始认同圪梁村了。她给黑亮及其家人做饭,跟着麻子婶学习剪纸,学着接受当地的生活习俗,她曾在恍恍惚惚中打过求救电话,但之后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小说写道:“我”学会了做搅团,做荞面饸烙,骑毛驴……她学着如何做圪梁村的好媳妇,这种生活对她而言,是具体而又实在的。
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对城市的叙述很少,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胡蝶与城市之间其实有着一段无法对接的距离感。相对而言,作者对圪梁村的着墨颇多。这个村子唯一比较具有现代特色的交通工具便是黑亮的拖拉机。他们家也是全村吃食相对较好的一家,一日三餐都有土豆。这里地理环境差,资源贫乏,唯一值钱的极花也是愈发的稀缺,它就像农村的姑娘一般,稀缺而难以得到,好多村民也因它而丢了性命。这迫使村民转而去经营一种像男性生命力一样旺盛的血葱。这里的男女比例就像极花和血葱一样的不对等,所以村里的光棍非常多。为此,村里的石像女人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村里的女人们几乎都有着和胡蝶一样的想法——走向城市。为了传宗接代,为了保住村子,就连最具权威的老老爷、村长,甚至是当地的派出所所长都在包庇并参与拐卖事件。“这些年对于农村的现状,我是极其矛盾的。社会在前进的同时,社会的问题也在加剧,可以说,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积累了痛苦。”[6]可以说,贾平凹在《极花》中强调城乡对立关系的同时,也对当下乡村男性困顿的婚姻问题有所思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 ,当人们把现代性建构在单纯的物质追求上的时候,就已标志了一种精神力度的不足。因此,我们不需要惊讶于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小说中的城市挤压乡村的危机[7]。
(二)现实与超现实相结合的叙事手法
近年来,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复归与更新,成为了文学界的一种现象[8],比如贾平凹的《老生》《极花》。《极花》反映的乡村生活场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西部的乡村生活非常契合。当时,国家政策先惠及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还远远未惠及遥远的西部地区。具有先见之明的贾平凹,以一颗赤诚之心勇敢地直面当时城乡发展的极大悬殊的现状,犀利地指出了乡村的颓败问题。这样的“写真实”,或许违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但却真切地指出了当时大部分西部乡村的现状。另外,小说中对超现实视角的运用也增添了小说的魔幻色彩,比如胡蝶多次的“灵魂出窍”。第一次,是胡蝶逃跑被抓回来的时候。她完全裸光,就像蝼蚁一般任人撕扯,她的头发被人踩住,耳朵被扯,全身无一处幸免。当黑亮扑过来救“我”,并把“我”抱回窑洞的时候,“我”的魂跳出了身体,“我”成了一位旁观者,看着胡蝶穿上了黑家的衣服,成了黑家名义上的“媳妇”。第二次,是胡蝶被迫与黑亮发生性关系时。在黑亮爹的请求下,村里的六个男性帮助黑亮和她发生了性关系。当时,她的魂就从头顶出来,并站在装有极花的镜框上,看到了自己被施暴的场面。第三次,是胡蝶生孩子的时候。“我”站在窗格上目睹了胡蝶生孩子的痛苦过程,看到了黑家人包括老老爷对胡蝶以及孩子的疼爱。显然,在这些危急的状态下,胡蝶没有办法也很难做到自己在痛苦的时候,还能坦然叙述所有经过,为显现更加直观的效果,贾平凹采用了这种超现实的叙事手法。作者的其他作品也运用过这种叙事手法,例如《秦腔》中的“我”也是灵魂出窍。一个“我”坐着斗“狼吃娃”,还有一个“我”则跑到了果园,坐在新生家的楼顶,于是灵魂出窍的这个“我”就像《极花》中的胡蝶一样,开始叙述事件。这些超现实视角的运用在弥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缺憾时,也与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独特而丰富的叙事意象
中国的叙事文学之所以是一种高文化浓度的文学,主要得益于它的意象[9]。贾平凹在以二元对立的城乡叙事为主的画面中,也为我们建构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这样越是写得实,愈加的生活化,愈加的虚,越有意象。用实写虚,正是我的兴趣。”[10]《极花》有很多意象:星星、极花、血葱、白皮松、乌鸦、红狐狸等。极花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整个故事当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开篇,老老爷就说出了胡蝶和极花之间的影射关系,同时也为胡蝶最终扎根圪梁村奠定了基础。黑亮家的镜框里装了极花,所以就招来了“胡蝶”,因而圪梁村的其他男性也纷纷效仿黑亮在自家的镜框里装极花。极花就像有着阴柔之美的女性一般,使村里的光棍们可望而不可及。极花也使得因城市而伤痕累累的胡蝶,寻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圪梁村。与极花形成不平等关系的血葱,就像这个贫困乡村的男性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野蛮地生长。虽然血葱可以帮助人们助长性功能,但它越是泛滥地繁殖,就越发地像村里那些卑微的光棍们,始终没有被人珍惜的可能。
星星,是通过老老爷的视线将胡蝶定格在圪梁村的一个重要意象。老老爷是一名退休的民办教师,在这个凋敝的村子里,他是智慧的象征。也正是在老老爷引导下,胡蝶看到了属于自己和儿子的那两颗星。之前一直梦想回城的胡蝶,总是满怀期待地以为“我的星只有在城里才能看到”[2]13。可老老爷却说:“在哪不都一样啊!”[2]13后来,“我”便真的在白皮松之间看到了属于“我”和儿子的两颗星。于多数人而言,仰望星空是一种比较富有诗意和浪漫的场景,但贾平凹却将这一画面用到了一个被拐女子寻找栖身之所的境遇中,这样的别出心裁又为小说增加了一大亮点。乌鸦,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吉祥鸟,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晦气的象征。陈梅和王孝杰指出:“意象其实就是物象和主体情、意、理、趣、味相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受文化的影响。同一理念,置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便会有附加在其理性意义之上的不尽相同的联想含义,从而会导致不一样的心理反应。
乌鸦这一意象的创造是经过了人们独特的审美活动,是人们的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互交融的产物。”[11]小说中,胡蝶对乌鸦开始是极其厌恶的,她被关在窑洞里,听着“乌鸦在外面不停地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2]2,此时的乌鸦是比较晦气的。在小说中间和后半部分,乌鸦意象有了一定转变,也可以说是已经身怀六甲的胡蝶对圪梁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遇到下雨天,她会担心乌鸦没有栖身之地。以至后来出现了这样的自述“或许是由于乌鸦天天在白皮松上拉屎,已经习惯了臭味”[2]155,这样的变化表明胡蝶已经开始向命运妥协。
其他的意象如白皮松和红狐狸等,与之前的极花、星星、血葱一起构成了《极花》的叙事意象,同样,也建立了一种虚实相生的意境。这种虚实相生意境的营造,也是贾平凹式水墨文学的一种,他在以真实事件作为小说创作基础之上,再用意象构造出一种虚实相生的写意的意境,这样便把一个具体的故事展现了出来。
三、结语
小说《极花》通过以胡蝶为主的限知视角深刻揭示了当下乡村男性的生存状态。小说以拐卖妇女为聚焦点,引导读者思索当下乡村男性婚姻的真实境遇,有着极大的现实和文学意义。为时代和生活而歌的贾平凹,一直在用自己如椽的笔为人民讴歌。他在感应着文化和人类情绪的新脉搏时,总能将其捕捉并提出生活的新课题。作为读者,我们有理由坚持不懈地阅读他的作品,并且细细品味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