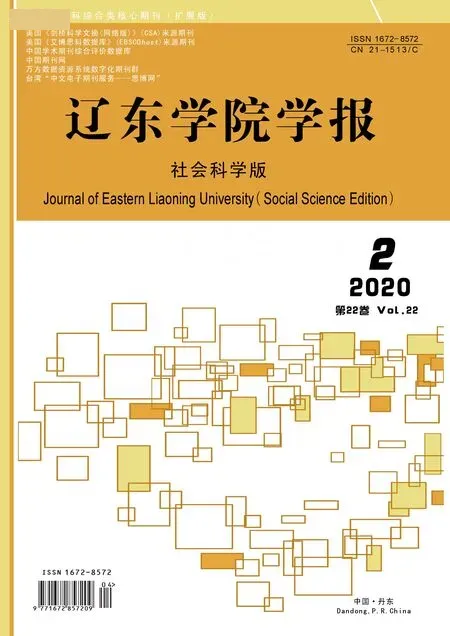李清照名下三词仍应存疑
——与徐培均先生《李清照词笺注》商榷
2020-03-03冯小禄
张 欢,冯小禄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负一代盛名之李清照词,由于传世版本的纷繁和学者的认识差异,产生了某些词的著作权争议,或以为易安作,或以为男作家作,或存疑,由此也影响到了现代“易安形象”的建构和“易安手法”的认识。笔者认为,至少其中三首词——《点绛唇》(蹴罢秋千)、《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和《浣溪沙·闺情》(绣面芙蓉一笑开),因与普世流行的男性欲望写作传统及手法之过于亲近,比较合理的做法,还是应结合易安前后的伦理、欲望书写状况,依近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漱玉词》例,列入“附录一存疑”[1]。
一
王延梯《漱玉集注》与赵万里意见相同[2]。不过,影响较大的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初版于1931年,名《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3]未述理由,却定此三词为李作。后出的徐培均先生《李清照词笺注》则主要根据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论李清照词之语:“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认为《点绛唇》词“写少女情怀,当为少年所作”,《减字木兰花》词“乃新婚后作”“尽情表现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浣溪沙》词“盖建中靖国元年新婚后作”,“风格所致,不应存疑”[4]1-2,10-11,亦定此三词为李作。由此不免误导近来一些年轻学人,因现代意义上的反封建礼教和女性意识论述需要,径将此三词当作李清照作品来论述,以为表现了李清照“执著而热烈的女性情爱意识”和“自恋、自强的女性独立意识”等等[5]。
当然,这种看法又是受到了之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研究看法的影响,譬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即以第一词为李作,认为“非常传神的塑造了一个顽皮、活泼而美丽的少女的形象,情调都是健康的、明快的”[6],评价甚高。夏承焘先生也曾将与此三词情调类似但赵万里先生谨慎存疑的两首词径作为李清照所作,而在1961年《文学评论》上撰文大加赞扬云:“是敢于写少女的爱情,‘眼波才动被人猜’;敢于写夫妇的幽情,‘今夜纱厨枕簟凉’;敢于讥笑有社会地位的男人,‘桂子飘香张九成’”,而宋代王灼的斥责“却正可见出她这些作品的敢想敢说的精神”。其意虽不是要“过分夸奖她是个觉醒的女性、是敢于向封建礼教作反抗的女性”,但也是要声张“她的思想意识无疑是和当时一般恪守闺范德家庭妇女不同,也和一般大家世族的才媛不同。”[7]这些定性般的认识就为近来十分流行的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解读留下了“合法”空间。
另外,如唐圭璋主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第二、三词为李作,第一词存疑,徐北文主编《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同;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第二词为李作,一、三词存疑;王璠《李清照研究丛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一、二词为李作,第三词存疑,陈祖美《李清照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3年版)同。为讨论方便,本文以徐培均先生《李清照词笺注》(以下简称徐著)为集中商榷对象,而主要从男性欲望的写作传统和手法来剖析此三词不大可能出自女性作者如李清照之手,而更可能为男性作家所为,并适当交代古今词集的不同处理情况。
二
先看《点绛唇》云:“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沾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其中,“沾衣”,他本多作“轻衣”;“见客入来”,他本或作“见有人来”。徐著认为“此词写少女情怀,当为少年习作,似难与成年后词风相比”,复根据上述王灼《碧鸡漫志》论李语,认为此词与之“如合符契,似应为清照所作无疑。”[4]2
如仅从此词文本内容看,似也难确定作者的性别:它可以是女性的自画像,因为人物的惶遽动作、天真害羞确实“酷肖小儿女情态”(清李继昌《左庵词话》)[4]4。但结合本词的书写传统,则当看作是体现了男性心理欲望的男性写作,写一位外来男性与闺中少女的邂逅事件,有较明显的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艳遇性质。晚唐韩偓《偶见》诗即云:“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暎中门。”本词与韩诗的承传关系一目了然,而更加清晰地展现了这一虽不露骨却相当富有戏剧性的情色遭遇经历。少女纵情秋千游戏以至“薄汗沾衣透”的身体和因为外客猝然来到以至慌乱走避、鞋未穿、钗掉落的情态,以及“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既害羞又好奇的少女目光,都被不期而至的男性目光所截获捕捉,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更重要的是,本词还写出了深闺女性对于外来闯入男性之巡游审视目光的躲闪与回应(“见客入来”和“倚门回首”),其羞赧与大胆兼具的清涩少女特质,对外来男性有相当的诱惑力,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男性对待美貌少女的情色心理,符合一向相承的男性欲望写作传统。如萧纲《美女篇》云:“密态随羞脸,娇歌逐软声。”梁武帝《子夜歌》云:“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在这样一个以男性欲望表达为主的书写传统里,女性往往被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和采取攻击性姿态的男权社会塑造为柔弱、羞涩与娇媚、诱惑兼具的形象。“就性别来说,男性的想象(不论其为诗意的,还是性的),都不是‘靠自身而存在’。相反,它是靠一个本质上的‘他者’而存在,那就是那个女性化的人物,她必须回应男子的注视,才能完成‘诗的过程’。”[8]181这段本来是用来评述现代诗人戴望舒《雨巷》中如丁香般的女性的话,在此也可移评从南朝宫体诗到唐宋词男性书写女性情色的传统。
因此,本词应是男性作家所为,而非出身官宦世家、受过基本闺范教育的女性作家所能如此主动地去“照顾”男性的观看目光,满足于展示层层被看的境地。这一点,即使是向称大胆的同时代人朱淑真也未能如此,她最多在情感欲望的迫切表达上放肆一下,说:“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清平乐·游湖》)何况这首所谓的“李词”还有充满性欲望暗示的“薄汗沾衣透”呢?就更不可能是李清照所作了。据徐先生为本词所作校记,其所据底本日本东京大仓文化财团所藏彭氏知圣道斋钞《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调下原注“或作无名氏,此从《词林》”,又《词的》本作周邦彦词,杨金本《草堂诗馀》题作“佳人”,署为苏轼词,可见本词在历代文本传播中确有不少以为非李清照而是男作家所作[4]1。而一代治词大家唐圭璋先生《读李清照词札记》亦云:“且清照名门闺秀,少有诗名,亦不致不穿鞋而着袜行走。含羞迎笑,倚门回首,颇似市井妇女之行径,不类清照之为人。无名氏演韩偓诗,当有可能。”[4]4有理。
再看《减字木兰花》云:“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徐著复据王灼上述语和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反驳赵万里的意见,定为易安“新婚后作”,“尽情表现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4]10。
但本词仍应是遵循大胆放肆的男性书写传统之男性所为,以代言的方式体现了受男性心理控制下的女性自我容色审视与批评。在本词之前,唐代无名氏《菩萨蛮》云:“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面发娇嗔,碎挼花打人。”对话内容、情调的艳冶私密,本词与之可谓同出一辙:上片以花比人,人花合一,有较明显的性暗示意味;下片写女性喜悦又担心的复杂心理,很明显,表现的是评论女性容色的艳情传统和高高在上的男性得意心理[9]。晋孙绰《情人碧玉歌》云:“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梁武帝《联句》诗云:“倾城非人美,十载难里逢。虽怀轩中意,愧无鬓发容。”在男性的强悍欲望里,女性只能以艳丽容色事人,否则就应惭愧,或担惊受怕。很难想象,性格高傲、学识超旷的名门闺秀李清照会“女拟男声”,转换性别审视角色,如此卑下地去讨好新婚丈夫赵明诚。何况,本词所呈示的女性心理活动相当凄苦,并非徐先生所说的“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或许有人会说,在赵明诚面前,李清照作为女性的地位仍是卑下的,那么请看与本词情节类似的清代女词人沈采的《醉公子·写兰》:“妆罢研香墨,素练安排帖。却写一枝兰,檀郎偷眼看。/乍从明镜见,背后多人面。回首问檀郎,兰花香不香?”其间暗示的兰花与自己谁香的意味,表现的也仅是男女之间的亲密调笑,而非本词的故意卑下。
最后看《浣溪沙》云:“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徐著仍据王灼语,不同意清人王鹏运和近人赵万里否定和存疑李清照作的看法,而同意唐圭璋《全宋词》的做法,定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新婚后作[4]12。
其实一望可见,本词上片仍是站在男性的居高临下立场和生理欲望目光,来俯视女性的如花笑靥、性感香腮和挑逗眼语(“眼波才动被人猜”),这是一个被动又极具诱惑力的女性形象。下片还是站在迎合男性自高心理的被追求的约会叙述视角,用唐代元稹《莺莺传》幽期密约的故事,透过女性之口,要求再一次的生理欲望实现。“约重来”,既定格了相会的偷情私密实质,又解释了上片的俯视是男性欲望实现后的惬意目光。而“一面风情深有韵”的认识,也显示了男性欲望中女性形象的妖媚诱惑色彩,与《莺莺传》士妓相会的故实和“尤物”的认定若合符契。据陈寅恪先生考定,《莺莺传》亦名《会真记》的崔莺莺,身份多半是一位妓女。而元稹该书,也是将莺莺视为能祸害正人君子性情修养的具有极端诱惑力的“尤物”。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西·伊瑞格瑞说:“女人的快感主要来自触摸而不是观看,但当她进入一种支配性的观看机制,却再次表明她是被动的:她将是一种美德对象。她的身体因此而被色情化和妓女化,在展览和羞涩之间进行双重运动,以激发‘主体’的本能。”[10]125-126可用来说明本词及上二词的欲望书写思维。
因此,本词越是被后人评为“摹写娇态,曲尽如画”“更入趣”(明赵世杰《古今女史》卷十二)[1]12,越能彰显其男性欲望下的妓女形象书写实质。至此,恐怕是再“风流蕴藉”、享受过新婚宴尔之乐的李清照,也要有“所避忌”的(龙榆生《漱玉词叙论》)[4]13。这里再说两点:第一,如是李清照新婚所作,则大可不必用这个明显有道德缺陷的会真之典来降低贬辱自己的正妻身份,而且还是“月移花影约重来”的偷偷摸摸。这是事实的不可能。第二,从写作技术言,作为女性的李清照,如要完成本词的写作,须经好几番的性别意识转折:由女变男,由男看女,由女看自己的欲望形象。而这几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证之李词,除上述两例和《丑奴儿·夏意》(谭正璧先生《中国女性文学史》认为是李作,调名《采桑子》,徐著“存疑”)外,就再无这样需要层层转换性别欲望的作品。李词向称直率透明,直指一颗纯粹女性和文化女性的存在之心[11],她可以情绪化,但不会欲望化,更不会男性化为男性意识的代言人。
这里不妨再以都描写女性的慵懒无聊为例,来说明男女所作的视角和情调差别。男性词中多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男性窥视目光,流露出程度不等的情色欲望想象。如温庭筠《菩萨蛮》词云:“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精工描绘,从女性睡醒的样子、起床梳妆的姿态到充满强烈性暗示的人花相比和服装样式,五彩斑斓的妖娆女性的“感官意象”可谓“层出不穷”,告白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男性全能叙述者在巡游、窥视和刻画女性身体,而文字的镜头式捕捉和流线式进程,就是男性欲望的隐秘舞蹈。而这符合词在当时主要为休闲男性消费的审美状况。柳永《定风波》(自春来)延续了这种细描女性容貌体态、潜在传达男性窥视欲望的叙写传统,而又深入到代言女性的私密内心欲望活动,让女性大胆炙热地袒露情怀,以满足男性的欲望期待。且看其上片:“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恹恹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观察描写的女性容貌部位(肌肤、头发)、体态(犹压香衾卧)和行动节奏(恹恹)与温庭筠词一致,而更俗更集中。但作为女性的李清照就截然不同,虽有很多词也提到“慵懒”,如“髻子伤春慵更梳。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点绛唇》),“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销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凤凰台上忆吹箫》),“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武陵春》)但并不像男作家热切周到地去描摹女性特有的可以引发性想象的容貌体态,而是不稍停留,一笔带过,重在交代因为长时间等待而显出精神倦怠这件事情本身上,不给男读者以更多的性联想机会。
三
综上所述,基于《点绛唇》等三词皆有相当明显的男性欲望写作性质,我们认为均不大可能为李清照所作,而更可能为男性作家作。它们所塑造的形态不一的女性形象,都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男性的情色欲望和心理特征,是男性心理和欲望书写传统的产物,而非一个女作家“女拟男声”所为。“作者的作用是表示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的存在、传播和运作的特征”,福柯《作者是什么》之言可用来说明此种情况。征诸古代女性创作的实际,如此需要辗转曲折地去代言男性欲望下的女性情色被看和女性卑下特征,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征诸强大的男性欲望书写,例子却举不胜举。如周邦彦有《花心动》(帘卷青楼)写两性交欢的热烈情形,苏轼有《菩萨蛮·咏足》咏女性纤足。当然,对封建卫道者而言,即使是李清照那些不越礼教规范的孤独相思词,也会因作者的女性身份和情感的私密性问题,而觉得有碍观瞻、有伤风化,更何况李清照的很多词确实很真切地传达了封建时代女性的苦闷声音呢?王灼等人的批评之言,即应如是认识。但这不能成为《点绛唇》等三词为李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