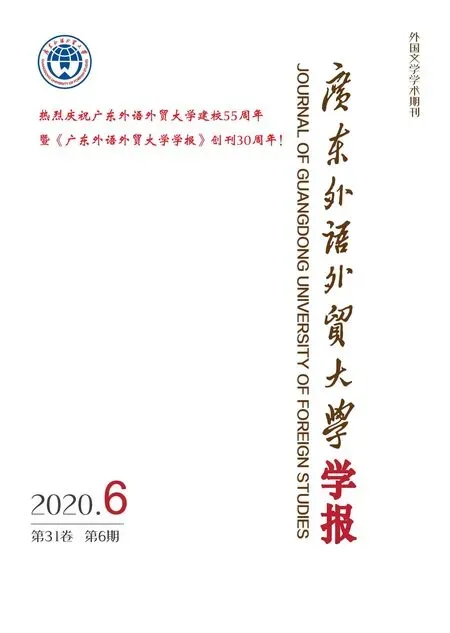“我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自在”
——《天意》中精神异化的空间表征与社会根源
2020-03-03林武凯黄美琪
林武凯 黄美琪
引 言
当代英国小说家安妮塔·布鲁克纳(Anita Brookner,1928-2016)曾以小说《湖滨旅店》(HotelduLac,1984)获得一九八四年布克奖。她的作品频频涉及单身知识女性的情感问题,刻画了许多渴望爱情而被动等待的单身女性形象,如《天意》(Providence,1982)中的凯蒂·莫勒(Kitty Maule)、《访客》(Visitors,1997)中的西奥·梅(Theo May)和《天使湾》(TheBayofAngels,2001)中的佐伊·坎宁安(ZoCunningham)。布鲁克纳的第二部小说《天意》以女主人公凯蒂的情感发展为主线,以她的工作经历为次要线索,讲述了英国移民后裔凯蒂一方面从大学临时教师成长为正式教师;另一方面对教授莫里斯(Maurice)的爱慕迟迟没有得到回应,最终恋爱幻想破灭的故事。
截至目前,多数评论家认定其为一部传统爱情小说,多从单身知识女性情感主题进行论述。例如,罗伯特·E·霍斯默(Hosmer,1993:30)认为小说讲述了“一个痛苦、敏感、孤独的女性的困境……与其说她是她爱情理想的牺牲品……不如说她因为无力主动自我表达而无法吸引和保持对方的注意力”。马尔科姆(Malcolm,2002:37)则一反传统,敏锐地观察到《天意》中的环形叙事模式,亦即布鲁克纳不仅在小说伊始用大量笔墨介绍凯蒂的身世,而且全书最终以一个表面略显突兀的关于凯蒂身世问题的对话结尾。基于此,马尔科姆(2002:37)指出,“(这一)环形叙事模式象征了主人公对融入所处环境的无力感”,亦即身份感缺失的精神异化状态。遗憾的是,马尔科姆忽略了凯蒂的精神异化状态与空间场域的关联,也并未对这一困境背后的社会根源进行深入挖掘,因此其论述流于表面。
纵观国内外学界,尚未见有学者以空间批评理论观照《天意》中的精神异化现象。笔者认为,小说中探讨的精神异化现象与空间场域密切相关:其一,全书第一句话便开宗明义:“很难说凯蒂·莫勒是怎样一个人”(Kitty Maule was difficult to place),她似乎“难以捉摸”(unplaceable)(布鲁克纳,2016:1-11)①。无论是动词place还是形容词unplaceable,都源于名词place。其二,小说呈现出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二元分布的文化特征格局,凯蒂身处的家庭空间有着浓厚的法国性,而社会空间则有着浓厚的英国性。凡此种种,均暗示出以空间叙事为切入点剖析移民后裔精神异化问题的可行性。
空间与异化是两个有交叉关系的概念。异化涉及个体身份与社会群体或空间场域的关系,指的是二者疏离和错位的状态,本质上体现为身份感缺失。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Rosa,2018:117-118)在谈及“空间异化”时指出,“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可见,异化尽管作用于个体自身,但是产生于个体在一定空间背景下的身份状态变化。因此,剖析个体所处的外部空间是深入探讨个体精神异化的重要路径。
小说中有两处显著的情景反讽分别集中体现了凯蒂在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精神异化:第一,外祖父母对凯蒂的关爱无微不至,但在凯蒂看来,“他们的爱并没有给她慰藉,相反,他们的爱是负担”;第二,在小说结尾,凯蒂工作得以转正,却在情场上一败涂地,因而“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好比在某种游戏中那样,尽管自认为一直遵守规则,却还是被罚回了起点”。
本文以空间批评理论对《天意》进行重新解读,深入剖析以上两处情景反讽所体现的移民后裔精神异化现象,试图说明该小说在爱情主题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布鲁克纳对移民后裔群体精神状态的人文关怀,进而将精神异化的空间表征与客观历史语境进行对照,从而挖掘凯蒂精神异化表征之下的社会历史根源。
精神异化的家庭空间表征:不愿融入
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一书拉开了当代西方思想界“空间转向”的序幕。在列斐伏尔的空间观中,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庸、纯粹的地理景观或者“脱离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科学客体”,相反,“空间总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是一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Lefebvre,1976)。如前所述,《天意》呈现出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二元分布的文化特征格局,前者有着浓厚的法国性,后者则有着浓厚的英国性。可见,空间作为文化表征场域,蕴含着鲜明的文化特性和意识形态。凯蒂在两种空间、两种文化特性的夹缝中丧失身份感、产生精神异化,足见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身份认知有着潜在影响。
个体的身份认知首先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家既是一个物质性的地点……也是一个建构身份和意义的空间”(May,et al,2006:225)。然而,凯蒂的家庭并没有给她带来身份认同,恰恰相反,凯蒂的精神异化与她的家庭背景直接相关。“这是一个古怪而异常的家庭”:凯蒂的外祖父母瓦金(Vadim)和露易丝(Louise)具有法国背景,其中,露易丝是法国人,瓦金虽是俄罗斯人,但他年轻时便到巴黎工作,早已适应并接受了法国文化。他们在婚前移居英国,从事颇具法国特色的行业——时装业,并育有一女玛丽-特蕾斯(Marie-Thérèse)。这个在英国出生但有着法国血统的姑娘长大后闪婚嫁给了英国上尉约翰·莫勒(John Maule)。可惜好景不长,两人度完短暂的蜜月,约翰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法国气息浓厚的家庭增添一些英国性,就奔赴战场,随后不幸牺牲。凯蒂是遗腹子,她兼具英法两国血统,是家里唯一具有英国血统的成员,因此,“对全家人来说,她是个神奇的外国人”。凯蒂的三个亲人保留了传统的法国生活方式,“几乎偶然地,通过一段战时婚姻,这三个亲人曾经和英国的生活习俗有过接触,却都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具有纯正英国血统的父亲去世后,只能作为一个符号在家里存在。这个家庭的实际结构是三个纯正法国人和一个在法国家庭里缺乏身份感的人。这样一个法国家庭在英国社会中如同一个孤岛,而凯蒂在这个有着浓厚法国性的家庭中则像是孤岛中的孤岛。
凯蒂在家庭空间的精神异化表现为“不愿融入”,体现出异化的典型特征,即“[个体]倾向于疏离的能动状态”(Kon,1967)。实际上,外祖父母并没有冷落这个“外国人”,而是对她百般疼爱。“瓦金热衷于厨艺,常常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把一碟碟食物放到她面前,催促她品尝他最新的创造。这些食物通常既香气浓烈又别出心裁”。露易丝则喜欢“给她做衣服”,凯蒂穿上这些“做工优良的精美衣着”显得“引人注目”。尽管如此,凯蒂仍然陷入精神异化状态,不能平等接纳自己的双重属性,而是极力抗拒法国性自我,过分放大英国性自我。“凯蒂热爱英格兰,这种热爱的强烈程度,只有当一个人不完全是英格兰人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对她来说,露易丝、瓦金和玛丽-特蕾斯几乎都令她难堪”。在凯蒂的自我身份认同中,这三位亲人共同代表的元素被排除在外,“凯蒂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因此,当有人问起她的身世时,“她通常说:‘我父亲是军人。我出生前他就死了。’她说的虽是实情,却不是全部真相。她把家史中首要的角色分派给了父亲”,因为她父亲是这个家庭中存在过的唯一英国人,唯一与英国主流社会有直接联系的人。可以看出,作者关注“家与个体身份之间的关系,家这一概念唤起人们的地方感,归属感或者异化感,这些都与人的自我认知密切相关”(Blunt,2003:73)。对凯蒂而言,这种“家与身份认同”的联系有主观选择的余地,凯蒂在构建主体身份中抗拒了在家庭空间中占据主导的法国性,片面选择了处于次要地位的英国性。
在凯蒂的心理空间中,凯蒂双亲的地位形成一个强烈对照。父亲在凯蒂出生前便英年早逝,而母亲陪伴她到成年后才去世,按理说她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本应更深厚,然而在她的心理空间中,母亲仿佛在她出生前就已经死去,在她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微乎其微,因此她对母亲极少流露出怀念之情。相反,父亲却一直活在她的世界里,她认为父亲才是她身份的根基,因此在谈及自己身世时频频提起的反倒是父亲,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她对法国性自我的排斥和对英国性自我的认同。
凯蒂的精神异化除了内在体现于她心理上与外祖父母、母亲三个亲人的疏离外,还外在体现于具体的居住空间——房子。母亲去世后,凯蒂从外祖父母家搬到自己租住的公寓。从此,“凯蒂有两个家。一个家在切尔西,是一小套公寓房间。她父亲的照片就放在那儿……另一个家,是她外祖父母在郊区的房子”。每个周末,凯蒂都要去外祖父母家。从社会空间回到家庭空间,就如同从英国回到法国,“那儿,只要一进大门,闻到的各种气味、见到的各种陈设、听到的持续不断地交谈,都令人恍如置身于巴黎或者更加偏东的某地的某所公寓”。家庭对话总是夹杂些许法语,家庭生活也相当具有法国特色——把服装和食物置于中心地位。这种法国性无疑是凯蒂所排斥的。在凯蒂眼里,“那儿有一种昏暗的外观,一种古板的舒适氛围……那儿有巨大的悲哀,编织起简单而空虚的日子”。“古板”“悲哀”和“空虚”这些字眼与其说是外祖父母家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凯蒂厌恶情绪的心理投射。然而,凯蒂碍于亲情不得不例行公事,每个周末都去拜访。面对外祖父母事无巨细的关心,凯蒂没有直接表现出抗拒情绪,而是表面顺从。拜访结束后,她回到独自居住的小公寓,“内心隐约地感到不安,渴望成为某一种人或者另一种人”。此时,“她探询地端详照片上的父亲,这个在她心目中是‘父亲’的人”。此句中,“照片上的父亲”指的是字面意义的父亲,即约翰·莫勒,而引号中的父亲,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性的父亲,即她所认为的自我身份的根基,也就是她的英国性自我。她渴望成为的就是像父亲一样的纯正英国人。可见,凯蒂在自我认同中对英国性自我过分偏重,最终使自己在家庭空间中格格不入,缺乏身份感。
作为具有两国血统、两种文化属性、两个自我的移民后裔,凯蒂本应该接纳和认同自己的双重身份,然而她的心理空间却与家庭空间发生错位,她片面地否定家庭空间中的法国元素,从而陷入精神异化状态。因此,尽管外祖父母对凯蒂的关爱无微不至,但在凯蒂看来,“他们的爱并没有给她慰藉,相反,他们的爱是负担”。如果说凯蒂在家庭空间的精神异化表现为“不愿融入”,那么她在社会空间的精神异化则影响了其社会行为,导致她“无法融入”社会。
精神异化的社会空间表征:无法融入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1991:26)在纯粹客观化的物理空间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并指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张一兵(2019)对此分析道,“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人在其中活动的物理场所,它的建构是编织这些活动的关系构式, 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个体正是在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空间生产,在他者的镜像之下建构自我身份。“个体的身份构建在很大程度要依赖我们曾经和现在存在的空间……同时也会因为此时此地的需要而进行调整”(王卉,2016)。凯蒂为了建构其英国人身份,一方面排斥对其身份建构造成阻碍的家庭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利于其身份建构的英国性社会空间产生了偏执性的渴望。这也表明社会生产与交往行动中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当代理论家马尔库塞(Marcuse)和鲍德里亚(Baudrillard)关注那种导致个体从自由思想中异化出来的媒体、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弥漫性力量。社会对个体的力量更多的是“诱惑”(seduction)而非“宰制”(domination)(凌海衡,2007:435)。在小说中,凯蒂人格中的英国性自我与社会空间的英国性产生趋同,社会空间对她有着强烈的诱惑,使她产生过分美化主流社会与自我矮化的倾向。在《天意》中,社会空间主要从职场和情场两个方面展现。
凯蒂的职场生活颇为顺利,“她申请并且得到了某个地方性大学的一个研究性职位”,她目前仍然是临时教师,负责日常授课的同时等待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职业治疗专家黛比·拉里贝特-卢德曼(Laliberté-Rudman,2002)指出,个体可以借由自己的职业向自我和他者传递“我是谁”的信息。凯蒂试图通过求职和工作来确证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预期,同时也通过进入一个工作机构来探寻融入主流群体的机会。尽管如此,凯蒂融入主流社会仍然困难重重。同事保琳(Pauline)一针见血地指出凯蒂在职场中的疏离状态:“她是个外国人……在伦敦出生的……她给人的印象,就好像她在这儿不是特别自在。就好像她正在学规矩”。
作者将凯蒂职场生活的描写聚焦于全体教员会议这一场景。凯蒂对会议的态度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保琳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每学期一次教员会议的蔑视”。会议开始前,教授们“不大情愿地鱼贯而入”,并且在听取发言时“不约而同地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了起来”,有的在信手涂鸦,有的在列购物清单。会上并没有讨论什么重大议题,“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开会有事可做”。这分明是一幅会议作风散漫和工作态度消极的众生相,“但凯蒂却很喜欢这种会议。尽管她不总能理解会上讨论的事务,但她还是成功地让自己看上去很专心,她甚至还记笔记”。她认为作为一个社交机会,“这是她本星期的最佳时刻”,因此“为了开会她特别精心地打扮自己”。
除了同事的工作态度问题之外,会议室的空间环境也不尽如人意:“那丑陋不堪的房间,那朝北的采光,那混杂着烟味和复印纸气味的混浊气氛,除了她和莫里斯以外,每个人那不起眼的皱巴巴的穿着打扮”。这样“昏暗油腻”的空间环境本应该招致反感,但对她而言,“这里的场面充满了奇特的异国情调”,即英国情调,并认为“所有这一切,相比于她外祖父母家的、围绕着正规的服装和不规则的餐饮而变化的生活,都更为奇特也更合她的心意”。
出席会议的教授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凯蒂没有在会议上发言,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业余者身份,仅仅让她拥有与会资格”。如果说这个场景中的教师群体象征了英国主流社会,那么凯蒂的临时教师身份则是她移民后裔身份的隐喻。与移民后裔在英国的处境一样,凯蒂在职场里介于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渴望被接纳,对能够参加会议已是心怀感激。凯蒂对教师会议场景的认知与客观事实产生明显偏差,这是围城外的凯蒂下意识对围城内生活的美化。这既说明了本质上她与那个教师群体的疏离,也暗指移民后裔在英国社会中的精神异化。
对凯蒂而言,工作固然重要,但爱情和婚姻的成功才能确保她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在英国社会永久立足”(Malcolm,2002:37)。如果说凯蒂的职场生活体现出她下意识对英国社会的过分抬高和美化,凯蒂的情感生活则显露出她面对作为他者的主流群体时所产生的自我矮化倾向。她追求该校历史系教授莫里斯,与他保持暧昧关系,既因为他自身的才华与魅力,也因为他的纯正英国血统、社会地位和家族名望。“她把莫里斯当成了她心目中英格兰的理想”,因此,她在情感上的付出远多于在职场上的投入。例如,她“为莫里斯准备一个特别的菜所花费的时间,要多于写一篇论文或准备一个讨论班所需的时间”。此外,凯蒂对工作的喜爱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莫里斯的迷恋。她在内心对莫里斯坦言:“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觉得这份工作很轻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在为你而做”。然而,莫里斯从未明确表达对她的情感,小说中“难以捉摸”(vague)这个形容词频频用于描述莫里斯,他的态度与这份恋情本身一样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因此小说中凯蒂的大量心理活动都与猜测莫里斯心思、思考恋爱策略相关。在移民后裔融入主流社会的背景下,情感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既反映了双方在情感关系中的不平等,也折射出双方血统属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优势一方得以摆布和玩弄劣势一方。在这个情感关系中,一方面凯蒂表现出卑微、迎合与自我矮化,比如在莫里斯出现的场合,“她总是严格地控制好自己的表情,她谨小慎微的程度,堪比十九世纪的家庭女教师”;另一方面莫里斯则时而传递出满不在乎的态度,时而做出带有挑逗和玩弄意味的言行。这集中表现在小说着墨颇多的法国之行以及旅程前后莫里斯的邀约和凯蒂的两次乞求。
莫里斯做了一场关于英格兰大教堂的演讲,演讲颇为成功。随后他计划前往法国考察当地教堂。凯蒂得知这一计划后,希望与他结伴同行,并利用自己的法国背景和语言优势协助他的工作,从而增进两人的关系。她认为“要是他带她去法兰西,那就会是个兆头”,意味着他们能正式建立恋爱关系,她甚至认为法国之行“将会决定她自己的命运”。此时,“她主要的思虑是,莫里斯是否会邀她一起去法兰西……可怎么来提起这件事呢?肯定得由他来提”。终于,凯蒂等来了他的邀约,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他站直了身子,双手叉在腰间。“你应该和我一起去,凯蒂。”他说。她背过身去,好遮住自己颤抖的双手。“好啊,为什么不行呢?”过了一分钟,她这样说道。她的声音里没有特别的抑扬变化。“我亲爱的孩子”。他大笑起来,伸出一只长胳膊放在她的肩头。“你非常清楚为什么不行。只要想想你的名誉就知道了。”
这就是他的做派。凯蒂被他搞糊涂了。她不知道,是否在他的世界里,和一个适龄的并且有婚嫁意愿的女人结伴旅行,真会是一件丑闻……(布鲁克纳,2016:26-27)
莫里斯的态度显得随意甚至轻浮,自己主动邀约却在激起对方的兴致之后借故推翻,颇有玩弄的意味。而凯蒂则自始至终表现出过分卑微的姿态,任由对方左右自己的心绪。可见,凯蒂对融入主流社会的强烈渴望使她内心默许了这种不平等的存在,甘愿自我矮化,从而迎合和取悦对方。在随后的大量心理活动中,她甚至将自己贬抑为等待被“救赎”和“认领”的角色,认为“莫里斯选择的女人,会避免那些无人认领的女人可能遭受的羞辱”。
凯蒂不愿错过这个结伴同行的机会。于是,在未被邀约的情况下,凯蒂打算主动前往法国,并在临行前给莫里斯打了电话:
开展校本课程,例如英语戏剧课程,挑选经典作品,以电影导入,使学生了解主要剧情。教师介绍背景文化知识,拓宽知识面,增加学生词汇、短语、句型积累。课程以学生演出戏剧收尾,以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内化。
“我决定到巴黎去,稍微准备一下演讲稿。有几件事情我要去查证一下。我们能在那儿见面吗?”
他大笑了起来。“可能有些困难,我亲爱的。你知道,我会开着车到处转。你什么时候会在那儿?”
“我也不太确定。”凯蒂说,“可我们俩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却不见面,有点荒唐。”她意识到自己在央求,马上克制住了自己。(布鲁克纳,2016:91)
最后,凯蒂只身一人前往法国,并在巴黎的旅馆苦苦等待多日后,最终与莫里斯取得联系,并如愿协助他的考察工作。然而,莫里斯醉心于考察工作,“他对她视而不见,或者已经忘了她也在这儿,而她则对自己太没有把握、不敢轻易去打扰他”。并且仅仅一天后,莫里斯因故改变行程,准备于次日乘坐飞机返程,凯蒂不得不争取与他相处的时间:
她在几乎彻底的黑暗中偷偷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莫里斯,”她急迫地说,“时间太晚了。我们现在回家吧。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稍稍皱了皱眉头。“怎么会呢?”他说,“我可以在这儿待上好几个小时。”“可你明天就要回去了,”她乞求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布鲁克纳,2016:147)
乞求是一种下对上的言语行为,暗含了乞求者的无助与卑微以及被乞求对象的优越性与支配地位。在以上两次乞求中,从字面上看,凯蒂所乞求的仅仅是与莫里斯相处的时间。但在乞求背后,承载的不仅是爱情与婚姻的希望,更是凯蒂作为移民后裔通过婚姻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渴望。过度的渴望让凯蒂冲昏了头脑,不惜通过自我矮化来迎合对方,以博得对方的青睐,但这本身是畸形的恋爱相处方式。法国之行无果后,凯蒂仍对这段虚无缥缈的感情抱有幻想。在小说最后一幕的晚宴上,莫里斯向众人公开了他与凯蒂的学生费尔察德小姐(Miss Fairchild)的恋情,凯蒂极度失落之余不得不强装镇定,“试着控制自己颤抖的双手……还要挨过今晚剩下的时间”。尽管她的精神异化并不必然造成情感失败,却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异化的人格难以在恋爱关系中找寻自我并把握与他人关系的平衡点,这对亲密关系的建立有阻碍作用。
在社会空间中,无论是职场生活中过分美化主流社会的倾向,还是情感生活中自我矮化的倾向,都是个体与社会空间疏离的体现。尽管凯蒂作为移民后裔主观上渴望融入英国社会,但是这两种病态的倾向却往往使她的努力适得其反,客观上反而进一步拉远了她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强化了与主流社会的隔阂,最终“无法融入”。尽管最终凯蒂工作得以转正,但对她而言,那仅仅是一份工作,情感的失败则是对她彻底的否定。
无论是家庭空间的“不愿融入”,还是社会空间的“无法融入”,都可以集中统一为她的精神异化,即身份感缺失。凯蒂不愿平等接纳两个自我,极力抗拒法国性自我,过分放大英国性自我,从而盲目迎合英国主流社会,这样的人格在这两种空间中都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正如马尔科姆(2002:1)所言,凯蒂“虽然同时是两种文化的一分子(a part),但也同时游离(apart)于两者之外”。那么,凯蒂精神异化的社会根源何在呢?
精神异化的社会历史根源:排外心理
苏联社会学家伊·谢·科恩(Kon,1967)指出,“就其在社会科学中常见的意义来看,异化表示人格的部分或整体与经验世界的意义层面之间的疏远和分离”。无论是在家庭空间的“不愿融入”,还是在社会空间的“无法融入”,都是凯蒂精神异化状态的具体表征。然而,倘若将此具体表征与客观历史语境进行对照,便可以进一步挖掘出凯蒂精神异化表征下的社会历史根源,即二战后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排外心理。
英国社会对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的排斥情绪由来已久。在《天意》中,相关描述不在少数。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凯蒂主持了一个关于小说《阿道尔夫》(Adolphe,1816)的文学讨论班,课堂中凯蒂想了解学生费尔察德小姐对小说女主人公埃勒诺尔(Ellénore)的看法,于是向她提问。费尔察德小姐在明知凯蒂移民后裔身份的情况下,仍然直言不讳地回答:“这个女人很讨厌。她年纪又老,又是外国人”,此时,凯蒂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恼怒”。
小说结尾,凯蒂乘坐出租车前往莫里斯家参加晚宴,司机的排外言论更为直白:
一路上他阐述着自己惯常的主题。这个国家完了。没有人愿意老老实实地干活。出门彻底完蛋了。该死的外国人到处都是。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只有来一剂失业的猛药。像丘吉尔那样的人。我倒希望换换人,叫撒切尔夫人来干干……(布鲁克纳,2016:217)
莫里斯举办晚宴的目的之一是庆祝凯蒂演讲的成功。此前一天,凯蒂发表了关于浪漫主义传统的演讲,并顺利通过转正考核,成为该校正式教师。她满怀期待赴宴,以为莫里斯将在宴会上宣布与她确立恋爱关系,然而她抵达后却得知莫里斯不仅将离开该校到剑桥大学任教,而且还已经与凯蒂的学生费尔察德成为恋人。莫里斯的选择耐人寻味。他并非对凯蒂毫无好感,却最终拒绝大学教师凯蒂,选择了不学无术而且学习态度散漫的学生费尔察德。费尔察德不仅是纯正的英国人,而且属于上流社会,莫里斯居住的格洛斯特郡“差不多全是费尔察德家族的产业”。由此可见,血统问题和阶级差别是莫里斯选择恋爱对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凯蒂情感失败的客观原因。
在小说诸多涉及排外现象的描写中,全书最后一段的冲突最为激烈:
“我必须坦白,莫勒小姐,你来之前我们正在议论你呢。我们想弄明白,你的哪一半是法国血统。”那个罗杰·弗莱讲席教授的妻子,突然尖声爆笑起来。“是凯蒂的母亲。”莫里斯提供了答案。“是不是,凯蒂?”“我父亲是军人。”凯蒂缓缓地说,“我还没出生他就死了。”她拿起自己的勺子,准备用餐。(布鲁克纳,2016:221)
此段对话中并不存在有意冒犯,却有一种微妙的歧视意味。罗杰·弗莱(Roger Fry)讲席教授的妻子提出这个问题后“突然尖声爆笑起来”,尽管文中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提及在场其他人对她“尖声爆笑”的反应和态度,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场合“尖声爆笑”背后难以掩饰的优越感。从小说其他场景的描写来看,罗杰·弗莱讲席教授的妻子并非生性刻薄,却在血统问题上流露出优越感,更加说明这种排外心理深入骨髓。
凯蒂从小受到排外主义的规训,在这个场合也表现出微妙的不安与无奈。面对这个问题,凯蒂并不愿意在第一时间回应,反而是莫里斯代为回答。然而凯蒂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这个问题,莫里斯的回应需要凯蒂来确认,此时凯蒂仍然极不情愿,只是缓缓地说:“我父亲是军人……我还没出生他就死了”。这句话既没有直面回答罗杰·弗莱讲席教授的妻子,也没有直接回应莫里斯。从字面上看,听者仍然不能确定究竟“哪一半是法国血统”。根据赫伯特·保罗·格莱斯(Grice,1989:24-40)的会话含义理论,凯蒂的回答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而由此产生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凯蒂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对这个话题的反感。在回应中,凯蒂强调父亲的军人身份与他的早逝,对母亲的身世背景避而不谈。尽管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知道一方是英国血统就等于知道另一方是法国血统,但是在凯蒂的潜意识中,把话题集中于英国血统的父亲仍然能够减少自己的不安感。同时,回应突出了父亲对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暗示出凯蒂内心渴望获得英国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凯蒂作为移民后裔游离于英国主流社会之外而产生的精神异化。凯蒂原以为晚宴是她从英国社会的局外人转变为局内人的契机,却不料受到局内人们的凝视和话语宰制而落入窘境。
除了移民后裔身份外,凯蒂还具有混血身份。同样面临主流社会的歧视,普通移民或移民后裔或许选择认同母国文化,对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会产生过分强烈的渴望,凯蒂的母亲玛丽-特蕾斯便是一例。凯蒂具有两国血统、两种文化属性、两个自我,在大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失去心理平衡,无法平等接纳两个自我,导致精神异化。因此,作为移民后裔凯蒂的精神异化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布鲁克纳对移民后裔精神异化问题的探索具有自传色彩。布鲁克纳是波兰裔犹太人,“在谈及她的中欧家庭背景时,布鲁克纳多次强调她在英格兰的边缘感和异化感”(Skinner,1992:6)。她坦言,“尽管我生于此长于此,但是我在这里从未感到自在,完全没有”(Guppy,1987)。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歧视是种族主义观念作祟,那么为何法国血统的白人移民也受到英国白人社会的排斥?为何小说展现的英国社会如此强调血统和文化身份的纯正性?这一问题涉及排外心理措辞方式的演变。
当代社会学家韦雷娜·斯托尔克(Stolcke,1999)区分了二战后英国的两种排外论调,即基于种族主义的排外与基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排外,并认为,公开的种族主义因为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在二战后已为世人所不齿。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布鲁克纳创作《天意》的时期,英国经济日趋萧条,民众对移民的敌视加剧,右翼政党为争取选票采用经过美化的排外主义话语,基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排外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这种新的排外论调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互不相容、天然敌对,强调基于文化排他性的民族认同,因此移民对民族文化完整性构成威胁。倘若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Anderson,1991:6)所言,民族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基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排外则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恐外论。如果说传统的种族主义排外基于人种等级观念,鼓吹有失道义的种族优劣论,那么基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排外则避开了优劣之分,以文化差异性之名将排外心理合理化。相比种族主义直接露骨的人种贬低,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排外则是软性歧视。因此,小说中的几处排外言论,无论是费尔察德的课堂评论,还是出租车司机的怨言,所用的字眼都是“外国人”,所有不满发泄到外国人身上后便点到即止。可见,外国人遭受排斥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过错或者属性天然低劣,而仅仅因为外国人是“外人”,不是自己人。
显然,这种排外论的鼓动性强,易为政客所利用。小说中司机的怨言便体现了政客对民众的成功洗脑。斯托尔克(1999:26)指出,无论是何种反移民论调,都被利用来将“‘他们’有效地制作成‘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替罪羊”,政客往往将本国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这一弱势群体。一九七八年,时任保守党领导人的撒切尔夫人曾公开表示:“民众确实很担心这个国家被不同文化的人所淹没。你们知道,不列颠的特性对民主、对法律、对全世界起了重大作用。如果它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人民将做出反应,敌视那些进来的人”(Fitzpatrick,1987)。官方对“不列颠特性”的排他性推崇加深了英国社会的排外心理。在此影响下,布鲁克纳在一九八七年的访谈中发出“我是伦敦最孤独的女人之一”的感慨(Guppy,1987),尽管她一生仅在求学巴黎的三年间离开过伦敦。可见,这种新的排外论更具有排他性,是对除英国民族共同体之外的异质文化的一律排斥,连凯蒂这样的“文化混种”也概莫能外,因为“文化混种”的存在本身就被认为是对民族文化完整性的直接威胁。小说结尾由“你的哪一半是法国血统”这个问题开启了最后的对话,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等待解答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暗含预设的陈述。罗杰·弗莱讲席教授的妻子代表英国主流社会通过提出这个问题,间接指明凯蒂非我族类。因此,仅仅是这个问题,已有极强的排外意味,已足以令凯蒂感到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凯蒂的精神异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即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排外心理与凯蒂的特殊身份交织,从根本上决定了凯蒂主观层面的异化。
结 语
从空间批评理论审视《天意》中凯蒂的个人身份探索历程,可以清晰窥见移民后裔精神异化现象及其在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两方面的表征。而倘若进一步将精神异化现象置于英国战后历史语境之中,其社会根源便得以揭示。具体而言,凯蒂成长于排外主义盛行的英国大环境,长期以来她的两个自我难以调和,她极力抗拒法国性自我,过分放大英国性自我,因此她既不愿融入以法国性为主导的家庭空间,也因为英国客观上的排外主义与其主观上的自我贬损而无法融入以英国性为主导的社会空间,只能暗自哀叹“我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自在”。这既是凯蒂个人的悲哀,也是当代英国移民后裔尤其是移民混血后裔共同面临的困境。小说围绕这一现象的细致描绘和深入挖掘体现出布鲁克纳对移民后裔群体精神状态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二战后英国社会排外心理的深刻批判。
注释:
①本文有关《天意》的引文,皆出自安妮塔·布鲁克纳.2016.天意[M].锡兵,译.北京:作家出版社.此后不再一一标示。